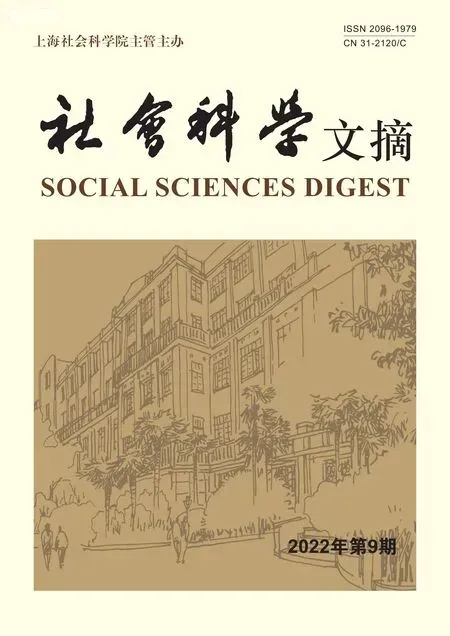倫理覺悟之艱難與倫理學(xué)通史之必要
文/鄧安慶
倫理覺悟之難,難在倫理是道義高地,是一個人或一種文化的面子,因而誰都想拔高自己的倫理信念;同時倫理也是制度和行為的規(guī)范性要求,這種要求可以檢驗?zāi)撤N倫理信念的真?zhèn)危驗檎嫘拍钜砸?guī)范的有效性證明自身之實存,而假信念僅僅是高喊的價值,不具有規(guī)范的有效性。倫理學(xué)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實存之義,但“道”與“義”具有“存在論差異”,形上之道只有落實為實存之義,才具有善惡之屬性,才由價值轉(zhuǎn)化為規(guī)范。因而倫理學(xué)研究只有伴隨著道義實存的歷史譜系學(xué)考察,才能讓人覺悟到倫理之為形而上學(xué)之道與作為實存之義相生相克的文明進(jìn)程。道德哲學(xué)通史研究正是在道義實存的文明進(jìn)程中,考察一種價值論思維規(guī)范的有效性路徑,讓道德哲學(xué)史本身成為一種哲學(xué)并成為一面鏡子,既防止單純主觀思維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義思維因過度追求義之實,而讓道義失去普遍性根據(jù)。
倫理覺悟之艱難
1916年2月15日,陳獨(dú)秀先生在其《倫理的覺悟》一文中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以來,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xué)術(shù),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dāng)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徜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覺悟之最后覺悟。”
當(dāng)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還只能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覺悟之最后覺悟”,而且不只是“吾人”,整個人類全都陷入“倫理”迷霧中。在如此感嘆覺悟之艱難時,我們能做的,無非是“分析”其原因。
“覺悟”一詞,通常含義是由感知性的“覺”(如感覺、知覺、覺察等)和理解性的“悟”(如“開悟”“領(lǐng)悟”“徹悟”等)兩部分構(gòu)成,但在漢語對這個概念的使用中是取其一義:“覺,悟也。”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更是注重“覺”的“悟性”功能:“佛”不是“神”,而是人生智慧和真相的“覺悟者”。“覺悟”就是對迷糊、蒙昧東西的“清晰洞徹”,既可能是當(dāng)下頓悟,也可能是由迷糊轉(zhuǎn)而清醒的“覺悟”過程。因此,這種覺悟相當(dāng)于西方哲學(xué)中的理智直觀,是對智慧、天道的直覺性把握,是“智性”之“清明狀態(tài)”的洞見。對于倫理,我們需要具有這樣一種覺悟。
但是,“覺悟”的一義化也導(dǎo)致一個問題,化“覺”為“悟”,使得“覺”的感知性前提消隱不見,就有可能讓“悟”脫離“感覺”之根本而入迷離之境。“倫理覺悟”,其所感知者都是具體可感的倫理性東西,“悟”是要從這些具體的倫理性東西中,“領(lǐng)會”出自身——倫理性東西——的造化機(jī)制、“立己”之本,從而是使物成為物,人成為人,使具體禮節(jié)成為普遍禮義的機(jī)制和機(jī)理。所“感”者為具體的特殊東西,是禮俗規(guī)條;所“悟”者卻必須是抽象的普遍理則、道義。“倫理覺悟”之艱難,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二者其實是具有存在論差異的,一為現(xiàn)象之“實存”,一為本體之“存在”。現(xiàn)象界的善心善意的復(fù)雜性也因此表現(xiàn)在這里。有沒有本體論上的善心、心體問題,不是關(guān)鍵;善心、心體之“發(fā)用”在現(xiàn)象界的規(guī)范有效性問題方為關(guān)鍵。作為本體之存在的善或善心只是一個價值理念,而作為現(xiàn)象界發(fā)用的善心卻是規(guī)范之有效性問題。價值理念是先天之“道”,其作用在于“引導(dǎo)”,是超善惡的“善”,而作為規(guī)范性的善心才是真正的“屬人之善”。價值與善的區(qū)別就在這里,而人們往往把它們混淆。把先天的形上之“道”這種超善惡之價值直接等同于形下之“義”,是倫理不能覺悟的一個根本原因。
道與義的混淆,屬于道義存在論差異的混淆,這種混淆的實質(zhì)在于不能“覺悟”到屬天之善與屬人之善的區(qū)別。倫理的覺悟就是要覺悟到倫理之善是“屬人之善”,形上之道卻無善無惡。因此,形而上之道只有落實為實存關(guān)系中的“相生之義”,才由價值轉(zhuǎn)化為規(guī)范。道與義的結(jié)合才把倫理的先天立法原則體現(xiàn)為倫理生活中的歷史的規(guī)范原則,從而使“道”在倫理生活中實存,并轉(zhuǎn)化為倫常之“義”。
沒有從高處而來的道德形上學(xué),就容易把各種特殊的規(guī)矩當(dāng)“義”,這是日常的倫理偏見;但有了從高處而來的道德形上學(xué),卻又容易導(dǎo)致另一種倫理偏見,把無善無惡的形上之道直接設(shè)定為“善”,從而把一個觀念或形上價值直接等同于實存的“屬人之善”。善惡之動,由心發(fā)軔,但要從行動原則究竟是相生還是相害來判斷。“為仁由己”,己欲善,斯善而至,善惡因而有“自由意志”(由己)之根。習(xí)俗的倫理偏見往往不懂此理,認(rèn)為“倫理”是外在的禮節(jié)規(guī)條,以為只要是先王之法、圣賢之道,就必然有理,這是最為常見的倫理之蔽。我們平時說人要懂“規(guī)矩”,這個“規(guī)矩”就是各個特殊世界認(rèn)同的“理”。但倫理的“理”不能等同于“規(guī)矩”,不是道德上的“地方主義”,不能是外在權(quán)威的命令。倫理覺悟的核心,需要基于自由意志與普遍法則之關(guān)系的考量。兒童隨著長大成人而有“倫理的覺悟”,關(guān)鍵有兩點(diǎn):一是懂得如何區(qū)別外在紀(jì)律、法律與倫理法則;二是要有作為一個人的自覺。
在成人的習(xí)俗倫理水平上,不能覺悟者,常常是錯誤地把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當(dāng)作是人本身。這時的倫理偏見從道德心理學(xué)上講,就是把行動的“對”或“正當(dāng)”理解為扮演一個“好角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都是人的角色,而不是人本身。如果一種“倫理”僅僅把人作為“角色”,而不把“角色”當(dāng)人看,就會失去倫理的根本之義——人義。這就是我們說,“角色倫理”還沒有達(dá)到真正的“倫理覺悟”的原因。
在有了對人的覺悟之后,倫理就會進(jìn)入“后習(xí)俗水平”的道德意識層面。科爾伯格稱“后習(xí)俗”最高水平上的倫理覺悟,是對“普遍的倫理原則階段”的覺悟。這個普遍的倫理原則是判斷一個倫理共同體一切規(guī)范與制度對錯善惡的標(biāo)準(zhǔn),被稱之為“正義”,它是引領(lǐng)人類文明上升的永恒倫理。人類文明需要永恒倫理的引領(lǐng)才能上升到高貴、高雅的高度,人也只有在崇高的倫理原則的引領(lǐng)和規(guī)范之下,才能活出生命的高貴與高雅。因為倫理的高度決定了人生的高度、德性的高度。
倫理學(xué)通史之闕如
對倫理的覺悟不可一蹴而就,倫理伴隨著人生,因而也伴隨著人類歷史之進(jìn)程。它讓人脫離動物性和“匪性”而讓人性向神性超越;它讓人類生活擺脫叢林法則而自覺順從禮法正義引導(dǎo)的自由法則,并憑借著這種自由法則的進(jìn)步而讓人類具有了“歷史”。所以,倫理的覺悟也就是對作為倫理生活世界之基礎(chǔ)的自由與正義之生成性原則的領(lǐng)悟,它必然會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始終。只要?dú)v史尚未“終結(jié)”,倫理的覺悟就不可能是“最后之覺悟”。倫理學(xué)史正是在此種意義上是描述倫理的發(fā)生史,屬于“描述倫理學(xué)”的范疇,但作為哲學(xué),它不可能是無反思、無建構(gòu)的單純“描述”,而是通過對倫理自身演進(jìn)的“覺悟”中呈現(xiàn)出的自由與正義法則來塑造人類生活的實存進(jìn)程。這種“覺悟”滲透著研究者的主觀反思和理論建構(gòu)而最終滲入實存的思想進(jìn)程中。但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只有西方哲學(xué)通史,卻無西方倫理學(xué)通史。
國外一般哲學(xué)史著作早已汗牛充棟。自從黑格爾使哲學(xué)史變成了哲學(xué),即在治哲學(xué)史中“做哲學(xué)”之后,哲學(xué)家的哲學(xué)思想通過對哲學(xué)史的學(xué)術(shù)梳理而得以表達(dá),從而在哲學(xué)史中把握世界及其精神走向。但是,倫理學(xué)思想史或道德哲學(xué)史,由于是從屬于哲學(xué)的二級學(xué)科,一般只有簡史,而從未見有通史。
我們見到的倫理學(xué)簡史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知名倫理學(xué)家寫的,如麥金泰爾的《西方倫理學(xué)簡史》、赫費(fèi)的《西方倫理學(xué)簡史》、羅爾斯的《道德哲學(xué)史》等。這類著作有兩個重要特點(diǎn):其一,作者的主觀性強(qiáng);其二,往往選擇最能表達(dá)本人道德哲學(xué)觀念的倫理學(xué)家或時代,對其他的則不顧。第二類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倫理學(xué)者撰寫的簡史。這類著作能夠比較客觀地介紹倫理學(xué)的簡要知識,如勞倫斯·貝克爾和夏洛特·貝克爾的《西方倫理史》、特魯爾斯·懷勒的《倫理學(xué)史——系統(tǒng)性的導(dǎo)論》等。第三類是重要的倫理學(xué)家寫的相對比較完整的倫理學(xué)史。例如,德國倫理學(xué)家弗里德里希·約德爾寫的兩卷本《倫理學(xué)史》、瑞士倫理學(xué)家安娜瑪麗·皮珀主編的《現(xiàn)代倫理史》、英國倫理學(xué)家哈德森主編的以“倫理學(xué)新研究”冠名的系列叢書等。
相比于國外的研究,國內(nèi)對西方道德哲學(xué)史的研究更加不夠。國內(nèi)最早的研究著作,應(yīng)首推張東蓀在20世紀(jì)30年代出版的《道德哲學(xué)》。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倫理學(xué)研究一度進(jìn)入沉潛期。從這個時期甚至一直延續(xù)到2000年之后的幾年,中國的西方倫理學(xué)研究都受惠于北京大學(xué)的周輔成提供的重要譯作。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國內(nèi)有兩本“西方倫理學(xué)史”著作影響深遠(yuǎn):一是由中山大學(xué)章海山編寫的《西方倫理學(xué)史》;二是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xué)的羅國杰、宋希仁編著的教材《西方倫理思想史》。1997年,萬俊人出版了《現(xiàn)代西方倫理學(xué)史》(上下卷),龔群則于2010年出版了《現(xiàn)代倫理學(xué)》一書。
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在倫理學(xué)史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對不同時期的倫理學(xué)思想、不同類型的倫理哲學(xué),都進(jìn)行了不同程度的有益探索,推動了國人對西方文明尤其是倫理學(xué)哲學(xué)的理解和把握,但總體而言,在哲學(xué)性和歷史性兩方面的推進(jìn)都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倫理學(xué)哲學(xué)的通史依然付之闕如,這就昭示了一個重要使命。
倫理學(xué)通史研究的必要性
大自然所有的生靈中只有人類有歷史。倫理學(xué)哲學(xué)事關(guān)天與人、自然與倫理、理性與信仰之關(guān)系,但更核心的是在人與人性、己與人、福與禍、利與義、公與私等問題上思考人類生存的倫理機(jī)制,思考如何才能讓人活出人性的光輝,活出人的德性之卓越。人不僅存在于當(dāng)下,更存在于歷史中。因此,對人的理解,需要理解人的歷史。倫理學(xué)本身研究“應(yīng)該如何”。“應(yīng)該”的意向性是未來的,但“應(yīng)該”要為現(xiàn)在之當(dāng)下的行動決斷提供規(guī)范有效性的命令,其理由卻必須具有歷史的淵源。如此一來,倫理學(xué)提供的知識視野,不僅是哲學(xué)的,而且是歷史的;不僅是普通的一般歷史,而且是通史,即“貫通于”人類倫理生活中的人性的道義法則的歷史。這種通史的必要性,是從哲學(xué)“認(rèn)識你自己”的需要中產(chǎn)生的。
蘇格拉底作為西方倫理之父,把“認(rèn)識你自己”作為哲學(xué)的首要問題提出來。由此我們知道,“知人”內(nèi)在地包含“知己”,但“知己”比“知人”更難,或者說,“知人”的核心是“知己”。“人”“己”關(guān)系是人的個體性與人的社會性之關(guān)系,每個人身上既體現(xiàn)了個體性也體現(xiàn)了社會性。而人的個體性和社會性需要放置于歷史進(jìn)程中去認(rèn)識,倫理學(xué)通史內(nèi)在地包含對人己關(guān)系的歷史認(rèn)知的維度。不懂得這一歷史,就不可能真實地認(rèn)識你自己、認(rèn)識人的人性。
但對倫理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單個的人性,單個人性之體面的虛榮,屬于個人對人性的主觀倫理自覺。倫理學(xué)對道義的自覺,不光是單個人對主觀倫理自覺的把握,而且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倫理共同體共同的倫理自覺,是一種文化的體面要求。因而,倫理學(xué)的道義通過落實在具體歷史中的人的德性,形成某個時代的倫理精神、某種歷史階段的普遍道德規(guī)范。這樣就出現(xiàn)了倫理學(xué)要求作為普遍道義與某個時代、民族和某種文化共同體所自覺形成的道德規(guī)范之間的張力。體面是個人的,但其體現(xiàn)的又是文化的、時代的,最終是某個民族的體面。倫理的普遍統(tǒng)一性就與道德的具體多樣性構(gòu)成了一對矛盾,而對這一矛盾的化解,只有通過倫理學(xué)通史的把握才有可能。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倫理學(xué)通史的研究,意味著我們可能永遠(yuǎn)只能達(dá)到對某個歷史時代、某種文化的倫理自覺,而不能覺悟到人類普遍的倫理法則。當(dāng)前流行的“中西古今”問題之所以變成對抗性的、撕裂性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原因就在于沒有“通史”概念,從而不懂得普遍的倫理道義與具體道德要求之間的張力與合力。強(qiáng)調(diào)其張力,把古代描繪為“黃金盛世”以貶低現(xiàn)代之不堪,或者把現(xiàn)代描繪為進(jìn)步的高峰而蔑視古代的落后,這就導(dǎo)致兩種不可調(diào)和的立場。如果沒有一種“倫理學(xué)通史”的視野,如果沒有對倫理的統(tǒng)一性和道德多樣性之張力與合力關(guān)系的自覺,就跳不出特殊性立場,問題就永遠(yuǎn)無解。
倫理學(xué)通史研究的意義就在于,我們以哲學(xué)追本溯源的固有方式,追溯到特殊性的倫理道德根源,回到每一種文明最初發(fā)源時的倫理覺悟,發(fā)掘人類原初倫理覺悟的經(jīng)驗,洞察本原倫理道義的存在論機(jī)制,這樣才能跳出“中西古今”的特殊性,回到倫理之本家——實存之道義。通過本原倫理的實存譜系的考察,我們就能夠具有一種超越的視野,見識每一種本原文化自身具有的倫理之“體面”。同時,倫理學(xué)通史的歷史學(xué)特征,更能讓我們看清,倫理道義的觀念史與倫理社會的經(jīng)驗史之間具有非同一性,以觀念代替實在,或以實在臧否觀念,都無法達(dá)到倫理的真正自覺。倫理既有觀念的理想性,因為它是“應(yīng)該”,同時又具有規(guī)范的有效性,即規(guī)范現(xiàn)實。尼采正是因為重視道德的譜系史考察,才發(fā)現(xiàn)人類迄今還根本不知善惡是什么,所以只有從一般的歷史學(xué)考察走向倫理學(xué)通史的研究,我們才能知道,倫理觀念與倫理生活之間存在復(fù)雜而多樣的斗爭。在現(xiàn)實的倫理生活中,善與惡沒有絕對的界限,假善為惡或亦善亦惡實為常態(tài)。只有透過倫理學(xué)通史,我們才能把握道義實存的方向性與現(xiàn)實的艱苦性;只有在倫理學(xué)通史的視野中,我們才能做到“同之與異,不屑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