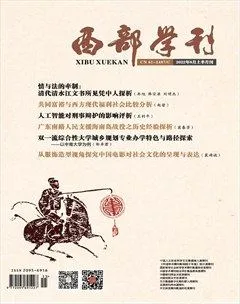論現代國家建構視域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詹 軼 魏世嘉 許諾婧
一、引言
對飽經風霜的近代中國而言,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轉折期。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無數愛國志士投身革命,但由于缺乏科學、系統的理論支撐和堅強有力的政治引領,他們或淺嘗輒止、或半途而廢、或抱恨而歸,均以失敗告終。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以具體國情為出發點,探索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往、有別于前人的革命道路,最終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綜觀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真正做到了“解累卵之危,緩倒懸之急”。然而,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定位、推行乃至改造的整個過程,仍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與分析,以便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以及“中國何以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等重大命題。發展政治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別樣的視角,其聚焦于后發國家于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問題,尤其關注如何在保障政治民主的同時建立起恰當的體制安排和政策策略。這恰與前述核心問題不謀而合。本文旨在明確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同時,將著重強調其作為現代國家建構的戰略意義,凸出其在該層面的過渡、轉化、銜接等調適性特征,從而在發展政治學的視角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一個歷史性的注腳。
二、現代國家建構視域下的“新型”革命
在闡釋“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時,主流做法是對其所倡導的理念進行解讀,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其在歷史進程中的階段性特征。若以革命運動本身審視之,其“創新”之處正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所在。而發展政治學另辟蹊徑,我們獲得了理解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是如何捍衛民族獨立、進行國家建設,從而建立現代化政治體系的一把鑰匙。
從官方定義來看,在目標指向明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主導力量清晰(“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的同時,它更是一項整體性、顛覆性的社會運動(“徹底完成奪取革命勝利的任務”)。這也是為何當我們提到“新民主主義”時,“革命”一詞總是相伴其左右,即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姿態示人。在經典政治學理論中,革命一般指激烈、影響深遠的變革過程,舊制度和舊秩序也因此被付之一炬。自然,以革命運動為錨定的新民主主義就必然會表現出極強的顛覆性特征。
如在“新”這一表述上,該特征就已初現端倪。1939年,毛澤東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并對其作了系統論述。其中,在提到領導力量時,毛澤東就強調:新民主主義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專政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雖仍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但從“陣線上來說”,其“已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換言之,此種顛覆性不僅在革命的目標、對象、動力等方面與以往的資產階級革命迥然不同,其在領導力量和性質層面的改變才最為關鍵。論“新”、論“顛覆”,莫過于此。可以認為,這是對當時中國歷史背景下一切既有革命的“革命”。
這一系列包含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的“顛覆”與“革新”亙古未有,從后果來看,其最大程度上推動了近現代中國的轉型和蛻變。可以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在很大程度上互為表里、同步衍進,前者作為革命手段本身是內嵌于后者之中的。
三、革命過程中的國家再造
實際上,在討論新民主主義時,“過渡性”等表述一再出現,如在討論“兩步走”的設想時,毛澤東同志就曾表示:由于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將中國變革為獨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第二步繼續推動革命向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可以發現,新民主主義運動不僅僅是以一個“顛覆”的、對舊體制進行純粹“破壞”的形象出現,而是在“革命”之外,被賦予了再造新體制、為了推進下一步“建設”而進行“過渡”“轉化”“銜接”的意味。簡言之,除了“破”,還有“立”,以及更重要的,在“破”和“立”之間的“調適”。
發展政治學視域下,現代國家建構被認為是政治主導團體以現代民族—國家及其相關體系為目標(中央集權、暴力壟斷、社會動員等),利用其所掌握的權力工具和社會資源,對舊的政治共同體進行的改造或是對新的政治共同體所進行的創立和維持。如上所述,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可以被視作中國共產黨這一政治主導團體,對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行改造并建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中間”過程。
其具體的“過渡”方式表現為:政治層面,新民主主義革命既貫徹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意志,又將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納入到統一戰線里來;經濟層面,不僅對地主和富農實施較為溫和的土地政策,甚至還適當地將發展資本化生產作為目標;社會文化層面更是直接體現了其包容性,只要是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所謂民族、科學與大眾的文化都可以與共產主義思想相兼容。陜甘寧邊區政權的“三三制”(中共中央在1940年3月6日首次提出,規定在政權機關人員配備上,共產黨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編者注)架構就可以視作為新民主主義在政治層面的一種策略應用,其核心便是“將敵人的界限一再縮小”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如對傳統土地擁有者及資產階級的態度緩和(減租減息、鼓勵辦廠),即是共產黨在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長期發展規律進行判斷后所作出的階段性安排。
如上所述,作為革命方略的新民主主義同樣可以在取得革命勝利后成為一種國家建設方略,就像“潤滑劑”一般,盡力緩解“破”與“立”“舊”與“新”之間的摩擦,保證兩種社會形態在切換過程中的平順轉型,積極回應國家現代化對于穩定與發展的雙重需求。期間,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盡顯無遺,一個“調適性”的革命/國家建設方略就此名留千史。
四、革命與現代國家建構的調適性方略
新民主主義之所以能成為新一代革命/國家建設方略,其深層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目標(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現實環境的桎梏(帝國主義威脅、國民黨專制統治、官僚資本統治城市、地主階級霸占農村、工業化水平低下且工人階級力量弱小等)之間產生了無法在短時間內克服的矛盾。以工業化水平為例,直到新政權建立為止,中國現代工業總產值還未超過當時國民總收入的3.5%,產業工人總數不及勞動力總數的1%。僅就這點來看,中國在短時間內并不存在發動城市工人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及奪權的可能性,即使取得了統治地位,也難以立即進入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軌道。1940年的中國內憂外患,種種結構性制約對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極為艱巨的挑戰。
為了彌合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一個過渡性方案便呼之欲出。新民主主義一改往日中國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的徹底決絕,成為建立統一戰線、鞏固并擴大紅色政權的合法性依據。同時,它巧妙地解決了上文中提到的內在矛盾,正如胡繩所言: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成熟,就等待著而不去奪取政權;也不能在奪取政權時(或奪取革命政權后)全然不顧經濟結構等外部條件、教條式地追求社會主義。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一條“迂回的道路”是必要的。故此,新民主主義正是在不失原則(黨的領導、堅持革命)的基礎上,為了更好地適應環境、有條件地調和矛盾而被毛澤東創造出來的一套過渡機制——這套機制包括了革命的理論部分和其實踐部分,它們貫穿了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到全面推翻國民黨統治、再到最終奪取政權并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整個過程,因而我們完全可以將新民主主義看作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建構方略,其能經受住歷史考驗,關鍵就在于靈活、務實和求變的特征。
追根溯源,此類調適性的國家建設戰略在我黨歷史上早已有之。早在1935年,黨中央就提出要轉變“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最終建立“人民共和國”——工農專政轉變為“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聯盟;1936年,黨中央通過了相關文件,提出要建立“民主共和國”,該方案除第一條綱領(抵御外侮)外都表現得較為寬泛和模糊。共產黨人意識到之前過于激進的階級斗爭政策不利于“團結更多的朋友”,故將重心從“反蔣”轉變為“逼蔣”。次年2月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展開后,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滿足,上一階段的“逼蔣抗日”也就順理成章地變為“聯蔣抗日”。毛澤東在分析當時的整體形勢時就認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故而“資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不應拒絕他們,而應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斗爭的聯盟”。可以認為,該階段我黨仍主張握有革命、抗日及建國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已經做出了國共分裂以來的最大讓步。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方略再次發生變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正式提出“三民主義共和國”(此處的“三民主義”指孫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編者注)的概念。雖然共產黨人始終承認孫中山先生革命先行者的地位,但認為三民主義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將是不全面、不徹底的,對立志打造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看來同樣不可接受。那為何仍舊提出這一概念?毛澤東給出解釋:為了渡過困難重重的抗日救國階段、表現出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團結,有在新形勢下為作長期斗爭而做出調適的必要。它不僅是擱置爭議、創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更是未來進一步共同建國的基礎。言下之意,我黨提出的三民主義建國綱領是建立在特殊的情境條件之上的,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和過渡性,故而較“民主共和國”而言其所作的妥協和讓步也更多。
國共合作不足兩年,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出臺并實施大量的反共政策,兩黨關系再次惡化。共產黨人開始對國民黨當局產生失望情緒,其原先的建國方略自然也受到沖擊。通過對中國的未來前途重新評估,“反蔣”又一次提上了日程。正如前述所言,“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作為對之前“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替代方案被逐步地建構了起來,一個可以銜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過渡的包容性的革命/國家建設方略也就應運而生了。
五、結語:調適性方略的終結與成就
毛澤東曾在1948年的政治局會議上給出過由“資”轉“社”的時間表,即參照蘇俄十月革命后的12年而提出的15年。但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短短三年之后,從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新中國邁上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新征程。
究其原因,這是客觀環境變化所致。新中國成立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經濟恢復與社會發展之上。三年內,人民政府基本穩定住了解放前的經濟亂象,使惡性通脹在1951年底降至可控的15%。同時,“一化三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簡稱,“一化”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即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編者注)等措施則使得公有制經濟的增長速度向前邁一大步。到1952年,80%的重工業與40%的輕工業已收歸國有,國營合作社營業額占當時總額的50%以上;同一年,土地改革使全部耕地近50%的所有權交到貧下中農手中,并使他們的收入較20年前翻了一番。面對此種形勢,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道:“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該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由此可見,雖然黨內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準備工作完成得如此之快也相當意外,但很顯然對新中國的階段性調適已經基本大功告成,在完成了歷史使命后,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國家建設方略也自然落下帷幕。當然,隨之而去的還有舊中國多年來的政治衰朽、經濟頹喪、民不聊生和一盤散沙,而留下的是團結一心的人民群眾和真正獨立、自主、富強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