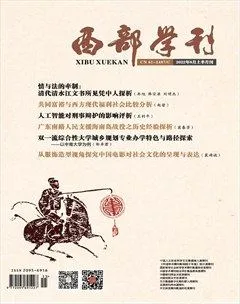二十世紀上半葉小說批評派對王熙鳳形象接受傾向淺探
張彥蕓
一、引言
二十世紀上半葉,《紅樓夢》研究開啟了新的篇章,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以胡適為代表的考據派紅學和以王國維為發端的小說批評派紅學成為《紅樓夢》研究的三大學派。小說批評派始于國學大師王國維,他是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來探討《紅樓夢》文本本身價值的第一人,他的這一研究方法開創了小說批評派的紅學研究之路。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存在于歷時態讀者的閱讀與接受中。接受美學理論的首倡者堯斯認為:“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轉換。”自《紅樓夢》誕生之日起,各個歷史時期的各類讀者對王熙鳳形象的接受正體現了這樣的審美接受規律。二十世紀上半葉,時代巨變,西學東漸,多種多樣的思想觀念導致讀者們的接受思維更加多樣和豐富,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這一時期小說批評派對王熙鳳形象接受傾向的特點。
二、季新:社會政治立場下的功利闡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我國正處在內憂外患交作、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改革救亡的政治主題成為當時的中心話題,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也滲透到學術研究領域。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梁啟超等人感到從思想上喚醒民眾的重要性,因此發起了一場“由下而上”的“新民”運動,“小說界革命”正是這次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嚴峻政治形勢的觸動下,在“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下,很多激進人物都認為文學要揭露舊社會,抨擊舊制度。革命派文論家天僇生認為《紅樓夢》主旨就是“哀婚姻之不自由”這一社會問題,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婚姻制度。
這種社會政治角度的闡釋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后進一步發展,成為當時紅學研究領域的主流批評模式。新文化運動吹響了反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擁護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號角。季新的《紅樓夢新評》正是在這種時代語境下誕生的。該文認為《紅樓夢》是“中國之家庭小說”,并認為專制是中國國家組織和家庭組織的特點,封建禮教則是專制的輔翼,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禮教則造就了一個虛偽的社會。用這樣的觀點來解讀《紅樓夢》中的人物,他認為鳳姐就是一個典型的“假孝假慈假友假悌之人”,“若鳳姐者,承歡色笑,宜若能盡婦道者矣,然其心但以能博老祖宗之歡喜,為一己顏面上之光榮,益得以遂其攬權專制之志云爾。”他將鳳姐作為當家人的弄權行為闡釋為“攬權專制”,連被一些封建文人所稱賞的鳳姐對賈母“斑衣戲彩”的封建孝道行為也被其看成是鳳姐“攬權專制”的手段。在季新看來,鳳姐就是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執行者和幫兇。
季新對鳳姐的解讀是立足社會政治立場的功利闡釋。這種接受視角首先和我國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有關。我國古代的政治家與先進士大夫都把文學的教化功能放在第一位。梁啟超弘揚小說的宗旨也是讓小說為政治服務,讓小說成為改造國民、喚醒民眾的政治工具。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影響到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使得人們在解讀《紅樓夢》時往往立足于社會政治立場。他之所以采取這樣的一個接受視角,還有其深刻的時代因素。這篇文章發表于1915年,正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前夜,國內政治形勢嚴峻,各種進步的政治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文學要揭露舊社會,抨擊舊制度,反抗專制,倡揚民主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界的主流價值趨向。因此,季新對鳳姐沒有進行傳統的忠奸善惡的道德評判,而是將其理解為舊社會中某類人的代表加以批判,其斗爭的矛頭最終指向舊的社會制度。
三、王國維、牟宗三:悲劇論視角下的審美觀照
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的各種文化思潮開始進入中國學人的視野和學術研究領域,這股西學東漸的狂飚也影響到了當時的紅學研究。晚清學者王國維正是在西學東漸之風影響下的一位學人,他所接納的思想是多元的,這種復雜的期待視野為他的《紅樓夢》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1904年,王國維發表了《紅樓夢評論》,該文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他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對《紅樓夢》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解讀。在此文中,王國維援引了叔本華的悲劇觀,認為世間的悲劇分為三種:“一類是倫理悲劇,由極惡之人制造悲劇;另一類是命運悲劇,盲目的命運造成悲劇;還有一類就是存在悲劇。”在王國維看來,《紅樓夢》屬于“存在悲劇”,這類悲劇的根源不在于道德層面或命運層面,而是由于小說中各種人物的位置、關系所造成的,悲劇的根源在于生活本身。王國維認為寶黛的愛情悲劇并非極惡之人肇禍,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因為各人的立場、境遇的不同而導致的必然結果。由此推之,賈母、鳳姐等人并不是千方百計破壞寶黛愛情的惡人,他們只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行為處事的普通人而已。在悲劇論視角的觀照下,王國維沒有將鳳姐視為大兇大惡之人進行譴責,而是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與寬容。
王國維對《紅樓夢》的哲學、美學闡釋在紅學界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鳴。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牟宗三發表了《紅樓夢悲劇之演成》一文,重點剖析《紅樓夢》悲劇產生的根源。該文認為《紅樓夢》悲劇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善、惡與灰色這三種人相互攻伐,而是因為書中人物“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見地之不同”造成。由此,他認為《紅樓夢》里面,“沒有大兇大惡的角色……”小說里的人物“在為人上說,都是好人,都是可愛……”基于這個前提,他認為鳳姐“是一個治世中之能臣,不是一個亂世中之奸雄”“……至于寶黛的悲劇,更不干她事,她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牟宗三從悲劇論的視角出發,也沒有將鳳姐解讀為大兇大惡之人,且在對鳳姐表現出理解與寬容的同時,多了一份贊賞和肯定。
在西學東漸的狂飆席卷下,晚清的思想界出現多元并存的局面并影響到學術研究領域。王國維作為一名前清遺老,眼看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深感前途渺茫,因此他選擇了叔本華的哲學,并將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與虛無主義同《紅樓夢》的悲劇精神相結合,從而表達他悲觀厭世的情懷。牟宗三之所以采取悲劇論的視角解讀《紅樓夢》,除了在學術方法上受王國維的啟發之外,更多的是對當時政治功利解讀方式泛濫的不滿。晚清以來,隨著政治形勢的日趨嚴峻,國內對《紅樓夢》的政治功利研究居于主流地位,政治索隱派和社會政治闡釋派大行其道。這些非文學性的解讀立場引起了一些學者的不滿,如牟宗三就認為索隱紅學和考證紅學都不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都屬于《紅樓夢》鑒賞的“圈子外的問題”。因此,他呼吁《紅樓夢》研究要擺脫政治功利意識,回歸文學性研究立場。王國維、牟宗三都以一種系統的美學理論為參照系來闡釋鳳姐,他們的接受態度散發著理性和美學意味的光輝。
四、李辰冬:抽象人性論視角下的文學性解讀
“五四運動”之后,盡管國內政治局面處于軍閥混戰的動蕩狀態,但文化思想的開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引入為人們審視《紅樓夢》提供了新的參照系。當時的很多學者紛紛用西方的文藝思想觀念來詮釋《紅樓夢》這部經典之作,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例。
李辰冬于1928年赴法留學,留學期間,他就非常喜歡法國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的思想并在其影響之下撰寫《紅樓夢研究》一文。他對鳳姐的看法見于該文的第三章《紅樓夢重要人物的分析》。李辰冬是抽象的人性論者,這種人性觀無視時代、階級等歷史性因素。從這種人性觀出發,李辰冬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物大都象征著一種普遍的、世界性的人性。關于鳳姐,李辰冬認為作者塑造她的目的“是讓她來象征著人類的才干和陰險”。他認為:“王熙鳳之所以喜歡做事,系一種恃強欲在那里沖動著。……是我們青年氣壯力強,野心勃勃時代所有的通性,”“喜奉承,好虛榮本是喜歡做事人的通病,也是我們人類的天性。”在抽象人性論的觀照下,李辰冬將鳳姐的“才干和陰險”“恃強欲”“野心勃勃”“喜奉承,好虛榮”等個性特點理解為人類普遍的天性,沒有對她進行道德層面的褒貶,在保持與審美對象一定距離的前提下作出了具有美學意味的觀照。
李辰冬還從文學創作方法的角度去解讀《紅樓夢》中的人物。他認為曹雪芹是“極端的自然主義者”,“他寫王熙鳳的才干,并不是想贊美她,寫王熙鳳的陰險、毒辣、貪財……也不是罵她,他的目的只在創造這一類人的一個典型罷了。”李辰冬認為在《紅樓夢》里,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賈雨村和薛蟠這六個人物是“最富時代性”的人物形象,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是“才子佳人”的代表,王熙鳳、賈雨村和薛蟠則是“一般人的性格”的代表。他將鳳姐明確列為一種具有時代性和普遍性的藝術典型。這種解讀方法實際上是對作者如何塑造人物方法的探討,本質上屬于文學研究。
李辰冬對鳳姐的解讀是抽象人性論視角下的文學性研究。抽象人性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有著一定的學術背景。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們認為藝術是為人生服務的,藝術應當反映人生,因而人性是有階級性的;以梁實秋為首的卻認為藝術與人生沒有直接關系,藝術是超功利的,應當為藝術而藝術,這一派多贊成普遍的人性論。李辰冬贊同后者,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觀。因而,李辰冬對鳳姐的解讀擯棄了人物的社會歷史內涵,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對人物作出了超功利的文學性解讀。
五、吳宓:跨文化語境下的道德批判
新文化運動之后,中西文化的交匯給《紅樓夢》研究帶來開闊的跨文化視野。1919年,吳宓的《紅樓夢新談》就是一篇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評論《紅樓夢》的專論。該文采用美國哈佛大學G.H.MAGNADIER博士的小說學理論中關于評定小說杰作的六大標準來衡量《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吳宓對人物的看法體現在對《紅樓夢》宗旨的理解中,他認為《紅樓夢》的宗旨正大主要表現在其寫情之深,《紅樓夢》寫了四個層面的情,且四種情分別以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和劉姥姥為代表。吳宓把作品的宗旨同某一人物聯系起來,這種解讀人物的視角有一定的新穎之處,但他在具體的闡述中又回歸到清代評點家常用的道德批判立場,如認為鳳姐是“弄權好貨之貽害大局”的奸雄,其“桀鷙自逞,喜功妄為,聚斂自肥……”,直接導致了賈府的衰敗。
1945年,吳宓撰寫了一篇人物專論《王熙鳳之性格》,這是他采用跨文化語境解讀《紅樓夢》的延續。這篇專論采用多重標準對鳳姐進行解讀,具體闡述如下:其一,從文學典型塑造和作者的情感態度出發,吳宓認為“十二金釵……乃指我(賈寶玉)一生所見,最可愛之女子……,舉例以代表之(今語曰人物典型)”。其二,吳宓按照基督教中將人分類的標準,對寶、黛、釵和鳳姐進行了分類。他認為寶、黛屬于上等人——天界的神仙,其立身行事本于真理和愛情,王熙鳳則是下等人——物界的魔鬼,其對人成功專憑機詐、勢力。其三,吳宓根據佛教將人分為“貪、嗔、癡”的標準,認為鳳姐在三類人中“屬于貪之一類”“又兼帶嗔,但并無癡之成分”。其四,吳宓還認為:“王熙鳳為霸道之政治家,即柏拉圖《理想國》書中所描寫之霸主或暴君Tyrant是也。”在這篇專論中,吳宓首先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出發將鳳姐認定為一個藝術典型,接著分別運用基督教、佛教和柏拉圖的思想等作為標準對鳳姐來了個大雜燴式的評價,但其實質仍是傳統的道德批判。
吳宓雖然將對鳳姐的解讀置于跨文化的語境之下,顯示出一定的獨特性,但最終仍指向道德批判。他的解讀方式既帶有鮮明的跨文化色彩,又打上了深深的傳統烙印。這種獨特的接受視角和他本人的生活經歷、學術信仰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吳宓生長于陜西一個比較富裕的官紳家庭,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在美留學期間,吳宓崇奉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思想,認為中國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他曾說:“我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釋伽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教導。”由此觀之,吳宓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加之受到其他西方文化思想的浸染,從而形成其獨特的思想體系。在文學觀上,吳宓始終提倡以文學來提高人的道德水準,凈化作家和讀者的靈魂。吳宓的世界觀、道德觀和文學觀在解讀鳳姐這個人物時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和體現。
六、結語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走進動蕩不安的變革時期,新文化運動舉起“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反傳統、反禮教成為這一時期主流的價值觀。在此語境下,季新和佩之等人對鳳姐的解讀帶有強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和社會批判意識。二十世紀上半葉也是一個西學東漸的時代,一批深受資產階級文藝思潮浸染的知識分子對《紅樓夢》的接受開始向文學性回歸。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引用叔本華的悲劇觀來闡述《紅樓夢》中的人物,在紅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以牟宗三、李辰冬、吳宓為代表的學者們,則厭惡學術為政治服務,追求學術的獨立地位。他們大多用西方美學理論或跨文化視角來解讀鳳姐,與社會政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綜觀二十世紀上半葉小說批評派對鳳姐形象的接受,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文學批評經歷了從感性走向理性,從全面借鑒西方到中西兼收并蓄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