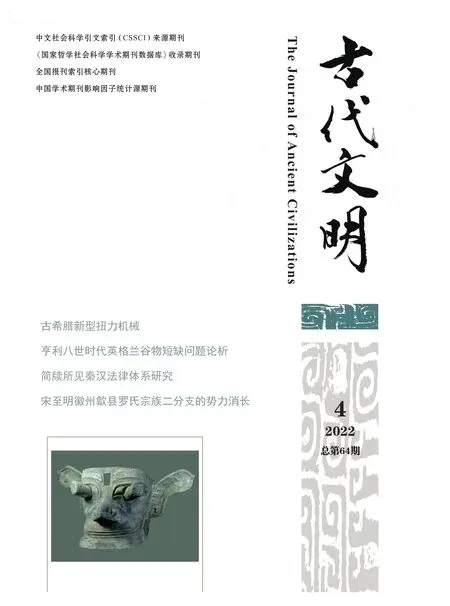《永恒條約》在赫梯—埃及外交中作用分析
郭智韞
提 要:《永恒條約》的締結是赫梯與埃及邦交中的重大事件。哈圖什里三世與拉美西斯二世時期,兩國王室間的外交通信在內容與行文兩方面均可與該條約形成對應關系。據上述外交通信中所見兩國外交實踐判斷,《永恒條約》中的各項原則與條款,大多得到了貫徹,即便未執行者也為相關外交事務的處理提供了依據。可以認為,《永恒條約》為兩國間具體事務的交涉提供了依據,也通過兩國的外交實踐得到執行。將赫梯—埃及外交通信與《永恒條約》對讀也為更加全面理解古代近東大國關系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視角。
一、《永恒條約》與埃及—赫梯外交通信
作為反映古代近東國際關系的基本文獻,赫梯—埃及外交書信反映出《永恒條約》框架下兩國外交往來所涉及的實際事務。除去無法確定主題的殘片,從內容來看,書信中常見的外交事務包括討論締結條約、贈送禮物、聯姻、派遣醫生、探問烏爾黑—泰舒卜下落。貌似這些內容中僅第一項與最后一項與《永恒條約》及其條款直接關聯。其實,禮物贈送與聯姻本是大國統治者結為“兄弟”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派遣醫生則是埃及獨特技術優勢在維持兩國和平關系與統治者間“兄弟”關系中的妙用。可見,這3項外交事務也無不與《永恒條約》所言“良好的和平”與“兄弟之情”有關。
上述對《永恒條約》的表述往往也見諸該條約的文本。《永恒條約》得名于條約起首提到的條約主旨。今天所見的條約開頭部分本已破損,是據阿卡德語A本后文的內容補齊,相關文字作:
二、“兄弟之情”的踐行

三、烏爾黑—泰舒卜與引渡及王位合法性條款
四、軍事相關條款的履行
五、結語
《永恒條約》與赫梯—埃及外交通信均為哈圖什里三世在位時期赫梯與埃及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獻。外交通信中所見外交事務可與條約中的條款形成對應關系,其行文中也時常提及條約作為理據。因此,可以通過梳理赫梯—埃及外交通信中相關邦交實況來評估《永恒條約》的執行情況。
條約中對哈圖什里與拉美西斯“兄弟之情”的強調,實質上使赫梯與埃及對等的大國地位得到互認,也為兩國間的和平往來提供了依據。信中所見兩國王室頻頻互贈禮物、拉美西斯與赫梯公主聯姻、赫梯王室成員屢次獲得拉美西斯提供的醫療幫助,無不是在這一原則下展開的。表面看來,這些積極的互動正與“兄弟之情”表達的溫情脈脈的家庭倫理關系相契合。實際上,其背后卻不乏現實的政治考量。可以說,外交通信中所見上述活動正是條約中“兄弟之情”政治內涵的具體表現。
被廢黜的赫梯前王烏爾黑—泰舒卜素對哈圖什里王權構成威脅,也是引發赫梯國內部分地區動蕩的原因之一。外交書信中可見雙方屢屢就此人的下落與引渡進行爭論。拉美西斯回信中往往聲稱,并未違背條約中的誓言,但實際上烏爾黑—泰舒卜并未按相關引渡條款遣返赫梯。不過,現有材料中卻未見拉美西斯支持此人對赫梯王位的主張;可以認為他的確承認了哈圖什里后裔的王位繼承權,履行了《永恒條約》中的相關條款,只不過此人下落未明,引渡條款也便并未被真正啟用。
此外,從外交通信中的相關內容可以判斷,在拉美西斯與赫梯公主聯姻時,兩國衛隊于邊境交接護送任務,實際上具有踐行《永恒條約》中“互不侵犯”條款的用意。不過,條約中有關軍事互助的誓約卻并未被履行。當然,大國間相約軍事互助本不過是循例而已。但就赫梯與埃及間軍事互助條款而言,似乎為兩國爭取到更為寬松的外部軍事環境,以另一種方式發揮出其作用。
可以說,盡管《永恒條約》結束了赫梯與埃及間的敵對關系,但斷然將締約后兩國的外交往來視為后條約時期的邦交則不免過于武斷。據赫梯—埃及外交通信,條約的締結固然解決了兩國間存在的部分歷史問題,但仍有一些問題雖由相關條款加以約束卻仍懸而未決,此外締約也不免為兩國的邦交添入了新的內容。應該說,《永恒條約》之后赫梯與埃及的邦交進入一個和平交往的時期,但這尚不能視為一個全新的時代。不過條約的締結確實為兩國間的外交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框架。兩國外交通信間所見外交實踐幾乎都可以在條約的框架中找到依據。這正是相關書信中反復提及《永恒條約》的原因。因此,這兩種產生于同一歷史時期的文獻可以互為解讀彼此文本內容的基本語境。赫梯—埃及外交通信與《永恒條約》的交互聯系,不僅為考察條約在兩國外交實踐中的執行情況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證據,也使理解條約框架下兩國邦交的具體方式成為可能。實際上,將赫梯—埃及外交通信與《永恒條約》進行對讀,可以將古代近東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條約路徑”與“書信傳統”相結合,進而為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近東大國邦交的模式提供獨一無二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