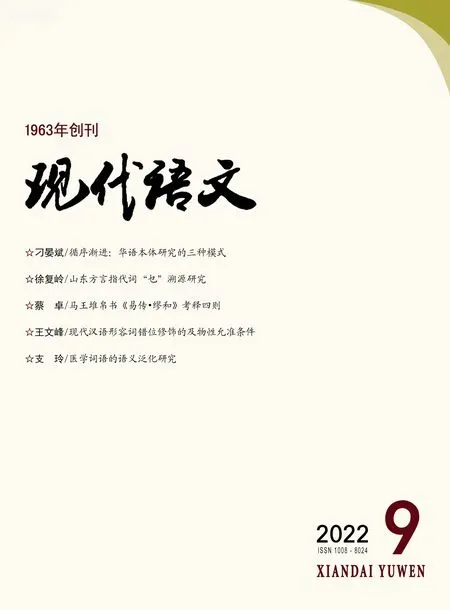新馬華語(yǔ)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歷時(shí)考察
一、引言
我國(guó)海外移民歷史悠久,由于具有地緣優(yōu)勢(shì),東南亞是我國(guó)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莊國(guó)土曾對(duì)此作了詳細(xì)考察,作者指出,自17世紀(jì)至今,中國(guó)人移民東南亞先后掀起了四次大潮,最近一次則發(fā)生在改革開(kāi)放之后
。歷經(jīng)數(shù)次移民潮后,新加坡和馬來(lái)西亞(以下簡(jiǎn)稱(chēng)“新馬”)成為東南亞十一國(guó)中華人最集中、人數(shù)最多以及華語(yǔ)最先形成、傳承最好的國(guó)家。
關(guān)于華語(yǔ)在東南亞的形成這一問(wèn)題,周清海
、施春宏
、李宇明
、刁晏斌
等學(xué)者都作了深入探討。周清海指出,1949年之前,中國(guó)很多知識(shí)分子移民東南亞(特別是新馬),移民群體所說(shuō)的“國(guó)語(yǔ)”在當(dāng)?shù)氐靡园l(fā)展并形成了“華語(yǔ)”
。可見(jiàn),東南亞華語(yǔ)是對(duì)中國(guó)早期國(guó)語(yǔ)的一種傳承。華語(yǔ)在東南亞傳播的歷史之悠久、規(guī)模之巨大、范圍之廣泛,都是世界其他地區(qū)所無(wú)法比擬的
。在華語(yǔ)向全球傳播的背景下,東南亞作為華語(yǔ)向世界擴(kuò)散與輻射的接力站之一
,探究華語(yǔ)在該地區(qū)的發(fā)展演變進(jìn)程,無(wú)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東南亞華語(yǔ)研究一般以新加坡和馬來(lái)西亞為立足點(diǎn),通過(guò)對(duì)個(gè)性的分析來(lái)揭示華語(yǔ)的共性特點(diǎn)和總體趨勢(shì)。
就目前的學(xué)術(shù)現(xiàn)狀來(lái)看,華語(yǔ)研究的總體情況是詞匯多、語(yǔ)法少,并且對(duì)于華語(yǔ)歷時(shí)平面的發(fā)展變化關(guān)注較少。有鑒于此,本文以新加坡、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為對(duì)象,以餐食類(lèi)名詞為切入點(diǎn),以“史”的眼光考察它們?cè)谛埋R華語(yǔ)中的歷時(shí)變化,并對(duì)比它們?cè)谠缙趪?guó)語(yǔ)和普通話(huà)中的使用情況。同時(shí),參照徐威雄
、劉曉梅
、徐祎
、刁晏斌
、盧月麗
對(duì)華語(yǔ)的歷史分期,并依據(jù)具體的語(yǔ)言事實(shí),將新馬華語(yǔ)語(yǔ)法發(fā)展史分為三個(gè)階段:1919—1944年、1945—1979年、1980年至今。
我對(duì)此深有體會(huì)。不知天性如此還是后天養(yǎng)成的懦弱,每逢遭遇挑戰(zhàn)面對(duì)抉擇時(shí),我便徘徊不定、猶豫不決。多少次,因?yàn)槲业莫q豫,導(dǎo)致上臺(tái)發(fā)言的機(jī)會(huì)被白送給不如我的競(jìng)爭(zhēng)者使我不服又無(wú)奈;導(dǎo)致錯(cuò)失進(jìn)球時(shí)機(jī)而使比賽失敗的我蒙受上強(qiáng)烈自責(zé);導(dǎo)致考試不敢下筆卻在考后發(fā)現(xiàn)我的思路完全正確……兀自嘆息卻不知如何改變,通往成功的航道,差點(diǎn)就要因我的優(yōu)柔寡斷而偏離。
本人從事動(dòng)物屠宰衛(wèi)生檢驗(yàn)多年,在工作實(shí)踐中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yàn),要做到正確鑒別判斷,首先應(yīng)從外觀檢查和病理組織的切片檢查相結(jié)合,然后再作出正確的判斷與處理,在此本人淺談一下鑒別與處理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學(xué)界對(duì)華語(yǔ)的共時(shí)研究多以書(shū)面語(yǔ)為對(duì)象,歷時(shí)研究則只能以書(shū)面語(yǔ)為對(duì)象。因此,本文也遵從這一慣例,選取相關(guān)書(shū)面語(yǔ)作為語(yǔ)料,主要包括兩類(lèi)語(yǔ)料:文學(xué)語(yǔ)料和新聞?wù)Z料。其中,文學(xué)語(yǔ)料涵蓋了評(píng)論、小說(shuō)、劇本、散文、史料等,主要來(lái)自于新馬地區(qū)的代表作品,如方修編《馬華新文學(xué)大系》(星洲世界書(shū)局有限公司出版,1919—1942年),方修編《馬華文學(xué)作品選》(馬來(lái)西亞華校董事聯(lián)合會(huì)總會(huì)出版,1945—1956年),陳政欣等主編《馬華文學(xué)大系》(彩虹出版有限公司與馬來(lái)西亞華文作家協(xié)會(huì)聯(lián)合出版,1965—1996年)等。同時(shí),我們還通過(guò)馬華文學(xué)電子圖書(shū)館(www.mcldl.com),獲取了比較充足的語(yǔ)料,這些語(yǔ)料涵蓋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學(xué)研究、文學(xué)評(píng)論、文學(xué)史料、文藝期刊、馬華古典文學(xué)、馬來(lái)西亞華人研究等。新聞?wù)Z料則來(lái)自新馬地區(qū)具有代表性的報(bào)紙,如《叻報(bào)》《星洲日?qǐng)?bào)》《光華日?qǐng)?bào)》
等。此外,由于本研究以早期國(guó)語(yǔ)和普通話(huà)為參照,因此,其相應(yīng)的對(duì)比語(yǔ)料庫(kù)分別是瀚堂近代報(bào)刊數(shù)據(jù)庫(kù)(https://www.neohytung.com/)、北京大學(xué)CCL語(yǔ)料庫(kù)和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BCC語(yǔ)料庫(kù)等。
(7)落實(shí)工作例會(huì),探討安全生產(chǎn)問(wèn)題。在每個(gè)季度,都要確保能召開(kāi)一定次數(shù)的安全會(huì)議。每月都要召開(kāi)安全生產(chǎn)管理人員會(huì)議,其主要主旨是學(xué)習(xí)、傳達(dá)有關(guān)安全工作的政策和文件,學(xué)習(xí)相關(guān)安全操作規(guī)范,分析當(dāng)前的安全生產(chǎn)形勢(shì),對(duì)于企業(yè)內(nèi)部近期的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及時(shí)的總結(jié),完善相關(guān)制度和措施,積極布置開(kāi)展安全活動(dòng)。
二、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歷時(shí)變化
名詞的功能主要是充當(dāng)主語(yǔ)、賓語(yǔ)和定語(yǔ),但是在實(shí)際使用中,名詞還可以作謂語(yǔ)。以使用頻率較高的餐食類(lèi)名詞為例,它在句中作謂語(yǔ)的用法由來(lái)已久,在早期國(guó)語(yǔ)中也不罕見(jiàn)。例如:
(1)(我)睡覺(jué)忘記了收拾墨水筆,任他放在桌上,今早起身后記得還看見(jiàn)在原處,不料到膳堂早餐回來(lái),這枝墨水筆已不知去向了,委實(shí)奇怪得很啊!(《社會(huì)之花》,1925-11-30)
到了第三階段(1980年至今),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的動(dòng)詞用法減少至22例,動(dòng)詞用法與非動(dòng)詞用法的具體數(shù)據(jù)如表4所示:
(2)亞蘭曰:“既如此說(shuō),可以休矣。”遂共小青、吳儂等同赴畫(huà)舫涯居早膳。(《小說(shuō)新報(bào)》,1920-11-11)
刁晏斌著眼于東南亞華語(yǔ)詞匯的整體發(fā)展變化,立足于百年華語(yǔ)的三個(gè)階段:1919—1945年、1945—1980年、1980年—今,將詞匯的發(fā)展演變歸納為四種模式:下行式(指從有到無(wú)或由多到少的變化),上揚(yáng)式(指從無(wú)到有或由少到多的變化),馬鞍式(指從無(wú)到有,再?gòu)挠汹厽o(wú),或者是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發(fā)展變化),浴缸式(指從有到無(wú),再?gòu)臒o(wú)趨有,或者是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的發(fā)展變化)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馬華語(yǔ)三個(gè)階段中,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演變呈現(xiàn)出一條馬鞍型曲線(xiàn),可歸入刁晏斌所說(shuō)的馬鞍式發(fā)展模式,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使用數(shù)量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二是使用頻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刁晏斌還對(duì)普通話(huà)中的三套餐食類(lèi)詞作了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第一,“膳”類(lèi)詞基本已經(jīng)退出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使用,反映出這類(lèi)原本用得就不太多的詞進(jìn)一步趨于萎縮;第二,動(dòng)詞用法全面退隱
。可見(jiàn),當(dāng)代華語(yǔ)和普通話(huà)的共同之處是在于:二者的“膳”類(lèi)詞都趨于退隱;它們的不同之處是在于:“飯”類(lèi)詞和“餐”類(lèi)詞的動(dòng)詞用法在華語(yǔ)中傳承下來(lái),在普通話(huà)中則已經(jīng)消失。
她腦后有點(diǎn)寒颼颼的,樓下兩邊櫥窗,中嵌玻璃門(mén),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開(kāi),就像有兩層樓高的落地大窗,隨時(shí)都可以爆破。一方面這小店睡沉沉的,只隱隱聽(tīng)見(jiàn)市聲——戰(zhàn)時(shí)街上不大有汽車(chē),難得撳聲喇叭。那沉酣的空氣溫暖的重壓,像棉被搗在臉上。有半個(gè)她在熟睡,身在夢(mèng)中,知道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過(guò)是個(gè)夢(mèng)。
關(guān)于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這一問(wèn)題,學(xué)界已進(jìn)行了一些探討。刁晏斌闡述了“晚餐”在早期國(guó)語(yǔ)里作謂語(yǔ)的用法
;李斐考察了港式中文里一組餐食類(lèi)名詞——晚膳、早餐、午膳的使用情況
;刁晏斌以早/午/晚飯、早/午/晚餐、早/午/晚膳三組餐食類(lèi)名詞為例,考察了它們?cè)趪?guó)語(yǔ)、普通話(huà)、華語(yǔ)中的動(dòng)詞用法
。實(shí)際上,在華語(yǔ)各個(gè)階段的語(yǔ)料中,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用法都一直存在著。下面,我們就以刁晏斌所討論的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為例,考察它們?cè)谛埋R華語(yǔ)中的使用情況。
在第一階段(1919—1944年),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的動(dòng)詞用法共有27例,動(dòng)詞用法與非動(dòng)詞用法的具體數(shù)據(jù)如表1所示:

由表1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得到兩點(diǎn)認(rèn)識(shí):第一,總體使用數(shù)量的排序。按由多到少的順序依次為:“飯”類(lèi)詞>“餐”類(lèi)詞>“膳”類(lèi)詞。在三組詞中,“飯”類(lèi)詞的口語(yǔ)性最強(qiáng),白話(huà)色彩最濃,它使用數(shù)量最多可能與東南亞地區(qū)受我國(guó)“五四”白話(huà)文運(yùn)動(dòng)影響較大有關(guān)。在本階段的使用中,飯”類(lèi)詞的總文本數(shù)為27個(gè)(8+8+11),高于“餐”類(lèi)詞的24個(gè)(12+7+5),“膳”類(lèi)詞的總文本數(shù)最少,僅為6個(gè)(2+0+4),其使用頻率要比其他兩類(lèi)詞低很多。第二,動(dòng)詞用法使用數(shù)量的排序。按由高到低的順序依次為:“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這與其總體使用數(shù)量有關(guān)。“膳”類(lèi)詞的總文本數(shù)僅為6個(gè),其動(dòng)詞用法自然更少。不過(guò),就使用頻率而言,“膳”類(lèi)詞的文言色彩最濃,作謂語(yǔ)的使用頻率最高,約為66.7%;“餐”類(lèi)詞和“飯”類(lèi)詞的使用頻率分別是50.0%、40.7%。
我們還考察了餐食類(lèi)名詞在文藝語(yǔ)體和新聞?wù)Z體中動(dòng)詞用法與非動(dòng)詞用法的使用情況,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在文藝語(yǔ)體中,“飯”類(lèi)詞和“餐”類(lèi)詞的總體使用數(shù)量、動(dòng)詞用法使用數(shù)量均高于“膳”類(lèi)詞;在新聞?wù)Z體中,“飯”類(lèi)詞僅有一例,“餐”類(lèi)詞和“膳”類(lèi)詞的總體使用數(shù)量、動(dòng)詞用法使用數(shù)量較多。一般來(lái)說(shuō),文藝語(yǔ)體口語(yǔ)性較強(qiáng),白話(huà)色彩較濃;而新聞?wù)Z體書(shū)面性較強(qiáng),文言色彩較濃。上述調(diào)查結(jié)果也驗(yàn)證了這一結(jié)論。從以下三個(gè)例子中,不難體會(huì)出其文白之別:
本研究選擇中文期刊數(shù)據(jù)庫(kù)“中國(guó)知網(wǎng)”作為數(shù)據(jù)獲取的載體,檢索時(shí)間為2018年05月07日。第一步,通過(guò)高級(jí)檢索精確限定主題為“旅游者+行為”“游客+行為”的期刊文獻(xiàn),共獲取“旅游者+行為”的文獻(xiàn)1 760篇、“游客+行為”的文獻(xiàn)1 804篇。第二步,為避免出現(xiàn)主題不符,對(duì)檢索得到的3 564篇文獻(xiàn)的題目進(jìn)行精讀,以“與旅游者的心理及行為主題密切相關(guān)”為篩選條件,進(jìn)行首次人工篩選,得到2 893篇文獻(xiàn)。第三步,為避免出現(xiàn)重復(fù)文獻(xiàn),進(jìn)行了二次篩選,最終得到2 576篇有效文獻(xiàn)作為初始數(shù)據(jù),并輔助下載了對(duì)應(yīng)的文獻(xiàn)記錄,作為后續(xù)研究的原始數(shù)據(jù)來(lái)源。
(4)昨日上午八時(shí)半許,早膳后,即偕港商李鑒墀與瑪利博士之女及倪兆泰,李燮華,夏迪文等,到中環(huán)購(gòu)物及定船位。(《總匯新報(bào)》,1934-04-03)
(5)九時(shí)許早餐,吃的是果子餃子和稀飯,味是廣東底,也頗合口。(《星光》,1925-11-27)
術(shù)后即刻及術(shù)后24個(gè)月側(cè)凸和后凸Cobb角與術(shù)前相比均顯著改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表1)。術(shù)后冠狀面及矢狀面偏移與術(shù)前相比稍有改善,但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表1)。盡管側(cè)凸和后凸Cobb角均有顯著改善,部分患者術(shù)后仍殘留冠狀面或矢狀面失衡,可能與骨盆傾斜等原因有關(guān)[15]。術(shù)后24個(gè)月SRS-22問(wèn)卷各項(xiàng)得分及總分與術(shù)前相比均顯著改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0.05,表2)。
這三類(lèi)詞的語(yǔ)體色彩差異還可以從用作名詞時(shí)與之共現(xiàn)的支配動(dòng)詞來(lái)感知:“飯”類(lèi)詞的支配動(dòng)詞是“吃”;“餐”類(lèi)詞多與“食、用”搭配,個(gè)別例子中用“吃”;“膳”類(lèi)詞的支配動(dòng)詞是“用”。
到了第二階段(1945—1979年),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的動(dòng)詞用法比第一階段增加不少,共有47例,動(dòng)詞用法與非動(dòng)詞用法的具體數(shù)據(jù)如表3所示:
(6)早飯時(shí)候差不多了,你還不回去吃飯。(《熱鬧人間》,1927-10-16)

通過(guò)上文的統(tǒng)計(jì)分析,不難看出,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在普通話(huà)中已經(jīng)退隱,在新馬百年華語(yǔ)里卻一直都在使用。這一現(xiàn)象可以從祖語(yǔ)(heritage language)的保守性這一角度進(jìn)行解釋
高虹、吳文、張廣勇、郭熙、李計(jì)偉等學(xué)者曾對(duì)heritage language的中文譯名問(wèn)題進(jìn)行了討論。其中,郭熙的論述較為全面,并將heritage language譯為“祖語(yǔ)”。本文也采用這一譯名。
。
值得注意的是,該階段餐食類(lèi)詞的文言色彩有所減弱,在“餐”類(lèi)詞、“膳”類(lèi)詞所處的語(yǔ)境中,白話(huà)色彩較為濃厚。例如:
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病例討論教學(xué)法可以提高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表2中實(shí)驗(yàn)組學(xué)生對(duì)教學(xué)法的滿(mǎn)意度為89.40%,學(xué)習(xí)興趣有了提高(90.07%),教學(xué)參與程度明顯提高(100.00%)。自主學(xué)習(xí)探索過(guò)程中,學(xué)生由被動(dòng)學(xué)習(xí)轉(zhuǎn)變?yōu)橹鲃?dòng)學(xué)習(xí),通過(guò)分析、討論病例,最后每名學(xué)生能獨(dú)立書(shū)寫(xiě)完整的護(hù)理計(jì)劃書(shū),充分提高了教學(xué)參與程度(100.00%)。該方法改變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惰性,提高了學(xué)習(xí)興趣,說(shuō)明該方法可以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學(xué)習(xí)能動(dòng)性。
高端:針對(duì)石油企業(yè)在線(xiàn)平臺(tái)建設(shè)存在的問(wèn)題,“管院在線(xiàn)”特別設(shè)計(jì)了自己的核心學(xué)習(xí)資源庫(kù),匯聚整合全世界最先進(jìn)的培訓(xùn)課程資源。培訓(xùn)課程主要來(lái)自哈佛大學(xué)、中歐商學(xué)院和中央黨校,涵蓋8 個(gè)領(lǐng)域,包括黨建、戰(zhàn)略、領(lǐng)導(dǎo)力、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國(guó)學(xué)等,以提升前瞻能力、綜合管理與領(lǐng)導(dǎo)力、創(chuàng)新與盈利能力,幫助企業(yè)實(shí)現(xiàn)發(fā)展愿景與目標(biāo)。
(9)又到金魚(yú)花園晚膳,晚膳吃后,并不付現(xiàn)鈔,只是用新成督察分局名義簽字記賬,于是又上仙樂(lè)舞廳去跳舞,然后再上外灘水上飯店吃冷飯,然后同去睡覺(jué)。(《總匯新報(bào)》,1946-09-13)
(8)還有葡萄牙前王馬浴艾爾也是一個(gè)不肯拋棄帝王排場(chǎng)的最后人物,一次他到菜館午餐,客人坐得滿(mǎn)滿(mǎn)地,誰(shuí)也認(rèn)不得這位九五之尊。(《星洲日?qǐng)?bào)》,1946-07-05)
(7)對(duì)于有錢(qián)的歌兒自然很苦,可是美國(guó)的老百姓,也不是見(jiàn)得任人在家里有個(gè)娘姨掃地,躺在床上早餐。(《總匯報(bào)》,1946-09-26)
“早餐”在《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全球華語(yǔ)大詞典》中只列出了名詞義,但是在例(1)中卻處于動(dòng)詞的位置上作謂語(yǔ),意思是“吃早餐”。類(lèi)似的用例還有:
(1)紅柳泉油田下干柴溝組下段圈閉主要為巖性圈閉,類(lèi)型有砂巖上傾尖滅巖性圈閉、物性封閉巖性圈閉(成巖圈閉)、砂巖透鏡體三種。

從表4可以看出,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的總體使用數(shù)量、動(dòng)詞用法的使用數(shù)量的順序依次為:“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動(dòng)詞用法使用頻率的順序依次為:“飯”類(lèi)詞>“餐”類(lèi)詞>“膳”類(lèi)詞。這一階段,“膳”類(lèi)詞的動(dòng)詞用法未見(jiàn)一例,極有可能已經(jīng)退隱。
(3)城外有城隍廟,遠(yuǎn)山不甚高。在西關(guān)外市鎮(zhèn)午飯。(《晨報(bào)副刊》,1923-11-14)
三、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演變?cè)?/h2>
該階段餐食類(lèi)名詞的總體使用數(shù)量發(fā)生了一定變化,按由多到少的順序依次為:“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在本階段的使用中,“餐”類(lèi)詞的總文本數(shù)最高,為109個(gè);其次是“飯”類(lèi)詞,總文本數(shù)為60個(gè);“膳”類(lèi)詞的總文本數(shù)最少,為9個(gè)。動(dòng)詞用法使用數(shù)量的排序與第一階段一致:“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從使用頻率方面來(lái)說(shuō),“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的使用頻率分別是33.0%、16.7%、11.1%,也是“餐”類(lèi)詞>“飯”類(lèi)詞>“膳”類(lèi)詞。
引入拉格朗日乘子,得到Γ=I(Y,Xu)-λ(uTu-1)/2,兩邊對(duì)u做偏導(dǎo),即可轉(zhuǎn)為對(duì)互信息矩陣的本征值和本征向量的求解問(wèn)題,根據(jù)本征值的降序排列,可得到對(duì)應(yīng)的本征向量集合,此即為因子的各個(gè)主成分轉(zhuǎn)換向量。
Montrul
、Polinsky
、Van Deusen-Scholl
、Fishman
、吳文
、張廣勇
、郭熙
等學(xué)者,均對(duì)祖語(yǔ)的內(nèi)涵作了界定。我們比較認(rèn)同郭熙的觀點(diǎn),即祖語(yǔ)是社會(huì)主體語(yǔ)言之外作為語(yǔ)言文化傳承的祖輩語(yǔ)言
,這一定義比較符合新馬華語(yǔ)的歷史實(shí)際和現(xiàn)實(shí)情況。郭熙
、李計(jì)偉與張翠玲
均指出,東南亞華語(yǔ)是一種祖語(yǔ),具有保守性。很多研究者都曾對(duì)這種保守性進(jìn)行了探討。Aitchison
、Montrul
基于對(duì)世界范圍內(nèi)的祖語(yǔ)的研究指出,移民群體的語(yǔ)言比留守故土者的語(yǔ)言更傾向于保守。Polinsky也談到:“一些研究人員對(duì)以下事實(shí)進(jìn)行了評(píng)論,即祖語(yǔ)往往聽(tīng)起來(lái)‘保守(conservative)’‘陳 舊(archaic)’和‘過(guò) 時(shí)(obsolete)’。產(chǎn)生這種保守性的看法是因?yàn)橹v祖語(yǔ)的人所使用的語(yǔ)言是上一代人的語(yǔ)言,與祖籍國(guó)的人不同,祖語(yǔ)使用者不會(huì)接觸到他們?cè)趩握Z(yǔ)環(huán)境下社交的同齡人群體。”
李計(jì)偉、張翠玲也明確指出:“相對(duì)于祖籍國(guó)的對(duì)應(yīng)語(yǔ)言,傳承語(yǔ)者的傳承語(yǔ)在發(fā)展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海外華語(yǔ)與現(xiàn)代漢語(yǔ)普通話(huà)同源異流,保守性讓今天的一些海外華語(yǔ)變體保留了當(dāng)前普通話(huà)中已經(jīng)退隱的一些詞匯語(yǔ)法特征,這是海外華語(yǔ)變體特色形成的一個(gè)重要成因。”
可以說(shuō),祖語(yǔ)的這種保守性使得華語(yǔ)能夠較好地保留早期面貌,一些在普通話(huà)中已經(jīng)消失的用法,在華語(yǔ)中卻得以傳承下來(lái)。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能夠經(jīng)過(guò)百年的演變?nèi)员A粝聛?lái),也是由于對(duì)早期用法的維持。
需要指出的是,東南亞地區(qū)的語(yǔ)言狀況比較復(fù)雜,華語(yǔ)與英語(yǔ)、馬來(lái)語(yǔ)、多種方言長(zhǎng)期并存,并且在不同的時(shí)代背景下,華語(yǔ)與普通話(huà)、國(guó)語(yǔ)等的交流有所差異,這些都會(huì)對(duì)華語(yǔ)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前所述,早期國(guó)語(yǔ)中已經(jīng)存在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用法,而華語(yǔ)作為一種祖語(yǔ),其語(yǔ)法結(jié)構(gòu)是對(duì)早期國(guó)語(yǔ)的遷移。因此,在第一階段,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主要是復(fù)制了早期國(guó)語(yǔ)的用法。此外,東南亞地區(qū)有很多國(guó)家在歷史上曾長(zhǎng)期作為英國(guó)的殖民地,英語(yǔ)在各個(gè)領(lǐng)域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際工具,英語(yǔ)里也存在類(lèi)似的表達(dá)方式。例如:
(10)There wasn’t time for breakfast, so I had to go without.(《牛津詞典》,2005)
——沒(méi)有時(shí)間吃早飯,我也只好不吃了。
在例(10)中,“breakfast”既可以作名詞,表示“早飯、早餐”;也可以用作動(dòng)詞,表示“吃早飯、吃早餐”。英語(yǔ)中名動(dòng)同形的例子有很多,除了“breakfast”之外,還有branch(n.樹(shù)枝/v.岔開(kāi))、breach(n.缺口/v.攻破)、figure(n.數(shù)據(jù)/v.計(jì)算)、fire(n.火/v.開(kāi)槍?zhuān)ouse(n.房屋/v.安置)、sense(n.感官/v.意識(shí)到)、witness(n.證人/v.見(jiàn)證)、place(n.地方/v.放置)等。就此來(lái)說(shuō),新馬華語(yǔ)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發(fā)展路徑也可能是英語(yǔ)—早期國(guó)語(yǔ)—早期華語(yǔ)—當(dāng)代華語(yǔ)。
到了第二階段,東南亞很多國(guó)家的語(yǔ)言政策發(fā)生了變化,這也對(duì)華語(yǔ)的使用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如新加坡實(shí)行雙語(yǔ)政策,即英語(yǔ)為主導(dǎo)語(yǔ)言、華語(yǔ)為第二語(yǔ)言。周清海指出:“新加坡雙語(yǔ)政策的實(shí)施使他們所說(shuō)的華語(yǔ)開(kāi)始受到英語(yǔ)語(yǔ)法的影響。”
可見(jiàn),這一階段華語(yǔ)受英語(yǔ)的影響很大,三組餐食類(lèi)同義名詞的動(dòng)詞用例比前一階段增加不少。周清海還指出,在中國(guó)實(shí)行改革開(kāi)放之前,所有的華人社區(qū)(包括歐美、東南亞以及中國(guó)港澳地區(qū)等),都和臺(tái)灣地區(qū)有密切的關(guān)系,臺(tái)灣地區(qū)的“國(guó)語(yǔ)”保留了許多五四前后期的特點(diǎn),很多華語(yǔ)區(qū)的知識(shí)分子都曾經(jīng)在臺(tái)灣受過(guò)大學(xué)教育,臺(tái)灣不少學(xué)者也到華語(yǔ)區(qū)從事教育工作
。因此,這一階段的華語(yǔ)語(yǔ)法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臺(tái)灣“國(guó)語(yǔ)”的影響,從而將早期華語(yǔ)中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用法保留下來(lái)。
在第三階段,華語(yǔ)受到普通話(huà)的影響很大,很多學(xué)者都對(duì)此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尚國(guó)文、趙守輝認(rèn)為:“新加坡華語(yǔ)在規(guī)范化過(guò)程中默認(rèn)的標(biāo)準(zhǔn)是普通話(huà),這在學(xué)界已有共識(shí)。”
周清海指出:“我一向主張新加坡華語(yǔ)必須向普通話(huà)傾斜,盡量靠近普通話(huà)。”
刁晏斌指出:“隨著中國(guó)國(guó)力的不斷增強(qiáng)和國(guó)際影響力的持續(xù)提高,普通話(huà)在全球華語(yǔ)圈內(nèi)的影響會(huì)越來(lái)越大。”
一些學(xué)者也以語(yǔ)言事實(shí)證明了上述結(jié)論。周清海指出,隨著中國(guó)影響的擴(kuò)大,華語(yǔ)有向普通話(huà)靠攏的趨勢(shì),如在新馬華語(yǔ)中使用的“特別好、特別想”等,現(xiàn)在逐漸讓位給普通話(huà)里的“特好、特想”;量詞“粒”逐漸讓位給“個(gè)”等
。刁晏斌調(diào)查了“搞”在華語(yǔ)中的使用情況,由華語(yǔ)第一階段的不見(jiàn)使用,到第二階段以后才開(kāi)始出現(xiàn)并較多地使用
,也證明了普通話(huà)對(duì)華語(yǔ)的影響。因此,“膳”類(lèi)詞在當(dāng)代華語(yǔ)中的近乎消亡,極有可能是受到了普通話(huà)通俗風(fēng)格的影響。
郭熙指出:“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的形成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從全球華語(yǔ)的角度看,有中國(guó)大陸的影響,也有臺(tái)灣的影響,同時(shí)還有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影響。從它接觸的其他語(yǔ)言角度來(lái)看,受到英語(yǔ)和馬來(lái)語(yǔ)的影響相當(dāng)明顯。”
其實(shí),不僅是華語(yǔ)的形成,華語(yǔ)的發(fā)展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華語(yǔ)語(yǔ)法當(dāng)然也是如此。
四、結(jié)語(yǔ)
新加坡、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是全球華語(yǔ)的重要組成部分,距今已有逾百年的發(fā)展歷史。現(xiàn)在新馬華語(yǔ)史尚處在提出階段,下一步首要的工作便是立足于華語(yǔ)的各個(gè)要素,分門(mén)別類(lèi)地進(jìn)行梳理,而語(yǔ)法就是其中的一個(gè)重要方面。本文立足于新馬華語(yǔ)的三個(gè)歷史階段:1919—1944年、1945—1979年、1980年—今,以三套餐食類(lèi)名詞——早飯/午飯/晚飯、早餐/午餐/晚餐、早膳/午膳/晚膳為研究對(duì)象,描述了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歷時(shí)變化,探究了其演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發(fā)現(xiàn),新馬華語(yǔ)一百年間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演變過(guò)程,呈現(xiàn)出一條馬鞍型曲線(xiàn),即使用數(shù)量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使用頻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新加坡、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中餐食類(lèi)名詞作謂語(yǔ)的演變路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華語(yǔ)作為一種祖語(yǔ)而具有保守性的影響,又有英語(yǔ)、漢語(yǔ)普通話(huà)與臺(tái)灣地區(qū)“國(guó)語(yǔ)”的影響。
[1]莊國(guó)土.論中國(guó)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J].南洋問(wèn)題研究,2008,(1).
[2]周清海.華語(yǔ)教學(xué)與現(xiàn)代漢語(yǔ)語(yǔ)法研究[J].語(yǔ)言教學(xué)與研究,2014,(5).
[3]周清海.“大華語(yǔ)”的研究和發(fā)展趨勢(shì)[J].漢語(yǔ)學(xué)報(bào), 2016,(1).
[4]施春宏.從泰式華文的用詞特征看華文社區(qū)詞問(wèn)題[J].語(yǔ)文研究,2015,(2).
[5]李宇明.大華語(yǔ):全球華人的共同語(yǔ)[J].語(yǔ)言文字應(yīng)用, 2017,(1).
[6]刁晏斌.全球華語(yǔ)的理論建構(gòu)與實(shí)證研究[M].北京:華語(yǔ)教學(xué)出版社,2018.
[7]羅驥,錢(qián)睿.東南亞華語(yǔ)傳播歷史研究:現(xiàn)狀與思考[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對(duì)外漢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版), 2014,(2).
[8]徐威雄.馬新華語(yǔ)的歷史考察:從十九世紀(jì)末到1919年[J].馬來(lái)西亞華人研究學(xué)刊,2013,(15).
[9]劉曉梅.豐富描寫(xiě)視角,強(qiáng)化引導(dǎo)功能——評(píng)《全球華語(yǔ)詞典》的性質(zhì)和功能[J].語(yǔ)言戰(zhàn)略研究,2016,(4).
[10]徐祎.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的歷時(shí)考察[A].Proceedings of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C].Memphis,TN USA:University of Memphis,2017.
[11]刁晏斌.東南亞華語(yǔ)詞匯歷時(shí)發(fā)展演變初探[J].語(yǔ)文建設(shè)通訊(香港),2021,(124).
[12]盧月麗.新馬華語(yǔ)“被”字式歷時(shí)考察[J].Global Chinese, 2021,(1).
[13]刁晏斌.初期現(xiàn)代漢語(yǔ)語(yǔ)法研究(修訂本)[M].沈陽(yáng):遼海出版社,2007.
[14]李斐.港式中文詞類(lèi)活用現(xiàn)象調(diào)查報(bào)告[J].漢語(yǔ)學(xué)報(bào), 2012,(4).
[15]高虹.Heritage language的由來(lái)及其中文譯名[J].中國(guó)科技術(shù)語(yǔ),2010,(2).
[16]吳文.繼承語(yǔ)研究:應(yīng)用語(yǔ)言學(xué)界冉冉升起的新星[J].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1).
[17]張廣勇.國(guó)外繼承語(yǔ)習(xí)得研究新進(jìn)展[J].現(xiàn)代外語(yǔ), 2014,(1).
[18]郭熙.論祖語(yǔ)與祖語(yǔ)傳承[J].語(yǔ)言戰(zhàn)略研究,2017,(3).
[19]李計(jì)偉.《傳承語(yǔ)習(xí)得》述評(píng)[J].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 2019,(2).
[20]Montrul,S.The Acquisi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21]Polinsky,M.Heritage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22]Van Deusen-Scholl,N.Toward a Defini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ociopolitical and Pedagog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2003,(3).
[23]Fishman,J.A.Acquisition, Maintenance, and Recovery of Heritage Languages[A].In Valdés,G.,Fishman,J.A.,Chávez,R. & Pérez,W.(eds.).Developing Minority Language Resources:The Case of Spanish in California[C].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2006.
[24]李計(jì)偉,張翠玲.傳承語(yǔ)的保守性與東南亞華語(yǔ)特征[J].華文教學(xué)與研究,2019,(3).
[25]Aitchison,J.Language change:Progress or deca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6]尚國(guó)文,趙守輝.華語(yǔ)規(guī)范化的標(biāo)準(zhǔn)與路向——以新加坡華語(yǔ)為例[J].語(yǔ)言教學(xué)與研究,2013,(3).
[27]周清海.華語(yǔ)研究與華語(yǔ)教學(xué)[J].暨南大學(xué)華文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3).
[28]郭熙.馬來(lái)西亞華語(yǔ)概說(shuō)[J].Global Chinese,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