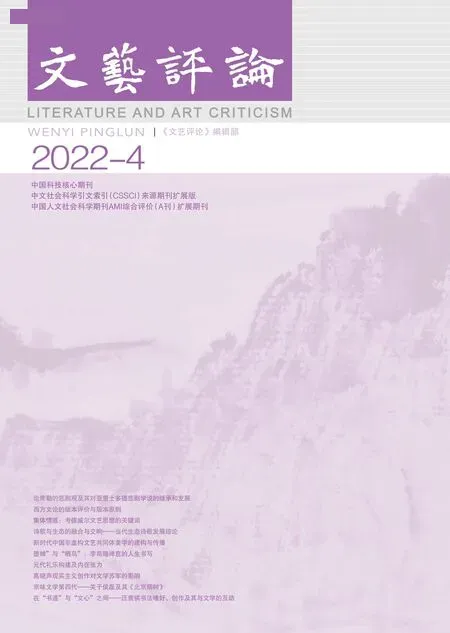曲牌變化對明代戲曲創作的影響
——以曲牌【三臺】【三臺令】為例
○苑杰
戲曲中以數字為開頭的曲牌不在少數,如【一寸金】【一枝花】【一剪梅】【二色蓮】【二賢寶】【二鶯兒】【三臺】【三臺印】【三臺令】等,這些曲牌顯示出數字在傳統戲曲中的特殊用法,《道德經》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道”至“三”依次相生,“三”則“生萬物”,很多時候“三”表達的是多而全的意思。戲曲曲牌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數值上表現得極為盡致,明代戲曲中以“三臺”為名的曲牌有著豐富的表達,本文以【三臺】類曲牌入手,探討曲牌變化的影響因素及對明代戲曲創作的影響。
一、三臺的喻義
一作地名。在四川西北,現四川綿陽地區,唐代稱梓州,宋代稱潼川。杜甫、元稹、李商隱等人都曾在三臺居住過。
二作星宿。《晉書·天文志》(上)中提到“三臺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臺……次二星為中臺……東二星曰下臺”[2],《三國演義》中有諸葛亮夜觀天象占卜命運的記載:“吾見三臺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3]三臺指的是文昌星附近的三顆星宿,常用來暗示命運禍福。記載中國古代全天星官的著作《步天歌》中提到“北門西外接三臺,與垣相對無兵災”[4],顯現出三臺星在古代天宮星宿中的地位,民間習俗發喪也有“頭頂三臺印,腳踏九州罡”之說。
三作官位。古代常把官員與星宿相匹配,顯示其與生俱來的光環,后衍化為重要官員的象征。漢代將尚書、御史、謁者統稱為三臺,《漢官儀》提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5]。宋代王應麟《小學紺珠》第八卷《三臺》中提到“謁者、符使、御史,魏三臺”[6]。《新元史》中也有記載“秩從一品,用三臺印”[7]。三臺作為重要官員大吏的稱謂,在歷代被沿用和變更。
四作筑臺。郭紹孔《詞譜》中記載“天子有靈臺、時臺、囿臺”[8],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中提到“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筑三座高臺(金鳳、圣應、崇先),客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9]。李匡又《資暇錄》記載“昔鄴中有三臺”(指曹操作銅雀、金虎、冰井),作為筑臺的三臺是滿足古代政治需求而建設的重要場所。
五作詞曲。《全唐詩》中一九五題名為《上皇三臺》,沈雄《古今詞話》中提到“《教坊記》亦載五、七言體,如‘不寐倦長更……’傳是李后主《三臺》詞”[10],《敦煌變文集》中記載“更兼好酒唱三臺”,宋代蘇說“余少年聞人唱三臺”,元人仇遠“當日凝香清燕,慣聽八拍三臺”。
三臺作為詞曲之用是由物到形的引申轉化,上文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中提到的筑臺送酒、以其曲名為三臺,五代馮鑒《續事始》中載錄的“漢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蔡邕曉音律,制《三臺曲》以悅邕,希其厚遺”[11]。《資暇錄》中提到的“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為宴游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12]。都是很好的例證。據任半塘考證,原為詞調的【三臺】因表達內容的需要,名前會附加“上皇”“江南”以及“宮中”等定語,“此制傳至宋雜劇內,用之不衰,如《崔護六么》、《四僧梁州》等皆是”[13]。任先生也對此種情況進行了擴展考證,并從唐宋金元時期與三臺有關的題材、調名進行了對比,進一步證實了【三臺】前加題以表達內容的論點。
除調名前加定語之外,三臺轉換為詞曲之后,還衍生出了多個名稱不同的曲牌,如【三臺令】【三臺印】【耍三臺】【疊字三臺】等,筆者選取了較有代表性的【三臺】做文體與音樂分析,探討該曲牌的延續與變化。
二、【三臺】的文體變化
唐代韋應物《上皇三臺》詩句“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為五言四句詩,其中“更”字為平韻,“行”“聲”為葉韻。《九宮大成》南詞中收錄有兩首【三臺】,其中《法宮雅奏》中【三臺】的文句為“如日如云煥赫,重輪重潤輝煌。京洛芳延芝苑,山川秀毓天潢”,唐代王建《雜曲歌辭·江南三臺四首》“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文句雖從五言四句變為六言四句,歸韻方面,第二、四句尾仍為葉韻;對比《九宮大成》收入的三首【三臺令】,《司馬相如傳奇》中【三臺令】“莫叫焚輪成橫擾,更休將銅鳥鬧喧……”言句變為七言十句,《南詞定律》收錄的【三臺令】“撫琴韻切能牽惹,聽琴聲娘行動情。款曲偷身步月行,遂扣向書齊求訊。與君結取鸞鳳侶,辨志誠同坐同行。愿永諧百歲琴瑟,似同心共綰并根”已變為七言八句,且歸韻已不再考究,全以表現內容為主。
可見,不同題材中【三臺】的結構形式變化、戲劇化的表達方式也不同,文詞的表達已由最初的定式向不定式方向發展,當中增加了夾白、襯字、增字、減字等,這些文詞結構的變化都是適應戲劇化表達的具體體現。
三、【三臺】之曲體變化
(一)【三臺】與【又一體】對比分析
以《九宮大成》收錄的2首【三臺】曲牌為例[14],樂譜如下:

圖1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收錄曲牌【三臺】與【又一體】曲譜
1.同質化內容。從結構來看,這首【三臺】與【又一體】的音樂結構完全相同,共分為四句,與詩句的首、頷、頸、尾保持一致,使用的音階為五聲音階,宮調為六調羽調式,板式為散板,音域跨度保持在兩個八度之間,字與音的匹配以一字一音為主,少有復雜節奏,結構為兩段式A+B型,A段句末落角音,B段句末落羽音;從詞體結構上來看,上下兩句詞體平仄均為:仄仄平平仄仄(句),平平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句),平平仄仄平平(韻)。從表達內容上來看,第一首詞描寫自然風景變換,第二首詞感嘆人生飛逝,表達的都是時光變換的內容。此外,《九宮大成》在對【三臺】的注語中提到“【三臺】一名【開元樂】”,《中國詞學大辭典》中也稱“【開元樂】即《三臺》”[15],在標記音樂的來源時,《九宮大成》提到【三臺】為教坊曲,而開元樂與教坊曲的稱謂都是唐代音樂術語。由此推斷,在唐代【三臺】最初的表達內容與時間變化有一定關聯。從詞曲關系來看,兩首詞都是二十四字,文句雖內容不同,但音樂基本相同,當為依曲填詞之作。
2.延展與變化。【三臺】的節拍句段為九、十、十、十一小節,【又一體】的節拍句段為七、十二、九、十小節,通過節拍的對比可以看出兩首樂曲在使用過程中發生的變化。首句對比骨干音為1 2 3 3-,首句節拍不同處主要體現在單個音的重復、加花等方面,如1音重復為1 1,2 3加花為2 12 3,這些都是節拍發生變化的具體體現;頷句的變化內容起始音為羽宮音變化為角徵音,雖然起音發生變化,音程的三度關系未改變,不影響原有的音樂風格,其中“輝”字的樂音在【又一體】的“人”字句上進行了延展,變化為5.6 11 16,在骨干音樂的基礎上進行小角度的延展擴充,以達到詞樂相配的目的;頸、尾兩句音樂基本保持原有樣式,以實現原曲牌與又一體的統一。
(二)【三臺令】與【又一體】對比分析
《九宮大成》收錄【三臺令】與【又一體】共三首曲牌,分別出自《法宮雅奏》兩首、《南詞定律》一首,這三首曲牌的宮調均為羽調式,筆者以前兩首為例做音樂分析。曲譜如下:

圖2 《法宮雅奏》中曲牌【三臺令】與【又一體】曲譜
1.同質化內容。這兩首【三臺令】的文詞,其中第一首是十句六韻,前五句為七言,第六句三言與第七句四言可合并成七言,第八、九、十句為四言;第二首是十句八韻,前五句為七言,第六句三言與第七句四言可合并成七言,第八、九句為五言,第十句四言,兩首曲牌的平仄關系變化不大。
兩首曲牌的句末落音如下:
可以看出十句文詞的落音基本也是保持一致,以宮、角、羽三個音為主,首句都是散板起音,每句落音相對固定,保持了曲牌音樂的調式屬性和風格的統一。
2.延展與變化。音樂的延展與變化主要體現在節拍和節奏的擴充與縮減上,【三臺令】共52小節,【又一體】27小節,兩曲牌文詞語句節拍數統計如下:

表1 曲牌【三臺令】與【又一體】句段落音一覽表
從節拍數量上來看,這首【三臺令】節奏數量接近【又一體】的兩倍,除去起始的散板弱起小節,其他語句分句基本按照【又一體】原有節拍的基礎上,以兩倍延展的形式進行節奏和旋律變化。以散板啟句為例,【又一體】音樂形式為為4/4拍一小節,【三臺令】中與之相對應的音樂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兩個曲牌的音樂延展使用的手法,主要是節拍時值的增倍,在音符不變的情況下,將一拍的切分節奏擴充為兩拍的切分,將一拍的時值變為兩拍的時值并擴展為新的小節。在保持音型的前提下,通過調整節拍時值達到擴增的目的,與現今調整音樂速度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詩詞曲賦辭典》中對【三臺】做如下介紹:“詞牌名。或稱【三臺令】,二十四字小令,與唐代韋應物等的《三臺曲》完全相同……又【調笑令】亦名【三臺令】與【三臺】不同。”[16]對比上文《法宮雅奏》中的【三臺】與【三臺令】,兩者在宮調、節奏等方面皆為不同的內容,【三臺】為六調,【三臺令】為凡調;【三臺】為一句一小節,句式較為規則,【三臺令】為一句多小節,句式不規則;【三臺】為六字句,【三臺令】為七字句,兩曲牌當為不同的曲牌形態。

表2 曲牌【三臺令】與【又一體】句段節拍數統計表
四、曲牌變化的影響因素
上文可以看出同以“三臺”為題名,【三臺】與【三臺令】的音樂曲調卻不同,且音樂的差異性較大,牌名相近,音樂卻不同,此類情況在戲曲曲牌中普遍存在,產生這類情況的影響因素主要有社會性因素和人為因素方面。
(一)社會性因素。
一是受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影響。現存的古典戲曲曲譜多以雕版或手抄的形式保存,且存量與典籍中著述的數量相比差距較大,受記譜方式影響,曲牌音樂行進的諸多變化在雕版的記錄中無法全貌呈現,如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朱權的《神奇秘譜》等刊印、發行數量少,還存在刪減、記譜減字等現象,給后續的音樂復原造成影響。另外文字譜、工尺譜的記譜方式僅能記錄宮調、音樂的骨架板眼等少數音樂表現形式,在記譜過程中制式不規范、標準不統一等,也嚴重影響了曲牌音樂的再現。加之,在曲譜傳播過程中有些詞匯的表意不明確,如樂曲、樂句、譜式等詞,在不同的戲曲劇作、不同年代表達的內容存在不同的理解,或為戲曲文詞的平仄音韻,或為板眼節拍的長短,或為音樂行進樂音的高低等,如《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題為“音”和“譜”,卻是按東鐘、江陽、支思等進行的分韻,類似的社會性因素給曲牌音樂的傳承增添了變化。
二是受中國傳統音樂民間性特征影響。曲牌的來源之一是我國傳統的民歌,民歌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變化,也存在很多的即興性,隨著傳播地域的不同也有旋律上的變化,如民歌《茉莉花》在傳播過程中就有江蘇、河北、東北等多個版本,且南北方的《茉莉花》在旋律上有很多的差異。作為曲牌的源頭之一民歌在傳播中產生的流變,很大程度影響著曲牌音樂的變化,曲牌音樂伴隨著戲曲的傳播也會產生流變,如曲牌【銀紐絲】在各個戲曲、說唱中就有四十多個曲種,[17]且每個曲種都有旋律的變化,這種影響在各個曲牌中是普遍存在的。
三是受演出形式和審美需求的影響。在戲曲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戲曲演出都是商業性的。在民間,從業者多與商賈的商業往來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戲曲的表演也會隨著商業的交往、觀劇者的審美進行一定的調整。在宮廷及私家演出中,也會根據節慶、時令的需要隨時調整,統一制式的曲牌音樂滿足審美多樣化的需求進行的調整,也加劇了曲牌的變化。如昆山腔原起于吳中,魏良輔改革昆山腔吸收了余姚腔、海鹽腔等其他戲曲聲腔的內容,改制為“水磨調”的昆山腔,改制后的昆山腔曲牌音樂的表現形式也得到進一步提升,極大豐富了昆山腔的表現力。
(二)人為因素。
一是受曲牌音樂在民間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影響。在民間,師徒制口傳心授是戲曲音樂的主要傳承方式,口傳心授的具體表現為師父以口傳的方式教授,不用樂譜;演員以模仿的方式進行學習;伴奏樂器的演奏者也以模仿和自學為主。口傳心授沒有規范的模板參照,傳承的標準和內容多靠參與教與學的記憶進行,記憶受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的影響,無法原樣保留,教與學的主體在傳承過程中都有個人理解的外在因素,因此無法實現全樣的復制,導致口傳心授在傳承中會出現片段或章節的變化或缺失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曲牌的傳承和變化。
二是受創作需要的影響。因戲劇表演需要,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戲劇表達內容需要,戲曲創作者在創編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內容的需要選擇不同表現的曲牌進行戲劇結構和音樂框架的搭建,而戲曲曲牌較為明顯的音樂特點是散板較多,甚至有些節無定拍。創作者所選取的曲牌,有時會根據需要增加節拍的速度或減緩速度,以實現戲劇表達的音樂需要。而節奏、節拍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音樂情緒的表達,如馬致遠創作的小令《天凈沙秋思》,為越調曲牌,強調越調實際就是進一步強化文樂關系的相適要求,以體現文詞要表達的內容,換成音樂激昂的調式則曲不達文。當固定的曲牌調式無法滿足文詞內容呈現時,創作者就會選擇相近的曲牌做調整處理,這也是曲牌形態發生變化的另一個影響因素。
三是受表演者二度創作的影響。舞臺表演的二度創作是戲曲作品靈魂呈現的關鍵點之一,優秀的表演者會根據作品戲劇表達的需要進行舞臺的細節處理,莎士比亞說“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千個竇娥的表演者也會呈現出一千個竇娥形象,每個人對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表演者的理解不同,舞臺呈現的人物角色和情感表達便不同,這種表演的二度創作實際就是對曲牌的創新,也是同一曲牌,不同的表演者賦予的外在表現不同的結果。
五、曲牌變化影響因素對明代戲曲創作的影響
一是經濟條件變化促使戲曲創作主體的多樣化。經濟條件的改善,尤其是戲曲作品的雕版刊印,促進了戲曲的傳播。明代以來不管是官方刊印還是民間刊印,戲曲作品在社會各階層中受到普遍關注,戲曲由最初產生于民間的俗文學到被文人大眾所接受,創作的主體也由最初的社會才人、娼妓優伶向士大夫階層轉變,其間諸多的文人作家加入,提升了戲曲作品審美趣味和文學價值。如明初戲曲家中的寧王朱權,士大夫階層的湯顯祖、沈璟、李漁、呂天成、葉憲祖等一大批文人作家,據日本學者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統計,明代僅雜劇作家和傳奇作家就有395人次之多;在戲曲作品方面,《牡丹亭》《西廂記》《琵琶記》《玉簪記》等戲曲名作不勝枚舉。
二是中國傳統音樂的民間性特征提升了戲曲作品的表現力,戲曲作品集曲化結構形態更加明顯。民間曲調的靈活多變衍生出更多的曲牌變化形式,如【又一體】【犯調】在明代戲曲中普遍存在。集曲是由不同的曲牌混合而成,曲牌數量的集增提升了集曲的表現力。《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中收錄南詞1335支,其中集曲541支,集曲比重占據了南詞總體的40%;《南詞新譜》則收錄集曲439支,占總曲目比例接近一半,可見集曲在南曲中的分量。集曲的出現是民間曲調、曲牌多樣化的產物,它在不脫離劇本的前提下,給了曲牌“無可窮盡、無可規范”的廣闊空間,實現了傳統音樂變化觀念與藝術創作實踐上的融合,極大地滿足了明代文人作家戲曲創作的沖動。
三是審美需求的變化所衍生出的對戲曲藝術表現的大討論。明代戲曲創作對后世的影響始終繞不開的話題之一是沈湯之爭,沈湯之爭的核心內容是戲曲文詞與音樂的關系。明代之前,選曲填詞一直是戲曲創作的主要形式,隨著文人作家的大量加入,社會審美需求的變化,對戲曲文詞與音樂的趨美也越來越明顯,從而產生的對戲曲美學的討論一直持續于戲曲創作中,以沈璟和湯顯祖為代表的戲曲家將戲曲創作的核心定位在文詞與音樂兩個主要方面,通過協調兩者間的關系來實現戲曲美學的藝術表達,對后世戲曲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是戲曲舞臺表演引發的對能否實現戲曲創作“表意”的關注。戲曲作品能否在社會大眾中受到認可,舞臺表演是關鍵要素之一,表演者的舞臺展現能否最真實表達出戲曲作品的內容和情感也是創作者關心的焦點之一。因此一個成功的戲曲作品不僅僅是文能達意,還表現在能否牽住觀賞者的內心情感,實現作品與觀賞者的情感統一。明代的戲曲創作除了作品本身,已經注重到戲曲表演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一點在潘之恒的《鸞嘯小品》和《亙史》中有具體體現。潘之恒在著作中除了記錄明代當時優秀的戲曲演員外,還對戲曲的創作與表演展開論述,他認為戲曲演員必需要具備“才、慧、致”,掌握了“度、思、步、呼、嘆”等技術技能方可進行戲曲表演,具備“能癡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寫情”,才能算是優秀的戲曲作家。這種角度獨特的戲曲理論對當時戲曲創作和舞臺表演有較強的影響,促進了戲曲創作與舞臺表演的有機結合。
綜上,戲曲曲牌變化其內在折射出的思維模式,是社會與人文綜合作用的產物,音樂家黃翔鵬在總結中國傳統音樂傳承時曾用“傳統是一條河流”給予形象的比喻,作為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戲曲的曲牌音樂也是如此。傳承與創新時時交織在一起,密切聯系、相互影響,使得同一曲牌的表現力不斷豐富,音樂的變化又使得同一曲牌的音樂內容不斷延展、擴充,甚至產生風格的變化,這也是我們看到的戲曲曲牌出現“同名不同樂”現象的根本原因,也對明代及明代以后的戲曲創作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