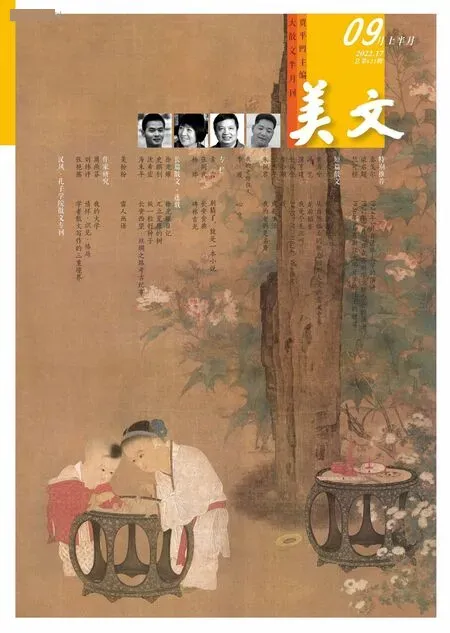我的老媽是名角
◎ 朱佩君
我的老媽是名角。這個從小我便知道,而且這是我在舅家村里小朋友當中稱王稱霸的資本。想當年,只要提起老媽演的《三滴血》里的周天佑,她的戲迷們就興奮得不得了,激動得眼放光芒。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劈山救母》里青年時期的劉彥昌,老媽那扮相別提有多俊了!再加上那一口的好唱腔和瀟灑的表演,活脫脫一個英俊才子,角色被她刻畫得惟妙惟肖,讓人津津樂道。仔細想想,當時的三原劇團可是很厲害啊!風格完全追隨省戲曲研究院,除了演員表演精湛,行當齊全,樂隊水平也可圈可點。讓我記憶猶新的是舞美設計實在太牛了。《劈山救母》中的精彩畫面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用塑料剪成雨條的二幕簾子在兩邊舞美人員不停地用力抖動下出現了傾盆大雨的效果,加之電閃雷鳴的音效和忽明忽暗的燈光,把雷雨交加的氣氛營造得特別逼真。媽媽扮演的英俊小生劉彥昌打著傘奔跑在雨中,那一圈圈的圓場形體動作與唱腔和舞美的配合相得益彰,非常完美。三圣廟內劉彥昌求簽跪拜,臺上圣母畫像在燈光的配合下,變幻真人姿態,那夢幻般的美感必引得臺下叫好聲、掌聲不斷。再看看圣母與劉彥昌分別時駕云飛天……哇!看得人如癡如醉,如夢如幻。
你要是問我老媽什么戲最拿手,那可就太多了,且聽我慢慢道來。媽媽的戲路特別寬,各個行當都能來兩出。古典戲里小生、青衣,老旦戲行行不擋,演啥像啥。現代戲《洪湖赤衛隊》里邊的韓英娘,《杜鵑山》里邊的柯湘,《劃線》的老太太,人物形象都刻畫得入木三分。《三娘教子》是老媽的看家戲,至今令人稱道。在悲涼的曲牌聲中,她臺步從容地走上舞臺,左手提著紡線籠,右手水袖隨著心理情愫自然輕抖“落地”,來一個得體的亮相,然后開機房門、上機織布、打結口、咬線頭,一招一式都非常細膩生動。媽媽的唱腔風格樸實深沉、高昂深厚、剛柔相濟、富有韻味,一聲“唉……”字的叫板拖腔便把觀眾帶入三娘的心酸往事中。以情帶聲,字正腔圓,行腔抑揚頓挫把握得很好,從輕聲“把冤家好比一枝蒿”到“澆的蒿兒長成了,用它與我搭座橋,娘行橋心橋斷了,半路里閃我這一跤”,把王春娥委屈、怨恨但又無奈的情緒表演得層次清晰。
教訓薛倚哥“不孝的奴才聽娘言”,悲憤激越中見深情;回憶從前,幾個“娘為兒”如泣如訴,“三九天凍得娘啪啦啦顫”一句,節奏突慢,字字頓出,“啪啦啦”輕聲輕氣,“顫”字如江河奔騰,—瀉千里,加之她雙手抱肩,渾身顫抖,將王春娥的滿腹苦楚表現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老媽聲情并茂的表演感染得臺下觀眾哭成一片。
再說說我那名角老媽光環背后的故事吧。
聽外婆講,老媽生下來的時候,外公因女兒太多,壓根就沒打算要這個多余的女娃。他狠狠心,提著嬰兒的雙腿,塞進尿盆,雙手緊緊捂在上面……嬰兒微弱的啼哭聲驚動了在隔壁房干活的二姨媽,她趕緊找來了在家里既有文化又有話語權的大姨媽及時阻止,才救了老媽一條小小的生命。誰成想到,后來她竟成了外公的驕傲、家族的榮光,出落成當地最紅火的名演員。
提起老媽的演藝生涯真是讓人忍俊不禁。用老爸的話來形容老媽,就是“混世魔王”。還真的沒有下過什么功夫,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一個名角兒。
媽媽1958年考進入陜西省藝校(我跟媽媽是校友)當學員,開學沒多久便出現了狀況。因為身體的原因不能練功,她只好改行學了舞美。得知消息的外婆心里總是不安,又舍不得她,所以千方百計地把她調回三原縣城,在劇團跟著舞美隊學畫面布景,搬搬道具。用媽媽的話講,就是整天跟著畫娃娃。一次偶然的機會轉變了她的命運,讓她脫穎而出。那年她十二歲,當時縣劇院演《狀元媒》,戲報貼出,票也賣空,晚上快開演時,扮演八賢王的演員臨時出現狀況,需要有人救場。團里能用的人都在臺上,實在沒有人可以頂替這個角色。無奈之下,在一旁埋頭整理道具的媽媽被劇團點名上場。上了戲妝的媽媽實在太好看了,上臺一個亮相,“好!”臺下掌聲雷鳴,大家嘖嘖贊嘆。“這八賢王太俊了,喔嗓子咋那么好聽哩。”“好!好!”媽媽就這么火起來,擁有了好多好多的戲迷。
媽媽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佳作不斷,特別是《三滴血》里扮演的娃娃生周天佑,迷倒了很多觀眾,收獲了一大批戲迷。有一個叫黃鳳梅的女人,是當時縣文教局局長的夫人,她天天趴在舞臺口看《三滴血》,媽媽演的周天佑看得她如癡如醉。十二歲的媽媽真是風光無限啊!不但唱紅了三原縣,在隔壁鄰縣也擁有了大批戲迷。那可是真火啊!要說我最愛看的,還當屬媽媽演的老旦戲。
媽媽演的青衣戲也非常出色,《五典坡》中的王寶釧就塑造得特別成功。《趕坡·回窯》可是我老爸老媽的經典保留節目。兩個人唱腔精彩,表演默契,說唱逗玩,生動有趣。特別是:“細觀他眉來眼去眼去眉來總有假,五典坡還要盤君家,你說我平郎丈夫他賣了我的話,誰是三媒六證家?”“這是銀子三兩三,拿去與你把家安……”“這錠銀子莫與我,拿回家……(這段要表現出王寶釧怎么著也是相府千金,但無奈還是被逼得罵了人)給你娘安家園。”這段對唱一問一答,王寶釧正言正語,薛平貴有意戲妻。兩個人物“一急一戲,一怒一皮”,兩個人表演得非常默契,現場氣氛熱烈。我真的很佩服老媽,她的唱腔底氣很足,唱幾小時不在話下!趕坡后面的這段大唱腔也非常出彩,特別是最后幾句:“這一錠銀子莫與我,拿回家與你娘安家園。量麥子來磨白面,扯綾羅來縫衣衫。你娘吃來讓你娘穿,把你娘吃得害傷寒,有朝你娘死故了,埋在十字大路前,叫和尚把經念,叫石匠把碑嵌,上寫你父薛平貴,你娘王寶釧,過往君子念一遍,軍爺,兒呀,把你的孝名天下傳……”這段表演要邊唱邊走,云步身段要配合協調,唱得給力,是很見功夫的一出戲!
老旦戲《汲水》也是老媽的代表作品,她憑借此劇獲得1989年陜西省中青年演員折子戲大賽一等獎殊榮。其中有個橋段在我腦海里非常深刻:老媽扮演的土衣步裙、白發蒼蒼的老太太,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提著水桶,顫顫巍巍地去井邊打水,思兒成疾的她好似有些失憶。看見臺上君子趕緊拉住喚兒,上下仔細端詳,才覺得自己搞錯了,遂傷心失望地唱道:“都怪我老婆子瞎了雙眼,把君子錯當成自家兒男,人老了心昏了錯事不斷,忙施禮望君子體諒包涵。”這段唱腔要把老太太失望、悲涼、凄苦的情緒表達精準,要讓看的人幾度落淚。
老媽是個多面手,戲路很寬。舞臺上,老媽還塑造了性格潑辣、表演夸張的《母老虎上轎》。
媽媽的前半生把一切精力都奉獻給了舞臺,奉獻給了秦腔,但對自己的親人卻留下了很多無奈和遺憾。因為常年下鄉演出,不能照管子女,無奈之下,她只能把年幼的我們分別托在親戚家照看。姐姐生下來就在舅舅家半個城喂養,我被托放在南鄉的一戶農民家中寄養。每當劇團回到縣城,媽媽便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半個城與南鄉之間。在一個大雨瓢潑的上午,媽媽在舅舅家看了姐姐,又得蹚過漲水齊腰的青河去看不到二歲的我。南鄉的看家很不地道,將母親每月送的奶粉喂養了自己的孩子,每天只用藕粉喂我,導致我營養不良常常生病。抱著身體虛弱瘦小、頭都抬不起來的我,母親哭得淚流滿面。她痛斥了那戶人家后,便抱著我頭也不回地到了縣城。幾天后,劇團又得轉點。那天寒風呼嘯,微雨中還夾雜著雪粒兒,爸爸背著鋪蓋,媽媽抱著病怏怏的我,心酸苦楚地踏上了劇團轉點的破舊卡車……幾經周折,無奈的母親又抱著我回到舅家,雖然很難為情,但還是將我交給了外公外婆看管。
劇團的下鄉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未改變,媽媽的戲也是越演越火,舞臺上風光無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省上決定恢復同州梆子劇團,媽媽被特別選中,要調回省戲曲研究院。時任主管文化的副縣長杏彬堅決不準,他說:“想要調走王亞萍堅決不行,就是給十個演員,我們縣也不同意換。”原本的命運轉折的機會被阻隔,媽媽的前程也就定格在了三原。
舞臺上媽媽簡直是拼命三郎,經常演三連臺。那年劇團在長安縣一個村子下鄉,她上午演了《鍘美案》的秦香蓮,晚上又演《劈山救母》的劉彥昌。因表演投入太深,非常恨戲。雖說是贏得了掌聲與喝彩,但由于過度疲勞累破了耳膜,從此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團里,媽媽是勞動模范,從未因家事影響過團里的工作。爸爸說:“你媽媽演了一輩子戲,當了一輩子先進。我們兩口子在團上兢兢業業,就是對你外公外婆有虧欠啊!”是啊,提起外公外婆,那可是媽媽一生最大遺憾。
外婆一生為我們家付出了很多心血,去世的時候都沒能與自己最喜愛的女兒見最后一面。噩耗傳來,在外地下鄉的媽媽強壓著極大的悲痛,堅持在舞臺上把戲演完。急匆匆趕回家中,眼前已是白門白幡,哭聲一片。“媽……”她撲倒在外婆的靈前,撕心裂肺地吶喊,由于極度悲痛,幾番哭暈在外婆靈前。
生活中,媽媽是個好妻子。她對爸爸的生活照顧真可謂是體貼入微。媽媽有一句名言至今還縈繞在我的耳邊:“夫主貴為天,妻賢理當然。”雖說這是一句戲詞,但在生活中,媽媽真是這句話的踐行者,一個好典范。
在我的記憶中,清晨,父親剛一睜開眼睛,媽媽便趕緊給坐在床上的老爸遞上熱毛巾讓他擦臉,隨后一大搪瓷缸的熱茶就端在了跟前。在父親面前,她從未有過名演員的矯情,時刻小心翼翼地看著父親的臉,生怕沒了親人在團里又遭受打壓的父親發脾氣。鄰居們時常看不過眼,就說:“你這么大個名氣的演員被訓來訓去,你咋就不吭氣呢?”媽媽說:“唉,他恓惶得缺肋骨少肺的(因為肺結核手術,老爸被切掉了三根肋骨和半頁肺),除了我娘家和三個娃,他自己老家一個親人都沒有了,心里憋屈,讓他發泄發泄心情能好些。”
這就是愛,溫暖且有力量,再大的付出媽媽也心甘情愿。但媽媽也是有個性、有脾氣的,可千萬別觸碰到她的底線,偶然的一次發作都相當有威懾力,嚇得大家都不敢吭聲。
媽媽和爸爸的愛情也讓人特別羨慕。他們永遠是出雙入對,夫唱婦隨,有時候忘情得都顧不上自己的子女。劇團的賈伯伯常常打趣說:“王亞萍,你是個好妻子,但可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哦。”母親笑笑說:“那這能怪誰,還不是在你的指揮下給劇團賣命哩,劇團那些年忙得光下了鄉了,哪來時間管娃嘛!”
媽媽在陜西有很多的戲迷,她和她們相處得似姐妹一般。柏社原上的姨媽就是其中一位。善良的姨媽給了我們家許多愛、許多暖。我的戲迷“姨媽”還有好多,幾十年來,媽媽和她們的關系從未間斷。因為稱呼“咱姐”過于親近,當年還曾惹得大姨媽有點吃醋:“還是咱姐?看你把外人叫得親的喲,誰是你姐?我才是你親姐呢。”
進入老年的媽媽變得有些敏感,稍稍一點小毛病到她那兒就變成了大麻煩。這時候,秦腔就是她的良藥。只要板胡一響,她頓時精神抖擻,一聲:“諸位英雄,請啊……哈哈哈哈哈哈……”《破寧國》里英俊瀟灑的朱元璋瞬間出現在大家眼前。
每次來到北京,我都會拉著她和老爸去參加北京的票友聚會。媽媽的拿手戲《三娘教子》唱得人聲淚俱下,和爸爸合作的《趕坡·回窯》配合默契,表演得天衣無縫。姜還是老的辣啊!讓媽媽最難忘的是我們全家都榮幸地登上過北京的大舞臺,盡情展現了一生摯愛的大秦之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