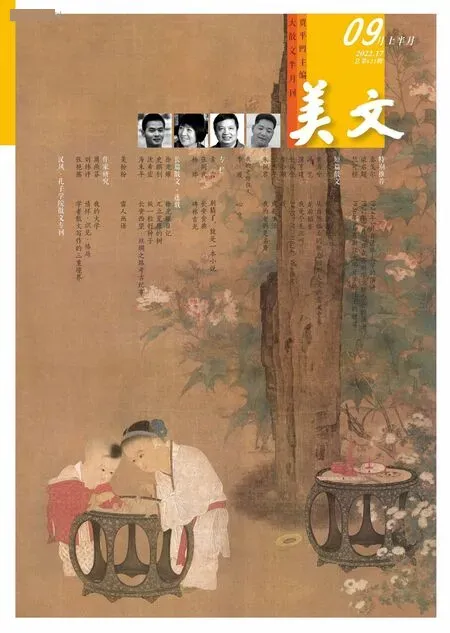我的大學
◎ 周燕芬
我的大學,叫“西北大學”,老校區坐落于古城西安西南城角,就是護城河由東到西再向北拐彎的地方。
我于1981年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是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制度以來的第五屆大學生。經過了77級以來的幾屆高考招生,對于我們這些高中畢業生來說,如何報考如何選擇學校和專業,按說是有些經驗可以借鑒,但在我的記憶中,除了成績這個決定因素外,好像并沒有多少個人的未來規劃參與其中。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陜北老家,父親做主說,女娃娃家的,不要走太遠,西安就最好。西北大學中文系在陜西是拔頭籌的,我的成績又剛好夠上了分數線,很順利就被錄取了。從榆林到西安,長途客車搖晃了兩天,暈得要死要活,迷迷瞪瞪地被高年級學長接進了西北大學的校門。
那是一個多雨的秋天,開學一個多月了,陰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加上極度地想家,給父親寫信說,西安哪有你說的那么好,連太陽都沒有,寫著寫著禁不住要哭。太陽終究還是出來了,西北大學的新鮮姿容和迷人風物展露眼前,吸引我去親近她融入她。大學生活日日變得緊張有序和豐富美好起來,唯一不同的是我離開了家,一年級的時候還是掰著手指頭期待著寒暑假。那時候不知道上大學對于我究竟意味著什么,也沒有意識到,大學正在為我尋找一個新的家,一個獨立自主的家,一個依托終生的家。
40多年過去了,我由一個西大的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入職當老師,直至今天變成學生眼里的老教授,西北大學120年的歷史,晚近的這40年,我也算是一個親歷者,西大是我的母校,而每每校友們弟子們歸來,我又代表著他們的母校,以這樣的身份來說西大,不可能不偏心不護短。記得2018年西北大學建校116周年慶典大會上,大學兄賈平凹有一段著名的發言,他說:“在我心中,我的母親是世界上搟面搟得最好吃的,我的母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學校。”這話說得很入心啊,不單因為是小說家會說話,更因為那是一種血緣親情的觸動,懂得感恩母愛的人一下子就意會和共鳴了這樣的表達。無需過多解讀,學子與母校之間,有這“一顆心”就足夠。
西北大學校史從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寫起,光緒帝朱批開辦陜西大學堂,成為西北大學創建的標志,也是高等教育在陜西乃至西北的發軔。其后幾度沉寂,又幾度興起,終于在1939年以國立西北大學統冠陜、京兩源,發展至今。中國高等教育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歷史景深中走來,西北大學與百年社會動蕩同波共振,有過領航西北的威名和榮耀,卻也經歷了更多的坎坷磨難。兒或不嫌母丑,卻并不等于著我們會遮蔽歷史的誤區,掩飾時代的傷痕,高教歷史恰是被身處高校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不斷檢視和省思著。我常想,西北大學正如一位飽經滄桑的母親,對于她的兒女們來說,那久遠的歷史積淀和艱苦歲月中的人文堅守,或許還帶著隱隱傷痛與悲情,卻是一份更值得后代珍藏的寶貴財富。
因籌備120周年校慶的需要,我參與了文學院中文學科史的撰寫工作,分給我執筆的歷史時段是1949年至1977年,眾所周知的特殊歷史時期。其實我自己也完全沒有經歷過這段校史,但不能推辭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我已是目前在職教師中年齡離這段歷史最近的人了。一切從頭開始,翻閱資料,走訪前輩老師,用了做學問的功夫。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學校頒發了《國立西北大學暫行組織規程草案》,重新規定校名為“國立西北大學”,1951年12月教育部通知,重新修正校名“西北大學”,一直沿用至今。自抗戰時期高校西遷之后,新中國的西大又經歷了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和1992年開始的高校合并,現代大學在中國發生發展的每一步,都在西北大學校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努力在1949至1977年的校史中尋找中文學科的發展脈絡,卻發現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起步階段應對高校各專業多次進行的分合拆制,愈來愈頻繁的政治運動也在不斷地干擾著高等教育的正常運轉,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隨著政策的起伏變化而呈現出時斷時續的軌跡,尤其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正常教學科研秩序遭到破壞,甚至相當長的時間內基本處于停頓狀態。這就更需要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在這一特殊的歷史區間里尋幽探勝、披沙揀金。
所幸是金子總會發光。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侯外廬校長的感召下,西北大學一時間俊彥薈萃、名師云集。其中張西堂、傅庚生、郝御風、劉持生等教授,是西大乃至全國高校中文系名號頗響的人物,他們治學精湛、個性卓然,無論學術、師德還是文人風骨,都令后輩追慕不已,只可惜這樣正常的學術歲月太短暫了。但即使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蒙受冤屈慘遭批判,先生們依然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堅守教育和學術陣地,據理自辯,不卑不亢,他們是校史中承載大學精神的典范,是最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標桿性學者。
翻閱史料的過程中,最令我無法釋懷的一件事情發生在1967年。老教授傅庚生先生和老干部張宣先生被造反派批斗凌辱,“孟昭燕老師給學生們講道理,卻被打得遍體鱗傷,臥床數月”。孟昭燕是我的老師,我20世紀80年代上大學后,她曾給我們上過中國現代戲劇文學專題課,記得她的講義是一個發黃的小本子,不緊不慢地坐在講桌前,標準的普通話里帶著好聽的京味。她講《雷雨》中的人物,抑揚頓挫地念出臺詞時,一個美麗而幽怨的蘩漪形象就活在眼前了。后來我們才知道,孟老師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經飾演過蘩漪一角,她是20世紀50年代北大畢業分配來西大的,是著名歷史學家張豈之先生的夫人。于是,孟老師在同學們心中愈加神秘起來,回回上課都想搶坐在前排。我心中這樣的孟老師,無法想象她當年竟遭如此厄運。一個年輕而文弱的女教師,能站出來保護老先生,在那樣的嚴酷環境中是需要膽量的。我吃驚于孟老師竟然用“講道理”來對待施暴者,靜下來想,以孟老師的身份和性格,她會用那個時代流行的斗爭方式來教育學生嗎?當然不會。她只會用師者的苦口婆心,甚至是女性的溫言軟語,讓孟老師挺身而出的或許不是我說的膽量,而是天性和教養。我看了中文系“新三屆”為畢業30年編輯而成的紀念文集,加上我們自己的《八一集》,每一屆回憶老師感念師恩的文章,都描述過孟老師當年的文學課堂,孟老師那詠誦話劇臺詞般的講課聲音,是如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讓他們幾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我理解,這就是文學感性的力量,是藝術美感發生了作用,這美感在作品中,也在孟老師身上。孟老師2016年去世時,我正負責著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工作,記得是一大早坐校車趕去殯儀館告別老師,站在孟老師靈前,腦子里盤旋的竟然還是老師上課的情景。斯人已去,聲猶在耳,那一刻我悟到了,老師是以她獨有的授課魅力,把她的文學教育雕刻在學生的心里了。
1981年我們這一級走進西北大學時,幾位前輩大師如傅庚生、劉持生和單演義等先生年事已高,不再登臺為本科生授課了。但我和我的同學依然非常幸運,遇上孟老師這樣一批文學的啟蒙老師。他們大都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大學畢業,或留校或從外地分配來西大工作。在那個歡樂與痛苦交織的時代洪流中,他們經歷了種種人生選擇和內心矛盾,革命的疾風暴雨確乎洗掉過知識分子曾經的傲岸和儒雅,而深藏于內心的,對知識的崇尚、對美的感應和對學問的敬畏,卻如披在靈魂上的無形袈裟,未曾真的離去。一旦會逢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時,積壓多年的學術熱情噴薄而出,很快就迎來屬于他們的學術黃金時代。我們八一級上大學時基本都是十七八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前幾級學長們相比,無論人生閱歷、知識積累和文學素養,都相差很遠,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張白紙,于是仰望講臺上的每一位老師,都有登堂入奧之感。給我們上過馬列文論的劉秀蘭老師每在校園和我見面聊天,總要提起我們八一級,說她最喜歡我們班了,上課時個個眼睛睜得圓溜溜的,求知欲特別強。這樣的課堂想來特別能激發老師的授課激情,很自然地將正在進行中的學術研究,很鮮活地帶到大學課堂上,不止于知識灌輸,而是啟發學生一起思考一起討論。張華老師的“魯迅思想研究”課第一次為我推開了魯迅研究這扇厚重的大門,趙俊賢老師的“當代作家作品選講”讓我對豐富多彩的當代文學現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我最早領受理論思辨的魅力,是在聽了張孝評老師的“文學概論”之后。師生共處20世紀80年代文學復興和學術回歸的歷史現場,當我們沉浸在獲取知識和精神營養的巨大滿足中,課余時間操場打球、宿舍彈唱、寒暑假游山玩水的時候,老師們正在廢寢忘食點燈熬油,埋首于各自的學術研究。“科學的春天”來得有點晚,真正起步學術研究時已是人到中年,他們想抓住教學之外的一切時間,他們交出休閑,交出健康,甚至有老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所有這一切,是當時年輕的我不曾意識的,其中的榮耀和犧牲、快樂和痛楚,更是我在經歷多年求學,走上同樣的工作崗位之后逐漸體味到的。后來我又反復閱讀過老師們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術著作,看到“教與寫”是如何互動生發,以及他們鉆研學問的路徑方法。想起魯迅那句“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而我們是直接汲取了“牛奶”的精華成長起來的。對于這一代老師,他們的學術之路可謂悲壯,對于這一代學生,我們又是何其幸運和幸福。
學緣和血緣一樣,講究的是代際傳遞,學問更是世代積累方能大成。每一代人都會立足自身當下,回首“從哪里來”的歷史,展望“到哪里去”的未來。西北大學走過120年而不衰,必有其薪火相傳的“大學之魂”,或曰“西大精神”。通過校史的回顧不難發現,愈是處于民族危難社會動蕩的關頭,愈能看到西大人不畏艱辛的家國情懷,以及對文化傳承使命的秉力持守。1913年,為加強中日高等學校的交流,西北大學曾派學生赴日留學,當時“西北大學創始會”成員和第一任“文科學長”崔云松撰文送別,他回憶了西北大學建校經歷的重重困難,特別慨嘆學校“處于財政方面問題上的艱難締造之歷史”,而后告誡學生:“經此層層困難之階段,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諸君之就學,始有選派諸君出洋之盛舉。然則吾陜之西北大學,苦學校也,經過之歷史,苦歷史也,諸君之入校肄業,苦學生也,此次之留學亦苦留學也。旅居之費,皆吾鄉同胞之脂膏,不可以任意揮霍也。留學之目的為建設之預備,不可以畏難茍安也。”(崔云松《送西北大學學生留學東瀛序》)此后的西北大學似乎總是難逃“苦學校、苦歷史、苦學生”的命運圈子,抗戰期間西北聯大在城固度過了八年艱苦歲月,1939年聯大校長胡庶華在一次報告中說:“我們西北聯大,設立在城固這個偏僻的地方,沒有電燈,沒有白開水,一切物質享受均談不到。可是我們師生依然要共同努力,發揚我們的能吃苦、有朝氣的精神,來領導西北的教育。”(《西北聯大校刊》第14期)即使是半餓著肚子,校舍極端簡陋,老師講課做學問依然兢兢業業,學生聽課上自習一樣刻苦用功。1949年天地翻覆,百廢待興,西北大學和共和國所有新生的高校一樣,經歷了國家經濟從復蘇到重整的艱難時日,1958年7月西北大學從“部屬”變成“省屬”,又極大地限制和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及至我們上學的1981年,第一次走進教室,那是什么樣的大學教室,驚涼了所有同學的熱切期待。班長劉衛平曾經在入校30年回憶文章中描寫道:“它是三間毫無裝飾的平房,屋頂苫著石棉瓦,外墻未涂白石灰,檐角甚多縫隙,屋內沒有暖氣設備。外面下大雨時,里墻也小有滲漏,外面下大雪時,里面也下小雪。”后來才得知,因為81級入學時,77級還有半年才畢業,五級同讀,校舍根本不夠用,只好臨時增建和改建了一些簡易教室,上課條件大概不比西北聯大時期好多少。而且據說因為這個緣故,我們這一級西大的所有專業都削減了招生人數,只招了計劃中的一半新生,真是好險啊。同學聚會時常常說起這些,都感慨自己考入西大是多么幸運,而那間透風漏雨的“第六教室”,竟也成了大學美好記憶的一部分了。
時至今日,地處欠發達地區的西北大學,辦學經費嚴重不足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學校整體上堅持保證教學科研的投入,我們的綜合實力和很多方面還在領西北之風騷。所謂大學精神,具體在每個學人身上,就是具有不為外在環境所左右的文化定力,是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還有自由包容的學術思想。回到20世紀80年代新思潮涌動的大學校園,西大經濟系出了兩個著名學生,一個是蔡大成,一個是張維迎。78級的蔡大成愛寫小說,發表在中文系77級創辦的《希望》雜志上。當時學生創辦《希望》,西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郭琦先生給過很大的支持,不但撥發經費給他們,還放手讓學生按自己的思路獨立辦刊。后來雜志出刊到第三期被有關部門強行叫停,蔡大成不服,竟主動提出退學以示抗議,又是郭校長再次出面力保學生,也使得當期刊物還能照常售賣。77級的張維迎本科畢業后繼續在西大讀研,他在1983年寫了一篇《為“錢”正名》的文章,提出中國的改革開放“要求我們幾千年所形成的價值觀念也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文章在《中國青年報》發表后引發熱烈討論,后來轉化成帶有政治意味的“批判”,在張維迎面臨可能被中斷學業的壓力下,還是老校長郭琦力排眾議,認為文章是“帶學術性的認識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經過一番“檢查”的周折后果斷停止了這場討論。最早聽聞這兩場“風波”的時候,低年級的我還懵懂無知,后來不斷在各種史料和懷念文字中讀到了郭琦校長,他在西北大學的開明作為和凌厲手段,對他治校能力、經驗智慧和人格氣度的口口傳揚,漸漸在心中疊加成一座宏偉的人物雕像。大學校長通常是一個大學的對外形象,有校長的大氣包容和臨危擔當,教師和學生的思想觸角才可能得到自由的伸展。北大蔡元培校長開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學風氣,中國一百多年來念茲在茲的大學精神,希望也能永遠成為我們西北大學引以為傲的精神追求吧。
2000年以來,西北大學從桃園校區又擴展到西安南郊的長安校區,學校的建筑規模和校園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綜合研究性大學的視野和水平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時光流轉歲月更迭中,我的前輩師長也漸漸走入了生命的晚景,最近這兩年,我們陸續失去了最親近的幾位業師,他們在告別校園時也告別了這個世界。我被悲傷刺痛著,反復醒覺生命的短促無常,不自覺中更多注目校園中的老先生們,用心捕捉他們身上的精神閃光,感受他們人格魅力。有一回在桃園校門外的理發店里,坐在我旁邊椅子上的是90歲高齡的老校長張豈之先生,我聽見他一直和年輕的理發師愉快地聊天,理發完畢后先走到收銀臺付了賬,回頭又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要給理發師,小伙子沒想到還有小費,有點不知所措地推辭說不需要,先生說辛苦了堅持要給,我不由得也勸小伙子拿著拿著,理發師不好意思地收下了,張先生這才滿意地又照照鏡子里的發型,很精神地邁步出門了。我回家后把見到的情景講給家人聽,然后一整天沉浸在張先生帶給我的特別溫潤的感動中。
另一位從桃園到長安校區經常見到的張先生是地質系的張國偉院士,他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也是我們西大的國寶級人物。張先生經常乘坐校門口的公交車出門辦事,普通得讓人覺得他就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鄰家老頭兒。搬到長安校區后,我和張先生住在了同一個單元門里,晚上散步經常遇到。今年年初西安遭遇疫情公寓樓被封,我被選舉為本單元的單元長,負責疫情期間核酸人員統計和安排蔬菜食品發放,依然沒有理由推脫,因為這回我好像是我們單元最年輕的在職教師。數學系的竇霽虹老師任樓長助理,我倆分工協作配合默契。老師們都非常體諒特殊時期的種種麻煩,特別是在逐戶敲門調查人口的時候,都能在單元群里積極應答,協助我們很快完成了住戶統計工作。重點要說的是張先生,因為年事已高不用微信,我就打印了紙質版讓竇老師送上去,說好先填表格隨后取回。大約半個小時候我們再去張先生家里取表格時,發現先生家的鐵門虛掩著,先生一直等在家里,免了我們再次敲門。這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和竇老師還是被大大地感動了。名師大家中有風骨有個性者,多具備純粹人格和高尚情操,既體現為他們一生做人的身正為范,也盡顯于日常生活的小事細節中,這也未嘗不是大學精神的另一種生動彰顯。教育家們說得好,大學之大,不在大樓之大,而在大師之大,常在校園看見老先生們的蹣跚背影,心里就覺得踏實,覺得有靠山,有和他們同在西北大學的那種自豪和驕傲。
記得前些年有一次也是校慶接待校友,當時的文學院院長、中文79級李浩學兄的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我們當年畢業留校工作,慢慢就成了“看家護院”的人,我們在家就在,大家多回來。我也是學文學的,很容易就被感染到。一代又一代,我們也終于熬到了“看家護院”的輩分,而且隨著年歲越大,愛家和護犢的情結就越發強烈起來。這一兩年去長安校區上課時,過馬路就看到停建很久的學術交流中心,還有幾棟教學樓也都在等待經費,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西大依然是個窮學校,我們依然還在過苦日子,但作為一個西大培養出來的學生,同時還在西大教書育人的一名老師,至少我不能嫌她窮嫌她苦。況且,西大還是“公誠勤樸”的西大,是自由包容的西大,是自強不息、努力拼搏的西大,是值得她的學子們為之守候和奮斗的西大。
西北大學即將迎來120周年華誕,時光不敗,青春常在,祝母校120歲生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