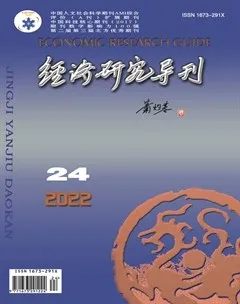我國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徐 好
(江西財經大學,南昌 330013)
一、背景研究及文獻綜述
繼2018年1月1日我國開征環境保護稅后,2020年9月我國“雙碳”目標正式提出,這使得經濟社會綠色轉型成為當今時代社會的必然追求,而稅制領域的轉型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在此背景下,綠色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當前稅收制度的綠化程度如何,是完善我國稅收制度改革、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明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從國外研究經驗來看,英國福利經濟學家Pigou早先提出的“庇古稅”被視為環保稅的雛形。其后,Pearce(1991)首次提出環境稅“雙重紅利”概念,即環保稅的征收不僅可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還可以減少現存稅收的扭曲作用,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社會就業率。Porter(1995)認為,適當的環境管制將刺激技術革新,提升企業競爭力。Grossman & Krueger(1995)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證明了收入分配狀況隨經濟發展呈倒U型曲線。
國內學術界對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也日漸增多。例如,張同斌(2017)指出,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高強度的環境規制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進而提高生產投入使用效率和要素邊際生產率。黃清煌等(2016)、王軍等(2018)則認為,綠色稅收政策在經濟增長中存在顯著的抑制效應,其質量效應和數量效應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性。另外一些學者,如蔣伏心等(2013)則認為,經濟效應取決于“創新補償”和“遵循成本”兩種效應誰占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學術界針對綠色稅制問題的研究頗豐,但結論尚未達成一致。鑒于此,擬基于中國數據,分析綠色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期拓展現有綠色稅制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相關研究,為我國稅制“綠化”改革提出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考察我國30個省份綠色稅收收入的經濟效應,以地區生產總值(GDP)作為被解釋變量,將環境保護稅(ET)作為核心變量加入原有模型,并選取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FAI)、城鎮單位就業人數(UL)作為其他解釋變量。由我國“費改稅”及相關政策可知,我國環保稅是由排污費平移得來的,故2018年之前的數據由排污費代替。綠色稅收收入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X)參考狹義綠色稅收指數的計算方式,即排污費/總稅收+排污費或環境保護稅/總稅收。
鑒于數據可得性,基于省際數據層面,所有變量時間跨度為2010—2020年,各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及《中國稅務年鑒》。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1可知,選取了30個省份2010—2020年共11年的數據,樣本容量為330個;部分變量值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區間較大,但取對數后的各變量值的標準差數值不大,其余平均值之間的離散程度很小。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稅收生產函數模型的設定與建立
基于早先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我國研究學者李紹榮、耿瑩(2005)首次提出將稅收結構份額引入生產函數當中,以此探究對生產要素效率產生的影響。本文將狹義綠色稅收收入引入該函數中,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i,t分別表示第i個地區在第t年的指標,GDP表示各省份研究年度內地區生產總值;FAI表示各省份各研究年度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UL表示各省份研究年度內按行業分城鎮單位的就業人數,ET表示各省份各研究年度內環境保護稅,x表示狹義綠色稅收指數;e為隨機誤差項。
對(1)式取對數,得到模型如下:

其中,參數α和β各自代表了綠色稅收收入份額的變化使得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對產出效率的影響變化;δ代表在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條件一定的情況下,除去資本要素產出彈性和勞動要素產出彈性的影響之后,經濟發展隨環保稅變化而產生的規模變化。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模型選擇
研究面板數據可以使用混合回歸、固定效應、隨機效應三種模型進行分析。在對混合回歸與個體效應模型的選擇過程中,Stata結果分別顯示為Prob>F=0.0000及Prob>chibar2=0.0000,強烈拒絕“不存在個體效應的”原假設。由于混合回歸的基本假設無法研究個體差異性,從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當中進行選擇。
Hausman檢驗結果為Prob>=chibar2=0.0000。結果顯示,P值為0.0000<0.01,即在1%的置信水平下強烈拒絕“個體效應與解釋變量不相關”的原假設H0,繼而選擇備擇假設H1,則該模型在固定效應下是最優的。
(二)回歸結果分析
將各省、自治區的各變量輸入Stata軟件當中,得出實證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表2顯示,F檢驗值為0,且lnET、xlnFAI和xlnUL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且該模型的調整后R=0.442,認為該模型的擬合效果良好且可以接受。根據回歸結果得出式(3):

由表2可知,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稅收體系中,狹義稅收指數x每增加1%會使得經濟產出中的資本要素產出彈性增加0.435%,同時會導致經濟產出中的勞動要素產出彈性減少0.85%;而環境保護稅ET每增加1%會使得我國經濟總產出增加0.269%。從實證結果可知,我國綠色稅收結構份額的增加有利于增加社會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但其并沒有弱化失業效應,實現促進就業增長的第二重紅利。然而,這些影響從回歸系數上來看是有限的,這可能是由于我國現階段的綠色稅收在總稅收中的占比仍然處于較低水準。
(三)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各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程度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環境規制強度等因素差別,按照各省份于2018年公布的環境保護稅征繳標準,將綠色稅收水平劃分為高中低三檔。其中,將大氣、水污染物稅額設置在每污染當量1.2元和1.4元的視為低水平;大氣污染物稅額設置在每污染當量1.8~3.9元之間,水污染物稅額在每污染當量2.1~3.5元之間的視為中間水平;大氣污染物稅額設置在每污染當量4.8~12元之間,水污染物稅額在每污染當量4.8~14元之間的視為高水平,具體回歸結果如下頁表3所示。
表3結果與全國范圍的實證結果一致,從回歸系數來看,環境保護稅結構份額的增加對低稅收水平地區的資本要素投入彈性作用最為明顯。環保稅負較低能夠增加企業的經營性現金流,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刺激企業增加投資。在抑制勞動要素產出彈性方面,高稅收水平地區的環境保護稅份額增加對勞動要素的抑制作用較其他地區更小。這可能是因為征稅較高的地區一般為經濟發達或環境污染程度較高的省份,這里的企業一般綜合實力較強或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其資金流運作和勞動力需求彈性受稅負水平影響小。從綠色稅收對經濟總產出的促進作用來看,處于中間水平的稅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最佳。這說明,從長期來看,過高或過低的環境保護稅稅率對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是最有益的,環境保護稅稅率的設置應遵循“拉弗曲線”理論和最優稅制理論,強調稅收的效率與公平,進一步減少稅收對資源配置的扭曲作用,最終促進經濟福利最大化。

表3 稅收水平異質性分析
四、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總體上,綠色稅收收入份額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資本和勞動要素的產出效率的差異性,但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較弱,且存在一定的地區和稅負水平差異。從長期來看,過高的稅負水平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因此,我國綠色稅制稅率較低、征稅范圍較窄、稅收優惠政策單一零散、稅收征管體系不完善等問題仍待解決。
(二)啟示
1.要擴大征稅規模,適度提高環境保護稅稅率。聚焦“雙碳”目標,我國應在現有基礎上將二氧化碳納入環境保護稅當中并對不實施低碳行為的經濟主體課征高稅收。
2.要細化優惠政策,擴大優惠范圍。對企業的污染治理、生態保護、資源循環利用、綠色創新、綠色低碳等行為提供稅前扣除、投資減免、加速計提折舊、財政獎補等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做好環保工作。
3.要構建綠色稅收配套機制。首先,需形成政府部門之間的聯動機制,提升稅務部門和環保部門在征管中的信息溝通和送達效率,為環保稅的征收提供便利。其次,要加強稅收征管信息系統建設,提高政府部門的行政檢測能力。最后,可以充分借鑒OECD國家經驗,基于雙重紅利效應、稅收法定準則和稅收中性原則等理論,實現綠色稅收專款專用和補償返還機制,各地綠色稅收收入最終用于改善生態和環境治理以保障綠色稅收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提高各部門和企業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