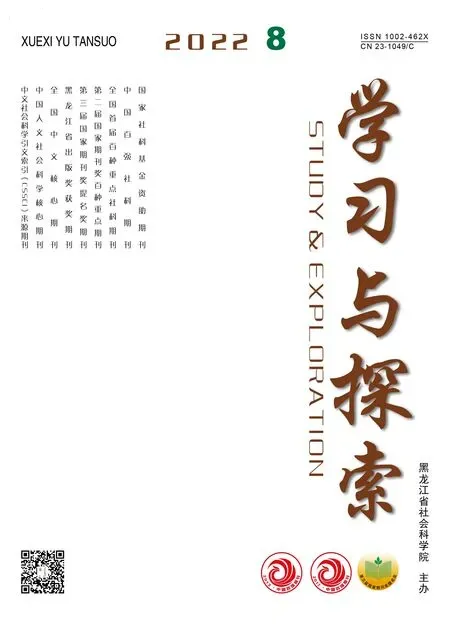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
高 杰,王 軍
(西南財經大學 a.會計學院;b.經濟學院,成都 610074)
一、引 言
隨著全球科技創新的日新月異,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國產業結構調整,也為經濟增長帶來了新的發展動能和競爭優勢。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已經從信息化發展階段進入數字化發展階段,并向深度數字化邁進,產業數字化重構逐漸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作為產業結構轉型重塑的主要組成,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對業務進行升級,進而提升生產的數量以及效率的過程(肖旭和戚聿東,2019)[1]。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減速,傳統發展模式難以支撐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要推動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新應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釋放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1]。擴大內需是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消費作為其核心要素,近年來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自2001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支出逐年遞增,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001年的5350元上升至2020年的21210元。在國際經濟形勢嚴峻的當下,我國消費市場同樣受到了一定影響。2020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和鄉村消費品零售額比上年分別下降3.9、4.0和3.2各個分點。但消費升級類商品銷售卻增速加快,限額以上單位通訊器材類、化妝品類、金銀珠寶類商品零售額均有所增長,全年全國網上零售額比上年攀升10.9%(1)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不難看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新型消費需求仍表現出較大拓展空間和發展潛力,是提振消費的重要著力點。而這一著力點正需要以數字技術應用為代表的產業數字化滲透。因此,正確認識產業數字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和作用機制,有利于在消費領域釋放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倍增作用,也有利于新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二、文獻綜述與內在機制分析
(一)文獻綜述
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和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保障,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這種作用的發揮往往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曹靜和冉凈斐,2020)[2]。傳統研究認為,消費主要受到消費者當期可支配收入、他人的消費行為、儲蓄、心理、年齡、階層地位、模仿、炫耀及習慣等因素的影響(Keynes,1936[3]。其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學者們對于消費影響因素的日益深入,認為消費還會受到金融發展、居民收入及其預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貨幣支付方式等因素的影響。此外,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外生沖擊也會對消費市場產生影響(陳國進等,2014)[4]。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消費市場提供了新動能,新消費模式與行為的出現帶來了傳統消費的升級更新,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直播經濟等新業態迅速涌現并逐步走向正軌。既有研究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對消費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具體而言,互聯網的發展,通過助推消費升級、提升消費信息匹配效率,對居民消費產生了積極效應(杜丹清,2017)[5];數字技術的應用與擴展,改變了居民原有的消費結構與消費行為,促進了居民新型消費需求,大數據的發展推動了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促進消費模式的高級化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通過優化資本結構,吸引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減輕住房資本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促進居民消費提升(林晨等,2020)[6]。既有研究多從數字經濟這一宏觀維度,或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視角探討數字經濟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內涵,產業數字化發展直接關系到一二三產業的產業效率、產業組織、產業競爭等多個方面的提升[1],三產發展的重要推進因素,有利于提升相關從業人員收入水平,促進新型產品供給與配置,滿足消費市場的新型需求。
(二)內在作用機制分析
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利用數字技術進行轉型升級,進而提升生產數量、生產效率、產品供給的過程。產業數字化在消費領域表現出三個顯著特征,一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依托,促使生產與消費在時空上進一步分離,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創造新的消費需求;二是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實現產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從而提升產業產值,促進收入增加;三是通過數字技術、大數據在產業間的滲透,使得企業能夠更好地把握市場中的消費需求,降低由于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供需雙方不匹配矛盾,更好地滿足居民需求。同時,數字技術的變革也會對居民消費行為產生影響,從而倒逼產業數字化發展,推動產業數字化的動態演進。具體地,產業數字化發展對于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提升效應。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廣泛滲透與應用不僅帶來產業間協作方式的改變,也推動生產效率的提升。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完善,大型互聯網以及科技公司逐漸切入產業價值鏈,利用自己積累的數據、技術提高工廠效率,為后端價值鏈賦能,企業在數據獲取、存儲、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得以增強,并且創造了可觀的銷售業績。在數字化管理以及資產組合管理等方面,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普遍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麥肯錫(2021)的研究發現,通過數字化,整個工業領域的公司可以增加高達4%到7%的收入和利潤(2)Frank Coleman III, Tarun Khurana, Asutosh Padhi, Justin Sanders, and Jannick Thomsen“, The next wave of M & A in advanced industries: Are you prepared?,”Mckinsey & Company, 2021.,數字化轉型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驅動產業效率的升級,也帶來了更為豐厚的報酬。進一步地,相關從業人員因企業績效的提升,得以獲得更多的收入、更加完善的醫療教育住房保障,在個人福利得以滿足的基礎上,收入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消費的提高,也即是產業數字化所帶來的收入水平提升效應。
二是產品供給擴張效應。產業數字化不僅改變了企業生產與消費者行為,對企業的產品供給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通過提升產品供給的多元性、高質量和與市場需求的匹配程度,促進居民消費提升。具體而言,其一,在產業數字化過程中,大數據、互聯網等數字技術使居民消費理念及消費行為發生了較大變化,兼具安全性和便捷性的數字支付方式,拓展了原有的消費渠道(周楠,2018)[7];平臺經濟的發展推進了產品的可視化、普及化發展,激活了消費者的內在需求,居民對商品的需求趨于個性化和定制化,并追求更高的質量和性價比。需求的改變,使得前端消費互聯網帶動后端產業變革,倒逼產業供給端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加適配于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推進前端消費提升。其二,產業數字化進程中,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滲透,企業生產成本得以降低,與此同時,大數據的應用使得企業能夠更加快速地“捕獲”市場中的需求信息;信息技術的使用使得企業對物料供給的整合力度將加大,無縫對接趨勢加快,供應體系的智能化水平將不斷提高,進而帶動全社會供應體系的協同效率大幅提升。據此,企業一方面可以依據市場需求生產相應的新型產品,另一方面能夠有效提升產品供給數量,滿足需求相對較高的產品,實現供需匹配,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
三、模型、指標與數據
(一)模型設定
為了更好地考察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本文通過構建年份、省份雙固定效應模型,展開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影響的探討,基準回歸方程如下所示:
consumeit=θ0+θ1dedciit+θnXit+μi+φt+εit
(1)
其中,i為省份,t為年份,consume為分省總消費、生存性消費、發展性消費,dedci為各省產業數字化水平,Xit為方程中的控制變量,包含福利水平、性別比、政府干預和產業高級化結構,此外, μi和φ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控制效應,εit為誤差項。
式(1)中對產業數字化水平與居民消費的直接傳導機制進行了檢驗。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為探尋產業數字化水平對消費的影響機制,本文參考王軍和詹韻秋(2021)[8]關于中介機制的研究,在式(1)的基礎上,分別將收入增加與產品供給作為中介變量與產業數字化水平、居民消費納入同一分析框架,設立回歸方程如下:
mediationit=α0+adedciit+αnXit+μi+φt+εit
(2)
consumeit=α0+c′dedciit+bmediationit+αnXit+μi+φt+εit
(3)
其中,mediationit是中介變量,代表收入增加與產品供給,式(1)中的θ1是產業數字化對消費水平的總效應,a、b是中介效應,c′是直接效應。具體中介效應分析如下:在α1顯著的情況下,檢驗系數a、b的顯著性,若a、b均顯著,則檢驗c′的顯著性,若顯著,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a、b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需要進行sobel檢驗,檢驗通過,則說明中介效應顯著。
(二)變量與數據
1.被解釋變量
本文對居民消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費總量與消費結構(生存性消費和發展性消費)兩個方面。參考王軍和詹韻秋(2021)[8]的思路,分別將居民在衣著、食品、住房、醫療方面的消費支出和在教育、交通、休閑娛樂方面的消費支出定義為生產性消費和發展性消費。
2.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產業數字化水平,為了更好地對產業數字化水平進行衡量,結合產業數字化的內涵及數據的可得性,從農業數字化、工業數字化、服務業數字化三個維度對產業數字化水平進行測算,具體指標如下所示。

表1 產業數字化指標體系
根據表1,在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通過熵值法賦予權重,測算了2013年至2020年我國30個省份的產業數字化綜合發展水平,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據表2可知,自2013年以來,我國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逐年遞增,且增速迅猛,年均增速高達23.19%,凸顯出這一新興發展模式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然而,盡管從總體上看產業數字化水平均值提升,但省際間發展水平差距仍然較大,可能原因在于產業數字化發展需要依托良好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數字資源豐富,數字信息技術的接入使用程度較高,更有利于產業數字化發展;而欠發達地區囿于教育、資源的缺失,產業數字化發展相對落后,從而形成了省級間較為突出的差距。與此同時,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化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服務業數字化發展程度最高,農業、工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且數值較為接近,可能原因在于,其與互聯網前端消費聯系最為緊密,產業數字化發展更多依托于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應用,通過前端消費互聯網帶動后端產業互聯網發展,倒逼服務業進行數字化改革。

表2 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
3.中介變量
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選取如下控制變量:(1)收入水平,數字產業化變革對于居民收入有重要的影響,故采用平均工資水平對該中介變量進行衡量。(2)產品供給,數字產業化發展對于產品供給端的質量和規模具有較大的影響,從而促進其與消費端的匹配,據此本文采用三大產業增加值對產品供給進行衡量,并將其作為中介變量。
4.控制變量
為了更好地分析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本文對以下變量進行控制:(1)社會福利水平,社會福利水平是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重要因素,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減少居民未來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居民的消費規模,故采用醫療與教育投入水平作為代理變量,對其進行控制。(2)男女性別比,性別與消費行為息息相關,普遍認為女性在消費行為上表現更為沖動,而男性消費相對理性,故采用分省男性與女性人口之比進行測量。(3)政府干預,政府干預會對消費市場影響一定影響,采用政府財政支出表示,進行控制。(4)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水平,采用二三產業之比作為表征指標。
上述變量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以及各省市歷年統計年鑒直接或間接計算而得。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3中的模型(1)為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總量的影響結果,模型(2)、(3)為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基準回歸分析結果。平均來說,產業數字化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消費總量提升0.090個單位,即產業數字化能夠較好地促進省際間消費總量的增加。與此同時,產業數字化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居民生存性消費增加0.015個單位,發展性消費增加0.062個單位,即從消費結構來看,產業數字化對居民發展性消費的影響更為突出,有利于滿足居民發展性需求,也即對于居民在教育、交通、休閑娛樂方面的消費促進程度更為突出。就控制變量而言,福利水平每提升一個單位,消費總量增加0.644,意味著居民福利水平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在消費上的支出會相應增加;各省中男女性別比每增加一個單位,消費總量下降0.002,表明女性在消費行為上表現得更加突出;政府干預程度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每增加一個單位,消費總量分別下降0.644和0.073,政府干預程度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費增加。
(二)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本部分在基準回歸基礎上,增加了異質性分析,從產業維度和地域維度考察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異質性。表4中的模型(4)-(6)是不同類別產業數字化水平對居民消費總量的異質性分析結果。據表4可知,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的提振效應存在產業差異,其中服務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最大,農業與工業數字化影響程度相似。其可能原因在于,服務業數字化有效地解決了供給端、需求端信息不對稱與供需時空匹配的問題,大幅提升了服務業能力和產品供給效率,對居民的生活消費具有直接的影響,從而在該產業中表現最為突出;而農業、工業數字化通過將原材料供應商、中間服務提供商等與最終銷售網絡連接起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供需的匹配度,有利于消費增長,但與消費者的緊密程度相對服務業而言較小,因而影響程度相對服務業而言較弱。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表4中的模型(7)-(9)為產業數字化轉型與居民消費的區域異質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力度由大到小依次為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影響力度反而更大,存在一定程度的后發優勢。可能原因在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而產業數字化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原有的市場起到補充、促進的作用,有效地整合市場資源、促進市場中供需的有效配置,從而彌補西部地區因市場化程度、經濟水平較低而導致的供需失衡;而對于市場化程度、經濟水平相對較高的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產業數字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彌補市場在供需配置中的不足,促進居民消費的提升,但其作用程度較西部地區而言,相對較弱。

表4 異質性分析
(三)內在機制分析
表5中的模型(10)-(12)為收入水平中介效應分析結果。從模型(10)可知,產業數字化水平對居民消費的總效應顯著為正。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收入水平的正向效應顯著,而在將居民收入與產業數字化納入回歸模型共同考察時,收入水平對總消費的間接效應不顯著。由于存在至少有一個不顯著的情形,因此進行了Sobel檢驗。經檢驗,Sobel值為2.61大于0.97(p<0.05),同時直接效應顯著為正,意味著在產業數字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間,存在以居民收入水平為傳導機制的部分中介效應。樣本區間內,產業數字化轉型帶來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從而促進消費總量的增長。

表5 中介效應檢驗
表5中的模型(13)-(15)是產品供給中介效應分析結果。在模型整體顯著的基礎上,對a、b進行驗證。由模型(14)可知產業數字化與產業增加值在1%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即a顯著為正,同時產業增加能夠顯著地提升各省的總消費水平,即b顯著為負。進一步地,直接效應顯著為負,表明部分中介效應顯著,即產業數字化會通過提升產業增加值影響總消費。具體來說,產業數字化的發展有利于在質量上、規模上促進產品供給的增加,更好地適配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提升居民消費總量。
(四)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本文共運用三種方法對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1)替換被解釋變量,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2)刪除極端值,我國各地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相差甚遠,有可能對回歸結果造成影響,故刪除北京、上海、天津以及重慶的數據后,再進行回歸分析;(3)將產業數字化指數進行1%水平上縮尾處理。通過上述三種分析發現,產業數字化水平對居民消費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差異不大,故本文的研究結論穩健可靠。
進一步地,運用差分GMM模型將消費總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來提高研究的準確性,表6中的模型(19)為檢驗結果。在GMM回歸結果中,產業數字化水平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可見,產業數字化轉型對居民消費的作用不受內生性影響,本文回歸結果穩健。

表6 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產業數字化的飛速發展與建設,有助于提升我國居民消費,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測算出2013—2020年30個省份產業數字發展水平,與居民消費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如下結論:(1)在研究的樣本期內,我國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進步明顯,但是產業間、區域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2)產業數字化能有效地提振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有益于擴大內需,也可以促進居民消費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3)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的促進效應在不同產業、不同區域不盡相同,其中服務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最大,工業、農業數字化次之;產業數字化對居民消費的促進,西部最大,中、東部次之。(4)產業數字化可通過作用于收入水平及產品供給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即產業數字化不斷發展可促進居民收入提升和產品供給結構合理化進而影響居民消費。基于此,要提升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需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數字化發展。首先,需要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優化數字基礎設施空間布局,加強城鎮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數字化持續、穩定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其次,要推進產業數字化發展,應當健全激勵機制,探索協同治理模式,加強對數據安全的法規指引,鼓勵企業更多地參與到產業數字化進程中,形成數字化生態,探索企業、社會、政府協同治理模式,為企業這一產業數字化發展的重要組成創造發展條件;同時也需要推進規制改革,創造有利于產業數字化發展的制度環境,禁止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壟斷行為。
第二,保障社會福利,切實提升居民收入。社會福利水平與居民收入是消費的重要影響因素,居民生活多元的需求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穩定的收入水平上。因此,為了促進居民消費,一方面,應當不斷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落實福利保障的動態調整機制,使社會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幅度的調整相互聯系起來,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不斷拓展人們的收入渠道,推進三次分配的實施,共享“數字紅利”,切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保障了居民的社會福利、收入水平,居民才能夠真正實現其生存性、發展性需求,促進我國居民消費的持續、穩定增長。
第三,豐富產品供給,滿足居民多元需求。居民消費的提升,離不開產品的供給與需求的匹配,供需的不平衡不僅會造成企業產品的積壓,也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新型需求。因此,一方面,應通過數字技術,更好地把握居民的切實需求,通過產業數字化建設提升產業生產效率、生產規模,促進食品、衣著、交通等生存性產品與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數量;另一方面,基于人們在教育、文娛、醫療保健等方面的發展性需求,要進行相應的產品、服務創新,拓展發展與享受型商品或服務的消費,滿足人民新的消費需求。此外,在發展產業數字化的同時,要提高信息通信技術的接入與使用,縮小區域間、群體間、城鄉間的“數字鴻溝”,便捷居民消費方式,提升供需的匹配程度,切實滿足人民需求,提升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