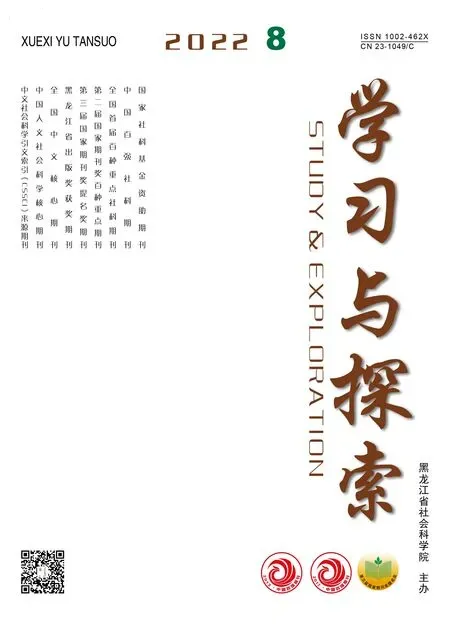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建構
——以災害社會工作的角色實踐為例
黃 紅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哈爾濱 150028)
一、引論:社會工作介入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中國語境
從社會工作發展歷史來看,早期的社會工作就特別強調在戰爭、自然災害以及危機情況下的緊急服務。專業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服務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以個案工作模式為主,目的是幫助案主解決個體、家庭、社區的災后社會和心理需求[2]。其后,實務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服務發展于美國,普及于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研究與實務領域也逐漸從單一“施賑者”擴大到與生理、心理、社會健康有關的多個領域。我國社會工作介入重大突發災難以2008年“汶川地震”為起點,其后數年間,圍繞數次大小不一的重大突發事件,社會工作者在其中承擔了傷亡撫恤、心理輔導、家庭重建、社會照顧、社區重建、就業輔導等工作,使得救災過程中“人”的重要性被彰顯,災后的社區及心理重建被關注。回顧國內對于社會工作介入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探討,多鎖定在災害救援模式、社會工作者角色與任務、社會服務資源網絡以及社區重建四個議題上,具有明顯的實踐取向[3]。與此同時,相關研究所關注的對象集中在受災居民的災害救援服務和一線社會工作者身心關護方面,對于本土社會工作介入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機制缺乏深入探討。
在2014年的“魯甸地震”救災過程中,由民政部統籌組建了我國首個社會工作災害服務支援團,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社會工作介入應急管理的制度化探索[4]。基于對實踐的反思,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災害應急管理的研究也在晚近,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展開。圍繞社會工作在參與應急治理過程出現的“體系之外”邊緣化尷尬和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治理存在各種障礙和困難等相關議題,一些學者認為社會工作未被合法納入國家突發公共事件治理體系是最為關鍵的原因。由此引申出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國情境中專業社會工作于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治理中有何功能與角色?主要能提供哪些不可替代的專業服務?社工組織能否得到公眾的信任并參與突發事件救助?以上問題都指涉一個核心問題,即基于中國語境的社會工作介入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是否具有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一詞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意思是“宣稱合法”,一般表示正當性。合法性與“法律性”(legality)不同,政治哲學家一般將合法性視為道德或理性原則,社會科學家則通常從社會學角度來理解合法性,正如韋伯所言,這種視野下的合法性,表示的是對“治理權力”[5](right to rule)的認可。在韋伯看來,這種源于對正式的和慣常的法律規則之尊重的合法性的外在基礎包含著一種合理的有效性要求,這種有效性分為三種類型,它們分別建立在歷史與習俗(傳統型權威)、人格力量(個人魅力型權威)和正式的法規框架(法理型權威)的基礎之上。
既有研究對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討論可歸納為兩條路徑,即資源路徑和制度路徑。資源路徑將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視為一種資源,一般采取管理視角,強調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可操作性、目的性和資源特征;制度路徑則將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視為一種制度力量,通過強調社會工作的專業和技能特質,產生更為廣泛的社會建構,進而實現制度化進程。本文運用韋伯的合法性理論引申出一組分析概念,即社會合法性、專業合法性、規制合法性,從社會合法性—社會化共識、專業合法性—能力性權威、規制合法性—法規性保障三個維度,嘗試建構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框架,以期回應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身份困境”。
二、社會合法性: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社會化共識
所謂社會合法性就是一個組織因為符合某種社會正當性而贏得民眾、群體的承認乃至參與,而社會合法性最主要的基礎是已經成為傳統的規范[6]。“合法性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來自有關規范所判定的、‘大眾’據以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和‘適當性’。”[7]對于社會工作者與社工組織而言,介入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就必須獲得政府、社會公眾及受助對象在內的多方主體認可,才能獲得社會合法性。如果社會工作對利他主義等價值的追求構成合法性的基礎,那么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應急管理的社會合法性的實質就在于如何獲得利益相關者對這種價值取向的承認。由于社會工作服務的特殊性,其質量和結果主要體現在受眾的主觀評價上,專業性則更多地體現在對規則和文化認知的技能實踐。因此,社會工作對規則的規范程度影響著其工具性資源的獲取,對文化的不斷傳導則轉向了“符號性”的認知,影響到其對社會認可與信任的獲得。
(一)身份符號的社會認同
系統管理學派認為,一個組織或一門學科的存在必定要履行它對社會環境的一定功能,這樣才能從社會環境中獲取組織賴以生存的文化認同資源[8]。價值理念規制著社會工作者或社工組織活動的行為,其社會基礎取決于這種價值理念能否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即能否契合社會成員的基本價值觀。如果社會工作的價值追求構成了其社會基礎的價值本體,那么其社會合法性的客體就指向了如何獲得社會成員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其價值本體的承認。社會工作實務中的平等、尊重、理解、合作理念實際上都是其價值標準的物化形式,因此,這種基于社會普遍價值觀的專業認同、承認與支持不是公共權力決定的,社會公眾對于社會工作的認同來自于社會工作能“解決”多少社會問題。與此同時,這種認同又有主客之分,前者指涉社會工作參與災害應急管理獲得“誰承認”,后者指涉“承認什么”[9]。
社工組織的發展是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中進行的,社會公眾對社會工作的認知會轉化為對社工組織“符號”和“身份”的判斷。通過近四十年的專業發展與政府的推動,社工組織形態已逐步契合中國當前民眾社會心理特點。通過基層社區治理實踐,社會工作在基層場域中具有了一定“公”的成分,由此獲得了公眾的前導性社會信任,社工組織也以超常規的速度發展成長。就災后社會重建而言,“應急”這一服務場景既給社會工作提供了發揮專業優勢獲取認同的機會,同時也對社會工作提出了挑戰。在災區這個復雜的現實場域中,因災害而驟然凸顯的各種矛盾會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其復雜性不僅源于地理空間的災情差異,亦源于隨災情變化而出現的社會心理波動、不確定性與矛盾演進。社會工作者和社工組織介入災害應急管理,不僅要處理各類主體的恐懼感和悲傷情緒,使受災群眾盡快從災難映像中走出來,還要協助災區民眾發展生計。社會工作是一門應用型學科,在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歷程中,針對不同服務領域和服務對象形成了不同的專業知識領域,如災害社會工作、醫務社會工作、老年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等。從數次救災實踐的經驗來看,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救援服務與社會重建是一項極為龐雜的系統性工作,幾乎涵蓋了所有實務社會工作的潛在服務對象。面對種種任務,社會工作的應對策略便是提供最恰當的服務和進行最精確的角色定位,形成災害社會工作領域服務的多元取向。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87年恢復重建以來,社會工作學科就緊緊地與政府治理、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等政治領域改革進程連接在一起,特別是在近十年已成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其被賦予了某種非公身份的政治功能,又因為社會工作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和諧穩定、社會變遷秩序目標而被建構,這種功能就具有了較強的剛性特征[10]。從近十幾年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歷程來看,社會工作力量本著強烈的專業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積極投入到災害救援和恢復重建工作中,面向喪親者、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提供情緒輔導、課業輔導、成長陪同、照護、生計支持等專業社會工作服務,初步形成了社會工作介入重大突發事件的工作模式,得到了政府、社會公眾及學界的認可。
(二)“知識域”的功能認知
社會治理實踐和社會科學知識中的行動邏輯問題,構成了現代社會治理模式重構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如果行動邏輯只能靠強制力而形成,那么改善社會治理模式就幾乎沒有其他的空間。如果可以將社會工作的價值與知識作出相對隔離,那么社會工作知識生產的核心就可以聚焦于行動方式和行動技能這個“知識域”之中。在這一認知下,政府將社會工作納入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行動主體中,隱含的目標就是對更為理想的集體行動模式的追求。
數據同體積顯示,PE為0.302,PA為0.683,經Kappa計算顯示為0.546,在塵肺病診斷中直接數字化攝影檢查和高千伏胸片檢查存在較好的一致性,且0.756為相關系數,具有一定相關性,P<0.05,統計學展現組間分析研究意義。
在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離不開公共服務敘事。社會工作在災難中的弱勢群體救助、資源鏈接、災難親歷者的危機干預和心理疏導、傷亡者家屬的哀傷輔導和社會支持、疫情防控緊急狀態下志愿者的動員和組織管理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專業作用,成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柔性力量,發揮著社會的“穩壓器”的作用[11]。以上服務無疑是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終端”,在這一行動系統中,權力是保證集體系統組織順利運作的力量,社會工作透過政治系統中的合法性資源,運用“知識域”產出修復社會的力量。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社會工作參與災害應急管理的實踐中,決策力量對社會工作“作用”的影響遠高于社會工作“知識域”所塑造的專業形象,故在社會工作專業的認知發展及實務需要上出現了落差。決策力量所關切的是專業體制建構內容能否回應社會事件,非決策力量則延續著社會工作專業化行動所需的條件,使得社會工作“知識域”的功能認知呈現出既重疊又斷裂的現狀。這樣的狀況又使得災害社會工作對社會產生的“話語—知識”建構效應偏向了決策話語,因此,專業權威與決策權威之間的關系就出現了張力。邁向治理現代化的曲線性流變使得這種張力所處的環境漸次改變,在現代化轉向期間,決策力量對社會工作“知識域”具體形態的認知流變大致呈現出集體行動共同體的律動特點。
三、專業合法性: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能力性權威
我國存在兩次社會工作發展期,第一次是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初期,這也是歐美社會工作快速專業化、科學化的發展時期;第二次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中國的社會工作在不斷回應政府、社會需求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災害(disaster)是人為或非人為的破壞力量,未預警地對人類常態社會功能產生重大的瓦解性影響,災害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重要領域之一,也是專業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的一個示范領域。自2008年社會工作介入“汶川”地震的災后緊急救援、臨時安置和恢復重建起,災害社會工作在多次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全方位展示了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豐富了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內涵。
(一)作為學科的災害社會工作
一門學科體系趨向成熟應包括三個層層遞進的必要條件,即完備的概念體系、明確的對象范疇以及對現象規律的理論總結。概念體系是其中最為基礎的部分,“一門學科真正的力量往往在于,形成了只有經過長時間努力才能夠把握的高度專業化的概念框架”[12]。災害社會工作目前還不成熟,無論是以領域來建制還是以學科來建制,災害社會工作研究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體系是客觀事實。就學科建設而言,從當前社會工作理論研究的實際情況出發,做好理論體系的基礎就是建構災害社會工作的概念體系,并進一步提煉出相應的對象范疇,進而運用范疇總結出理論規律。
縱觀近十年國內現有的災害社會工作學的研究著作,在體系建構上多為教材式羅列或經驗式總結,主要由一些工作概念或專業術語支撐,學術性的概念不多。僅有的以理論體系建構或向理論范式過渡為目的的研究當中,部分陷入了邏輯起點的誤區或沒有找準本土災害社會工作學的概念重建[3]。這些研究雖尚未建立起公認的學科范疇,但基本概念已逐漸明朗,運用現實邏輯與歷史經驗的方法構建災害社會工作學的概念體系的時機已經來臨。未來災害社會工作學科體系建設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概念體系生產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提煉出更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并進一步利用有關范疇去總結實務社會工作中的某些規律,從而為災害社會工作的本土理論建構打下基礎。
如果說學科體系建構強調的是學術規范和行為規則等內在制度,那么學科建制則強調的是學科的社會建制,即學科的外在制度。費孝通認為,一門學科的社會建制大體上應包括五個部分,即學會、專業研究機構、各大學的學系、圖書資料中心和學科的專門出版機構[13]。學會、機構和學系在社會建制和社會運作層面上的范式建構,都指向了學術共同體(academic community)的形成[14]。作為學科規訓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科建制的體系完備與否十分重要。就像新聞與新聞學之間存在著根本不同,災害社會工作與災害社會工作學也有著很大的差別。災害社會工作的合法性植根于社會需要,處于變動之中,而災害社會工作學的合法性則更多地植根于學術共同體的認同。發達國家災害社會工作研究有關的研究人員、資料、期刊、人才培養等層面的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即在社會建制層面和高校建制層面的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并得到了政府與社會的認可,獲得了學科的行政合法性與社會合法性[15]。我國災害社會工作學仍然欠缺理論體系的構建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尋找本學科學術合法性的本土基礎,并基于此重新對學科的理論體系進行構建以區別于其他社會工作分支學科,這是獲得本學科學術合法性的必然選擇。
(二)作為實務的災害社會工作
作為專業力量,社會工作者和社工組織有序參與到救災工作中所發揮的作用已得到廣泛贊許,服務模式不斷豐富,價值日益凸顯。與此同時,經過十余年的探索與發展,社會工作介入災害應急管理的程序及標準問題也逐漸顯現,如北京、安徽等地針對應急管理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工作參與應急管理的標準等問題已開始了先行探索。(1)參見北京市應急管理局:《應急管理社會動員和社會組織建設項目公開招標公告》,http://ccgp-beijing.gov.cn/xxgg/sjzfcggg/sjzbgg/t20220509_1424876.html;安徽省民政廳《“社會工作參與應急管理”標準研制項目競爭性磋商公告》,http://mz.ah.gov.cn/public/21761/120382331.html.
社會工作介入“災害”,可分為災害預防(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災害處置(Interventions During a Disaster)和災后干預(Interventions Following a Disaster)三個階段[16],各階段采取的行動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關聯。而“應急治理”則更多涉及災害處置期間。從十余年我國實務社會工作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樹地震”、2013年“蘆山地震”、2014年“魯甸地震”、2016年“鹽城特大龍卷風冰雹災害”等救災中的服務實踐來看,作為服務主體,實務社會工作在災害應急管理中的救難期、應變期和恢復期的服務內容涉及以下諸方面(見表1),服務內容的規制有助于專業權威的建立,并對社工組織的災后服務提供程序性遵循。

表1 災害處置期實務社會工作的服務內容
社會重建是一個抽象范疇,而實踐的前提就是要將抽象的社會重建對象化,因此,社會工作介入社會重建的先導就是要將對象范疇操作化,而操作化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找到社會工作的介入點。以災害社會工作為例,在災害處置期的實務目標可總結為用專業服務幫助受災家庭、個人及救災人員以穩定的狀態回歸正常生活軌道。社會工作者和社工組織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應隨著每個災害應急管理階段的目標與需求不同而有所改變,動態修正服務內容,回應應急治理的災害救援目標。在具體的實務工作中,災害社會工作的角色可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部分。在微觀層面,具體實務包括對災民及其家屬的心理重建、協助個人與家庭連結資源、介入社會支持網絡、提供資訊等。在中觀層面,社會工作者同時扮演了資源整合及協調、社會力量整合、社區福利傳導、減少受災居民被標簽、為服務對象賦能、協助災后重建等。在宏觀層面,倡導相關政策的改變。
四、規制合法性: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法規性保障
在社會科學領域,C.E.佛瑞茨(CE.Fritz)、A.H.邦頓(A.H.Barton)、E.L.庫朗特利(E.L.Quarantelli)等研究災害與社會關系的學人都把災害看作一種社會系統因遭受突發的而且具有破壞性的沖擊而偏離常態的現象[17]。其中以E.L.庫朗特利為代表的“結構和功能”流派從組織論視角出發,以結構和活動內容為兩根軸線,探討了社會系統災害應對中的組織角色問題。災害社會工作在近十年的快速發展,對于助力我國數次自然災害的災后社區重建和災民社會融合發揮了重要專業作用,但仍然顯現出一些問題,如在社工組織的動員模式上出現了“重動員、輕協調”的現象,災害應急管理的社會工作參與雖然在體制上不斷改革推進,但機制性保障仍存在巨大空白。
(一)角色建制化:行政權力與專業性質的互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已由“總體性社會”轉向“后總體性社會”,國家對資源和社會活動空間的壟斷不斷弱化,社會正在成為與國家并列的、相對獨立地提供資源和機會的源泉[18]。然而,在“后總體性社會”中,政治和行政因素仍然是一種輻射力和穿透力極強的資源,即使是完全在市場中流動的其他資源,也仍然要受到政治與行政力量的巨大影響[19]。雖然這種影響仍然巨大,但社會已經成為具有一定自生性的規則與邏輯場域。在應急救災領域,隨著2018年國家應急管理部正式成立,“應急管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策領域,社會工作參與災害應急管理的政策制度也進入了加速創立期(見表2)。

表2 社會工作參與災害應急管理的政策制度演進
上表呈現了不同時期社會工作在國家應急治理體系當中被賦予的位置。由應急救災領域的政策法規文本中對社會工作的認可可以看出,社會工作參與災害應急管理的角色建制化是在國家認可的框架中進行的。角色建制化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納入政府合法體制的過程。用角色建制化作為一個討論體制形塑的起始點,可以透過這個概念來分析制度發展的結果。從發展階段來看,2018年國家應急管理部成立可作為一個分界。2018年之前為追求專業化階段,在此階段中,災害社會工作處于專業邊界不夠清晰、人才隊伍專業化程度不高、服務體系不明確的時期;2018年之后為辨識建制化時期,在此階段中,災害社會工作的法律地位及其權利義務逐步得到明確,與角色相關的服務內容逐漸清晰。從國家權力與專業權力的角度切入,可以發現災害應急管理的專業力量需求與災害社會工作的發展形成了互構關系,即在成為一種專業的期待之下,規制成為了社會工作建立專業權威的一種表征,從制定、確立到執行的過程中,災害社會工作的專業樣貌也逐漸被形塑出來。
雖然在兩階段中國家采取了不同的發展策略及路徑來推進災害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發展,但都緊扣“專業性”,即專業隊伍和專業技能是明確災害社會工作“法律地位及其權利義務”的基礎。這樣的行動選擇來自于社會工作在我國發展的歷史脈絡,也來自于現實困境,包括但不限于社會工作師與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區劃、專業社工組織與志愿者組織的角色定位、社會工作師與心理咨詢師的專業介入對象劃分等。以上問題都需要在災害社會工作的發展與前進中解決,在政府、學者及社工組織三方交互運作之后,形塑出社會工作角色建制化的合理樣貌。
(二)機制再生產:協商合作治理的探索性命題
不同的治理模式會形成不同的運作機制[20]。從我國的歷史來看,傳統的統治型災害治理模式形成的是“權威—服從”的權力機制,當代的管理型災害治理模式形成的是“契約—紀律”的法律機制。近年來,我國社會工作參與的數次災害救援的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共性問題,如片段且重復的需求調查、一線社會工作者人力與素質無法滿足災后的服務需求、部分社工組織持續提供服務的可行性不足、專業社工組織人力與災民需求對接不暢等。究其原因,是在管理型災害治理模式下,居于治理中心的單一主體,其自上而下治理機制的工具理性影響了災害治理中效率的提升。在單一中心治理結構約束下,客觀排斥了社工組織作為災害治理主體的合法身份,由此造成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供給的標準化與社會需求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之間的沖突。
目前,我國災害社會工作在社會治理層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嵌入性視角,認為社會工作專業應與國家治理相適應,在政府的監督和管理下參與到社會服務當中[21]。災害社會工作要爭取政府的信任與支持,把自身作為一個主體融入到災區的管理體系之中[22]。這樣的視角將災害社會工作置于管理型政府中的公共服務“短缺性”服務供給者的地位,這樣的角色特質使得社工組織難以主動優化災后服務的供給,若要形成一種符合公共服務再生產規律及需求的制度模式,就需要調整現有的災害管理機制。作為一種探索性命題,探討專業社會工作在災害應急管理中的主體地位不僅是公共服務的供給再生產,同時也是社會責任倫理的再生產,即專業自反性的本體成長,這樣社會治理中的倫理“返魅”又恰是當代治理理論一個最顯著的特色[23]。在這種主體位置的主張下構建的將是“協作—商談”型的災害應急管理機制,這樣的運作機制有別于既有災害應急管理“中心—邊緣”結構下的附屬型協作機制,其功能在于優化社會工作在災害應急管理中的服務供給,按照合乎公共應急服務再生產的要求,形成新的管理機制安排。這種機制在關系上呈現出一種“嵌合”的特征,即結合、合作和協同發揮作用的過程和機制[24]。
近年來,我國治理現代化道路上的多元治理觀念日趨成熟,“治理”在自反性建構中逐漸超越了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非此即彼的思維邏輯,“協商”機制和“合作”觀念逐漸成為公共領域政府與社會達成共同目標的實踐路徑。災害應急管理中,新的制度安排所指涉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把握權威治理主體與社會治理主體的關系,其在宏觀上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中觀上是行政權威與專業權威的平衡問題,在微觀上是主動參與和被動安排的程序問題。災害應急管理上的協商合作治理,其治理觀念可以概括為用“合作”來代替以政府為中心的“控制”導向,“合作”并不否認政府的權威,權威治理主體在“合作”中享有自主性。將社會工作作為治理主體,是在行政權威與專業權威的平衡后,基于公平和相互信任,主動參與到謀求公共利益當中的一種模式。在具體實踐領域,協商合作式災害應急管理的表征就是允許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和社工組織發育程度,自主選擇不同的社會工作介入模式,采用具有差異化的管理模式,提升社工組織的回應性和反應能力,從而獲得更好的治理績效。
五、余論
因應政治制度差異或文化、歷史、習俗等特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可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社會工作,正是其間的差異性突顯了社會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活力與潛力。就我國災害社會工作本身而言,它的出現必然是與它所能產生的作用或所能達成的目標、效果有關。筆者通過對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本土化合法性建構的分析,發現社會工作的專業合法性更趨向一種內部合法性和實用合法性,而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不僅需要適應事件現場的技術環境,而且受制于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制度環境,這兩個環境場域則趨向一種外部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合法性機制對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作用存在于強意義的和弱意義兩個層面上,強意義指制度環境所具有的強大約束力使社會工作的專業行為和技能輸出呈現出一種被動選擇的境況;弱意義指社會環境通過認知激勵方式或資源分配方式,對社會工作的進場和行動施加影響。合法性建構意味著社會工作要通過發揮策略性回應的能力倡導新的制度規則,提出新的規范標準以及營造新的認知模式等來回應“身份焦慮”,只有這樣,社會工作才能找到自身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治理的話語基礎和實踐場域,進而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