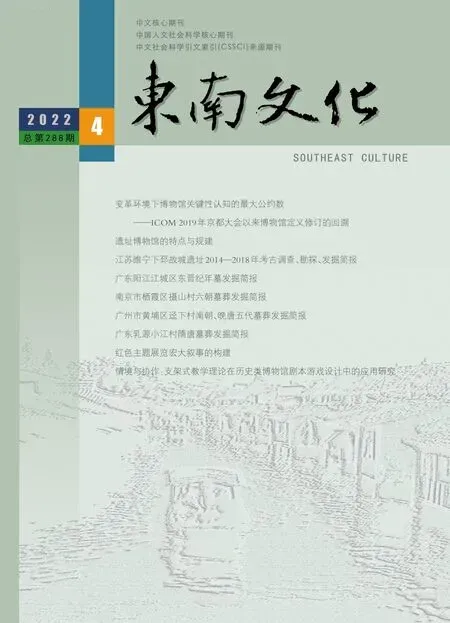滿意與復愈:博物館觀眾體驗及其對行為意向的影響
龔金紅 朱嫦巧 殷小平 劉穎穎
(1.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642;2.廣州博物館 廣東廣州 510045)
內容提要:識別和區分不同觀眾群體的體驗是博物館觀眾研究的重要課題。對廣州博物館“城標·城史——廣州歷史陳列”參觀觀眾進行跟蹤觀察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觀眾在觀展體驗上存在顯著差異:女性觀眾的實物體驗顯著高于男性觀眾;受教育程度低的觀眾,其認知體驗比受教育程度高的觀眾更強烈;與親戚或家人同行的觀眾,其社交體驗高于獨自一人或與朋友結伴的觀眾;知識學習型觀眾的復愈體驗和內省體驗,均高于休閑放松型和家庭活動型觀眾。復愈體驗和社交體驗對觀眾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實物體驗、內省體驗和認知體驗并無顯著影響。隨著博物館觀眾研究逐漸從“人的行為”轉向“人的內心及其體驗”,關于博物館觀眾體驗的類型及其前因后果,仍需學界和業界進行更多探討。
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在很長時間內局限于其對終身學習的貢獻,但即使是最廣義的學習成果,也無法完全涵蓋博物館體驗所帶來的利益[1]。隨著博物館社會職能的轉變,國外研究者開始突破必不可少的教育價值,從其他方面探討博物館給觀眾帶來的有益體驗,討論觀眾體驗的類型劃分,其中扎哈瓦·朵琳(Zahava Doering)的滿意體驗(satisfying experience)框架被廣為引用[2]。20世紀90年代,美國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卡普蘭(Stephen Kaplan)指出,博物館是一種讓人獲得復愈體驗(restorative experience)的理想環境,它能讓觀眾休息、放松,從壓力中恢復過來[3]。
對于博物館觀眾體驗的多樣性以及環境的復愈性,國內學者雖有關注[4],但相關的實證研究較少。雖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展覽內容,對于不同類型的觀眾來說,博物館體驗的構成或有不同,但觀照國外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有益的參考。本研究以廣州博物館(以下簡稱“廣博”)鎮海樓展區“城標·城史——廣州歷史陳列”(以下簡稱“‘城標·城史’展”)為例,在問卷調查基礎上,通過量化研究探討觀眾滿意體驗的構成以及復愈體驗的表現,比較不同類型觀眾的體驗差異,分析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對觀眾行為意向的影響,同時輔以跟蹤觀察數據,解釋說明量化研究結果。
一、博物館觀眾體驗的類型
體驗是個體對非日常環境中的活動、環境或事件的主觀反應,這種反應可能是即時的,也可能持續一定時長[5]。國外學者較早對博物館觀眾體驗展開研究,如謝爾頓·安妮斯(Sheldon Annis)最早關注博物館象征性體驗(symbolic experience),將博物館視為精神空間(dream space)、實用空間(pragmatic space)和認知空間(cognitive space)的統一體[6]。在此基礎上,納爾遜·格雷本(Nelson Graburn)提出,博物館可以滿足觀眾對敬畏、聯想和教育體驗的需要[7]。盡管這一觀點在當時被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AAM)采納,但在博物館實踐中仍然側重于教育體驗。
卡普蘭等學者認為,除了教育功能外,博物館還能發揮復愈性作用[8]。復愈是指個體恢復因持續努力而減弱的身體、心理和社會能力的過程。根據注意力恢復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將注意力持續集中在特定活動中的能力會因精神疲憊而降低或喪失,這種狀態即為“定向注意力疲勞”,而復愈性環境能讓人從心理疲勞和壓力中恢復過來。復愈性環境通常具備四個要素:遠離(being away)、豐富/連貫性(extent/coherence)、吸引力(fascination)和兼容性(compatibility)。這四類要素也存在于博物館中,即觀眾參觀博物館能遠離日常環境、被豐富的內容吸引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由此觀眾感覺放松、平靜或安寧,進而從精神疲憊和壓力中重新恢復,這一過程可稱為復愈體驗[9]。其他學者對博物館觀眾體驗的分類也提到了與復愈相關的概念。例如,麗莎·羅伯茨(Lisa Roberts)指出,觀眾體驗不僅包括信息和求知欲,還包括社會交往、回憶、幻想、個人參與和恢復(restoration)[10]。尼爾·科特勒(Neil Kotler)等學者將觀眾體驗歸納為六類,即休閑體驗、社會交往、學習體驗、審美體驗、慶祝體驗和著迷體驗[11],其中,休閑體驗和著迷體驗都與復愈體驗有關。朵琳通過對美國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下屬九家博物館的深入訪談、抽樣調查和觀眾留言分析,將觀眾體驗分為實物體驗(object experience)、認知體驗(cognitive experience)、內省體驗(introspective experience)和社交體驗(social experience),合稱為“滿意體驗”[12]:實物體驗是觀眾在博物館看到真實存在過的物件或珍稀事物,因其美好而感動;認知體驗側重于體驗的解釋或智能方面,是指獲得信息、知識,或者豐富對某些事物的理解;內省體驗聚焦于個人內心的感受和體會,包括因參觀而引發的想象、反思、回憶和關聯;社交體驗是指與親友、其他觀眾或博物館工作人員的互動體驗。賈恩·帕克(Jan Packer)和羅伊·巴蘭坦(Roy Ballantyne)整合研究文獻中的概念,提出了觀眾體驗多切面模型,具體包括物理體驗、感官體驗、復愈體驗、內省體驗、變革式體驗(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享樂體驗、情感體驗、關系體驗、精神體驗和認知體驗[13]。
國內對博物館觀眾體驗研究的進展相對緩慢。部分學者介紹了國外相關研究成果[14],也有學者參考滿意體驗框架論述博物館如何塑造更豐富的觀眾體驗[15],還有學者從情緒反應(愉悅度、喚醒度)和行為反應(停駐時長)兩方面測量觀眾體驗,分析博物館展示環境對觀眾體驗的影響[16]。
總的來說,現有研究從多方面探討了博物館觀眾體驗的類型,但不同研究中多個術語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種體驗,如教育體驗、學習體驗與認知體驗,審美體驗、實物體驗與感官體驗,社交體驗與關系體驗等。回溯研究文獻中出現的多種體驗類型,朵琳的四類滿意體驗與卡普蘭的復愈體驗比較具有代表性,相關實證研究比較了不同類型的博物館、觀眾之間滿意體驗和環境復愈性的差異[17],初步分析了它們所帶來的復愈性效果[18],但未考慮其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本研究試圖在國內博物館情境下檢驗觀眾滿意體驗的構成,描述觀眾復愈體驗的表現,分析各類滿意體驗、復愈體驗與觀眾行為意向之間的關系。
二、研究過程及方法
本研究以廣博“城標·城史”展的觀眾為調查對象,先觀察記錄觀眾行為,待觀展結束后再向觀眾發放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觀眾基本信息(人口統計特征、居住地、到訪次數、同伴類型、參觀目的)、觀展體驗、行為意向以及對廣博的整體印象。對滿意體驗的測量主要參考安德魯·佩卡里克(Andrew Pekarik)等學者的觀眾體驗列表(The List of Satisfying Experiences)[19],由兩位研究者分別挑選出最能反映各類體驗的描述,然后結合展覽內容進行討論,最終確定了8個測量項目。對復愈體驗的測量主要參考特里·哈蒂格(Terry Hartig)等學者的環境復愈性量表(measure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ness)[20],從每個維度中選擇因子載荷最高的3個項目,共11個測量項目,其中“遠離”維度僅有2個項目[21]。觀眾行為意向包括3個測量項目:“愿意再來廣博參觀”“會向他人正面宣傳廣博”以及“會向他人推薦廣博”。
觀眾調查時間為2021年5月9—23日。本次調查采用分層抽樣,先根據可觀察到的同伴特征,將觀眾分為獨自一人、結伴同行(不帶小孩)以及帶小孩的家庭觀眾三類;再通過方便抽樣選擇目標調查對象,共觀察了156位觀眾,有152位觀眾填寫問卷。其中10位觀眾是初中學生,2位觀眾在填答過程中受到小孩干擾,4位觀眾將所有量表式問題(包括反向問題)全部打分為“5分”。筆者將這些問卷剔除,保留了136份有效問卷用于量化分析(表一)。

表一// 觀眾調查樣本概況
數據分析過程包括三個步驟。首先,運用SPSS 19.0軟件[22]對滿意體驗的8個測量項目進行因子分析。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檢驗已有的關于滿意體驗的類型劃分,所以按照現有研究結論直接將因子數量固定為4,即按照現有研究,將滿意體驗分為認知體驗、實物體驗、內省體驗和社交體驗四類。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并通過正交旋轉加大因子載荷的區分度。其次,分別以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居住地、參觀次數、同伴類型以及參觀動機為分組變量,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23]檢驗不同類型的觀眾在各類體驗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最后,根據因子分析結果,用對應測量項目的算術平均值作為四類滿意體驗的分值,以四類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為自變量,以觀眾行為意向為因變量,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來探討觀眾體驗對行為意向的影響。
三、研究結果
(一)觀眾滿意體驗的構成
因子分析結果(表二)[24]顯示,滿意體驗由4個因子組成,內容分別對應于朵琳的分類框架中的認知體驗、實物體驗、內省體驗和社交體驗,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3.779%,說明4個公因子對原始數據有比較強的解釋力。這一結果為現有關于滿意體驗分類的論述提供了實證支持。

表二// 因子分析結果
實際上,根據觀眾在觀展過程中的交談內容,也能發現四類滿意體驗的存在。例如,一位現居廣州但首次參觀廣博的年輕女性,在閱讀完“廣州得名”展板文字后,對同伴說道:“廣州的名字由來原來跟孫權有這么大關系。”(認知體驗)
展品本身也給觀眾帶來感官上的審美體驗。如夸贊展品“好看”、拿出手機拍照,從這些行為中可見一斑。至于展品屬于哪個年代、是文物還是復制品,觀眾會結合文字說明來判斷。例如,關于“銅壺滴漏”展品,一位媽媽讓小孩“過來看古代的計時器”,逐字逐句讀完文字說明后,強調“這是一個復制品”。(實物體驗)
觀眾還會將展品與當下生活中的事物或現象結合起來,閱古思今。例如,看到“淺黃真絲地繡花卉紋流蘇罩衣”這件展品時,一位女性觀眾與同伴討論:“我感覺這件最好看,這件放到現代也不過時,現在不是很流行vintage嗎,這就是我們中國的vintage。”在觀景臺看門聯時,她又感嘆道:“現在的小孩都只會寫現代字了,沒有古代書法那么正規。”(內省體驗)
除了獨自參觀的觀眾,結伴同行以及帶小孩的觀眾在觀展過程中都會有一些言語或肢體上的互動,帶來社交體驗。這些互動既有圍繞展品展開的,如指引、講解、討論等,也有與展品無關的內容,比如有的小孩反復催促家長結束觀看返回酒店。
(二)觀眾復愈體驗的表現
從復愈體驗測量項目的均值結果(表三)來看,觀眾的復愈體驗主要表現為遠離感,即“遠離了喧囂與煩惱”以及“擺脫了日常生活而感覺放松”,它類似于約瑟夫·派恩(Joseph Pine II)和詹姆斯·吉爾摩(James Gilmore)體驗經濟分類框架(the experience economy)中的逃避體驗(escapism experience)[25]。博物館展示內容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讓觀眾感覺被吸引,“想要深入了解這家博物館”,這與科特勒等人提出的著迷體驗相近。在博物館參觀,觀眾“感覺很自在”,能自得其樂,說明博物館的環境兼容性強,不會讓觀眾覺得格格不入。觀眾對展覽內容豐富性/連貫性的體驗不太強烈,將三個反向測量項目——“對展覽內容感到困惑”“受干擾因素影響而無法專心看展”“展覽內容讓我感覺混亂”轉換為正向測量,其得分均值都較低(分別為3.49、3.66、3.66)。一方面,可能部分觀眾在填寫問卷時未注意到它們是反向問題;另一方面,可能也與觀眾的觀展行為有關。本次調查的“城標·城史”展以時間為主線分布在五層樓的各展廳中,在沒有講解人員導覽的情況下,大部分觀眾的觀展動線比較隨意,并未按展覽內容的邏輯順序觀展,部分觀眾甚至沒有到5樓展廳,而直接從3樓或4樓折返。

表三// 復愈體驗測量項目的均值
關于復愈體驗,從觀眾對鎮海樓展區整體印象的描述中也能窺見一二。例如,有觀眾提到“展覽內容豐富”“樓層年代清晰”“有吸引力”“比較有意思”以及“環境舒適”“安靜”“氛圍良好”“有時光倒流的感覺”,以上描述反映了博物館環境的復愈性特點(如豐富性、吸引力、遠離性),而復愈體驗正是復愈性環境帶給觀眾的一種經歷。
(三)不同類型觀眾的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觀眾在實物體驗上存在顯著差異;不同文化程度的觀眾在認知體驗上有顯著差異;與不同類型的同伴參觀的觀眾在社交體驗上存在顯著差異;出于不同動機看展的觀眾,在內省體驗和復愈體驗上都存在顯著差異,在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條件下,F值分別為15.388、3.767、9.059、3.304、13.222,Sig.值均小于0.05。
1.不同性別的觀眾
本研究中,女性觀眾的實物體驗要顯著高于男性觀眾(圖一)。可能是因為男性觀眾在評價打分時相對“保守”一些,也可能與視覺系統的性別差異有關。行為學研究表明,在視覺信息的處理上男女各有優勢:男性有著更好的空間視敏度和運動知覺能力,女性則對物體特征、顏色知覺和物體分類更為敏感[26]。本研究的實物體驗是一種基于展品外在特征的感官認識,因此女性觀眾的感受可能更強烈一些。

圖一// 不同性別觀眾的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四類滿意體驗以及復愈體驗如果按均值大小排序,無論是對于女性觀眾還是男性觀眾而言,最突出的都是認知體驗和實物體驗,其次是復愈體驗和社交體驗,內省體驗相對弱一些。這意味著對于普通觀眾而言,博物館首先是一個認知空間,其次是一個實用空間,最后才是作為精神空間的存在。
2.不同文化程度的觀眾
從文化程度上看,中學學歷(初中、高中)的觀眾認知體驗最強,研究生學歷(碩士、博士)的觀眾認知體驗相對來說最弱;前者的內省體驗比復愈體驗更突出,后者的復愈體驗比內省體驗更突出(圖二)。內省體驗與認知體驗有較強的關聯性[27],觀眾的內省體驗(如聯想、回憶、反思)往往是基于對展品的感知和認知。中學學歷的觀眾認知體驗更強,相應的內省體驗也更強一些。為何觀眾的學歷越高,其認知體驗反而越弱?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本研究對認知體驗的測量屬于增值測量,是測量在觀眾已有知識基礎上本次參觀所帶來的增量,也就是說,低學歷觀眾比高學歷觀眾能獲得更大的知識增量。其二,這與不同文化程度的觀眾對展覽的期望有關,高學歷觀眾可能對專業性知識的期望更高,但為了覆蓋面更廣,展覽在滿足大眾需要的同時可能會讓專業觀眾有所遺憾。

圖二// 不同文化程度觀眾的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3.不同同伴類型的觀眾
觀眾體驗的強度也會因同伴類型而異。與親戚/家人同行的觀眾,其社交體驗比另外兩類觀眾更強烈,而且其社交體驗也比復愈體驗和內省體驗更突出(圖三)。本研究中有70%是親子觀眾,與其他的同伴類型相比,親子觀眾的互動頻率更高,互動內容也更為豐富。例如,在觀展過程中,一位父親不斷用言語引導小孩觀看視頻、模型、展板、展品,為小孩講解,回答小孩的提問,解釋相關術語的含義,并且教育小孩保持正確的觀展行為。

圖三// 不同同伴類型觀眾的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三樓:“蘇哈爾”號船模)
父:“看,這是船的模型,注意不要碰它。”
(三樓:宋代流通的各朝銅錢)
子:“這個放大鏡是什么?”
父:“這是為了方便看清銅錢上的字。”
(四樓:象牙鏤絲紋章花卉紋折扇展柜)
子:“為什么不能用閃光燈?”
父:“用閃光燈會對展品有影響。”
(四樓:套紅花鳥紋玻璃窗)
父:“看上面的窗,玻璃上有蝴蝶。”
(兒子走到樓梯邊,工作人員指引兒子下樓方向,父親把兒子拉回來,并對工作人員解釋道“他只是想看窗的背面”,然后再對兒子解釋)
父:“看展是有順序的,有開始也有結束。”
4.不同參觀動機的觀眾
本次調查使用填空式問題“您今天來廣州博物館參觀主要是為了________”,讓觀眾填寫參觀動機。根據填答內容,可以將參觀動機歸納為三類:學習知識(如“了解廣州歷史”“了解當地文化”“了解廣州發展”),休閑放松(如“逛公園順便來參觀”“放松心情”“旅游散心”),以及家庭活動(如“帶家人游玩”“帶小孩增長見識”“陪孫女參觀博物館和完成作業”)。前兩類是觀眾為了滿足個人的求知或休閑需要;第三類則是出于對家人的考慮,這類觀眾將參觀博物館作為一種家庭活動形式,其主要目的是陪伴家人或親子教育。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學習型觀眾的復愈體驗顯著高于其他兩類觀眾,而且其內省體驗也相對更強烈(圖四)。與休閑放松型觀眾相比,知識學習型觀眾在各展廳停留的時間更長,知識學習型觀眾平均停留時長為33.93分鐘,休閑放松型觀眾平均停留時長為27.22分鐘。知識學習型觀眾的投入度更高,對展覽內容更感興趣,更容易沉浸其中,他們的逃離感和被吸引的程度更強,所以復愈體驗和內省體驗更強一些。相當一部分家庭活動型觀眾是出于親子教育的目的,但其復愈體驗和內省體驗均低于休閑放松型觀眾,可能是因為他們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親子互動,留給自己思考、想象的時間比較少,而且親子互動也需要耗費定向注意力,并非毫不費力就能做到。

圖四// 不同參觀動機的觀眾的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三)滿意體驗和復愈體驗對觀眾行為意向的影響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復愈體驗和社交體驗對觀眾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實物體驗、內省體驗和認知體驗對觀眾行為意向無顯著影響(表四)[28]。一方面,本次研究對象是常設展覽,在已經看過展覽的情況下,觀眾如果再次到訪,更大的可能性是陪別人或者帶小孩參觀。所以,認知體驗、實物體驗以及與二者緊密關聯的內省體驗都不是觀眾重訪意向的主要驅動因素。另一方面,博物館內部空間及其展示內容所營造的環境,能讓觀眾從日常生活中抽離出來、放松身心和自在觀賞,這種氛圍所帶來的復愈體驗也會成為觀眾重訪的動力之一。在口碑宣傳方面,復愈體驗和社交體驗的顯著影響則說明觀眾傾向于向他人推介博物館是一處“放松身心”“值得帶家人和小孩去的地方”。當然,推薦者這樣推薦,并不意味著被推薦者就一定會以休閑放松和家庭活動為參觀動機。

表四// 觀眾調查樣本概況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發現,個人因素(如性別、文化程度、參觀動機)以及社會因素(如同伴類型)會導致觀眾滿意體驗的差異。這與約翰·福克(John Falk)和林恩·迪爾金(Lynn Dierking)的觀點一致,他們認為觀眾體驗是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和博物館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29]。然而,并非所有個人因素都顯著影響觀眾體驗,本研究中不同年齡段觀眾的內省體驗無顯著差異,初訪者與重訪者之間的實物體驗和社交體驗也無顯著差異,這與佩卡里克和朵琳對觀眾滿意體驗的研究結果略有不同。佩卡里克等學者所調查的博物館類型和展覽類型更加多樣,涵蓋了歷史類、藝術類以及科學與技術類博物館及其展覽,本研究集中關注歷史類展覽,研究結論的普適性還需要通過擴大研究范圍來檢驗。
博物館觀眾的復愈體驗突出表現為遠離感,即遠離日常環境而放松身心的體驗。復愈體驗不僅能給觀眾帶來復愈效果[30],對博物館也能發揮積極作用,如帶來更多的正面宣傳推薦以及重訪觀眾。未來研究可圍繞博物館復愈體驗的內涵及其影響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總的來說,博物館給觀眾帶來的不僅是認知體驗、實物體驗、內省體驗和社交體驗,還有復愈體驗,多重體驗的存在印證了博物館社會價值的多樣性。五類體驗中認知體驗和實物體驗排在前列,復愈體驗、社交體驗和內省體驗排在后位,說明藏品始終是塑造觀眾體驗的核心,這也是博物館不同于其他文教場所、風景名勝、休閑區域、社交空間的核心所在。即便是在“以觀眾為中心”的服務導向下,博物館仍需以藏品為核心,通過有效地闡釋和傳遞藏品所承載的信息,為觀眾帶來多樣化的體驗。
博物館觀眾體驗需要引起學界和業界的更多關注。從博物館觀眾研究的發展脈絡來看,其研究重點已逐漸從“人的行為”轉向“人的內心及其體驗”[31],從專注于學習體驗擴展為關注觀眾的整體體驗[32]。未來研究可以針對特定類型的博物館進一步設計觀眾體驗的測量量表,也可以針對特定人群(如青少年群體、老年群體)的參觀體驗開展專題研究,還可以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等量化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博物館展覽環境、展覽內容、解說服務等要素對觀眾體驗的影響。博物館從業者也可以通過觀眾研究系統地收集和分析數據,認識和理解觀眾期望獲得的體驗和實際獲得的體驗,為展覽策劃和展覽評估提供一些參考。比如,可以參照滿意體驗清單列表,讓觀眾從中勾選自己最為期待的體驗和最為滿意的體驗,通過兩相比較來分析、評估展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