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勒根道海
■ 席慕蓉(中國臺灣)
彎 泉
人的名字,是一種歸屬與辨別的標識,土地的名字也是。
人的名字在一生里通常不會更改,土地的名字原來也應該如此。
可是,在人類歷史上,為什么每次在政權轉換了之后,總要先將土地重新命名?
我的家鄉在近代就換了許多不同的名字。父親年輕的時候在籍貫欄上填的是“察哈爾盟鑲黃旗”,我的戶口簿上寫的是“察哈爾盟明安旗”,而如今,在家鄉的族人們卻又要稱這塊土地是“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了。
朋友說,我的遭遇還不算太悲慘,總比要被迫把自己美麗的故鄉改口叫做“仁愛鄉”“忠孝鄉”要好一點,起碼還有一部分是來自自己文化的根源。
可是,如果要呼喚故鄉,如果在生命的路途上要回頭呼喚故鄉,有誰不渴望能夠找到一個古老、樸素,是由自己的祖先所命名,而又到如今還存活著的名字呢?
因為,只有這樣的名字,才能更貼近那塊土地,也只有這樣的名字,才能更貼近我們的心。哪怕只是座荒涼的山,哪怕只是條淺淺的溪流,只要能夠逃過了被更改、被涂抹的命運,留下了一條可以與“昔日”相連接的線索,就是給后世的子孫們最好的禮物了。
這份禮物,終于給我找到了。
三年之前,初次見到父親的那片草原,才知道她保有了一個古老的名字——“寶勒根道海”,用漢文的意思來說,就是“彎泉”。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最早來自哪個年月,也不知道還能保留多久。我只知道,今天,這是父親與我以及我們的族人之間,唯一可以共享的愉悅和安慰。
彎泉,寶勒根道海。我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依靠的線索,開始去尋找一個古老而又樸素的文化。每次翻閱那些歷經浩劫的斷簡殘篇,仿佛能夠隱隱地感覺到民族血脈的躍動,充滿了頑強的生命力。
正如人類學家利瓦伊史陀所說的一樣,每種文化都有著要強烈保持自身本色的愿望,因為,唯有如此,她才不至于消失和滅亡。

林任菁 暖秋
幾十年都過去了,一直要到踏上草原之后,要到了今天,我才開始了解:原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那因為蒙古而流下的淚水并不完全是“沖動”,那在心中固執的渴望也并不完全是“狹隘”,所有的現象都牽連于一種內在的需求,是文化與種族加諸每一個團體之上的,不得不如此的需求。
一切都不過只因為我是一個蒙古族人罷了。認識了這樣的處境之后,心里反而釋然了,重壓卸下,那蒙古文化里明朗美麗的特質反而在處處向我顯現。在這里試著把這些心情寫下來,就用草原的名字作為篇名,獻給遙遠的故土。
胡馬依北風
蒙古人實在是個愛馬的民族。
從最早的蒙古史詩開始,以及在后來許多的文學作品里,英雄總是與他的駿馬同時出現。在遼闊無邊的高原上奔馳,兩者仿佛合為一體,共同分擔一生的憂患與悲喜,成為被后世所頌揚的勇氣、熱情、智慧與德行的象征。
而在真實的生活里,馬也一直是蒙古牧民倚靠與敬重的朋友。
今年五月,在臺北舉行的蒙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哈勘楚倫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就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探討馬在蒙古文化里的獨特地位。
在談到蒙古馬特別強烈的方向感,以及眷戀故土的優異性的時候,他舉了個真實的例子——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蒙古政府曾經贈送給越南友邦幾匹馬作為禮物。可是,在專人隨車送到目的地的時候,其中的一匹騸馬竟然獨自逃脫,走過千山萬水,在半年之后回到了蒙古高原上舊主的家中!
這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啊!
想一想,它要經過多少道關卡?不但要渡過長江、渡過黃河,還有那其他許多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河道支流,還要翻越過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嶺,還要跋涉過荒寒的戈壁;最不可思議的是:它怎么躲得過人類的好奇與貪欲?在這條不知道有幾千幾萬里長的回家的路上,它難道從來不需要經過任何的村鎮和城市?從來沒被人攔阻過和捕捉過嗎?
這樣的一匹馬,它要具備的是怎樣的勇氣與堅持?怎樣的智慧與判斷力?
一位年輕的蒙古學者告訴我,十三世紀左右,中亞的旅行者就曾經在游記上記載了他們的觀察與推測。他們說:蒙古馬在出發之前,總會昂首向天長嘯一聲,也許在那個時候,它們就記住了天空中星座的方位,好為歸來的路途預作準備。
我很愿意相信這樣的揣測。不過,如果是在白天出發的話,又該怎么辦呢?并且,蒙古政府送出這批禮物的時候是用汽車與火車來載運的,而這匹孤獨的馬,卻只能靠著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往北方的老家走回來的啊!
回到自家牧場邊上的馬兒,淚水不停地流了下來,驚詫激動的主人在想明白之后,更是忍不住抱著它放聲大哭。據說主人大宴親友,并且從此宣告,誰也不能再讓這匹馬離開他的身邊,誰也不準再讓這匹馬受一點兒的委屈。據說,這匹馬中的“尤力息斯”在許多年之后才在家鄉的草原上老病而逝,想它的靈魂一定能夠快樂地安息了吧。
故事到了這里,算是有了個完美的結局。可是,不知道為什么,我反而會常常想起另外的那幾匹留在越南的馬兒來。在會議過后,我再去追問了哈勘楚倫教授,到底是什么在引導著蒙古馬往家鄉的方向走去?他回答我說: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應該是一種北方的氣息,從風里帶過來的吧?”也許是這樣。
就像古詩里所說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每個生命都有他不同的選擇與不同的向往,有他自己都無從解釋與抗拒的鄉愁。
因此,我就會常常想起那幾匹羈留在越南的蒙古馬來,當它們年復一年在冬季迎著北風尋索著一種模糊的訊息的時候,心里會有怎樣的惆悵和悲傷呢?
故 居
七月的正午,在新疆的戈壁灘上只剩下酷熱君臨一切。
我們的越野車就像是一只干渴的小甲蟲,正腳步蹣跚地沿著塔里木盆地的邊緣往前緩緩爬行。車窗外是我從來也沒見過的奇異風景!一片荒寂大地無邊無際,寸草不生的巖礫間滿是些黑色的巨大石塊,雖然已經被風沙侵蝕得千瘡百孔,卻依舊矗立,并且像漩渦一般的往四周延伸分散,遠遠望去仿佛是置身于干涸的海底,又像是超現實畫家筆下所描繪的世界的盡頭。
而酷熱實在逼人,不僅從外面煎烤,就連身體最里面的血管都開始燃燒起來,讓我坐立不安。巴岱先生從前座回過頭來向我說:
“熱吧?再忍耐一下就好了,到前面的綠洲就會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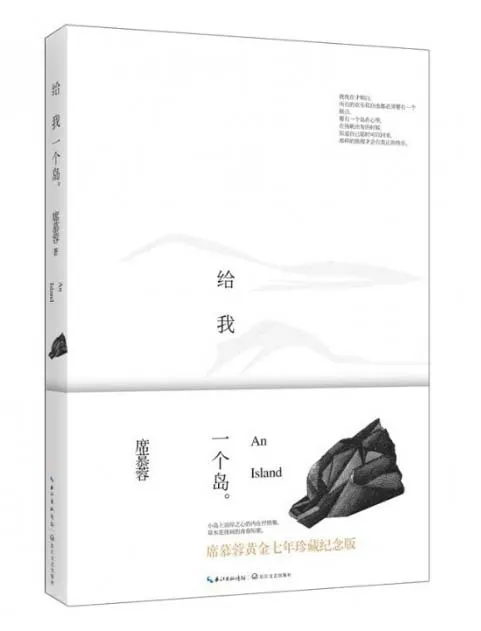
巴岱先生是世居新疆的土爾扈特蒙古人中的長者。他精通蒙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漢文,不但同時用這四種文字來寫作,并且更用盡心力來維護這一塊土地上的珍貴文化。我對這位長者仰慕已久,這次能夠和海北一起來新疆拜看他,并且在此刻能夠與他同行,實在是我求之不得的機緣,總該表現得好一點才對。所以,我趕快坐正了回答:
“還好!還不算太熱。”
海北卻在旁邊取笑我了:
“你當然不能叫熱!不是還立志要去橫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嗎?”
是啊!我的丈夫是知道我的。塔克拉瑪干、樓蘭、羅布泊都是我的夢!是從小就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只要稍微碰觸就會隱隱作痛的渴望!要怎么樣才能讓別人和自己都可以明白?那是一種悲喜交纏卻又無從解釋的誘惑和牽絆啊!
巴岱先生忽然問我:
“你知道塔克拉瑪干這個名字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但是海北說他知道,去年,他曾經從甘肅進去過,向導說這個名字是“死亡之海”,也有人說直譯應該就是“無法生還之地”的意思。
巴岱先生卻說:
“解釋有很多種,每個民族都說這是用他們自己的文字起的名字。我倒是比較喜歡維吾爾文里的一種翻譯,說‘塔克拉瑪干’的意思就是‘故居’。”
我的心在猛然間翻騰驚動了起來,原來謎底就藏在這里,這是多么貼切的名字!
今日荒寂絕滅的死亡沙漠原是先民的故居,是幾千年前水草豐美的快樂家園,是每個人心中難以舍棄的繁華舊夢,是當一代又一代、一步又一步地終于陷入了絕境之時依然堅持著的記憶;因此,才會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這一種在心里和夢里都反復出現的鄉愁了吧。
故居,塔克拉瑪干,在回首之時呼喚著的名字。此刻的我在發聲的同時才恍然了悟,我與千年之前的女子一樣,正走在同樣的一條長路上。
有個念頭忽然從心中一閃而過,那么,會不會也終于有那樣的一天?
幾百幾千或者幾萬年之后,會不會終于有那樣的一天?僅存的人類終于只好移居到另外的星球上去,在回首之時,他們含淚輕輕呼喚著那荒涼而又寂靜的地球——別了,塔克拉瑪干,我們的故居。
經 卷
1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在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博物館里,我能夠體會那位年輕的博物館員心中的焦急。
她說:
“怎么辦呢?眼看著這些經卷就要全毀在這兒了!”
在那間陰暗而又不通風的房間里,見不到任何防潮或者調溫的設備。在我們眼前,如山般堆積著的是每一部都用藍色絲絹當封皮,仔細地包了起來的長方形經卷。不但塞滿了所有的架子,連沿著墻邊的地上也堆得都是,感覺上就好像是座窒悶的大山一樣。
年輕的博物館員說:
“都好幾年了!就這么堆著。再不想辦法的話,很快就會壞了的啊!”
2
陪著遠客到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觀,得到院方的熱忱款待,給我們展示了院藏的蒙古帝后畫像。在小小展覽室的一角,還放了兩部剛從庫房里拿出來的經卷。像這樣的手抄經卷,通常是用泥金或者珊瑚粉寫在黑色或者藍色的底上,做成連接的冊頁。最外部是兩塊夾經板,雕刻師與畫工就在這兩塊板上大顯身手。有的更是用絲線一針一針繡出來的,光彩奪目,令人不敢逼視。
展覽室外站著警衛,展覽室內的溫度濕度都有各種儀器來監控,每個人在進入的時候,還要戴上一層薄薄的白色紙質口罩,講話只能輕言細語,心情也誠惶誠恐了起來。
后來和一位在臺北故宮工作過的朋友聊天,說起那令我印象深刻的口罩,朋友卻說:
“戴口罩除了是要保護文物,避免受到參觀者呼吸里的濕氣影響之外,也是有保護參觀者的作用。因為,就算設備再好,長年放在庫房里的文物,還是會藏著一些霉菌的。”
3
一九九〇年的秋天,第一次到烏蘭巴托的甘丹寺拜謁,同行的蒙古朋友向喇嘛請求了之后,我們得以參觀寺中的藏經室。
那天天氣雖然寒冷,陽光卻很好,透過玻璃窗照進來,滿墻的佛幡和滿室的經卷都光芒燦爛,仿佛走進了一個千彩萬色的世界。
接待我們的喇嘛舉止從容,他先為我們大略介紹了一下院藏經卷的內容,然后再從架上拿下一卷,平放在我們眼前的長桌上。
經卷外面包著的是一種金黃色的錦織方巾,要先把這層錦織打開,里面才是經卷,打開經卷的夾經板,那雕工繁復精致華美到無法形容的藝術珍品就展現在我們眼前了!
我注意到喇嘛在拿取經卷的時候非常慎重,一層一層打開的時候,也非常仔細,可是,他向我們展示的時候卻毫無戒心,就像是在向我們展示一件他日日都會用到的對象一樣。
在回去旅館的路上,我把心中的疑問向朋友說了,朋友是這樣回答我的:
“本來這就是他們日日都會誦讀的經卷,藏經寺就是寺里喇嘛的圖書館。當然,這些經卷都是寶物。可是,你要知道,常常有人誦念的經卷才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寶物,不容易壞的。”
大雁的歌
這是蒙古草原上的一首歌,據說是從十七世紀末就開始流傳的民謠。
老人在草原上看見飛過的大雁,覺得似曾相識,不禁仰首問:
“大雁啊!大雁!那有著碧藍海洋圍繞的南方,是多么溫暖和美麗,你為什么不在那里長久停留?非要千里迢迢地飛回來呢?”
大雁聽見了,就低飛下來回答:
“春天花開了,草原就是幸福的天地,有一種呼喚帶領我們回到家鄉。”
老人俯首行禮,表示歡迎和祝福。大雁正要展翅飛離,忽然又回頭輕聲詢問:
“我記得你原來是個多么年輕的少年啊!怎么變得這么老了呢?”
老人長嘆一聲說:
“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變老的,實在是這時光無止盡的循環,讓我不得不老去的啊!”
我是在前年春天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在臺北中廣的錄音室里,從蒙古來的巴達拉老先生應邀演唱幾首蒙古民謠。每唱一首,他都要先向我解說歌詞的大意,好讓我能向聽眾作簡短的介紹。幫我們兩人翻譯的杜布興巴雅爾,在翻譯到這首歌最后一段的時候,忽然停頓了下來,哽咽不語。
這位朋友處事一向沉穩,我很少看到他這樣失態過,不禁有點訝異。可是,在幾秒鐘之后,等到他終于把最后一段歌詞翻譯出來的時候,我也有了相同的感受。
“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變老的,實在是這時光無止盡的循環,讓我不得不老去的啊!”
老先生站在錄音室中間,穿著蒙古長袍,仰首高歌,好像就是那個站在草原上的老人,仿佛空中真有大雁飛來與他應答,高亢蒼涼的歌聲,唱出了生命的疼痛與無奈。
每一首會流傳下來的歌,應該都是從我們心里最痛的地方唱出來的吧?
巴達拉老先生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在草原上采集與傳授蒙古民謠。他說:
“我想,人活著總有些天真的理想。這么美麗的歌謠既然是祖先從心里面唱出來給我們聽的,那么,就讓我們再把它唱進子孫的心里面去吧。”
去年八月,巴達拉老先生因為急病在烏蘭巴托逝世。我一直想向他表達的謝意,以及臺北的朋友們想為他錄制專集的心愿,如今都再也沒有實現的機會了。
當大雁再飛回北方去的時候,草原上有誰能夠再回答它呢?
父親教我的歌
從前,常聽外婆說,五歲以前的我,是個標準的蒙古娃娃。雖然生長在中國南方,從來也沒見過家鄉,卻會說很流利的蒙古話,還會唱好幾首蒙古歌,只可惜一入小學之后,就什么都忘得干干凈凈的了。
隱約感覺到外婆語氣里的惋惜與責備,可是,我能有什么辦法呢?
對一個太早入學,智力體力都不如人的孩子來說,小學一二年級可真不好念哪!剛進去的那些日子里,真可以說是步步驚魂,幾乎是把所有的力氣,把整個的童年,都花在追趕別人步伐,博取別人認同的功夫上了。
要班上同學愿意接受你并且和你做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偏偏還要跟著父母四處遷徙。那幾年間,從南京、上海、廣州再輾轉到了香港,每次都要重新開始,我一次又一次地更換著語言,等到連那些說廣東話的同學也終于接納了我的時候,已經是小學五六年級了。我普通話標準、廣東話標準,甚至連他們開玩笑時拋過來的俏皮話,我也能準確地接招還擊。只是,在這樣長時間的努力之后,我的蒙古話就只剩下一些問候寒暄的單句,而我的蒙古歌則是早已離我遠去,走得連一點影子也找不回來了。
那以后外婆偶爾提起,我雖然也覺得有點可惜和慚愧,但是年輕的我,卻不十分在意,也絲毫不覺得疼痛。
那強烈的疼痛來得很晚,很突然。
一九八九年夏末,初次見到了我的蒙古原鄉。這之后,一到暑假,我就像候鳥般地往北方飛去。有天晚上,和朋友們在鄂爾多斯高原上聚會,大家互相敬酒,在敬酒之前都會唱一首歌,每一首都不相同,都很好聽。當地的朋友自豪地說:鄂爾多斯是“歌的海洋”,他一個人就可以連唱上七天七夜也不會重復。
那高亢明亮的歌聲,和杯中的酒一樣醉人,喝了幾杯之后,我也活潑了起來,不肯只做個聽眾,于是舉起杯子,向著眾人,我也要來學著敬酒了。可是,酒在杯中,而歌呢?歌在哪里?在臺灣島,我當然也有好朋友,我們當然也一起喝過酒,一起盡興地唱過歌。從兒歌、民謠一直唱到流行的歌曲,可以選擇的曲子也真不算少,但是,在這一刻,好像都不能代表我的心,不能代表我心中渴望發出的聲音。
此刻的我,站在原鄉的土地上,喝著原鄉的酒,面對著原鄉的人,我忽然非常渴望也能夠發出原鄉的聲音。
不會說蒙古話還可以找朋友翻譯,無論如何也能把想表達的意思說出七八分來。但是,歌呢?用原鄉的語言和曲調唱出來的聲音,是從生命最深處直接迸發出來的婉轉呼喚,是任何事物都無法替代也無法轉換的啊!
在那個時候,我才感覺到了一種強烈的疼痛與欠缺,好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糾纏著撕扯著的什么忽然都浮現了出來,空虛而又無奈。
因此,從鄂爾多斯回來之后,我就下定決心,非要學會一首蒙古歌不可。真的,即使只能學會一首都好。
但是,事情好像不能盡如人意。我是有幾位很會唱歌的朋友,我也有了幾首曲譜,有了一些歌詞,還有人幫我用英文字母把蒙文的發音逐字逐句地拼了出來。但是,好像都沒什么效果。看圖識字的當時,也許可以唱上一兩段,只要稍微擱置下來,過后就一句也唱不完全了。
一九九三年夏天,和住在德國的父親一起參加了比利時魯汶大學舉辦的蒙古學學術會議。在回程的火車上,父親為朋友們輕聲唱了一首蒙古民謠,那曲調非常親切。回到波昂,我就央求父親教我。
父親先給我解釋歌詞大意,那是個羞怯的青年對一位美麗女子的愛慕,他只敢遠遠觀望:何等潔白清秀的臉龐!何等精致細嫩的手腕!何等殷紅柔潤的雙唇!何等深沉明理的智慧!這生來就優雅高貴的少女,想必是一般平民的子弟只能在夢里深深愛慕著的人兒吧。
然后父親開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唱:
采熱奈痕查干那!
查日布奈痕拿日英那!
……
在起初,我雖然有點手忙腳亂,又要記曲調又要記歌詞,還不時要用字母或者注音符號來拼音。不過,學習的過程倒是出奇的順利,在萊茵河畔父親的公寓里,在那年夏天,我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學會了一首好聽的蒙古歌。
回到臺灣島之后,好幾次,在宴席上,我舉起杯來,向著或是從北方前來做客的蒙古客人,或是在南方和我一起成長的漢人朋友,高高興興地唱出這首歌。令我自豪的是,好像從來也沒有唱錯過一個字,唱走過一個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和姊妹們約好了在夏威夷共聚一次,有天晚上,我忍不住給她們三個唱了這首歌。
是在妹妹的公寓里,南方春日的夜晚慵懶而又溫暖,窗外送來淡淡的花香。她們斜倚在沙發上,微笑注視著我,仿佛有些什么記憶隨著這首歌又回到了眼前。
我剛唱完,妹妹就說:這個曲調很熟,好像聽誰唱過。
然后,姊姊就說:
“是姥姥!姥姥很愛唱這首歌。我記得那時候她都是在早上,一邊梳著頭發一邊輕輕地唱著這首歌的。”
原來,答案在這里!
姊姊的記憶,填補了我生命初期的那段空白。
我想,在我的幼年,在那些充滿了陽光的清晨。當外婆對著鏡子梳頭的時候,當她輕輕哼唱著的時候,依偎在她身邊的我,一定也曾經跟著她一句一句唱過的吧?不然的話,今天的我怎么可能學得這么容易這么快?
我忽然安靜了下來,原來,答案藏在這里!轉身慢慢走向窗前,窗外花香馥郁,大地無邊靜寂,我只覺得自己好像剛剛走過一條迢遙的長路,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
一切終于都有了解答。原來,此刻在長路的這一端跟著父親學會的這首歌,我在生命初初啟程的時候曾經唱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