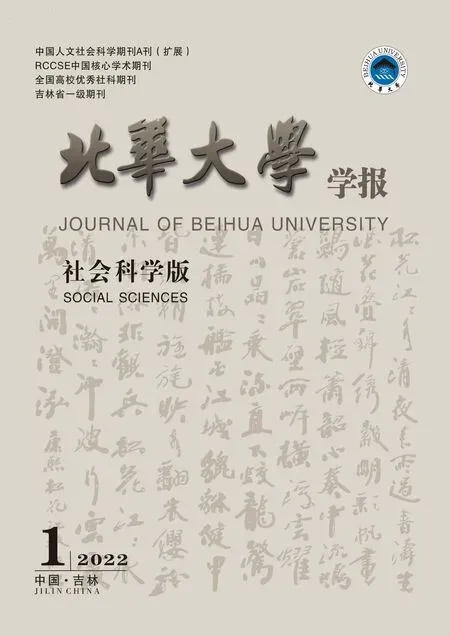中亞五國語言生態(tài)及政策的共性研究
張治國
引 言
中亞五國分別為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前三國與中國領土接壤)。國名都以“斯坦”(-stan)結尾,所以,中亞五國也叫“斯坦五國”。“斯坦”是古波斯語中的一個后綴,意為“地方”或“國家”。五國總面積約400萬平方公里[1],截止到2020年總人口約7 000萬[2]。中亞五國在地理、人文、民族、宗教、歷史、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都有許多共同點,所以,“中亞”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政治和文化概念,為此,國際上眾多學科常把中亞五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同樣,對于中亞五國的語言政策,我們除了需要進行國別研究外,[3-6]也需要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國外學界做得比較好,已有專著[7]或編著[8]等厚重學術成果出現(xiàn)。盡管國內學界也有一些這方面的論文成果,[9-15]但總體上缺乏對中亞語言生態(tài)及語言政策的整體化研究。語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語言生存的背景或環(huán)境,即語言生態(tài)。只有了解了大概的語言生態(tài),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語言政策。故此,本文擬做一些這方面的嘗試——探究中亞五國1991年獨立后的語言生態(tài)變化及語言政策特點。
一、中亞五國語言生態(tài)的共同特點
(一)五國具有大體相同的社會語庫結構
社會語庫(linguistic repertoire)是指某一社會中所使用的各種語言及其變體的總和。中亞五國都屬于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16]“無論是從社會的角度還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多語都是中亞語言的一個顯著特點”[17]157,各國語言的總數(shù)都百種左右,它們的社會語庫結構大體相同,都由以下四類語言構成:
第一類是名義語言(titular language)。名義語言是指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即名義國家(titular nation)的國語。在蘇聯(lián)時期,這些語言在俄語的強勢環(huán)境下顯得黯然失色,僅有名義上的地位。這些加盟共和國獨立后,其名義語言的地位開始凸顯,都成了各國名副其實的國語,但名義語言術語仍在學術界使用。中亞五國的名義語言分別是其主體民族所使用的語言,即哈薩克語(Kazakh)、吉爾吉斯語(Kyrgyz)、塔吉克語(Tajik)、烏茲別克語(Uzbek)和土庫曼語(Turkmen)。如表1所示,獨立初期,各國名義語言在家庭域中的使用率都不算高,其中最高的是土庫曼語(達62.8%),最低的是哈薩克語(33.6%)。[7]213但經(jīng)過二十幾年的語言改革和推廣后,中亞五國名義語言的普及率已大有提高。中亞五國語言的總體特點是:以本國主體民族的語言為名義語言,同時也使用周邊鄰國的名義語言。如哈薩克斯坦的名義語言是哈薩克語,但同時也使用中亞其他四國的名義語言,只不過其他四國的名義語言只算是哈薩克斯坦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其他四國的語言情況也是如此。

表1 中亞五國名義語言及俄語在家庭中的使用情況(1993) /%
第二類是俄語。在蘇聯(lián)時代,俄語是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的官方語言,地位顯赫,影響深遠。中亞五國獨立后,俄語依然是這些國家的強勢語和族際交際語,[18]這里仍算是俄語世界(Russophone)的一角。中亞五國的俄語影響度(或受俄語的影響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7]201表1顯示的俄語在中亞五國家庭中的使用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哈薩克斯坦之所以受俄語的影響最深,是因為在蘇聯(lián)時期,哈薩克族是蘇聯(lián)中亞地區(qū)各民族中俄羅斯化最高的民族,因而很多哈薩克族國民以俄語為第一語言。加之,哈薩克斯坦在地理位置上緊鄰俄羅斯,境內具有中亞五國中比例最高的俄羅斯族人口。土庫曼斯坦之所以在中亞五國中受俄語的影響最小,俄語地位較低,使用范圍較窄,其原因是多重復雜的,如下幾個因素是主要的:自1995年起土庫曼斯坦成了一個中立國家,2005年退出獨聯(lián)體,也未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國內的俄羅斯族人僅占全國人口的1.8%,在俄羅斯工作的人是中亞五國中比例最小的。[8]
第三類是本國的非名義語言(non-titular language)或少數(shù)民族語言。這些語言是中亞五國除各自的名義語言和俄語外的其他語言。它們數(shù)量龐大,使用者不多,地位不高。各國非名義語言的主要語種大致相同,即其他四國的名義語言、阿塞拜疆語、德語、韃靼語、維吾爾語、卡拉卡爾帕克語(Karakalpak)等。[19]中亞五國家庭語言的使用狀況(見表2)也證明了這一事實。另外,表2還表明中亞五國之間的跨境語言較多,語言障礙較少。

表2 中亞五國非名義語言在家庭中的使用情況(1993) /%
第四類是外語。中亞五國的外語主要是歐洲語言(如英語、法語、德語等)及東亞語言(如漢語、朝鮮語或韓語等),其中有些語言(如德語、土耳其語、朝鮮語或韓語)既屬于外語,也屬于本國的非名義語言。表3反映了中亞五國各國人民對外語的渴望度。

表3 中亞五國國民外語學習意愿情況(1993年) /%
表3顯示,中亞五國各國人民最想學習的外語是英語,其次是土耳其語;俄語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但在語言實踐中,俄語的使用率還是不低的;此外,不想學習任何外語的比例在各國也不低,這說明中亞五國在建國初期對外接觸不多,國際化程度不高,所以外語學習的動機還不強。
(二)五國名義語言具有大體相同的語言屬性
在中亞五國的名義語言中,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和土庫曼語都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Turkic languages),而塔吉克語則歸為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Indo-Iranian languages)。突厥語族,也稱土耳其語族,是阿爾泰語系中最大的一個語族。它包含了40多種語言,其中土耳其語的使用范圍最廣,使用人口最多。突厥語族的人口分布很廣,數(shù)量達1.65億至2億人,分布地域從東到西由中國一直伸展到俄羅斯及東歐。突厥語族分為東突厥語支(如維吾爾語、烏茲別克語),南突厥語支(如土庫曼語),西突厥語支(如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和北突厥語支(如阿爾泰語、圖瓦語)。印度—伊朗語族是印歐語系中最東方的一族,下分為印度—雅利安語支(Indo-Aryan)、伊朗語支和奴利斯塔尼語支(Nuristani)。伊朗語支分布在伊朗(古波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高加索等地。該語支包括波斯語、普什圖語、庫爾德語、俾路支語、奧塞梯語、塔吉克語、法爾西語、達里語、回回語等。而塔吉克語與波斯語很相近,許多人把它看作是波斯語的一種方言或變體。可見,中亞五國的名義語言除塔吉克語屬印度—伊朗語族外,其余四國的都屬突厥語族。所以,人們根據(jù)名義語言的屬性稱塔吉克斯坦為波斯語國家,其余四國為突厥語國家(Turkic states)。
同語族的特性使得中亞五國名義語言(除塔吉克語)之間以及這些名義語言與其他部分非名義語言(如維吾爾語、柯爾克孜語、韃靼語、卡拉卡爾帕克語)之間的互懂度(intelligibility)較高。而且,現(xiàn)代突厥語族下的各民族語言之間的差別遠小于印歐語系、漢藏語系等語系中同語族語言之間的差別。突厥語族的各分支語言有許多共同的語匯、相似的語法和發(fā)音特點。加之,突厥人在歐亞大陸的分布區(qū)域極廣,又彼此長期混居,同時還分別與操其他語言的民族相鄰,這就使得突厥語內部諸語言的互懂度較高。
(三)五國都存在政治變革導致語言使用人數(shù)突變的情況
語言的地位和活力與語言的使用者數(shù)量存在一定的關系,從而影響語言政策的制定。[20]中亞地區(qū)社會政治的變化帶來了民族結構及人口數(shù)量的變化,進而影響到語言的地位與活力。1990—2000年的十年是中亞五國的人口動蕩和變化期,各國的人口總數(shù)、民族比例、俄語和各名義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的比例等數(shù)據(jù)每年都有較大變化。中亞五國獨立初期,都出現(xiàn)了人口大遷移或民族大洗牌現(xiàn)象:多數(shù)人都回歸到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而且,五國的遷出人口大于遷入人口,導致各國人口總數(shù)減少。各國遷入人口主要是周邊加盟共和國及其他國家的同族人口,遷出人口情況則正相反,但主要是俄羅斯族人(詳見表4),他們大多都遷往俄羅斯聯(lián)邦或其他西方國家。[21]

表4 中亞五國俄羅斯族人口統(tǒng)計(1989—2005年) /萬
表4顯示,俄羅斯族人口減少幅度最大的國家是塔吉克斯坦(64.7%),最小的是哈薩克斯坦(33.3%),各國平均減少率為52.68%。也就是說,中亞五國有一半多的俄羅斯族人口外遷。人口數(shù)量的大變化使各國的民族語言(尤其是名義語言和俄語)的地位和活力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各國名義語言的地位和活力上升,俄語的地位和活力下降。
中亞五國獨立后之所以出現(xiàn)大量的人口移動和民族大洗牌現(xiàn)象,主要是出于民族身份及語言身份的考慮。語言一直是“集體身份”或“民族身份”兩個概念中的核心內容,是人類集體文化感知中的關鍵因素。當人們意識到國家的語言政策會給自己的集體身份或民族身份帶來威脅時,上述感覺就會更加強烈。中亞五國剛獨立時,這些國家的許多人都遇到了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的問題。[7]5Katagoshchina指出:“身份危機是導致中亞五國少數(shù)民族外遷的一個重要原因。”[23]26于是,中亞五國獨立后都吸引了周邊國家中的同族人口遷入,自然,這些國家的主要外遷人口都不是各國主體民族。
(四)五國都受到同樣的外國勢力及其語言的影響
第一,受俄羅斯和俄語的影響。俄羅斯對中亞五國的影響歷史悠久,俄羅斯及中亞各國的俄羅斯族人都希望中亞各國保留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若國內名義語言與俄語的關系處理不好,就會影響到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外交關系,乃至引起國內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中亞各國的語言政策制定者都已經(jīng)認識到俄羅斯政府對中亞各國俄羅斯族人口的支持。因此,俄羅斯的影響是這些國家在制定語言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外在因素,[7]209各國都不能無視俄語的存在。
第二,受土耳其和土耳其語的影響。土耳其原本在中亞就有一定的影響,自從中亞五國獨立后,土耳其的一些機構和組織(如總部位于土耳其安卡拉的突厥文化國際組織)就更加不遺余力地在這里推廣土耳其的語言和文化,并反復強調突厥人共同所具有的民族、語言和文化之根,試圖把土耳其語打造為地區(qū)共同語。[24]土耳其想加強突厥族語言使用國家之間的聯(lián)系,形成突厥語世界(Turkic World)。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的有關突厥語言和文化的學術會議也的確加強了中亞各國彼此的認同感。盡管土耳其竭力推廣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但中亞各國都想樹立自己獨有的國家身份,他們大多僅接受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的思想,尤其是語言文化方面的泛突厥主義。盡管土耳其語在中亞的傳播速度很快,但土耳其語在中亞的推廣也面臨著各種域外語言的競爭:首先是歐洲語言(如俄語、英語、德語和法語),其次是亞洲語言(如朝鮮語或韓語、日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漢語)。[7]14因此,土耳其語“還算不上是該地區(qū)的通用語”[17]178。
第三,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英語等語言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大國在“9·11”事件后打著反恐的旗號開始更加關注和強勢介入中亞事務,使得英語等西方強勢語言在中亞的影響也隨之擴大。[17]而且,中亞許多年輕一代由于受到美國流行文化及電腦等產(chǎn)品的影響而喜歡英語(表3數(shù)據(jù)反映的中亞五國國民的外語學習渴望度也說明了這一點),各國都有不少的英語培訓中心,也建有一些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高校。
第四,受伊朗和波斯語的影響。伊朗一直聲稱在文化、宗教和語言方面對中亞(尤其是對塔吉克斯坦)有一定的影響力。塔吉克斯坦是中亞五國中唯一主體民族不是突厥族的國家,它屬于波斯語國家,而且,塔吉克語被看作是伊朗波斯語的一種變體。出于語言、地理、歷史和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的考慮,塔吉克斯坦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朗及波斯語的影響。[17]語言的聯(lián)系使得塔吉克斯坦與伊朗“走得更近,關系更好”,這是“中亞其他四國未有的現(xiàn)象,也是塔吉克斯坦與其余四國所不同的地方”[24]142。
第五,受東亞國家及其語言的影響。中國的語言(尤其是漢語普通話、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在中亞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中亞人想學或正在學漢語普通話,而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是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跨境語言,在詞匯上會相互影響。此外,中亞本身有不少朝鮮族人口,加之,近年來韓國政府對韓語教學的積極推廣,因此,朝鮮語或韓語在中亞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例如,韓國注重與中亞兩個較強國家——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經(jīng)貿(mào)關系,而且,這兩個國家分別有0.6%和1%的朝鮮族人口,這些因素推動了這兩個國家的朝鮮和韓國研究,并建立了韓國語言文化教育中心,韓國政府為該中心提供經(jīng)費及教材。而且,近來由于受到韓國多方面的影響,這兩個國家的語言學習從原先的朝鮮語變體轉向了韓語變體。[17]179-180
二、中亞五國語言政策的共同特點
(一)地位規(guī)劃特點及分析
在語言的地位規(guī)劃方面,主要是解決名義語言和俄語的地位之爭問題,與此同時卻都忽略了本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地位問題。
蘇聯(lián)解體后,中亞五國皆面臨著如何處理本國名義語言與俄語的關系問題。“這些國家獨立后都試圖提高本國名義語言的地位,并以此來抗衡俄語(這是主要目的)和本國的其他少數(shù)民族語言(這是次要目的),于是,它們紛紛對本國原有的語言政策進行修改”,[25]164并通過各自的憲法及語言法規(guī)定本國的名義語言為國語、官方語言,結果“各國都發(fā)生了語言轉用,從原先的強勢語言俄語轉用現(xiàn)在的名義語言”[7]201。在這場自上而下的語言轉用運動中,本國“其他少數(shù)民族語言或非名義語言則被邊緣化”[7]17。
誠然,國家獨立有利于這些國家主體民族語言或名義語言的地位提升。但是,俄語在這一地區(qū)的影響以及俄語作為高階語言(H variety)的地位是這些名義語言無法在短期內所撼動的。不過,這些國家在語言政策上重名義語言、輕俄語及忽略非名義語言的做法也不是空穴來風,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這些國家獨立后都遇到同樣的一個身份困境,即如何處理國家在全球化變革時代由國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地方身份(subnational identity)和跨國身份(transnational identity)所構成的身份多樣性問題。[7]198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剛獨立時都在尋找一種新的民族特性,以便樹立自己的國家身份。[7]1國語是國家身份的一個象征,“在重新界定新的國家身份時,語言政策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24]165于是,中亞五國都必須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即去俄羅斯化(de-Rissianization)或去蘇聯(lián)化(de-Sovietization),然后才樹立自己的國家身份。最顯性的去俄羅斯化就是去俄語化,同時,加強國家身份的最顯性方式是推廣本國的名義語言,提升本國的名義語言地位。
把名義語言提升為強勢語言的行為必然會帶來語言排斥(language exclusion)現(xiàn)象,或者說,必然會降低其他語言的地位和作用。[7]3這些國家的語言地位規(guī)劃都遇到程度不同的各種阻力,來自國家內部及外部的壓力使得它們都無法擺脫俄語的影響,并對鄰國名義語言予以適度考慮:在國內方面,各國俄羅斯族及其他民族的關系都變得緊張;有些國家的主體民族與其他民族也存在矛盾(如吉爾吉斯斯坦國內的烏茲別克族與吉爾吉斯族之間關系特別緊張)。在國外方面,中亞五國在制定語言的地位規(guī)劃時都必須考慮本國俄語的地位及俄羅斯對此的感受;有些國家還不得不考慮鄰國間的關系(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曾存在緊張的外交關系),以免因語言地位規(guī)劃帶來外交沖突。此外,對于中亞五國的不少人而言,俄羅斯情結揮之不去,他們對俄語是愛恨交加:就實用性和國際性的角度而言,俄語更有用,但從情感和尊嚴的角度來說,他們情愿選擇自己的名義語言或民族語言。后來,中亞五國都只好放寬了俄語在本國的使用限制,并恢復提高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如今俄語依然是這些國家上層社會以及知識界學人主要使用的語言,但俄語在中亞五國的地位、聲望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使用范圍有所收縮。
總之,中亞五國獨立后,語言已經(jīng)明顯政治化,這些國家語言政策及規(guī)劃的制定幾乎完全取決于各國政府首腦及相關的智囊團。[26-27]而且,他們盡力通過語言地位和語言使用的概念化來鞏固國家的地位和加強國家的團結,[7]21但事實上,蘇聯(lián)的突然解體導致中亞五國各項語言政策的制定“準備不足”[1]序言,匆忙應對,且有些操之過急。
(二)本體規(guī)劃特點及分析
在語言的本體規(guī)劃方面,主要涉及名義語言書寫符號系統(tǒng)的選用問題,同時,也有意抑制或消除俄語詞在名義語言中的大量借用。
中亞五國在名義語言的書寫系統(tǒng)上都大概經(jīng)歷了如下幾個過程:最初使用了幾十年的阿拉伯字母(Arabic script);20世紀20年代曾短暫地使用過拉丁字母(Latin script);并入蘇聯(lián)后(即20世紀40年代)則改用西里爾字母(Cyrillic script);1991年獨立后就名義語言的書寫系統(tǒng)問題又產(chǎn)生了分歧——是恢復拉丁字母或阿拉伯字母書寫系統(tǒng),還是保留西里爾字母書寫系統(tǒng)的問題。[28]例如,吉爾吉斯斯坦想恢復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系統(tǒng),贊同者認為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系統(tǒng)有助于同其他突厥族語言的使用者交流;反對者則認為應該保留西里爾字母書寫系統(tǒng),只要做些適當?shù)男薷募纯桑駝t成本巨大;還有人提倡轉用拉丁字母書寫系統(tǒng),以便與世界接軌。總之,在中亞五國剛獨立的頭幾年,書寫系統(tǒng)比較混亂(詳見表5),而且“書寫系統(tǒng)的變換使得不少人變成了文盲”[7]206。

表5 中亞五國書寫符號系統(tǒng)的應用情況(1993年) /%
現(xiàn)在,俄羅斯族人口較多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仍有很多俄羅斯族人采用西里爾字母書寫哈薩克語和吉爾吉斯語。塔吉克斯坦盡管擁有的俄羅斯族人口不多,卻依然在其名義語言上堅持使用西里爾字母,足見塔吉克斯坦與俄羅斯的親密關系。烏茲別克斯坦的名義語言則采用了雙字母制(two parallel alphabets)——西里爾字母和拉丁字母,有的領域(如學校)依然使西里爾字母書寫烏茲別克語,有的領域(如公共場所)選用拉丁字母來書寫路牌等公共標識,還有的領域(如網(wǎng)絡)則兩者均用,但國家的最終意圖是要逐漸過渡到拉丁字母的使用。1993年土庫曼斯坦時任總統(tǒng)尼亞佐夫(Niyazov)發(fā)出總統(tǒng)令——該國名義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tǒng)將從1996年開始從西里爾字母改為拉丁字母。[7,27]
在語言的本體規(guī)劃方面,中亞五國都試圖將本國國語的書寫符號系統(tǒng)從原先的西里爾字母改為拉丁字母,但字母拉丁化(Latinization)的困難要比預想的大得多。此外,中亞五國在本體規(guī)劃上還有意抑制或消除本國名義語言中的一些俄語詞。中亞五國有些民族主義者把俄語看作是“蘇聯(lián)語言帝國主義的遺產(chǎn)”[7]4。
中亞五國獨立后都試圖實現(xiàn)名義語言的本國化或本土化(indigenization),尤其是恢復名義語言的書寫系統(tǒng)以及凈化名義語言的詞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這些語言改革都經(jīng)常引起嚴重的語言混亂,并帶來容易導致政治、文化沖突的新問題。”[29]
(三)習得規(guī)劃特點及分析
在語言的習得規(guī)劃方面,主要是竭力解決教學媒介語問題,同時,也重視英語教育。
教學媒介語(medium of instruction)是指學校的教學語言,它是語言習得規(guī)劃的重要內容,也是語言重要性的反映。中亞五國獨立后都試圖解決本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媒介語問題,力求以本國名義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現(xiàn)在各國教學媒介語使用情況如下:小學階段以名義語言為主,俄語為輔,幾個較大的非名義語言為點綴;中學階段以名義語言為主,俄語為輔;大學階段則正好與中學階段相反,以俄語為主,[30]主要原因是名義語言在師資、教材、參考資料以及語言的現(xiàn)代化和書寫符號系統(tǒng)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如名義語言缺乏許多現(xiàn)代科技術語的表達,其科技文獻也很少),而且,不少學生及其家長也都更喜歡選擇以俄語為教學媒介語的高校(詳見表6)。

表6 中亞五國高校教學媒介語使用情況(2006年) /%
中亞五國的語言習得規(guī)劃主要面臨如下困境:新獨立的主權國家當然首先應該是發(fā)展和推廣國語(即名義語言);考慮到本國的地緣結構、語言文化淵源、外交關系及為數(shù)不少的俄羅斯族國民等因素,各國又必須重視和推廣俄語;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受到各國教育部門及國民的青睞,各國還不能違背這種國際大趨勢及民意,也須重視英語的教育;在國內少數(shù)民族母語訴求的壓力下,各國也不能太忽視少數(shù)民族語言(即非名義語言)的教育,尤其是在小學低年級階段。因此,受錯綜復雜因素的影響,各國須往“四語”(即本國名義語言、俄語、英語和本國非名義語言)教育方向發(fā)展。但是,“四語”教育對國家、學校及家庭等都將帶來經(jīng)濟、資源及精力等方面的壓力,于是,權衡之后,各國都在向“三語”教育方向發(fā)展,即重視本國的名義語言、俄語和英語教育,而相對薄待本國的非名義語言教育了。
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中亞五國的語言生態(tài)內容豐富,語言政策動蕩較大,造成這些現(xiàn)象的原因復雜,但主要緣于社會政治的動蕩變化。中亞五國在語言生態(tài)及語言政策方面有許多共同點,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同時,也要看到塔吉克斯坦在名義語言的種類及由此帶來的周邊外交關系與其余四國存在一些差異。至于中亞五國語言政策施行的效果,現(xiàn)在評判也許還為時過早,因為語言政策的影響是緩慢的和漫長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本文的分析中獲得如下兩點啟示。
(一)中亞語言生態(tài)及政策與我國關系密切
中亞五國的語言生態(tài)及語言政策與我國的“一帶一路”及與周邊國家互聯(lián)互通建設關系密切。中亞五國連接歐亞大陸(Eurasia),無論是在地緣政治還是在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占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對于中國更是如此。因為中亞五國是中國的鄰國或近國,是“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的必經(jīng)之路,也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互聯(lián)互通建設的對象國,還是中國在反恐、緝毒等領域的合作國,其中四國與中國同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土庫曼斯坦除外)。中國與中亞五國的政治互信、經(jīng)濟互惠、人員互通都需要以文化為背景、以語言為橋梁,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去了解、研究中亞五國的語言生態(tài)及語言政策,以便建立更多更牢的語言橋梁,并通過語言橋梁增進彼此的了解,尊重彼此的文化,融洽彼此關系,為中國與中亞五國之間的合作與發(fā)展提供科學的語言管理和優(yōu)質的語言服務。
(二)重視英語、俄語和中亞五國名義語言教育
我們從中亞五國的語言生態(tài)及語言政策可知,除了各國的名義語言外,俄語和英語是該地區(qū)最重要的語言。無論是從地緣政治和經(jīng)濟發(fā)展,還是從語言活力和語言安全來看,這兩種語言也是我國非常重要的外語,需要得到教育部門的重點關注。在中國,對英語教育的重視有目共睹,但俄語教育似乎還有提高的空間。盡管我們無需全面推廣俄語,但鑒于我國與俄語國家、俄語使用區(qū)(如中亞地區(qū)、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國)及上海合作組織都有許多密切的政治、外交、經(jīng)濟、人文等聯(lián)系,我國還是要重視俄語教育的發(fā)展,尤其要重視俄語教育的區(qū)域性發(fā)展,強化我國東北和西北地區(qū)的俄語教育。同時,在國內尤其是東北和西北等地區(qū),要加強對中亞五國名義語言的學習和交流。
致謝:感謝本文責編李開拓老師提出寶貴修改意見及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教育學院王輝教授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