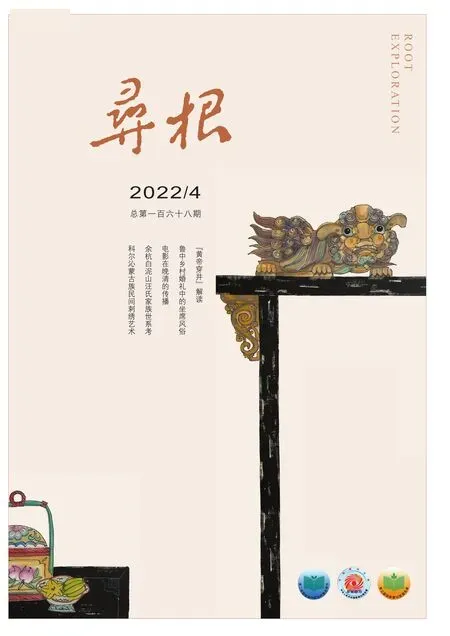金華磐安梓譽(yù)蔡氏宗族文化
□王 科
一
磐安蔡氏源于福建建陽(yáng)蔡氏。建陽(yáng)蔡氏在南宋以理學(xué)聞名天下,從蔡發(fā)開(kāi)始經(jīng)蔡元定、蔡淵,家族內(nèi)接連涌現(xiàn)九位大儒,世稱“蔡氏九儒”。其中蔡元定與朱熹相交四十余載,亦師亦友。在這一過(guò)程中,蔡元定協(xié)助朱熹治學(xué)、講道,對(duì)朱熹理學(xué)發(fā)展和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蔡氏家族因而被朱熹贈(zèng)“理學(xué)名宗”的牌匾。

◇蔡氏宗祠“理學(xué)名宗”牌匾
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因“慶元黨禁”案,朱熹被罷黜,蔡元定受到牽連被貶放湖南道州。為避禍,蔡元定的長(zhǎng)子蔡淵攜子蔡誥旅居浙江金華。后因蔡元定病逝,蔡淵回家奔喪,其子蔡誥留守金華。蔡氏最初定居在浙江金華磐安的顧嶺,第三世蔡炎遷居雙溪鄉(xiāng)安仁里。為讓子孫后代銘記“理學(xué)名宗”的榮譽(yù),遂從“桑梓譽(yù)重”一詞中摘取“梓譽(yù)”二字作為村名,并沿用至今,已有八百余年。由此可見(jiàn),“桑梓譽(yù)重”或“梓譽(yù)”代表了蔡氏先祖對(duì)“理學(xué)名宗”這一家族清譽(yù)的重視。“桑梓譽(yù)重”是梓譽(yù)蔡氏先祖對(duì)其后代子孫最為重要的教誨,構(gòu)成了這一家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傳承之一。
二
蔡氏宗族文化的主流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聲譽(yù)的重視,同時(shí)又要求淡泊名利,以坦然、淡然的態(tài)度對(duì)待毀譽(yù)問(wèn)題。
梓譽(yù)蔡氏先祖以其學(xué)識(shí)、言行奠定了“理學(xué)名宗”這一家族的榮譽(yù)。《梓譽(yù)蔡氏宗譜》歷代序言都在最為顯要的位置強(qiáng)調(diào)其祖蔡元定與朱熹之間不一般的關(guān)系,如譜序中載曰:“(蔡元定)雖在弟子(朱熹的學(xué)生)之列,文公(朱熹)以老友稱之。”朱熹與蔡元定經(jīng)常“通夕對(duì)床不寢,相與講論四十余年”。朱熹曾贊美蔡元定“人讀易書(shū)難,通(蔡元定,字季通)讀難書(shū)易”,稱其有“精詣之識(shí)、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蔡元定在朱熹理學(xué)中的地位不可替代。蔡、朱四十余年相與講論、共同著述使二人言說(shuō)早已合二為一、水乳交融。如《梓譽(yù)蔡氏宗譜》記載其事曰:“其平生問(wèn)學(xué)多寓于熹書(shū)集中。”他的獨(dú)著也多是朱熹為之寫(xiě)序。蔡元定的四個(gè)兒子皆為理學(xué)、易學(xué)大家。

◇蔡氏宗祠
“斷不負(fù)所學(xué),此心天可知。”蔡氏先祖用行動(dòng)踐行了理學(xué)人格,奠定了這個(gè)家族高風(fēng)亮節(jié)的聲譽(yù)。宋慶元元年(1195年),權(quán)臣韓胄專權(quán),朱熹理學(xué)被定為“偽學(xué)”。第二年,蔡元定受牽連以布衣之身被貶放湖南道州。在這場(chǎng)劫難中,蔡元定并沒(méi)有因此而感到辱沒(méi)了家風(fēng),敗壞了家族聲譽(yù),反而是一種坦然面對(duì)、淡然處之的態(tài)度。如被貶放途中,踐行者多感傷泣下,而蔡元定則無(wú)異于平常,泰然自若,并賦詩(shī)一首曰:“執(zhí)手笑相別,毋為兒女悲。輕醇?jí)研猩鰮u動(dòng)征衣。斷不負(fù)所學(xué),此心天可知。”
由此可見(jiàn),蔡氏家族所重之譽(yù)并非沽名釣譽(yù)的世俗之譽(yù)。前者以性理的“道德”為標(biāo)準(zhǔn),后者則以權(quán)勢(shì)、名利為標(biāo)準(zhǔn)。標(biāo)準(zhǔn)不同,其所重之譽(yù)的內(nèi)容也不相干。
蔡元定的后人恪守“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事故”的理學(xué)原則,以實(shí)際言行不斷維護(hù)理學(xué)世家的清譽(yù)。《梓譽(yù)蔡氏宗譜》將這些通過(guò)踐行理學(xué)原則、發(fā)揚(yáng)先祖精神來(lái)維護(hù)家族聲譽(yù)的人物都以傳記的形式予以記載。如《惟忠公傳》稱贊他“為人也溫恭謙讓,家道殷富,常懷忠正之心,矜孤恤寡、哀苦憐貧、施仁布德,每遇荒旱賑濟(jì)救急”。《澹寧號(hào)說(shuō)》贊頌自號(hào)“澹寧”的蔡炳文曰:“養(yǎng)心以廉,養(yǎng)智以約,好善不倦,處樂(lè)不淫,何其恬也。不為勢(shì)拘,不為威怵。欲不之動(dòng),利不之歆,何其靜也。居室則善,不競(jìng)不,敬直義方。”
綜上可知,梓譽(yù)蔡氏宗族對(duì)“譽(yù)重”的強(qiáng)調(diào),有著明確的價(jià)值導(dǎo)向,其所重之譽(yù)主要是對(duì)“理學(xué)名宗”學(xué)術(shù)聲望以及對(duì)先祖高風(fēng)亮節(jié)、恪守儒家道統(tǒng)原則之聲譽(yù)的重視與維護(hù)。因而,其所重之“譽(yù)”自然與世俗的沽名釣譽(yù)之“譽(yù)”、名利場(chǎng)上的聲色犬馬之“譽(yù)”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三
梓譽(yù)宗族的譽(yù)重文化是中國(guó)聲譽(yù)、信譽(yù)和名節(jié)文化的一個(gè)縮影。聲譽(yù)、信譽(yù)、名節(jié)文化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guó)聲譽(yù)文化對(duì)“譽(yù)”有兩種態(tài)度:一是重聲譽(yù)、美譽(yù),二是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毀譽(yù)要淡然處之。如何調(diào)處二者之間的矛盾一直是人們爭(zhēng)論不休的話題,也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一個(gè)問(wèn)題。
根據(jù)儒家思想,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在中國(guó)古代,君子是學(xué)習(xí)、弘揚(yáng)、踐行道學(xué)文化的人。他們的聲譽(yù)標(biāo)準(zhǔn)不以世俗為類。君子重“譽(yù)”以道德為內(nèi)核,以率性為要求,小人重“譽(yù)”以權(quán)勢(shì)為內(nèi)核,以名義為標(biāo)榜。所謂“君子以道德輕重人,小人以勢(shì)力輕重人”(《古今藥言·憧然錄》)。那么,君子所重之“譽(yù)”的這個(gè)道德內(nèi)核和率性要求究竟為何物呢?它與小人所重之“譽(yù)”之間最為深層的差別究竟是什么呢?為了回答這兩個(gè)問(wèn)題就要探討一下中國(guó)文化的道學(xué)文化。
儒家“道學(xué)”之名起于兩宋,其本意為堯舜、文武、周公和孔孟之道。如較早使用“道學(xué)”一詞的王開(kāi)祖(1035—1068)有言曰:“由孟子以來(lái),道學(xué)不明,我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極之門(mén)。”要言之,所謂“道學(xué)”就是以“性與天道”為對(duì)象的學(xué)說(shuō)體系。“性道之學(xué)”為其核心要義。《中庸》有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性”就是“天命”,所謂“道”就是率性,所謂“教”就是修率性之道。這就以簡(jiǎn)明的話語(yǔ)闡明了“天命、性、道、教”之間的關(guān)系,構(gòu)筑了道學(xué)的基本含義。
《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jiàn)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dú)也。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dá)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àn)物育焉。”這段話闡明了率性的這個(gè)“道”具有“不可離”以及“不睹不聞”的“隱微”特點(diǎn)。那么,這種既不可離而又隱微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dá)道也。”可見(jiàn),所謂的“率性之道”就是“中和”之道,而修道就是修“致中和”的功夫。用簡(jiǎn)單易懂的話來(lái)表述,這個(gè)“中”就是具有隱微特征的那個(gè)道體,她看不見(jiàn)、摸不著、聞不到(不睹不聞的隱微特性),但卻又遍滿虛空,充塞宇宙(因而不可離,因而君子要行戒懼慎獨(dú)之事)。“中”作為無(wú)處不在、無(wú)時(shí)不有而又不可見(jiàn)、不可聞的天下之大本大源究竟為何?
宋明理學(xué)家對(duì)此有經(jīng)典的解讀。程頤言“不偏之謂中”。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wú)過(guò)不及之名。”何為不偏?何為不倚?何為無(wú)過(guò)無(wú)不及?這究竟是一種什么狀態(tài)呢?大家都知道,萬(wàn)物無(wú)不有“對(duì)”。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有我就有人,等等。那么,“中”就是不偏于上也不偏于下、不偏于左也不偏于右、不偏于我也不偏于人的一種狀態(tài)。只有不偏才能包容一切,從而利于一切(既利于上也利于下等)。這樣才能見(jiàn)“道”。
上下、左右、人我無(wú)偏,因而利于一切,因而“道并行而不相悖,萬(wàn)物并育而不相害”,從而形成世間萬(wàn)物“各正性命”“各得其所”的狀態(tài)。
總而言之,道學(xué)是理解君子聲譽(yù)標(biāo)準(zhǔn)的根本依據(jù),構(gòu)成中國(guó)傳統(tǒng)聲譽(yù)、信譽(yù)、名節(jié)文化的內(nèi)核與靈魂。梓譽(yù)蔡氏“譽(yù)重”文化作為一個(gè)典型縮影則用生動(dòng)的實(shí)踐詮釋著中國(guó)傳統(tǒng)聲譽(yù)、名譽(yù)和名節(jié)文化的這一本質(zhì)特征。
四
“譽(yù)”不是為了“聲譽(yù)”而聲譽(yù),不是追名逐利式的沽名釣譽(yù)。對(duì)于這樣的“譽(yù)”,梓譽(yù)蔡氏的基本態(tài)度是極力摒棄的。他們甚至可以為了“理”,為了“道”而淡泊名利,甚至?xí)陨硌车馈?/p>
梓譽(yù)蔡氏“譽(yù)重”文化作為中華信譽(yù)文化的一個(gè)典型縮影,它啟示我們:君子所重之“譽(yù)”無(wú)他,就是對(duì)“理”、對(duì)“道”的拳拳服膺,內(nèi)修外踐,做“親民”的功業(yè)而自然獲得的一種榮耀。這種榮耀的“外顯”以“理”“道”為宗,而“理”“道”在心性上則以“誠(chéng)”為體,所謂“誠(chéng)者天之道也”。所以這種因踐行“道”而來(lái)的榮耀在本質(zhì)上就是“誠(chéng)”之外化。誠(chéng),即“坦誠(chéng)”,坦誠(chéng)意味著對(duì)一切敞開(kāi),接受一切、容納一切。這就沒(méi)有偽。無(wú)偽自然無(wú)偏。無(wú)偏而“中”,也就契入了“道”和“理”的境界。梓譽(yù)蔡氏“譽(yù)重”之“譽(yù)”就是通過(guò)體認(rèn)、傳播、踐行這種一覽無(wú)余的坦誠(chéng)之“道”、之“理”而自然獲得的一種榮耀。
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為基礎(chǔ)的高度分化的陌生人社會(huì)。
首先是市場(chǎng)的普遍化。市場(chǎng)的普遍化意味著一切皆可標(biāo)價(jià),生活就是生意。生意場(chǎng)就是名利場(chǎng),追名逐利、沽名釣譽(yù)滲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這樣一個(gè)高度名利場(chǎng)化的時(shí)代,人們的名譽(yù)之重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近乎利益化的趨勢(shì)。有的為了出名不惜一切代價(jià),不管令名、惡名,只要出名就是好名。那些已有“令名”而又害怕臭名遠(yuǎn)揚(yáng)者,為了保持聲譽(yù)也是極力包裝、兜售,各種遮丑,各種表演。
其次是在普遍市場(chǎng)化基礎(chǔ)上,人員流動(dòng)頻繁,宗族等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解體,社會(huì)高度分化,熟人社會(huì)不再。人與人之間或者是根本不相識(shí)的純粹陌生人,比如在網(wǎng)絡(luò)空間,我們根本不在乎購(gòu)買(mǎi)產(chǎn)品的客戶究竟是誰(shuí)。傳統(tǒng)社會(huì)以宗法、宗族為紐帶,以親朋鄰居為主體,其所依托的是相互之間的熟識(shí),大家知根知底,如若丟了信譽(yù)就會(huì)失去立足之地。而在現(xiàn)代陌生人社會(huì)之中,人們失去了傳統(tǒng)熟人之間的制約,丟棄信譽(yù)和臉面有時(shí)不僅不會(huì)影響生存,反而可能在短期內(nèi)因此獲益。
梓譽(yù)蔡氏“譽(yù)重”文化啟示我們,作為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譽(yù)”有其內(nèi)在的“根據(jù)”。這根據(jù)就是“道”或“理”,凡是違反“道”“理”的事情即使可以獲得一種影響力,一種“好名聲”也是決計(jì)不為的。其所求(也是一種淡泊名利的求而無(wú)求)之“譽(yù)”也必然是因尊道、循理而獲得的好名聲。因而,并非所有的“譽(yù)”都是值得提倡的。那種沽名釣譽(yù)、以信譽(yù)為名利的行為就與中華傳統(tǒng)聲譽(yù)、信譽(yù)文化的根本要求相背離。而要在“名利場(chǎng)化”、陌生人社會(huì)為背景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構(gòu)建起信譽(yù),其一是要以法治與外在信用體系的組合手段來(lái)對(duì)治陌生人之間天然缺乏信任和榮譽(yù)感的問(wèn)題。其二就是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采取教育、宣傳等立體化、系統(tǒng)化的傳播手段,利用現(xiàn)代人受教育程度高的優(yōu)勢(shì),將傳統(tǒng)信譽(yù)的精華熔鑄到現(xiàn)代人的思想之中,從而為信譽(yù)社會(huì)建設(shè)提供內(nèi)在精神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