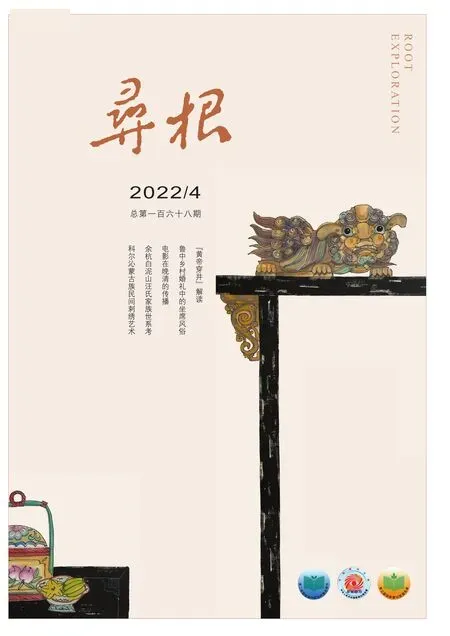繆鉞致胡厚宣一封信年代的考釋
□劉振剛

◇1980年10月,繆鉞(左)與胡厚宣合影
繆鉞(1 9 0 4—1995),字彥威,江蘇溧陽人,著名文學史家、歷史學家。胡厚宣(1911—1995),河北望都人,著名甲骨學家。二人有師生之誼。繆、胡二人之交往,起于胡厚宣的中學時代,止于兩先生逝世,前后70年。胡厚宣小學畢業后,考入保定培德中學。在培德中學,他遇到了國文老師繆鉞。繆先生在培德中學開國文、國學概論及中國文學史三門課程,又指導學生課外讀書,其間胡厚宣在國學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冰繭庵論學書札》收錄繆鉞致胡厚宣函十二通,對了解二人以及學術史有重要的價值。其中有一通,談及約稿和郵寄新作等事,錄之于下:
厚宣吾弟如晤:
手書奉悉。本期《匯刊》稿件大部集齊,即籌備付印,聞在宥先生極愿得吾弟論文以光篇幅,已專函奉懇。惟有一事,須告弟者,金大研究所來函言,此次編印《匯刊》,哈佛燕京社取消齊大經費,弟諒已聞之。惟數年以來,齊魯與金陵、華西諸研究所密切合作,而《匯刊》中亦屢載吾弟之文。此次編印,無論齊大是否出經費,此間仍以能刊載弟文為光寵。弟近在京、滬、濟南見到大批甲骨,整理研究定有新著,極希惠賜一二,能于二月十五日以前航寄到蓉,尤所感盼。專此,即頌。
冬祺
鉞拜上 一月十日
原信未署年。整理者認為:“此札無法確定具體年份,約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其說誠是。筆者認為,從內容判斷,這應該是1947年的信。
胡厚宣北京大學畢業后,入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0年,胡厚宣聘轉在成都的齊魯大學,先后出任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和中文系、歷史社會系兩系主任。胡厚宣入職齊魯大學,因“顧先生告,齊魯大學有明義士所藏甲骨需要整理,故約我同往”。明義士是加拿大人,酷愛甲骨文收藏與研究。1933年,明義士到齊魯大學教書,他的藏品一部分運抵濟南。抗戰全面爆發前,明義士返回加拿大,來不及帶走的甲骨裝箱封存在齊魯大學。抗戰全面爆發后,齊魯大學停課,除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設備遷往成都華西壩辦學。1942年,日軍占領濟南齊魯大學,明義士的朋友們將甲骨藏了起來。抗戰期間,繆鉞所謂“弟近在京、滬、濟南見到大批甲骨”乃不可能的事。胡厚宣赴京、滬、濟南見到大批甲骨必在抗戰勝利后,詳后文論述。“一月十日”所系年代不得早于1946年。
信中所言的《匯刊》即《中國文化研究匯刊》,1941年創刊于成都,年刊,由當時在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該刊每年9月出版,至1951年,共出10卷,在當時頗有名氣。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受哈佛燕京學社津貼資助。1945年8月,吳克明就任齊魯大學校長,企圖加強國學研究所的力量,遭到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綏夫的強烈反對。葉綏夫要求廢除國學研究所,節省經費,加強本科教學。葉綏夫在12月9日致董事會的信中,提出哈佛燕京學社旨在“造就一個專修水準有力的中文系”,而“不是來幫助學者的研究計劃”。1945年葉綏夫威脅若下學期不改進,就不給齊魯大學撥款。其實撥款一直未停止,齊魯大學的國學教學人員一直受到資助。1945年齊魯大學尚參加《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的編輯。1946年齊魯大學名義上取消了國學研究所。同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六卷編輯者為金陵、華西兩大學,齊魯大學退出了。齊魯大學不在《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編印方面出資不能早于1946年。
1946年秋,胡厚宣才返回濟南齊魯大學校本部(詳見后文所引材料)。1946年初,胡厚宣還在成都。繆鉞當時在遵義的浙江大學,不可能讓胡厚宣把新著“極希惠賜一二,能于二月十五日以前航寄到蓉”。1945年秋,胡厚宣在40多天的時間里,搜集了一些平津甲骨,并沒有到達濟南。回到成都后,胡厚宣舉辦了展覽會。繆鉞母親1946年秋一度寄居胡厚宣家中,二人關系很深。胡厚宣1945年秋沒有去成濟南,繆鉞必定耳聞。1946年年初,繆鉞信中不可能說“弟近在京、滬、濟南見到大批甲骨”。
1938年10月,繆鉞應聘為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41年升教授,先在宜山,后遷遵義。抗戰勝利后,1946年浙大復員,因浙江物價昂貴,繆鉞未能隨浙江大學返杭州,“遂向浙大請假一年,應華西大學和四川大學兩校之聘,于1946年8月來到成都”。繆鉞于1946年8月任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同時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前已說明,此信晚于1946年。繆鉞作為《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的主辦方約稿,不能早于1947年。
任何一個人在寫作時都可能有修改。辛德勇曾提及史念海先生,“親見先生致人信函,通常都要先平心靜氣,略加思索,打好腹稿,始動筆寫字,而所書字跡,則盡可能排滿頁面,使之布局妥帖,以求美觀”。前輩學者信函精心結構可見一斑。繆鉞工為文章,以為自己行文“能夠免去繁冗蕪雜之弊”。他對寫作很有一套看法,晚年嘗言其行文原則“即是簡明清暢”。《冰繭庵論學書札》有的信就是源自原信底稿。既然有底稿,則寄出去的信就是另抄寫的。繆鉞對書信行文很重視。我們討論的這封信是“原件掃描件,由胡振宇先生提供”。胡振宇是胡厚宣之子,故此信必為繆鉞寄出的定稿無疑。既然此信是其定稿,必然遣詞造句十分精確。若胡厚宣此刻離開了齊魯大學,繆鉞沒必要在信中談及“此次編印,無論齊大是否出經費,此間仍以能刊載弟文為光寵”事。是則胡氏此刻還在齊魯大學工作。繆鉞信中謂“此次編印《匯刊》,哈佛燕京社取消齊大經費,弟諒已聞之”。斟酌其行文語氣,胡厚宣此時應該是齊魯大學的人,故能知曉“哈佛燕京社取消齊大經費”。繆鉞信中兩次說到齊魯大學的經費問題,并非無關宏旨的陪襯之言。
胡厚宣說:“1947年初在滬,我去暨南大學訪老友丁山及陳述兩教授,他們約我同去復旦大學看望周谷城,周先生那時主持歷史地理系,同我初次見面,相談甚歡。他同丁、陳兩位說:‘咱們留下他好不好?’于是他找文學院院長伍蠡甫,又找校長章益,三言兩語,就把我留下了。”《中國文化研究匯刊》主要刊登上述四研究所專任人員的作品,不收外稿。則繆鉞此信不應該晚于1947年。
據“弟近在京、滬、濟南見到大批甲骨”,則繆鉞寫信時距胡厚宣看到這批甲骨的時間很近。胡厚宣后來回憶他在抗戰勝利后兩次搜集甲骨說: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我馬上從成都到重慶,想去濟南齊魯大學原校部,探訪明義士的這批甲骨。在重慶遇到史語所傅斯年所長,他說去濟南我替你想辦法,山東省主席何思源現在重慶,你可以搭他的專機去,我想了想:濟南戰事正累,我乘何主席的專機去,他能用專機送我回來嗎?最后我還是與袁同禮先生同機飛回北平。抵平后,袁先生是接收北平圖書館,我還得設法去濟南,但火車、飛機什么交通工具都沒有,想回老家望都探望一下也不可能。聽說在淪陷期間,安陽出了很多甲骨,流傳在寧、滬、平、津,我決定就用獲獎的這筆錢,乘機搜集下平津流散的甲骨。這一停留,前后四十余天,竟也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我遍訪北平琉璃廠、前門、東四、西單及天津天祥商場和文廟一帶的古書鋪、古玩鋪、碑帖鋪和舊貨攤,凡戰后新出或未經著錄的甲骨,無論實物、拓本,有見必收。一些公私藏珍,亦多方設法借拓鉤摹,計得甲骨二千片,拓本六千張,摹寫二千幅,共約萬片而強。
…………
1946年秋,我隨齊魯大學回到濟南,得悉明義士甲骨還留在學校,由醫學院外籍院長杜儒德代管。杜氏答應我函詢明氏,待有回信,便可參觀。因內戰爆發,濟南被圍,城外炮響,局勢難測,加上我的書籍材料都不能帶去,工作無法展開。在濟南住了兩個月,寒假我回南京取書,飛機突然停航,從南京來上海,打算坐船去青島,膠濟線亦中斷,我被陷停在滬上,夙愿只得放棄。于是又乘此時機于寧、滬一帶探訪甲骨,也有收獲。先于昭通路禹貢古玩行收到一批,計六七百片,又在中國古玩社買到一二百片,此外于商肆、藏家零零碎碎收到些,共計一千而強。
據胡厚宣的說法,1945年秋,他搜集到平津的一些甲骨;他在1945年秋和1946年秋沒有看到濟南齊魯大學的甲骨。胡厚宣的兒子胡振綏說:“直到解放后,父親才在各博物館(包括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又見到了明義士留下的那批藏品……”1946年冬,胡厚宣在上海搜集到一些甲骨。這與信中的“一月十日”結合判斷,繆鉞寫信時應該為1947年1月。從時間上看,1947年1月正合1946年秋冬的“近”。且1947年年初到1951年胡厚宣供職復旦大學。胡、繆兩人私交甚善,信中暢所欲言,應該早已告知繆鉞他換了單位。若在1948年1月到1951年1月之間寫信,繆鉞沒有必要在約稿時把他看作齊魯大學的人了。
總之,繆鉞這封信的寫作年代,應該是民國36年(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