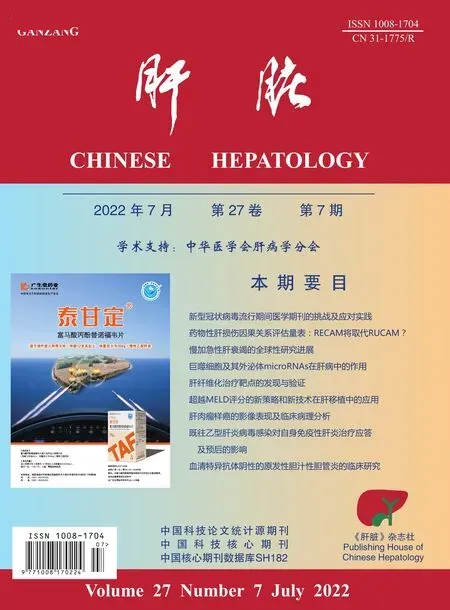既往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對自身免疫性肝炎治療應答及預后的影響
蘇雨 孫小怡 王倩怡 趙新顏 賈繼東
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是一種病因不明的肝臟慢性炎性疾病,常見于中年女性患者[1],典型的實驗室特點為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ic aminotransferase, AST)、免疫球蛋白(IgG)升高和自身抗體陽性[2]。肝穿刺組織活檢可見界面炎、匯管區淋巴-漿細胞浸潤及玫瑰花結[3]。肝穿刺病理活檢對于AIH的明確診斷至關重要,主要依據簡化評分系統和描述性診斷積分系統對AIH患者進行評估[4-5]。所有活動性AIH患者均推薦接受標準的免疫抑制治療,以獲得并維持肝臟組織學緩解,避免疾病進展,影響遠期生存[6]。據報道,接受免疫抑制治療的患者10年和20年累積生存率分別為91%和70%[7-8]。
已有研究表明,基線時出現肝硬化、膽汁淤積、鐵蛋白升高和維生素D缺乏是阻礙AIH患者實現完全生化應答的因素[9-11]。中國是HBV感染的高發區域。據報道,在中國加權后的HBV核心抗體(Anti-Hepatitis B Core Antigen, 抗-HBc)陽性率為34.1%[12],總人群中約1/3為既往HBV感染的患者。在我們的臨床實踐中,發現部分AIH患者合并既往HBV感染,在免疫抑制治療過程中,既往HBV感染是對AIH患者的生化應答及預后的影響仍待驗證。因此,本研究通過回顧性隊列研究探索既往HBV感染對AIH治療應答及預后的影響。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入排標準
研究對象為2002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確診的AIH患者。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②AIH簡化表評分≥6分和/或AIH描述性診斷評分系統≥10分[4-5];③接受糖皮質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治療;④完善HBV五項檢查。排除標準:①合并嗜肝病毒性肝炎(如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肝炎)和非嗜肝病毒性肝炎(如巨細胞病毒、EB病毒感染等);②合并藥物性肝損傷、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酒精性肝病、遺傳代謝性肝病等;③有骨髓或者肝移植病史;④基線和隨訪資料缺失嚴重。
二、資料收集
(一)基線資料收集 通過檢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病歷系統,收集患者的基線資料,包括:①性別、年齡、既往史、家族史和用藥史等;②血清學指標(血常規、肝臟生化、凝血功能、免疫球蛋白和補體、自身抗體和HBV五項);③影像學檢查結果(肝臟硬度、腹部超聲、CT和MRI)、胃腸鏡檢查和肝臟病理資料,以及④治療方案。
既往HBV感染定義為:乙型肝炎核心抗體陽性(抗-HBc>1 S/CO)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陰性(HBsAg<0.05 mIU/mL)[13]。
(二)隨訪 通過檢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病歷系統,對患者的實驗室檢查和臨床結局等進行隨訪。完全生化應答定義為:ALT≤40 U/L、AST≤40 U/L及IgG≤1600 mg/dL[14]。肝臟相關終點事件包括:肝癌、肝移植和肝臟相關死亡。
三、數據統計及分析
所有數據資料均使用SPSS 25.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計數資料用例數(百分比)表示。連續變量比較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用χ2檢驗;線性回歸模型或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和COX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既往HBV感染和無既往HBV感染患者基線特點比較
2002年1月—2020年12月期間診斷為AIH患者共207例,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共納入114例AIH患者(圖1)

NAF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ALD:酒精性脂肪性肝病;DILI:藥物性肝損傷
114例患者中,101例(88.6%)為女性患者,年齡56.0(51.0, 62.0)歲。40例患者抗-HBc陽性(既往HBV感染組),其中36例(90.0%)為女性患者,年齡58.0(54.0, 64.5)歲;74例患者抗-HBc陰性(無既往HBV感染組),其中65例(87.8%)為女性患者,年齡57.0(43.0, 62.5)歲。兩組患者的性別比例及年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729,P=0.222)。
既往HBV感染患者的ALT、AST顯著低于無既往HBV感染患者(中位數:99.5 vs. 178.0,P=0.046; 137.2 vs. 161.0,P=0.049),其余生化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血清學方面:既往HBV感染組患者的IgG、抗核抗體陽性率較無既往HBV感染患者更高,抗平滑肌抗體陽性率較無既往HBV感染組更低,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既往HBV感染組患者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陽性率顯著高于無既往HBV感染組患者(35.7% vs. 4.8%,P=0.028)。與無既往HBV感染的患者相比,既往HBV感染組患者肝硬化的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88,見表1)。

表1 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臨床特點比較
在114例患者中,共82例患者行肝臟穿刺活檢,其中既往HBV感染組28人,無既往HBV感染組54人。兩組患者在匯管區炎癥和界面炎方面表現類似(中位數:2.0 vs. 2.0,P=0.241; 2.0 vs. 2.0,P=0.675)。既往HBV感染組患者的點灶狀壞死及纖維化較無既往HBV感染患者嚴重(中位數:3.0 vs. 2.0; 4.0 vs. 3.0),HAI評分高(中位數:16.0 vs. 15.0),融合壞死相對較輕(中位數:4.0 vs. 5.0)。兩組患者的病理表現差異無統計學(表2)。

表2 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病理特點比較(Ishak分期分級系統)[15]
二、既往HBV感染對AIH生化應答的影響
與無既往HBV感染的患者相比,既往HBV感染組患者在治療后的3、6、12和24個月時生化應答率更低,整體生化應答時間更長,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3)。

表3 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生化應答率的比較
經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既往HBV感染不會影響AIH患者的生化應答(OR=1.06, 95%CI: 0.03~1.21,P=0.106)。而球蛋白(OR=1.06, 95%CI: 1.01-1.11,P=0.03)及3個月IgG復常(OR=3.75, 95%CI: 1.22~11.49,P=0.021)是免疫抑制治療12個月時實現生化應答的獨立預測因素(見表4)。

表4 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治療12個月生化應答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三、既往HBV感染對AIH預后的影響
共10例患者出現終點事件,既往HBV感染組患者5例(原發性肝癌:1;死亡:3;肝移植:1),無既往HBV感染組患者5例(原發性肝癌:1;肝移植:2;死亡:2)。兩組在終點事件發生率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5% vs. 8.1%,P=0.670)。
經COX生存分析發現,既往HBV感染與AIH患者預后無關(HR=1.68, 95%CI: 0.42-6.75,P=0.463)。肝臟硬度(HR=1.06, 95%CI: 1.00-1.12,P=0.045)及失代償期肝硬化(HR=7.54, 95%CI: 1.27-44.72,P=0.026)是AIH患者預后不佳的獨立危險因素(表5、圖2)。

表5 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COX生存分析

A 既往HBV感染與AIH患者預后的K-M生存曲線:兩組患者的生存率無統計學差異。B 失代償期肝硬化與AIH患者預后的K-M生存曲線:失代償期肝硬化的AIH患者生存率明顯降低
討 論
在我們的隊列中,共40例(35.1%)既往HBV感染患者,與全國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大體一致(抗-HBc的加權患病率為34.1%)[16-17]。通過比較兩組患者的生化應答率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既往HBV感染并未影響AIH患者的生化應答。
免疫抑制治療3個月時的IgG復常是治療1年時完全生化應答的獨立預測因素。Ma等[18]在一項705例患者的隊列研究中發現,實現生化應答的患者在治療3個月時的IgG水平更低,對免疫抑制治療的早期應答是完全生化應答的可靠預測因素。Pape等[19]在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中發現,AIH患者在治療8周后的AST復常與治療1年后的轉氨酶復常相關。這與我們的研究結論類似。因此,當AIH患者在隨訪早期出現應答不佳時應考慮及時調整治療方案,以盡早實現生化應答。
本研究共10例患者出現終點事件,既往HBV感染患者的終點事件發生率更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5% vs. 8.1%,P=0.670)。經COX生存分析證實,既往HBV感染不會影響AIH患者的預后。Chen等[20]在一項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的隊列研究中發現,既往HBV感染不會影響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患者的預后。因此這也提醒臨床醫師,既往HBV感染不應該是阻礙AIH患者接受免疫抑制治療的因素,對于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也應及時啟動免疫抑制治療,以獲得與AIH患者相似的生化應答及預后。
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在應用免疫抑制劑后,可能造成HBV再激活(HBV reactivation,HBVr)[21]。但根據APASL發布的關于免疫抑制治療相關乙型肝炎再激活的臨床實踐指南[22],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為HBVr的低危患者。此外,從臨床指標及數據分析方面表明,有/無既往HBV感染的AIH患者生化應答率和預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既往HBV感染不會影響AIH患者的生化應答和預后。
本研究共納入114例接受免疫抑制治療且隨訪[4]資料相對齊全的AIH患者,是一項隨訪時間較長的隊列研究。目前尚未有研究報道既往HBV感染與AIH患者治療應答及預后的相關性。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因基線及隨訪資料不全而排除的患者占22.5%,發生終點事件的患者數少 [10例(8.8%)],在探究終點事件的危險/保護因素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這也反映了開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