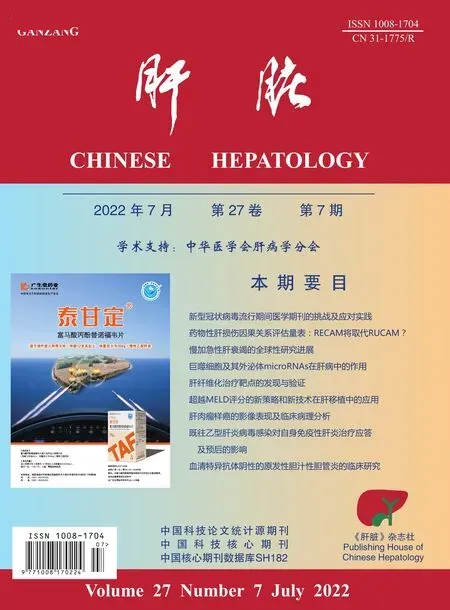肝纖維化治療靶點的發現與驗證
沈鎮揚 陸倫根
各種病因引起的慢性肝損傷已造成全球健康負擔,每年導致近200萬人死亡[1]。肝纖維化作為慢性肝損傷期間所觸發的一系列傷口愈合表現,其特點是細胞外基質(ECM)的廣泛積累,從而破壞了正常的肝臟結構[2]。未經任何治療的慢性肝損傷和ECM過度積累可能導致肝臟瘢痕形成,并最終發展為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3]。經過數十年基礎、轉化和臨床研究的發展,人們已經對肝纖維化的發病機制以及其對終末期肝病的影響有了很多的認識。但是迄今為止,由于缺乏精確的治療靶點和良好的靶點驗證方法,成功治療肝纖維化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困難,且尚未有抗肝纖維化藥物得到批準。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更多準確可靠的治療靶點以及靶點驗證方法,以期獲得更好的臨床轉化價值。
一、抗肝纖維化靶點的發現
(一)基于分子的已知功能識別靶點 作為目前最經典的靶點識別方法,其根據已知分子的生物學功能以及其拮抗或激動劑來確定該分子是否影響肝纖維化的發生。為了識別潛在的肝纖維化相關分子,需要對公共數據庫以及從動物和人體組織、細胞中提取的潛在靶標基因和蛋白數據集進行全面而細致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流行的單細胞測序分析能夠構建纖維化肝臟全面而詳細的細胞異質性圖譜,闡明不同肝臟疾病中肝星狀細胞(HSCs)的亞型分類,這對我們確定肝纖維化候選靶點的有效性以及減少肝臟靶向治療過程中出現的意外脫靶效應具有重大意義[4-6]。此外,這些龐大而復雜的數據集還需要強大的生物信息學技術來提煉相關信息,以便根據其表達、定位以及特定生物學功能偏好快速識別潛在靶點。
(二)新興的高通量靶點篩選 除了上述提及的“假設驅動”方法,還有不假設分子在肝纖維化中作用的靶點篩選方法。這種方法主要通過應用特定的基因干擾操作,如CRISPR篩選,以確定其能否抑制HSCs活化所需的關鍵通路或介質。盡管該方法主要用于揭示癌癥靶點,但也可用于探索體內和分離細胞的纖維化相關靶點[7-8]。此外,通過整合空間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以及轉座酶及染色質測序(ATAC-seq)等技術可以進一步無偏倚地發現潛在靶點。這些技術還可通過機器學習方法進一步加強,以細化靶點識別和驗證,并提高臨床成功的可能性[9]。
(三)現有藥物的再利用 藥物再利用已在許多疾病中得到驗證,通過對現有藥物的可能作用機制進行預測,篩選出一批現有藥物,并觀察它們在體外實驗中逆轉疾病基因特征的能力,從而確定具有潛在有效,但初始適應證與肝纖維化無關的候選藥物[10]。例如,索拉非尼是一種酪氨酸激酶受體抑制劑,可阻斷腫瘤細胞中生長因子信號傳導,其也被證實可能通過限制肝損傷誘導的基質和血管生成來改善肝纖維化[11]。
(四)特定基因變異與疾病的關聯研究 潛在的靶點可能出現在無偏倚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這些研究將特定的基因變異與疾病聯系起來。例如,含Patatin樣磷脂酶域蛋白3(PNPLA3)基因的多態性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病風險相關,該基因不僅影響肝細胞脂質代謝,還能起到增強HSCs活化的作用[12]。由于基因組變異通常在以前未知的基因中發現,這些方法可揭示該變異的生物學途徑。通過增加保護性變異或拮抗致病變異,得到這種類型基因組信息演變而來的治療方法。例如,先前研究發現,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9(PCSK9)基因的一種變體能夠預防冠狀動脈疾病,后續在治療上通過拮抗PCSK9發揮降脂作用也取得了較大成功[13]。同樣,通過改變PNPLA3的功能,也可以作為基于疾病相關變體的NASH治療策略。
(五)抗纖維化靶點的重要特征 盡管目前在活化的HSCs上表達的纖維化靶點沒有單一的理想特征,但應具備以下一些重要特征:(1)目標易于接近。除了直接作用于細胞表面受體,將細胞內有效成分傳遞至HSCs的方法也在不斷發展。例如,維生素A偶聯脂質體傳遞系統可以實現向HSCs內傳遞小干擾RNA(siRNA)的功能[14]。(2)靶點的抑制或改變不影響正常HSCs和肝功能。比較有前景的策略是靶向那些僅在活化的HSCs上表達的分子,從而最大限度減少對正常HSCs穩態功能的影響。例如,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β(β-PDGF)受體在肝臟損傷過程中被顯著誘導且僅在活化的HSCs上表達[15]。(3)靶點在受損肝臟中表達最強或選擇性最強。盡管沒有HSCs絕對特異的靶點,但仍可通過查詢基因表達數據集來確定候選靶點在正常肝臟和其他組織中的表達水平,從而將脫靶效應降到最低。
二、抗肝纖維化靶點的驗證
(一)抗肝纖維化靶點的驗證模型 在進行臨床試驗之前,抗肝纖維化靶點的驗證一般要經歷從細胞、嚙齒動物到非人靈長類動物,從簡單的系統到復雜的系統驗證的過程。對于旨在減弱HSCs活化的分子而言,若其在體外的表達與體內表達相似,那么嚙齒動物和人的原代、永生化HSCs都是強大的前期驗證工具。最近,多能干細胞誘導生成的HSCs提供了對細胞內特定遺傳背景的認識,可能有助于對肝纖維化發病風險和發病機制的了解[16]。為了更好地模擬人肝纖維化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特性,用于檢測靶點效果的模型也得到了改善和擴充,包括運用單細胞或多細胞類器官[17],從正常或患病的嚙齒動物和人的肝臟上精確切取的肝臟切片[18],以及使用人工肝裝置系統復制人肝中所需的各種要素[19]。此外,這些技術可通過3D打印獲得更進一步的優化[20]。
(二)驗證模型的重要特征 任何抗肝纖維化靶點驗證的模型都應具備以下關鍵要素:(1)纖維化模型的行為和發病機制應與人體相似。(2)候選治療靶點應在模型和人的相同類型細胞表達且表達水平接近。(3)療效應在多個模型中進行驗證。(4)應在疾病確定后驗證療效,而不是單純預防。(5)藥理學作用應當在模型與人體中相似。(6)應有明確靶點參與的證據,藥物作用應直接歸因于與其預期靶點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脫靶作用。
(三)驗證模型的局限性 盡管幾十年來嚙齒動物肝纖維化模型一直是藥物靶點驗證的主流,但它們與人體藥物療效的相關性相差甚遠。雖然基于動物研究的許多藥物有較好前景,目前還沒有一種藥物被批準用于肝纖維化的臨床治療。因此,我們需要對驗證模型的局限性有更多關注:(1)微生物組的潛在貢獻。人和動物模型的微生物組之間的區別可能影響藥物療效,使用與人體微生物組接近的動物模型或許能更準確地預測后續人體試驗的結果。(2)動物模型患病時間短。人類肝病經過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演變,引起ECM逐漸交聯且極難降解,最后導致肝臟結構扭曲。然而,在驗證抗肝纖維化藥物的嚙齒動物模型中,這些關鍵特征可能無法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全復制。(3)疾病可能由多個分子或通路驅動,僅針對單一分子或通路較難達到預期。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NASH肝纖維化的發生受到復雜的基因表達網絡調控[6],這意味著可能需要影響多個通路才能獲得治療效益。(4)肝纖維化可能具有不同亞型。例如,NASH可能由不同亞型組成,而不同的亞型具有不同的疾病驅動因素,因此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治療靶點[21]。
三、總結及展望
利用強大的新技術來識別、優化治療靶點,探索生物標志物,通過對臨床試驗中患者的肝臟樣本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確定哪些靶點和標記物能使治療獲益。這樣不僅能更好發現療效相關的分子驅動因素,還能識別出肝纖維化相關的候選生物標志物。在改進當前動物模型的基礎上,輔以更復雜的類器官和其他先進的體外模型,能更好地預測靶點在人體中的療效。結合數據驅動原理,多靶點聯合的抗纖維化治療也應得到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