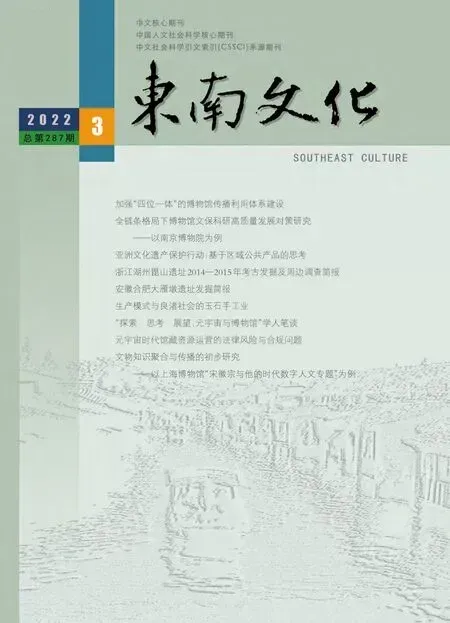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及相關問題
李 娜丁 品
(1.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 陜西西安 710127;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內容提要:環太湖地區的側扁足鼎最早出現于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期一度在環太湖核心區消失,后又在本地傳承和錢塘江流域因素的影響下,于良渚文化晚期重新出現并逐漸流行。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發展過程經歷了數量逐漸增加的“量變”和最終取代T形足鼎的“質變”兩個階段。從文化面貌看,“質變”后形成的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一類新遺存應該屬于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
一、前言
側扁足鼎指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一種側裝扁足陶鼎,鼎足截面呈扁圓形或扁方形,素面居多,少量單側面或兩側面有豎向刻劃紋。也有研究者稱之為扁側足鼎、素面魚鰭形足鼎、素面翅形足鼎、扁方足鼎或扁鏟足鼎等。
環太湖地區的側扁足鼎在21世紀前鮮有學者關注。浙江蕭山茅草山遺址(2000年)的發掘者較早注意到了側扁足鼎,并在2003年的簡報中首次提出該遺址中以“扁圓形足鼎”(即側扁足鼎)為代表的晚期遺存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在年代上應介于良渚文化與歷史時期文化之間[1]。幾乎與此同時,浙江余杭文家山遺址(2000—2001年)也在疊壓住良渚文化晚期墓地的第二層堆積中出土了大量的側扁足(鼎)[2]。稍后,隨著上海松江廣富林(2001—2005年)[3],浙江余杭卞家山(2003—2005年)[4]、余杭三畝里(2004年)[5]、諸暨尖山灣(2005年)[6]等遺址的先后發掘,側扁足鼎開始引起相關研究者的關注。而在文家山、三畝里等遺址的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遺存中還發現了少量弧背魚鰭形鼎足,這又讓研究者多了一些疑惑。
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2005年、2008年)[7]的兩次發掘在環太湖地區新確立了一支以弧背魚鰭形足鼎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錢山漾文化(以錢山漾一期遺存為代表)。它的相對年代介于良渚文化與廣富林文化之間,這為探討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提供了重要的比較資料。而余杭良渚古城(2006—2007年)[8]特別是對四面古城墻及內外壕溝的發掘中[9]都發現有側扁足鼎,而且其數量由早到晚逐漸增加,到上部堆積時,側扁足鼎完全取代了T形足鼎。這表明側扁足鼎在探究良渚古城遺址的使用及廢棄過程中也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目前關于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晚期和錢山漾文化之間還存在一個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發展階段,已初步形成共識。但對這個發展階段的性質和歸屬則仍有分歧,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它是良渚文化的延續,屬于“良渚文化末期遺存”[10]或“良渚文化晚期后段”[11];另一種認為應歸入錢山漾文化或明確指出應屬于錢山漾文化早期[12]。
鑒于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在探討良渚古城廢棄過程、良渚文化衰亡和錢山漾文化內涵及分期等重要學術課題中占據關鍵地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進行系統梳理,把握其演變發展脈絡和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節點。在此基礎上,再來探討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新遺存的內涵和性質,以期對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二、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溯源
(一)崧澤文化晚期的側扁足鼎
從現有資料看,至遲到崧澤文化晚期[13],環太湖核心區已經出現少量與良渚文化晚期[14]側扁足鼎形制相近的陶鼎,質地多為夾砂紅陶,偶有粗泥陶,足兩側均為素面。
據初步統計,此階段共發現29件基本完整的側扁足鼎,依形態特征可分盆形(A型)、罐形(B型)兩大類。A型又可分為束頸深弧腹(Aa型)(圖一︰1—4)、無頸淺腹(Ab型)(圖一︰5—8)和無頸深弧腹(Ac型)(圖一︰9—11)三個亞型。盆形鼎(A型)居多,足大多較寬,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的浙江湖州地區(安吉芝里[15]、湖州毘山[16]、安吉安樂[17]、長興紅衛橋[18])、杭州地區(良渚石馬兜[19]、良渚官井頭[20])和太湖東南的浙江嘉興地區(海寧小兜里[21]、嘉興南河浜[22])。罐形鼎(B型)足較窄高,截面扁圓,有的接近圓錐足,主要見于太湖西北的江蘇常州新崗遺址(圖一︰12—14)[23]、江陰南樓遺址[24]。

圖一//崧澤文化晚期側扁足鼎
可以看到,崧澤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常見形制已基本確立,主要有盆形和罐形兩大類。此外,后來成為良渚文化典型炊器的魚鰭形足鼎也大約同時出現。
(二)良渚文化早中期的側扁足鼎
到良渚文化早期,側扁足鼎的數量已經明顯減少。經初步統計,此階段僅發現5件基本完整器,零星散布在環太湖各區。依形態也可分盆形(Aa型)(圖二︰1—4)、罐形(B型)(圖二︰5)兩大類(型的劃分與崧澤文化晚期一致,下同)。盆形鼎略多,總體形態與崧澤文化晚期比較接近,腹部略變淺,鼎足變瘦,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地區(余杭后頭山[25])、太湖東南的嘉興地區(海寧達澤廟[26])、太湖以東的蘇滬地區(上海青浦金山墳[27])和寧紹平原(余姚鯔山[28])。罐形鼎的總體形態比崧澤晚期要寬矮,鼎足更扁平,見于太湖東南的嘉興地區(海鹽仙壇廟[29])。

圖二//良渚文化早期側扁足鼎
到良渚文化中期,目前僅在良渚文化外延區的錢塘江流域(詳見第四節)發現有側扁足鼎;而在環太湖核心地區,無論是在生活堆積中,還是在數量眾多的良渚文化中期墓葬中都不見側扁足鼎。據此初步判斷,在環太湖核心地區,良渚文化中期側扁足鼎應該已基本消失或僅偶見,側扁足鼎可能被排擠或禁用,這可能與良渚文化中期的墓葬禮儀制度得到嚴格執行有關。

1.父戊爵(金寨0023)

2.父戊爵局部(金寨0023)

3.獸面紋尊(金寨0025)

4.父乙斝(金寨0026)
三、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與流行
(一)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與流行
歷經中期沉寂,到良渚文化晚期,環太湖核心區的側扁足鼎突然重現,并逐漸流行起來。
經初步統計,此階段共發現15件基本完整的側扁足鼎,以夾砂紅陶為主,還有少量夾砂黑陶。依形態也可分盆形(Aa型)(圖三︰1—3)和罐形(B型)(圖三︰4—7)兩大類。其中以盆形鼎居多,總體形態與良渚文化早期接近,口沿加寬,部分顯領。出土地點包括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良渚古城葡萄畈[30]、良渚古城美人地[31]、良渚卞家山)和太湖東南的嘉興地區(桐鄉新地里[32]、海寧金石墩[33]、海寧蓮花[34])和太湖以東的蘇滬地區(上海馬橋[35])。罐形鼎(B型)相較于良渚文化早期,口部變小,沿面加寬,部分顯領。出土地點有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良渚卞家山、蕭山茅草山)、太湖東南的嘉興地區(桐鄉叭喇浜[36])和太湖以東的蘇滬地區(上海金山亭林[37])。

圖三//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
除上述完整器出土地點外,環太湖核心區出土側扁足鼎的良渚文化晚期遺址還有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的良渚古城四面城墻解剖的北城墻(TG2⑦—?層)、火溪塘城門(⑤層)、東城墻(G6③—⑤層)、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老虎嶺、鐘家港南段和中段、里山、姜家山[38]、反山[39]、姚家墩、沈家頭、朱村墳、嚴家橋[40]、廟前、馬家墳、茅庵里[41]和吉如[42];太湖東南的桐鄉大園里[43]和太湖西北的常州寺墩[44]等;屬于良渚文化外延區的寧紹平原出土側扁足的遺址有寧波慈湖[45]、寧波魚山[46]、北侖沙溪[47]、象山塔山[48]和奉化下王渡[49]等。
經統計,發現側扁足(鼎)的遺址共計36處(圖四),基本遍布整個環太湖地區。其中,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有19處,分布最為集中,嘉興地區次之。

圖四// 出土側扁足(鼎)的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分布圖
(二)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時間與流行過程
1.生活堆積
桐鄉新地里遺址是嘉興地區出土側扁足(鼎)數量較多的地點。從分期看,出土側扁足鼎的最早單位是歸入新地里第四段的H7,共出土各類鼎足33件,其中側扁足僅1件;歸入新地里第五段的G1②,共出土各類鼎足147件,其中側扁足僅2件;歸入新地里第六段的H1,共出土各類鼎足117件,其中側扁足10件,還有1件側扁足鼎(H1︰30)相對完整。
在良渚卞家山遺址,被發掘者推定為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階段的G1①中僅出土有少量的側扁足,到屬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晚階段的河埠頭和碼頭堆積中,側扁足數量明顯增多。
相似地,良渚古城西城墻葡萄畈段外壕溝的⑦—⑨層被發掘者認為屬于“良渚文化晚期前段”,其中側扁鼎足的數量從⑨層到⑦層逐漸增多,及至與T形足旗鼓相當。
2.墓葬材料
目前已發表的以側扁足鼎作為隨葬品的良渚文化晚期墓例僅有5座,分別為桐鄉叭喇浜M8、桐鄉新地里M122、海寧金石墩M13、海寧蓮花M1和金山亭林M6(圖五)。對照新地里分期標準,這些墓葬大致約當新地里第四至五段(亭林M6的年代不甚明確)。

圖五//良渚文化晚期隨葬側扁足鼎的墓例
由于很多發現側扁鼎足的遺址出土遺物不多,不足以判斷其準確年代。所以,關于環太湖核心區側扁足鼎的重現時間,就目前資料看,大致相當于新地里第四段(即新地里H7和叭喇浜M8的年代)。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從良渚文化晚期早段到晚期晚段,側扁足鼎從重現到逐漸流行,是一個量變的過程,該階段遺存的性質并未改變,仍為良渚文化。
(三)側扁足鼎與良渚文化晚期社會出現的新勢力
良渚文化晚期新出現了一批器形,如寬把杯、闊把壺、實足盉、貫耳壺、瓦足盤、弦紋壺和弦紋盆等,這些器物都順利地進入到良渚文化墓葬的陶器隨葬品組合中。
但也有一些良渚文化晚期陶器存在著特殊的現象。據統計,在已清理的眾多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中僅發現5座墓葬隨葬側扁足鼎。這與側扁足鼎在生活堆積中的重現及逐漸流行情況頗不相稱。側扁足鼎好像被有意識地排除在隨葬品陶器組合之外,并且始終未被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會所接納。處于同樣境遇的還有袋足鬶,袋足鬶在良渚文化的出現較晚,約當新地里第五段。在環太湖地區找不到這類袋足鬶器物演變發展的源頭,表明它不是良渚文化的傳統器形。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袋足鬶應該是良渚文化晚期社會的新生力量吸收或借鑒了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鬶形器再加以改造而來的,這種粗矮頸肥袋足鬶在良渚文化晚期出現后便引起特別關注,更被一些研究者定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在良渚文化晚期遺址的生活堆積中可以見到較多鬶的口頸部或袋足的殘片,表明它在良渚文化晚期階段是比較流行的陶器。但是,袋足鬶卻基本不進入良渚文化晚期墓葬的陶器隨葬品組合中,類似的陶器還有矮圈足盤和錐刺紋罐等。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良渚文化晚期出現的以側扁足鼎、袋足鬶、矮圈足盤和錐刺紋罐為代表的器物群可能代表了良渚文化晚期社會的某些少數群體。更具體地說,是在器用傳統等方面與良渚文化主流社會刻意保持差異的利益集團。他們通過制作和使用與主流群體不同的器物,來彰顯他們的少數群體身份和對社會的不同利益訴求。如果說以T形足鼎為代表的器物群代表良渚文化晚期社會相對保守、陳舊的傳統勢力,那么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器物群應該代表了良渚文化晚期社會相對開放、創新的一種新勢力。盡管這種新勢力始終未能得到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會的完全接納,但他們不斷發展壯大,并且在良渚文化嬗變過程中脫穎而出,取代了以T形足鼎為代表的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會群體,從而使環太湖地區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側扁足鼎、袋足鬶和矮圈足盤正好就是良渚文化嬗變后形成的這類新遺存的主要器形。據此筆者推測,良渚文化晚期社會形成的這股新勢力實際上也就是后來顛覆良渚文化的主要力量。
四、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重現的原因分析
環太湖核心地區側扁足鼎在良渚文化晚期突然重現,背后的原因耐人尋味。
在年代約當良渚文化晚期階段的其他考古學文化中,如在山東大汶口遺址[50]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中已出現側扁足鼎,但形態為三角形,與環太湖地區差異較大;屈家嶺文化晚期(如湖北肖家屋脊遺址[51])出有與環太湖地區形態較為接近的側扁足鼎,但數量很少,不是當地主流炊器。進入龍山文化時期,在長江中游、淮河中下游等諸多遺址,如安徽肥西古埂遺址[52]、蚌埠禹會村遺址[53]都出土有側裝三角形扁足鼎,但年代顯然晚于良渚文化。所以,可以基本排除環太湖核心地區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可能。從本地文化的傳承來看,有兩條可能的途徑。
一條是對環太湖核心區自崧澤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就出現過的本地因素的繼承。良渚文化晚期的Aa型鼎、B型鼎與崧澤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的同型器,無論是鼎身或鼎足的形態,都非常接近,說明它們之間應有一定淵源關系。但是,考慮到它們之間又存在良渚文化中期近二三百年的缺環,僅依據形制相近就斷言它們之間有直接的繼承發展關系難免武斷,或可視之為復古現象,即一種特殊的繼承形式。

圖六//塘山背遺址出土的側扁足鼎
出有側扁足鼎的11座墓葬年代,較早的以M10為代表,較晚的以M44為代表。經比對可知,M10大致相當于新地里分期的第二段,M44大致為新地里分期的第四段。據此可判斷塘山背隨葬有側扁足鼎的墓葬年代跨度約當良渚文化中期偏早到良渚文化晚期偏早,基本貫穿塘山背良渚墓地始終。也就是說,在良渚文化中期,側扁足鼎在環太湖核心區基本消失時,錢塘江流域的塘山背遺址卻仍然非常流行,并且還是常見的隨葬炊器之一。從時間節點看,錢塘江流域側扁足鼎出現之際正是前文談到的環太湖核心地區側扁足鼎消失之時,時間上有驚人的巧合。

圖七//塘山背遺址和良渚古城遺址出土陶器對比
鑒于環太湖核心區與錢塘江流域的互動關系,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應該與這種反饋有關。換言之,錢塘江流域的側扁足鼎可能在環太湖核心區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重現、流行及最后取代T形足鼎的過程中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五、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質變”
(一)“質變”后的側扁足鼎
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的“質變”是指側扁足鼎基本取代了T形足鼎,以側扁足鼎為代表的一類新遺存基本取代了以T形足鼎為代表的良渚文化晚期傳統遺存。這里的“質變”實際上就是新舊文化的更迭過程,即良渚文化被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所替代。
經初步統計,新遺存階段較完整的側扁足鼎共12件,以夾砂紅陶為主,少量為夾砂灰陶或黑陶,余杭三畝里遺址的標本數量最多。其中Aa型3件(圖八︰1、2;另1件為良渚葡萄畈T0405④︰2),整體形態與良渚文化晚期接近;新增的Ad型9件,盆形,扁鼓腹或折腹,部分折肩(圖八︰3—10;另1件為良渚卞家山T1?︰15)。

圖八//錢山漾文化早期側扁足鼎
除上述完整器出土地點外,其他可判斷屬于新遺存階段的遺址主要集中分布在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如文家山、仲家山、鐘家港南段和中段、里山、姜家山、古尚頂、莫角山[55]、美人地、扁擔山[56]、毛竹山[57]、朱村墳,良渚古城四面城墻解剖的外壕溝上部堆積也均發現有這類新遺存。其他地點還有紹興仙人山[58]、桐廬城堂崗[59]和慈溪茂山[60]等。
(二)新遺存的文化面貌及性質
首先觀察該類新遺存的文化面貌:陶系上,比較明顯的是夾砂紅陶數量大幅增加,同時夾砂黑(皮)陶、泥質黑(皮)陶數量明顯減少,與良渚文化晚期區別顯著(表一)。陶器裝飾上,新出現了拍(壓)印的籃紋、繩紋、交錯繩紋、方格紋和刻劃的水波紋等紋飾。陶器器形目前可明確的有側扁足鼎、弧背魚鰭形足鼎、袋足鬶、矮圈足盤、細高把豆、寬把豆、垂棱豆、盆、泥質罐、夾砂罐、夾砂繩紋罐、壺、圈足盉、杯、缸和器蓋等(圖九)。

圖九// 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典型陶器(側扁足鼎除外)
新遺存中有些器物雖然與良渚文化晚期有著一定繼承關系,但其形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如頸部逐漸變細高的袋足鬶、形態多樣的矮圈足盤等。傳統的Aa型鼎雖仍然存在,但新出現的Ad型鼎后來居上,在三畝里晚期遺存、尖山灣早期遺存、茂山下層遺存以及仙人山、城堂崗等遺址中都已是炊器的主流形制。而盤壁有弧突的寬把豆、敞口弧腹細高把豆、淺腹或深腹盆、夾砂缸、夾砂繩紋罐、帶把杯和乳丁足罐等則是這個時期新出現的器形。相應地,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系列典型器物如T形足鼎、竹節柄豆、雙鼻壺、貫耳壺、三鼻簋、三足盤、實足盉、錐刺紋罐、寬把杯和闊把壺等都突然集體消失不見,說明從良渚文化早中期以來演變有序的陶器發展鏈條已經就此斷裂。另外,作為良渚文明重要象征的玉器除了地層中發現有少量錐形器外,尚沒有其他發現,或至少說明這個階段的玉器加工制作發生了嚴重的衰退。

表一// 良渚文化晚期和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的陶系統計對比
新遺存與良渚文化晚期文化面貌上的巨大差異,或許暗示新遺存在取代良渚文化晚期文化過程中可能采取了一種比較激烈的方式。因此,這類新遺存不宜再歸入良渚文化中。
再將這類新遺存與錢山漾一期文化遺存作一比較:陶質上,兩者都以夾砂陶居多,其中又以紅陶占多數;裝飾上,錢山漾一期流行的拍(壓)印的繩紋、籃紋、弦斷繩紋、弦斷籃紋、交錯繩紋、條紋、方格紋和刻劃的水波紋等紋飾在新遺存遺址中也有發現,但總體數量不多,紋飾種類也較少;器形上,袋足鬶、矮圈足盤、細高把豆、寬把豆和盆等是兩者共有的器物,只是形態略有區別。此外,錢山漾一期腹部常常裝飾有弦斷繩紋或籃紋的甕或深腹罐、袋足甗等陶器在這類新遺存遺址中很少見。最突出的差異體現在炊器上,即錢山漾一期的炊器是以弧背魚鰭形足鼎為主導,有部分側扁足鼎和鴨嘴狀鑿形足鼎等,而新遺存的炊器則以側扁足鼎占絕對主導地位,稍后開始出現弧背魚鰭形足鼎,且在年代略晚的這類新遺存遺址中,弧背魚鰭形足鼎數量呈現逐漸增多的趨勢。
這樣看,這類新遺存的文化面貌與錢山漾一期文化既有顯著共性,又有明顯區別。共性反映了兩者所處的相近時代背景和它們之間的某種內在聯系,特別是茂山遺址的新材料顯示:新遺存的側扁足鼎與錢山漾一期遺存的弧背魚鰭形足鼎既長期共存又此消彼長。據此可以將新遺存和錢山漾一期遺存作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早晚連續發展的兩個階段。而造成這兩類遺存文化面貌區別的主要原因正是二者在年代上存在早晚關系。
因此應把這類新遺存歸為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它與主要屬于錢山漾文化晚期階段的錢山漾一期文化遺存共同構成較為完整的錢山漾文化。
六、余論
通過本文梳理可知,良渚文化晚期側扁足鼎是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本地特征明顯的一種主流炊器(圖一〇)。最早可追溯到崧澤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期一度在環太湖核心區消失不見,后又在本地傳承和錢塘江流域因素影響下重現并逐漸流行,最終取代良渚文化晚期的T形足鼎完成了質變,質變后的新遺存應該屬于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

圖一〇//環太湖地區側扁足鼎演變圖
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的確認,為考察環太湖各地發現的側扁足鼎和弧背魚鰭形足鼎共存的諸遺址(如余杭文家山、余杭三畝里、紹興仙人山、桐廬城堂崗、諸暨尖山灣和慈溪茂山等)文化性質和發展階段提供了依據,更為深入探討錢山漾文化的內涵和年代打下了基礎。
錢山漾文化早期遺存的確認,也使困擾學術界多年的良渚文化消亡問題有了初步但明確的答案,即錢山漾文化直接取代了良渚文化,而這一取代過程應該是良渚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展開的一次顛覆性大變革。出土側扁足鼎的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和質變后形成的新遺存遺址大多集中分布在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暗示著這場變革首先發生在良渚古城及周邊地區。稍后,太湖南岸和東岸的史前先民在外來的龍山文化禹會村類型的強烈輻射和影響下,形成以弧背魚鰭形足鼎為代表的錢山漾文化(錢山漾一期文化遺存),并迅速往環太湖各地擴散傳播,從而使環太湖地區加快融入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化進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