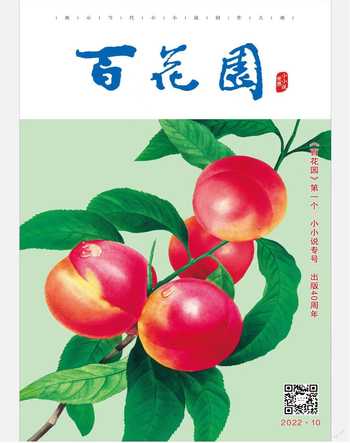較真兒
李林

韓醫(yī)生長(zhǎng)得矮小,戴黑框近視眼鏡,穿白大褂兒,顯得玲瓏小巧。見面后,我常套用魯迅的腔調(diào)調(diào)侃他:“別露出褂子下的‘小來。”他不惱,只是笑笑。
我認(rèn)識(shí)韓醫(yī)生,是從訂報(bào)紙開始的。當(dāng)時(shí)我在晚報(bào)做副刊編輯,報(bào)紙銷量不好,讓記者和編輯定量征訂。我是坐班編輯,沒記者門路廣。訂不出報(bào)紙要扣工資,我只好找到在福利院當(dāng)院長(zhǎng)的三叔,讓他訂20份報(bào)紙,以解燃眉之急。
幾日后,我去福利院取訂報(bào)款,見到一個(gè)小個(gè)子醫(yī)生,手里拿著一摞晚報(bào),與我三叔爭(zhēng)辯:“分院只有三個(gè)醫(yī)生、五個(gè)護(hù)士,醫(yī)護(hù)人員人手一份,滿打滿算,只能分?jǐn)?份報(bào)紙。給我們訂15份,剩下的7份,讓誰看啊?”三叔說:“報(bào)紙由總院訂,費(fèi)用不用你們分?jǐn)偅銈兪盏骄托辛恕!毙€(gè)子醫(yī)生糾正道:“報(bào)紙是用來讀的,收到也不能當(dāng)擺設(shè)。醫(yī)護(hù)人員人手一份夠了,訂多了浪費(fèi)。”說完,扔下多余的報(bào)紙,匆匆地走了。
小個(gè)子醫(yī)生走后,三叔向我介紹:“這個(gè)醫(yī)生姓韓,是新來的,是福利院分院的院長(zhǎng)。”我問三叔:“這人咋這么多事呀?”三叔說:“他是個(gè)好人,就是太愛較真兒。其實(shí)他說得對(duì),但你也不容易,這多出的7份我自掏腰包結(jié)賬吧。”
隨后,三叔給我講了韓醫(yī)生的故事。
早先,韓醫(yī)生從上海醫(yī)科大學(xué)畢業(yè),被分配到市里一家精神康復(fù)醫(yī)院工作。韓醫(yī)生醫(yī)術(shù)精湛,治好了不少精神病人,在患者中頗有口碑。韓醫(yī)生一門心思看病,給患者開的處方上都是些既便宜又能治病的藥。因?yàn)獒t(yī)生的工資是與處方緊密掛鉤的,韓醫(yī)生每月的收入都在全科室墊底兒。韓醫(yī)生氣不過,與刁難他的科室主任較真兒,最后甩了一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科室主任也不尿他,說:“你走呀,誰留你呢?”
韓醫(yī)生虎落平川,自尋出路,到一家私人開的養(yǎng)老院謀生。這家養(yǎng)老院位于郊外,住院的老人不多,只有三個(gè)護(hù)理員,三班倒輪流護(hù)理老人。有個(gè)護(hù)理員叫柴俊,愛打麻將,下班打,上班期間也溜出去打。柴俊溜出去打麻將時(shí),就把一定量的安眠藥投入暖壺,老人們喝后昏昏欲睡,有的還因躺得太久生出褥瘡。那兩個(gè)護(hù)理員怕?lián)?zé)任,向院方反映柴俊的問題。柴俊是個(gè)蠻纏的人,院方也不敢管他。韓醫(yī)生初來乍到,聽到護(hù)理員反映的情況,暗中跟蹤柴俊,看到他向暖壺投放安眠藥時(shí),當(dāng)即拎起暖壺朝他潑去。多虧里面的水是昨天灌的,柴俊沒被燙傷。最終柴俊被辭退,韓醫(yī)生停職檢查。韓醫(yī)生不寫檢查,辭了職,這才托朋友找到我三叔,應(yīng)聘到福利院。
韓醫(yī)生能跟我熟絡(luò),還是靠晚報(bào)牽的線。韓醫(yī)生不愛看報(bào)上的新聞,只愛讀副刊上的文學(xué)作品。他看了我編的《清河》副刊,感覺不錯(cuò),就托我三叔把他寫的散文交給我,想投個(gè)稿。我當(dāng)時(shí)對(duì)他有怨氣,沖三叔說:“多訂一份晚報(bào),他都要較真兒。現(xiàn)在想發(fā)稿了,他倒不較真兒了?”三叔說:“你先瞅瞅,若寫得不好,就別給他登。”我粗略地看過,寫得還行,就答應(yīng)三叔給他編發(fā)。接著韓醫(yī)生又寫了幾篇散文,每篇都好,我都給他發(fā)表了。后來,我與韓醫(yī)生成了文友,彼此興趣相投,都是性情中人,在工作上都屬于愛較真兒的人。
直到經(jīng)歷了那檔子事兒,我們才成了真正的朋友。
那些年,我得了一種怪病,發(fā)病前一點(diǎn)兒癥狀也沒有,病一來,就覺得鼻孔被堵住,只有進(jìn)的氣兒沒有出的氣兒,憋得我死去活來,每次都必須打120、掛急診,用氧氣才能把我的這口氣兒撈上來。我發(fā)病的癥狀很像心梗,給我看病的馬醫(yī)生也這樣說:“你的心臟出現(xiàn)了早搏,不行就安支架吧!”我膽兒小,每次犯病都拖著,沒敢安支架。
那天我的病又犯了,憋得上不來氣,被120送到醫(yī)院急診室。馬醫(yī)生見了,果斷地說:“抬到手術(shù)室,立刻做支架!”當(dāng)時(shí)韓醫(yī)生也趕到了,向馬醫(yī)生喊道:“你是什么醫(yī)生?動(dòng)不動(dòng)就給病人做支架!”馬醫(yī)生說:“我是什么醫(yī)生不重要,你這個(gè)福利院精神科的醫(yī)生,別不是走錯(cuò)門了?”韓醫(yī)生說:“你把他做過的24排冠脈造影拿來,讓我看看。”馬醫(yī)生不屑地說:“你看得懂嗎?”又轉(zhuǎn)過頭對(duì)我說:“你做不做?不做命沒了,可別怪我!”
還沒等我說出做還是不做,韓醫(yī)生架起我走出了急診室,邊走邊沖我說:“心梗的搶救時(shí)間只有幾分鐘,你要是心梗還能拖到現(xiàn)在?”我有些轉(zhuǎn)過神來,問他:“我這是啥病?” 韓醫(yī)生說:“急性焦慮癥。我給你開些藥吃,保你藥到病除。”我吃了韓醫(yī)生開的帕羅西汀、坦度螺酮之后,竟然真就好了。
后來我才知道,那個(gè)馬醫(yī)生與韓醫(yī)生是老同學(xué),但韓醫(yī)生卻和他尿不到一個(gè)壺里去。韓醫(yī)生很是看不起他的老同學(xué),經(jīng)常對(duì)我說:“他現(xiàn)在怎么變成了這樣?要想掙錢,他該去經(jīng)商啊!”
韓醫(yī)生邊行醫(yī)邊搞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工作和生活還算如意。我三叔退休,新院長(zhǎng)上任,韓醫(yī)生仍然改不掉愛較真兒的性子。有個(gè)在分院住過院的輕癥病號(hào),想拿到醫(yī)院開具的精神病鑒定證明,提前辦理病退手續(xù)。也不知他與新院長(zhǎng)是什么關(guān)系。那天新院長(zhǎng)來找韓醫(yī)生,委婉地問他能否給辦。韓醫(yī)生當(dāng)下甩了臉子,說:“他的病早好了,我再鑒定證明他有病,我就是失職!”新院長(zhǎng)說:“他就是想辦個(gè)病退,也沒啥大不了的,你通融一下嘛。”韓醫(yī)生說:“你想給他辦,你來辦。我通融不了!”新院長(zhǎng)表面沒再說什么,背后卻開始處處給他“穿小鞋”。
韓醫(yī)生不是個(gè)能忍氣吞聲的人,可身在屋檐下,他不忍工作就不好干了。我擔(dān)心韓醫(yī)生忍出病來。那天我去看韓醫(yī)生,他好像喝多了酒,紅頭漲臉地立在一面鏡子前。我走到韓醫(yī)生身后,他沒發(fā)覺我,竟對(duì)著鏡子喊道:“你是一個(gè)高尚的人,一個(gè)純粹的人,一個(gè)有道德的人,一個(gè)脫離了低級(jí)趣味的人,一個(gè)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是一塊鑲著白求恩頭像的老式水銀穿衣鏡。
韓醫(yī)生已經(jīng)淚流滿面了。
[責(zé)任編輯 吳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