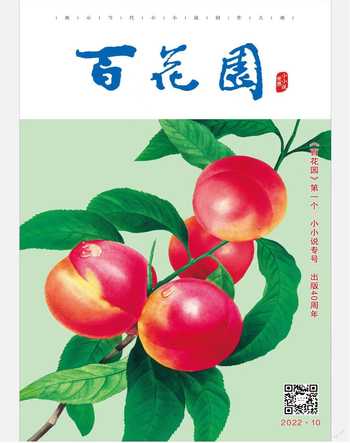大寫家
趙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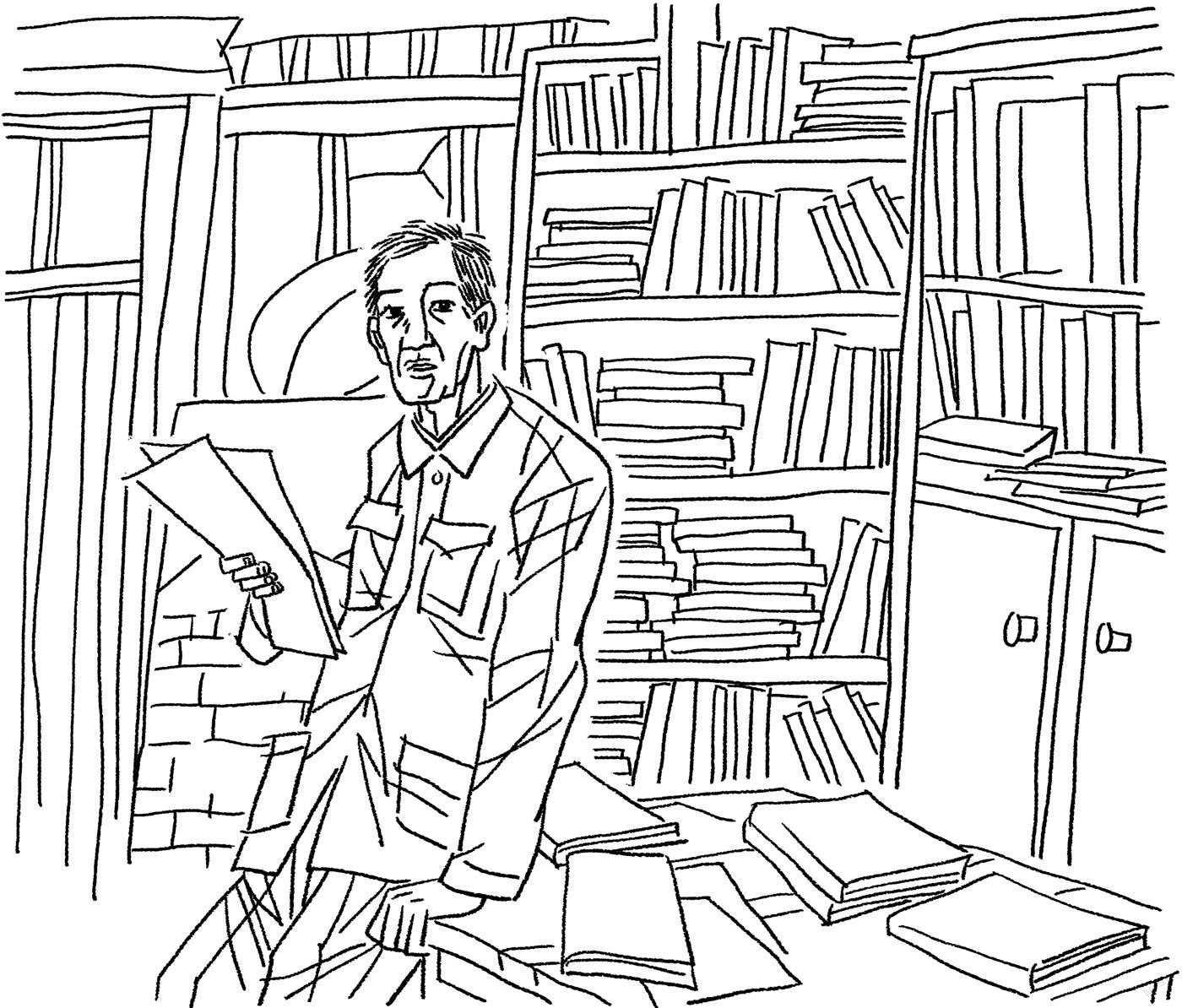
錢瑞峰好寫。
墻上寫,地上寫,沙上寫,樹葉子上寫。鋤把兒上寫“錢氏瑞峰之鋤”。所用的毛筆,也在筆管上刻著“錢氏瑞峰之筆”。后來,學了普通話的小孩子們拿著他的筆一個勁兒地念誦,大人們笑,他就改成“錢氏瑞峰之用”。
錢瑞峰好寫,在于他寫得好,至少,是袁店河上下字能拿得出手的為數不多的人。大字,不好寫,在墻上,如簸箕,錢瑞峰能駕馭。站在梯子上,錢瑞峰揮著大掃帚,在洋鐵桶里一蘸,稍一頓,趁著墨汁不滴,唰唰唰——“人有多大膽”,飛龍走蛇,氣勢磅礴。墨汁很簡單,濃石灰,和了袁店河中有黏性的白泥,寫上去,不滯不淋;再挪一下梯子,再一蘸,再一頓,一聲吼:“地有多大產!”后面的感嘆號,像個粗墩墩的樹樁,尾部收了一下,又放大,圓點兒實實在在。
那些年頭,錢瑞峰有干不完的活兒。上山挖梯田,紅旗招展。錢瑞峰不用下大力,指揮著人在他劃定的框框里填石頭——羅漢山上少有的白青石,白中泛青,青中泛白,與框框外的黃土、青草、樹木相比,很顯眼。框框很大,人們起初看不出來個啥。一天,兩天……半月后,那字就顯出來了——“農業學大寨!”每個字有二層樓高,就在面向公路的山坡上,是一景。多年以后,封山育林,用這幾個字的石料,竟蓋了一溜兒的護林房。錢瑞峰很心疼:“唉,你們不懂啊,這是文物啊!實體文物,不能拆的。”人們不信,等信了,晚了。
錢瑞峰寫字,沒有人教,就是自學,自己琢磨。《人民畫報》《人民日報》就在生產隊的廣播室里,他總是去看,琢磨上面的書法作品,按照報刊上的樣子劃拉。有一回,他劃拉“毛主席萬歲”那幾個字,劃呀劃呀,硬是將畫報上偉人的臉磨出了一個小洞。好在婦聯主任發現了,將畫報一收,讓他趕緊走了,就將畫報放在桌子一角。第二天,隊長發現了,要追查,誰都說不知道。
婦聯主任對錢瑞峰好,因此,錢瑞峰可以到生產隊的廣播室里看報。一些舊報刊上的書法作品,錢瑞峰就剪貼起來,放在《毛澤東選集》里,厚厚的。晚上睡覺時,還要比畫,拿指頭在腰腹上的被子上畫。日子長了,也畫出來個洞洞。曬被子時,人笑。他問:“笑啥?”人們說:“你的勁兒真大……”
大家就都笑起來,錢瑞峰一臉茫然。婦聯主任心里嘆了口氣。
錢瑞峰喜歡上山。羅漢山、豐山上各有一個廟:漢山寺、豐山寺。因為“破四舊”,寺里早已沒有了香火,一片荒草,臥著被砸倒的各色石碑,碑上有真、草、隸、篆的字。他就看,蹲著,趴著,彎腰,側身,不覺得累。不能耽誤生產,他就趁晌午頭兒,趁大清早,拿了饃,提一瓦罐水上山。渴了,餓了,就地解決。他帶著紙、筆,慢慢地描,慢慢地畫。有天,隊長帶著倆民兵突然到了他身后,長槍指著他。他招招手:“隊長,你看這個‘壽字,多好!”
隊長不耐煩:“老子以為你在找寶呢!你老祖爺沒有給你留下藏寶圖?”
錢瑞峰就不再吭聲,把那幾張紙卷好,放進“為人民服務”的黃挎包里,順著他踩出來的小道,下山,一路心想:老祖爺呀,我知道你建寺所留下的寶了,就是這些碑刻——歷朝歷代的字呀!
錢瑞峰的祖上做過數省巡撫,后來回到袁店河,在羅漢山和豐山上建寺,把在各地搜羅的石碑運來,鑲嵌在廟基、寺墻上,立在寺院里,各形成了一處很好的碑廊……
有些日子,村里不需要錢瑞峰的字了,他就守在郵局,免費代寫書信——毛筆小楷,豎行,很古雅。過了些日子,人家不讓他寫了,說:“豎行,看著太累,寫得又太古。”錢瑞峰長嘆一聲。
錢瑞峰還好寫各種文章,小說、詩歌、散文、評論,都寫,小楷字看起來很舒服。他只管寫,寫好了,就存起來,標上年月日、天氣、地點,很清楚。只是很少發表。天天寫,月月寫,年年寫,每年總是一大包,就放在自己屋里的床下、梁頭。有一天,婦聯主任來他家,要給他收拾一下屋子。他趕緊攔住了:“你別動!我的東西我知道在哪里……”
遲疑了一下,人家走了,汪著淚。然后,錢瑞峰鋪紙,潤筆,閉目,流淚,搖頭,寫下一個字:愛。又寫一個:愛;再寫一個:愛;再寫一個:愛;再寫一個:愛……寫了大半夜!
[責任編輯 王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