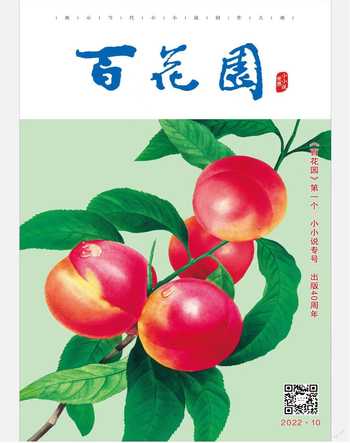文字神圣
張港
地球上,沒(méi)有語(yǔ)言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絕大多數(shù)民族并沒(méi)有文字,這些民族在借用別人的文字。即使是現(xiàn)有的通行文字,其實(shí)也就是那么幾個(gè)起源的變種。
文字真的神圣。
倉(cāng)頡造出了文字,“天雨粟,鬼夜哭”。這肯定是神話,但能夠流傳千年,顯然是由于文字的神圣感。過(guò)去有“惜字會(huì)”,這是文人的組織,每到年終,要將一年內(nèi)寫過(guò)字的紙張集中到孔廟中焚燒。寫過(guò)字的紙,不能隨便扔進(jìn)紙簍,更不可當(dāng)廢品賣掉或擦屁股。紙上有了文字,就不再是普通的紙,就與神靈有關(guān),就得還給神靈。杜甫說(shuō)“下筆如有神”,說(shuō)明他寫作時(shí)是感知著神的存在的。
小小說(shuō)限定1500字左右,這本身就是對(duì)文字神圣的最好詮釋,就是提醒寫作的人,對(duì)文字懷有敬畏之心,珍惜筆墨,淘洗語(yǔ)言。
“淘洗”,可用于沙里淘金,也是由生米到熟飯的必需環(huán)節(jié)。小小說(shuō)的文字也需要反復(fù)淘洗。
“用手拿起一根粗粗的木棍子,然后再用腳踹開門。”這是某作家的真實(shí)文字。明顯寫了好多廢字,浪費(fèi)文字不說(shuō),還把緊張的場(chǎng)面弄松懈了。要是放在小小說(shuō)里,就得改成“操起棍子,踹開門”,字要少,要用短句,營(yíng)造出緊張的氣氛。
魯迅曾說(shuō),“將可有可無(wú)的字、句、段刪去”。寧可把長(zhǎng)篇改成中篇,把中篇改成短篇。
我的小小說(shuō)《海布楞》,寫到老安代盼望兒子回來(lái),先寫的是“一年又一年”,覺(jué)得太普通太沒(méi)個(gè)性,就改成“雁來(lái)雁去”。可是雁可以引發(fā)多種聯(lián)想,容易將讀者帶到偏處,又改成了“草青草黃”,以表達(dá)年歲的流逝。“草青草黃”,有了草味,是草原的生活。可是又覺(jué)不夠,“草青草黃”,由青變黃,是從希望到失望,而老安代是懷有希望的,于是改為“草黃草青”,這是由失望到希望,這四個(gè)字才算定下來(lái)。這樣的修改煉字,給讀者的感覺(jué)極其微小,但卻影響著閱讀。“潛移默化”就這個(gè)意思。
老師引導(dǎo):“月亮像不像大大的玉盤?”學(xué)生問(wèn):“老師,玉盤啥樣子?”其實(shí)老師也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玉盤。老師讀到“鬼子像殺豬一樣號(hào)叫……”上海學(xué)生沒(méi)有聽過(guò)豬被殺的號(hào)叫,連真的豬都沒(méi)看過(guò)。老師是跟著參考書說(shuō)的,這樣的比喻可以稱之“濫喻”。所有的比喻全是因?yàn)闊o(wú)奈,最恰當(dāng)?shù)谋扔饕膊皇鞘挛锏谋举|(zhì)。使用比喻,是文學(xué)的重要手段,可是得小心。

我的《村名就叫賊拉犟》,村人初見(jiàn)下放來(lái)的老教授的眼鏡,這個(gè)眼鏡片的厚應(yīng)該怎樣形容呢?我先是寫了個(gè)比喻——“像啤酒瓶子底”,可是一想,當(dāng)年的鄉(xiāng)下人極少接觸瓶裝啤酒,這樣比喻不行。想來(lái)想去,最后寫“嗬——這眼鏡子,上秤盤子,得有半斤”。這才松了口氣,感覺(jué)這是符合人物的,是有個(gè)性的。
用成語(yǔ)是學(xué)生的必修本事。可是真的寫小說(shuō),就得少用,因?yàn)槌烧Z(yǔ)“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人人可用,處處可用,已經(jīng)不是針對(duì)特定語(yǔ)境的“那一個(gè)”。
“遍體鱗傷”,可用,但不具體,最好寫哪個(gè)部位什么樣子:鼻子什么樣,嘴巴什么樣,左臉、右臉、頭發(fā)等,一一寫來(lái)。“鳥語(yǔ)花香”,哪種鳥在叫?什么花香著?成語(yǔ)并沒(méi)有給出來(lái)。“天高云淡”,是抽象的,不如具體地描寫。用成語(yǔ),省事,省字,似乎是寫小小說(shuō)的法寶,可是,我極少用成語(yǔ)。
小小說(shuō)有時(shí)是要“啰唆”的——這簡(jiǎn)直是反著來(lái),但這恰恰是煉字。
“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看似重復(fù),實(shí)是妙筆。
東北過(guò)年,孩子能得到叫“磕頭了”的小蠟燭。《磕頭了》中,“我”將寶貝“磕頭了”藏在炕頭席子下。胖嬸來(lái)了,一屁股坐上炕頭。胖嬸一句一喘,對(duì)奶奶說(shuō):“我呢……昨天……買了呢……兩個(gè)蘿卜。一個(gè)紅的,還有一個(gè)呢,是青的。一個(gè)紅的,一個(gè)青的。紅的呢,包餡兒;青的呢,做湯。喀,喀!——大夫說(shuō)了,讓少說(shuō)話,說(shuō)多了傷肺。——我呢,買那兩個(gè)蘿卜,紅的大,青的小,其實(shí)呢,也差不多少……”
胖嬸的話無(wú)味而絮煩。用大量文字記下這些,看似浪費(fèi)筆墨,其實(shí),正寫出了孩子擔(dān)憂小蠟燭被坐扁坐彎的急切心情。這不是廢筆。
《狗鈴兒》中,“老蹦子”說(shuō)話,每句只蹦一個(gè)字,可是學(xué)習(xí)發(fā)言時(shí),卻蹦出兩個(gè)字,隊(duì)長(zhǎng)表?yè)P(yáng)他了。隊(duì)長(zhǎng)只有一句臺(tái)詞,是次要角色,即使這樣,他的話也得有個(gè)性。
隊(duì)長(zhǎng)說(shuō):“啊——這個(gè)啊——這個(gè)老蹦子,發(fā)了一個(gè)言,發(fā)得……很好。還要努上一個(gè)力,繼上一個(gè)續(xù),提上一個(gè)高。”
隊(duì)長(zhǎng)的話其實(shí)有語(yǔ)病,可是,用于當(dāng)年的農(nóng)村隊(duì)長(zhǎng),卻是恰當(dāng)。
文字是語(yǔ)言的高級(jí)層次。精理為文,秀氣成采。語(yǔ)不驚人死不休。
趙樹理等作家自稱“山藥蛋派”。這么說(shuō),是為了突出自然、質(zhì)樸、通俗的文風(fēng),絕非山炮、老土。有一回,趙樹理來(lái)了興致,對(duì)同事說(shuō):“哪位能將我老趙的小說(shuō)改動(dòng)仨字,就請(qǐng)吃烤鴨。”就沖烤鴨,說(shuō)什么也得改他三五個(gè)字,“的”“了”總有可改的吧。可是,同事們愛(ài)烤鴨更愛(ài)真理,一個(gè)字也沒(méi)改——?jiǎng)幽囊蛔侄疾皇嫣埂?/p>
中學(xué)語(yǔ)文一度盛行“擴(kuò)寫訓(xùn)練”:拿來(lái)古人、名人的作品,擴(kuò)而大之。這是最坑人的教學(xué)法。“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被擴(kuò)寫成“一輪白日依山盡,滔滔黃河入海流。欲窮明察千里目,更上鸛雀一層樓。”如果這樣好,王之渙咋不這么寫?難道非讓中學(xué)生超過(guò)王之渙?糟蹋名作,害了學(xué)子。狗尾草續(xù)貂,毛都不是。
孔子說(shuō):“辭達(dá)而已矣。”有人以為,把話說(shuō)明白就行了,以此認(rèn)定寫作并非難事。其實(shí),孔子的“達(dá)”,是恰到好處,不長(zhǎng)不短,不滯不澀不矯情,不干涸也不泛濫。如宋玉筆下的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zhǎng),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辭達(dá)而已矣,行文的基本要求,難啊!
寫作是心靈難得的獨(dú)立時(shí)光,現(xiàn)代的我們,靈魂被各種各樣的不自主支配著,然而,完成一篇好文章,獨(dú)自端詳自己摁鍵盤的十指,感覺(jué)心里甜甜的,然后關(guān)上臺(tái)燈睡覺(jué),夢(mèng)很美很實(shí)。
[責(zé)任編輯 王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