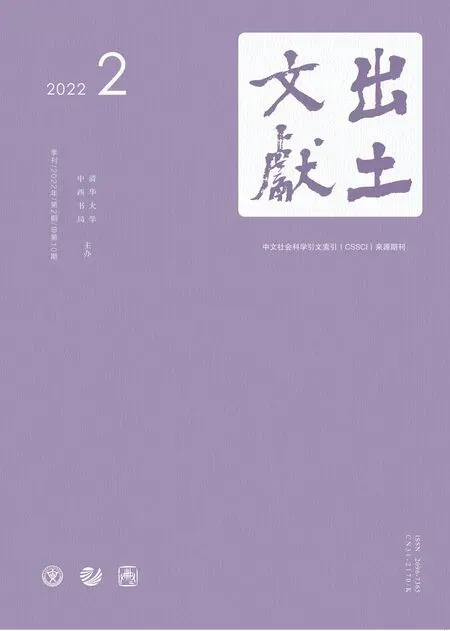吳虎鼎銘文補釋
謝明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1992年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申店鄉徐家寨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吳虎鼎(《銘圖》(1)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卷。文中簡稱“《銘圖》”。02446),現藏西安市長安博物館。其內壁鑄銘文166字(含重文2),研究者已對銘文作了很好的釋讀,本文準備對銘文的個別地方略作補釋。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意見先將銘文釋讀如下:
履,踏勘田界。同類用法的“履”,金文中多見。“履”后面一字,周曉陸先生、穆曉軍先生隸作“”。(5)穆曉軍: 《陜西長安縣出土西周吳虎鼎》,《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周曉陸、穆曉軍: 《吳虎鼎銘錄》,《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李學勤先生隸作“”,讀作“封”,解釋為“封樹疆界”。(6)李學勤: 《吳虎鼎考釋——夏商周斷代工程考古學筆記》,《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近出》徑釋作“封”。(7)劉雨、盧巖: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2冊,第238頁。文中簡稱“《近出》”。《銘圖》、(8)吳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卷,第282頁。《陜集成》、(9)張天恩主編: 《陜西金文集成》,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2卷,第118頁。文中簡稱“《陜集成》”。“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10)“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0709。葉正渤先生等亦皆隸作“”,括注“封”。(11)葉正渤: 《西周標準器銘文疏證(三)》,《中國文字研究》第14輯,鄭州: 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51—52頁。《新收》則僅隸作“”。(12)鐘柏生等編: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臺北: 藝文印書館,2006年,第523頁。文中簡稱“《新收》”。

據銘文,前后兩處內司徒顯然是同一人,后文的“內司徒”后面有“寺”,因此研究者皆將前文的“內司徒”后面的兩字釋作“寺”,并認為“寺”系人名似乎理所當然。但前文所謂“寺”之“”,《長安瑰寶》所錄拓本作“”,左側明顯從人,右側似從“又”。它與同銘的“”作“”“”等形迥然不同,絕非“”字。據形可隸作“僅”(與“僅”的簡體無關),或可釋作“付”字。但與同銘“(付)”字比較,其所從又形稍微靠下,也不排除是“及”之訛字的可能,它在鼎銘中作人名。“寺僅”之“寺”則是國族名,(33)由于缺乏相關資料,此“寺”與山東地區的“邿國”之“邿”是否有關,難以論定。猶如五祀衛鼎(《集成》02832,《銘圖》02497,西周中期前段)“內史友寺芻”、寺季故公簋(《集成》03817、03818,《銘圖》04759、04760,西周晚期)“寺季故公作寶簋”之“寺”。后文的“賓內司徒寺”后面一字,李學勤先生釋作“復”,括注“覆”。(34)李學勤: 《吳虎鼎考釋——夏商周斷代工程考古學筆記》,《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近出》釋作“復”。(35)劉雨、盧巖: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2冊,第238頁。周曉陸先生、穆曉軍先生疑是“璧”字。(36)周曉陸、穆曉軍: 《吳虎鼎銘錄》,《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新收》、《銘圖》、《陜集成》、《西周金文禮制研究》、“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等釋作“璧”。(37)吳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卷,第282頁;張天恩主編: 《陜西金文集成》,第12卷,第118頁;鐘柏生等編: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第523頁;黃益飛: 《西周金文禮制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53頁;“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0709。葉正渤先生釋作“復”,括注“璧”。(38)葉正渤: 《西周標準器銘文疏證(三)》,《中國文字研究》第14輯,第51—52頁。此字,《陜集成》《銘圖》所錄拓本分別作“”“”,顯然是從彳從韋之字,應釋作“徫”。(39)九年衛鼎(《集成》02831,《銘圖》02496,西周中期前段)銘文中的“”,舊或誤釋作“徫”。“賓內司徒寺徫”之“寺”即指前文“伯導內司徒寺僅”的“寺僅”,此處是承上省略了私名。以族氏名指稱個人,類似的例子如裘衛盉(《集成》09456,《銘圖》14800,西周中期前段)“矩伯”、曶鼎(《集成》02838,《銘圖》02515,西周中期后段)“匡季”都是“族氏名+排行”的稱謂格式,它們在各自的銘文中再次出現時可分別稱作矩、匡。而“徫”應該與下文“賓史韋兩”的“韋”聯系起來,“徫”“韋”表示同一個詞。也就是說,并不存在所謂的人名“寺”。(40)吳鎮烽先生《金文人名匯編(修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110頁)收錄人名“寺”,并介紹說:“西周晚期人,擔任周王朝的內司土之職,宣王十八年十三月丙戌日,參與周宣王授予吳虎土地的儀式,并參與勘界封疆,吳虎曾賓贈玉璧以謝。”(《金文人名匯編(修訂本)》第410頁亦有大致相同的介紹)從介紹來看,吳先生是采用了將“賓內司徒寺”后面一字釋作“璧”的意見。根據我們的論述,所謂人名“寺”應改作“寺僅”。

又比較九年衛鼎(《集成》02831,《銘圖》02496,西周中期前段)“(鞭)”字作“”,“”也可能是“(鞭)”的訛字,即所從“又”訛作了“氒”,且豎筆穿過中部橫筆部分并與上部相接。據九年衛鼎,“鞭”可歸入車器。如果吳虎鼎此字確是“(鞭)”的訛字,則其前的“韋”讀作“幃/帷”(義指車上的帳子)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我們歸納一下本文的主要觀點: (1) “履”后一字,應徑釋作底部加了一橫筆的“豐”,系“封”字初文;(2) “內司徒”之名應是“寺僅”,“寺”是國族名,“僅”是私名,并不存在人名“寺”;(3) “書尹友守史”后面一字,應釋作“囟/西”,不能屬下讀釋作虛詞“廼”,而應看作是史官的私名;(4) “賓內司徒寺”后面一字,應釋作“徫”。“賓內司徒寺徫”的“徫”與后文“賓史韋兩”的“韋”表示同一個詞,“賓史韋兩”的“史”指前文“書尹友守史囟/西”的“史囟/西”,“賓內司徒寺徫”的“寺”指前文“伯導內司徒寺僅”的“寺僅”,它們皆是承上省略了私名;(5) “徫”后之字,舊釋作“爰”,于形不合,可能是“(鞭)”的訛字;(6) 銘末一直被漏釋的字當是“用”字。
附記:本文蒙匿名審稿專家批評指正,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