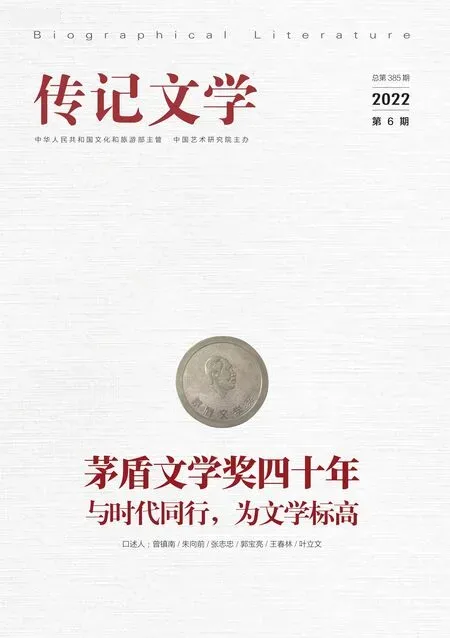茅盾文學獎四十年:與時代同行,為文學標高
本刊編輯部
茅盾文學獎是根據茅盾先生遺囑,于1981年設立、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一項國家級文學大獎。從1982年開始首屆評選,至今已四十年,歷十屆,共評出48 部長篇小說。在這四十年間,就其影響而言,無論作為衡量自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創作實績和藝術水平的標桿,并以此引導和昭示“國家文學”在發展進程中的應有樣態、影響,還是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建設中的重要一環,并為推動當代文學發展提供激勵機制、體制保障,“茅獎”都是國內其他任何文學獎項所無可比擬的。
事實上,作為當代中國最受矚目、最具影響力、傳播面最廣的文學事件和文化話題之一,“茅獎”早已溢出文化和文學界而為社會各界所關注。這也是長篇小說這種“重型”和“大型”現代文類本身包孕著的巨大思想性和藝術性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姑且不說《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長篇小說業已進入經典普及行列而深入人心,單就圍繞每屆評選過程所生成的釋讀、宣介、爭鳴等一系列文化活動而言,每一屆評獎就幾乎波及當代中國社會的各個群體和領域,并動輒引發經久不息的議論。“茅獎”不僅為全國各類型、各層次、各領域讀者進駐文學現場、認知長篇小說、領悟文學魅力提供了最佳契機,也為吸引人們廣泛參與公共話題、表達一己見解、呈現自我形象搭建了便捷、自由、寬闊的展示平臺。
“茅獎”有其普適性的評選標準: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啟人心智,要有藝術感染力,尤其要突出“時代性”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其中,那些把握和書寫國家、民族、時代發展大勢,具備史詩性和宏大敘事品格的長篇小說往往更容易脫穎而出。從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蛙》、李佩甫的《生命冊》等每一屆必有的及時反映現實生活和時代發展趨向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到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王安憶的《長恨歌》等以小說方式追溯或探尋民族秘史、文化精魂的已進入經典化路徑的長篇力作,再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等以文學方式重述歷史、重構歷史人物的歷史題材長篇小說,都無不折射出現實感、思想性、史詩性在彼時和此后長篇小說創作格局中的示范性、引領力。從這一發展趨向來看,茅盾文學獎為促進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為正面引領讀者閱讀趣味、豐富大眾精神生活,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茅獎”是目前最專業、較公正的行業大獎。這不僅因為每一屆都有其嚴格的篩選程序、規章和監督機制,更因為由國內最具專業素質的文學評論家、學者組成的評審團在審讀和評判的過程中,能從文學本體出發最大程度地達成共識。盡管每一屆評獎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甚至也評出過幾部爭議性比較大的作品,但無可否認的是,每一部入圍作品都有其不可忽視的獲獎理由和應有的歷史位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長篇小說最終能入選“茅獎”,基本都是評委們集體作業、多方博弈、求同存異的結果。評委是“茅獎”評選過程的親歷者、見證者,為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總結四十年來“茅獎”評選發展得失,我刊2022年第6 期特別策劃“茅盾文學獎四十年:與時代同行,為文學標高”封面專題,邀請曾鎮南、朱向前、張志忠、郭寶亮、王春林、葉立文共6 位“茅獎”評委,通過口述或訪談形式集中講述各自參加評獎的經歷以及對“茅獎”的評價與建議。
任何一部獲獎作品若進入經典化路徑或最終能完成經典化,首先必須接受不同時代讀者的不斷審讀、質疑、重構。在此過程中,“茅獎”則是初步篩選和驗證其是否具備經典特質的手段之一。實踐已經反復證明,凡是一經入圍“茅獎”者,即廣泛、快速、持續引來讀者和評論界關注、閱讀、闡釋,這對任何一部初具經典品相的作品來說,都是一個絕佳機遇。這充分表明,“茅獎”已成為匯聚文學批評力量、構建文學批評生態、有力促進文學經典化的重要文學制度之一。
當然,“茅獎”在運行體制和評選機制方面亦需不斷完善。如今,一些獲獎作品已被阻擋在了經典化大門之外,而展露文學和文學史雙料經典品相的未獲獎者并不少見,這也表明,是否獲“茅獎”,以及什么時間獲獎,與一部長篇小說是否具有經典品相及其可能,并不構成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茅獎”只是一種目前在國內影響比較大的專業獎項,是長篇小說經典化過程中重要的篩選手段或建構力量之一。長篇小說創作和評獎雖關聯密切,但畢竟不是互為目的的閉環式發展關系,而是互鑒、互補、互證的并行式發展關系。
長篇小說最能彰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成就,也最能代表一個國家文學發展的實力。無論在新時期,還是在新時代,“茅獎”都擔負著篩選、檢驗、振興當代長篇小說的重要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指出:“推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努力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在這種背景和愿景下,“茅獎”與新時代文學的深度關聯,以及在評介和引導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方面的責任與使命就愈發顯得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