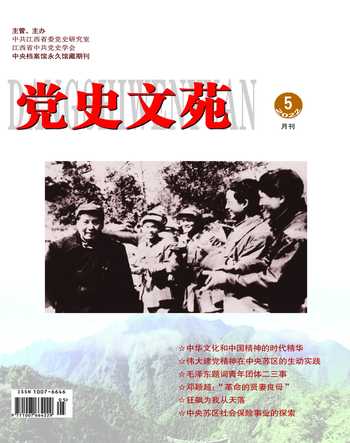蘇聯、蔣介石在皖南事變前后
史宇陽



蘇聯自1937年開始援助中國抗戰,寄希望于國民黨軍隊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上,讓蔣介石產生蘇聯“非借重他不可”的心態。隨著1940年國際形勢的變化,美英也加入援華行列中,蔣介石認為國民黨有了足夠的“要價”資本,選擇在此時機掀起反共浪潮,制造了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蘇聯向國民黨提出抗議,但同時要求中共保持克制,蘇聯的調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蔣介石停止反共,但也讓中共的決策和反擊受到掣肘。蔣介石雖未直接破裂中蘇關系,但國民黨同蘇聯的關系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惡化,中共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也發生轉變,蔣介石借機投向英美陣營,削弱了對蘇聯的依賴。
事變前蔣介石的對蘇態度
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意識到蘇聯援助對于中國抗日的重要性,一開始對蘇態度還算信任,但蔣介石的對蘇態度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在接受蘇聯援助的同時,蔣介石對蘇聯也是心存芥蒂的。這種對蘇態度的搖擺也影響著他對中共的看法。在蔣介石看來,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與蘇聯保持著微妙的關系,中共問題不是單純的國內問題。因此,蔣介石始終將中共及其軍隊視為蘇聯的代言人,對其保持提防。
蘇聯不希望同時面對東西兩線作戰的壓力,就必須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以期日本兵力被拖延在中國戰場而無力北上。但中國同時存在國共兩股勢力,讓蘇聯的援助工作必須進行多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中共作為自己的同志,斯大林深知“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切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作為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的正式政府,蘇聯無法繞過國民政府而將主要軍事援助給予中共,畢竟斯大林擔心“這種援助看起來像是向一個我們與之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會使蘇聯在國際輿論中陷入被動。
盧溝橋事變后,中共為爭取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寇,于1937年7月15日發表宣言,表明“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其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合作”。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回應,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以及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盡管蔣介石并不信任中共從“反蔣”到“聯蔣”的轉變,認為這是蘇聯的陰謀,但無論如何,國民黨軍隊翹首以盼的蘇聯軍事援助已經開始了。1937年10月17日,第一批蘇聯軍用物資由薩雷奧澤克運往蘭州,包括大炮、各式機槍、彈藥以及航空和裝甲設備共約6萬件。斯大林對國民黨的援助是誠懇的,除了軍用物資外,還愿意幫助中國擁有“自己的石油生產……發展自己的重工業”,蘇聯成為這一時期對華援助最大的國家。但蔣介石顯然更希望獲得英美的支持與援助,寄希望于布魯塞爾會議上英美等國可以幫助協調,而英美并不愿意過早地卷入中國戰場的渾水中,他們在布魯塞爾會議上“執行了犧牲中國人民討好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路線”,美國甚至在布魯塞爾會議前夕和會議期間“認為日本和中國都是戰爭禍首,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為一談”,相比之下,蘇聯在會議上明確表示“愿意參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行動”。面對英美含糊其詞以及缺乏實質性幫助的回應,蔣介石迫不得已選擇“聯蘇制日”。要聯蘇,那么蔣介石就無法回避中共問題。表面上的合作關系不能消減蔣介石對中共的忌憚,對中共的限制特別是中共軍隊的限制貫穿這一時期。1938年1月4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向蔣介石申請八路軍的武器裝備,但蔣介石竟以“連壞槍都發出去了”為由拒絕周恩來的請求。同年7月下旬,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時又以“國民革命軍已滿200個師的限額”為由拒絕再給八路軍新的部隊番號。
1939年8月23日,蘇聯為了緩解《慕尼黑協定》后形成的對己不利的國際局勢,同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同年9月,蘇聯又與日本簽署《蘇日諾門坎停戰協定》。蘇聯開始同德國、日本緩和關系,這讓蔣介石秉持的蘇日必戰的認知被顛覆。蔣介石對蘇聯更加不信任,認為蘇聯表面宣傳國際主義,而實際上已是大國沙文主義,其對德國和日本的態度表明,蘇聯“偏袒侵略國”,形成“左倭右德,以佐其稱霸歐亞兩洲”的局勢。蔣介石對蘇聯態度的轉變直接影響到其對中共的態度。1939年11月11日的國民黨密令中就提到,分布在中共邊區周邊的各縣,要“充實力量,逐步削弱偽邊區,使其范圍不致擴大”。但考慮到蘇聯的援助仍是必需的,蔣介石不急于公開反共。例如,1939年11月24日蔣介石得知國民黨無空閑飛機接送在延安受傷的周恩來至莫斯科養病后大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可見,蔣介石還在考慮中蘇關系的保持,他絕不愿看到蘇德日聯合,盡管蘇聯并無此種想法。
1940年,國際形勢迅速變化。歐洲戰場上德國不斷推進,意大利參戰,法國投降,英國退守本土,亞洲戰場上日本也欲乘英法等國無暇東顧之際,迅速結束對華戰爭以進攻東南亞地區,美國仍受國內孤立主義影響而舉棋不定。德意日三國簽署《柏林公約》后,英美為了阻止日本南下,由勸和日本的東方慕尼黑政策轉到利用中國牽制日本的政策,開始拉攏蔣介石。這樣,蔣介石就處在三股勢力同時拉攏他的形勢下。首先,德國希望勸和中日以幫助日本南下牽制英美,日本也希望借此機會停戰以南下開辟新戰場,是戰是和,蔣介石的選擇直接影響著世界戰爭的走勢。其次,蘇聯仍然保持著對國民黨的援助,蔣介石根據軍統中蘇情報所的消息,認為“此次日德意軍事協定,對俄之威脅,比對美尤為嚴重”,畢竟美國有大洋相隔而蘇聯直接與日德兩國相鄰,這無疑加大蔣介石向蘇聯“要價”的資本。再次,英美的橄欖枝也拋向蔣介石,包括向中國派遣美國志愿航空隊、向中央銀行提供貸款、英國重開滇緬公路等,蔣介石如愿以償成了英美在亞洲戰場最重要的盟友。“國際上三大力量這樣或拉、或誘、或援的結果,使蔣介石感到身價陡增,忘乎所以,好像歷史給了他一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難得機會。”似乎蔣介石頭痛已久的中共問題已可以從政治手段謀求解決轉向軍事手段了。
中共在1938至1940年的兩年多時間里,領導的抗日武裝部隊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中共勢力的發展壯大讓國民黨內部出現許多軍事反共的聲音,特別是1940年10月謀劃已久的黃橋戰役,不僅沒有打擊到新四軍,反而是新四軍殲滅國民黨軍韓德勤部一萬余人,讓蔣介石和一眾國民黨高層將領坐立難安。再加上江蘇、安徽作為中國的交通要道,是連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略要地,蔣介石自然不愿看到這一地區被中共所掌控。黃橋戰役后,國民黨將沖突的起因推到新四軍頭上,何應欽、白崇禧以此為由要求“新四軍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斗序列”,并在“壹個月內全部開到……規定地區內(即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面對國民黨的步步緊逼,毛澤東結合國際局勢的變化敏銳地意識到,蔣介石的反共行為是為投降日本做準備,而要想阻止蔣介石集團投降,就必須借助“蘇聯的壓力”,因為“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但此時的蘇聯為確保自己遠東地區的安全,急需中國加緊抗日以牽制日本。因此,蘇聯對中蘇關系極為重視,不僅斯大林親自致電蔣介石鼓勵其抗日,而且繼續向國民黨運送抗日所需物資,同時還派出崔可夫將軍來華擔任軍事總顧問。在崔可夫出發前,斯大林同他面談。斯大林希望崔可夫“摸清蔣介石陣營的情況,估量蔣介石的實力并利用蔣介石總軍事顧問的權力使中國軍隊積極作戰”,同時,還要“遏止蔣介石反對共產黨軍隊和對共產黨人控制的游擊區抱有的黷武圖謀”,換句話說,“就是阻止蔣介石打內戰,使他動員全國一切力量去反擊侵略者”。所以,崔可夫必須“協調中國紅軍和蔣介石軍隊的抗日行動,而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可見,斯大林的首要想法仍是從中調解國共關系以敦促兩黨同心抗日,哪怕明知他們之間存在分歧。
蔣介石顯然意識到自己的抉擇對于蘇聯的重要性,這讓他在面對崔可夫時有了充足的底氣。當崔可夫第一次與蔣介石會面時,蔣介石就曾告訴崔可夫,“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行善的施主,我的友誼,至少,我的中立,在希特勒軍隊撲向東方時,對你們是很有用的”。蔣介石沒有因為蘇聯的援助而對中共改觀,反而助長了他的反共信心,他深信蘇聯離不開中國對日本軍隊的牽制,這讓他敢于用武力手段同中共產生摩擦,盡管中共已經選擇做出讓步并準備退出皖南地區。
1941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余人向北轉移時,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隊圍攻,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經過一周的慘烈戰斗,被伏擊的新四軍除2000余人突圍外,大部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亦被扣押。
蘇聯和中共對事變的反應
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和蘇聯表現出不同的態度。皖南事變的爆發讓中共措手不及。在事變發生時,毛澤東不認為這是一次單純的軍事行動,而將其聯系為國民黨企圖投降日本的表現,因此在1月14日國民黨軍事行動一結束,毛澤東就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要求山東、蘇北的軍隊“待命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同日,為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毛澤東向共產國際發電報,說明事態及中共的計劃,表明“我軍有被徹底消滅的危險”,“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蔣介石所實行的這種廣泛的進攻以有力的反攻”。第二日,毛澤東在發給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中,再次提到“調和退讓論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先前對蔣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同時,他還要周恩來去質問新上任的蘇聯總顧問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可見,毛澤東此時極為憤怒,是決心準備以軍事手段反擊的。
崔可夫在事變發生前毫不知情。據他回憶,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軍官向蘇聯顧問們刻意隱瞞了這一事件,“我們的軍事顧問既沒有這樣的事實,也沒有這樣的文件。中國將軍們隨意欺騙他們”。崔可夫雖然迫切希望得知事變的消息,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發表意見時必須要仔細斟酌、小心謹慎,免得被視為蘇聯干涉盟國的內政,因此,崔可夫只能不斷詢問事件的經過和真相而無法表現出明確的反對態度。雖然崔可夫內心十分同情中共,但是,如果“公開講出這種同情,就會使蔣介石疏遠我們……同時,如果我們公開宣布支持共產黨,那么,蔣介石在他的西方庇護者和他的國民黨同僚們的壓力下可能再次使我們的關系產生麻煩,而這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可見,崔可夫還是站在蘇聯遠東政策即中國拖住日本、避免蘇聯遠東接敵的角度上思考皖南事變,他不希望因為事變而使國共走向徹底的對立。而在1月13日,崔可夫告知蔣介石,蘇聯先前答應援助國民黨的飛機已經到達了,這一原本就在蘇聯計劃中的援助被蔣介石錯誤地認為是蘇聯在以軍事援助換取國民黨對中共軍隊的“饒恕”。
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內各方勢力的反對聲音此起彼伏,但1月17日,蔣介石依然強硬決定“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蔣介石認定中共背后的蘇聯不會因此提出強烈抗議而與國民黨翻臉。中共雖意識到蔣介石的反共陰謀,但為抗日大局,并未直接將斗爭矛頭指向蔣介石本人,而是將國民黨中的親日派作為斗爭目標。在1月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中就聲明要求,“嚴懲陰謀消滅新四軍皖南部隊之罪魁禍首”,“肅清何應欽等一切親日分子”。
如蔣介石所料,蘇聯和共產國際確實沒有做出強烈的反應,但仍憑借其在國共兩黨之間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種措施來協調國共關系。1月17日的命令發布后,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蘇聯大使等人就頻頻向國民黨提出批評,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更以拒絕出席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宴會的方式顯示蘇聯的不滿。1月25日,蘇聯大使潘友新向蔣介石指出:“國民黨軍隊進攻新四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但蔣介石卻反口污蔑是新四軍先動手襲擊國民黨軍隊。在1月27日的《真理報》中,蘇聯刊發關于皖南事變的報道,指出皖南事變是出于國民黨的“黨派褊狹之動機”,此舉“無異擴大內戰,而內戰唯有削弱中國而已”。除了向國民黨方面顯示不滿,蘇聯和共產國際還向中共傳達建議。1月20日,季米特洛夫來電給毛澤東,告知“蔣介石請莫斯科將最近的事件(即皖南事變)視為地方上的軍事事件,不要賦予它政治意義并廣泛宣傳”的觀點。季米特洛夫希望中共不要主動破裂國共關系,只應將斗爭矛頭指向親日派,還要求中共為緩和與國民黨的關系作某些讓步。毛澤東收到季米特洛夫電報后回復,“既然蔣介石反對我們,那我們就不能再做讓步,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這種讓步不能團結群眾”,“我們必須全面抗擊蔣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讓步,要么是同他徹底決裂”,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堅決予以回擊,但在軍事上“暫時只能進行防御”。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做法是正確的,對國民黨的政治回擊不僅沒有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使中共博得了廣泛同情與支持,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
對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態度,毛澤東顯然十分不滿。據師哲回憶,毛澤東在皖南事變后向共產國際發了一份綜合、分析性長電,既總結了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也是“提醒和告誡遠方的一些無知、膚淺的人”。當時,對于中國共產黨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們主張以斗爭求團結,而共產國際則要求我們完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
事變后蔣介石的對蘇策略
1月17日的命令在國內國際都引發巨大反響。國內的中間派、進步人士和海外愛國僑胞都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譴責國民黨這一“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就連國民黨內部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和不解,如孫科、衛立煌、馮玉祥等人都極力勸和,堅定維護國民黨利益的王世杰也希望局勢緩和下來。在國際上,蘇聯率先表示不滿,英、美也同唱一個調,通過各種方式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府則顯得十分滿意,汪精衛在南京發表講話稱,“蔣介石近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只有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借國共不和之際,日軍出兵進攻皖南新四軍余部,之后又反過來“掃蕩”華中地區的國民黨軍隊,至1月下旬,日軍趁國民黨軍集中精力于華中之時大舉進攻河南。這一系列的形勢變化顯然出乎蔣介石的預料。
為了擺脫被各方指責的窘境,蔣介石及何應欽等人選擇隱瞞真相并收斂行動。1月19日,令王世杰通知中央通訊社,“對于新四軍事,不宜再發消息,刺激共產黨人”。1月24日時,又對王世杰說,“對于共黨,在軍事方面須嚴,在政治方面不妨從寬”。1月27日,何應欽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強裝鎮定發表演說,重復皓電、齊電的內容,還聲稱“制裁新四軍是為了整飭軍紀,加強抗戰”。而據2月1日的蔣介石日記,美國對皖南事變亦不支持,“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因受共產黨蠱惑,援華政策,幾乎動搖”。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與諒解,蔣介石在2月10日會見羅斯福總統代表居里時,解釋自己的目的即“阻止中國成為一赤化之共產國家”。可見,蔣介石雖不愿拉下臉來同中共妥協,但已決定采取一些緩和措施,以免失去其他國家的支持,因為他一直將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蘇這些大國的援助上。
蔣介石清楚地了解蘇聯為什么不以更激烈的措施來抗議皖南事變。從1937年蘇聯開始援華,主要的軍事裝備都給了國民黨軍隊,這絕不是因為國民黨同蘇聯的關系要好于共產黨同蘇聯的關系,而是身處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可以更好地拖住日本,以達成蘇聯的遠東戰略目標。因此,蔣介石依靠蘇聯是不得已而為之,并不希望將蘇聯作為長期依靠的對象,這也是他為什么更看重英美的態度。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態度更多的是韜光養晦,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大國的陸續參戰,他認定,“不患國際形勢不發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之決心”。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將這一方針形象地稱為“苦撐待變”。那么,隨著美國對華對日態度的轉變,蘇聯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就大不如前。若蔣介石在此刻低頭,不僅關系到國共兩黨關系,更關系到中蘇兩國關系,他擔心中共會在未來借蘇聯之勢壓制國民黨,這是蔣介石不希望看到的。蔣介石雖表面上沒有采取惡化中蘇關系的做法,但借這個時機提出修改對蘇合作政策的問題,聲稱,“從蘇聯獲得援助,就會使中國處于對共產主義國家的依附地位”。至《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和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對華援助逐漸減少。
抗日戰爭時期,蘇聯為避免遠東戰事向國民黨軍隊提供軍事援助,這讓蔣介石認為“蘇聯亦非借重他不可,遂放手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后,蘇聯又利用其與中共的特殊關系,通過共產國際來影響中共的政策,限制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從而給中共的反擊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蘇聯雖然沒有因事變而停止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但蘇聯表現出的反對態度是蔣介石迅速停止反共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見,蘇聯做法的兩重性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現實需要,而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缺乏考慮。盡管蘇聯本意是調和國共關系一致抗日,避免事態擴大,但無論中共還是國民黨都在皖南事變后疏遠了同蘇聯的關系。中共雖繼續保持著同共產國際之間的上下級關系,但在皖南事變后已更加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毛澤東于1941年5月19日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他已經深刻認識到不能“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只有獨立自主的決策才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更好地結合起來。而蔣介石趁世界形勢的變化迅速投向英美陣營,逐步削弱對蘇聯的依賴。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級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 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