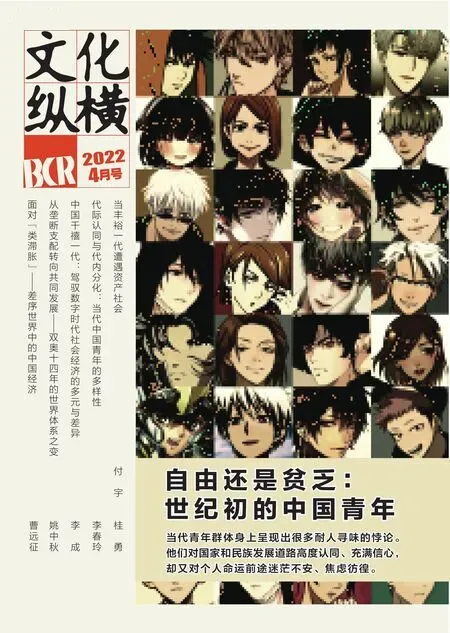自主抑或依附:印尼發展道路的三重陷阱
孫云霄
包括蘇加諾、哈達和普拉姆迪亞在內的印尼精英將中國的獨立自主視為現代化的可選擇道路,一度期待“中國的今天是東南亞的明天”。
在1952年印度尼西亞獨立七周年慶祝大會上,國父蘇加諾發表了印尼民族獨立的雄心宣言:“我們致力于建立一個豐衣足食、一切重要的必需品都能自給自足的國家。”[1]此后不久,印尼國家領導人與知識分子紛紛前往新中國“取經”。包括蘇加諾、哈達和普拉姆迪亞在內的印尼精英將中國的獨立自主視為現代化的可選擇道路,一度期待“中國的今天是東南亞的明天”。[2]但是,此后印尼的發展卻經歷了“遲滯的工業化”“早熟型去工業化”與“再工業化”的波折,建國一代堅定自主發展的國家意志在國外壓力與國內動蕩下不斷消磨,落入依附性發展的陷阱之中。印尼的工業發展歷程是東南亞眾多后發國家的縮影,它們在完成農業文明向工業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始終面臨著經濟、政治與文化困境。
一、擺脫外資依賴的國家自主道路
如大多數后殖民國家一樣,1945年獨立的印尼面臨的經濟情況并不樂觀。盡管荷蘭殖民者于20 世紀30年代在印尼本土開啟了工業化進程,促使制造業的總增加值在1932~1941年間達到了7%的平均水平。[3]但是,“二戰”的白熱化和日本的入侵迅速瓦解了這個并不成熟的工業體系;1945~1949年荷蘭殖民者的反撲進一步破壞了工業結構,阻礙了新生印尼工業的復蘇。
為了擺脫初建國家的工業困境,印尼于1949年發布了首份“特別工業發展計劃1950”。該計劃主要有三方面內容:擴大能夠使用本地原材料生產新產品的技術機構的數量;由外國專家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在特定大型工業企業中進行上游基礎產品的生產;使用62%的預算在1950~1954年間建立69 個工業中心,促進家庭手工業和小型工業的發展。特大型工業企業助力大城市發展,而遍及全國的工業中心惠及廣大農村地區。
資金與技術短缺是工業起步的難題。議會內閣先后于1951年和1956年推出“經濟緊急計劃”和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以具體落實工業規劃。“經濟緊急計劃”允許外國直接投資進入“非必要”產業。為實現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政府主動參與七項大型項目,以本土產品代替進口,節約外匯。在這個過程中,一批國有棉紡廠、椰干廠、印刷廠得以建立;一批大中型私有企業被政府收購,國有大中型企業數量從1940年的5473 家增加到1954年的9877 家。國家金融同時向紡織廠、橡膠加工廠等農村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和生產進口替代品的中型企業提供流動資金和設備投資的優先信貸。[4]“五年發展計劃”則試圖以外國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資為基礎,吸引國外制造商與本土商人合作生產進口替代產品,填補國內技術的空白。
1957年,蘇加諾重掌政權后,提出“有領導的經濟”,推出“八年發展計劃”,意在加強印尼經濟的國家自主性,糾正之前對外資的依賴性。
但這一系列工業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執行。20 世紀50年代初期,印尼實行議會內閣制,政治狀況混亂,政黨斗爭激烈、內閣頻頻更迭、地方分裂運動此起彼伏。在追求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依賴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工業政策受到廣泛抨擊。1957年,蘇加諾重掌政權后,提出“有領導的經濟”,推出“八年發展計劃”,意在加強印尼經濟的國家自主性,糾正之前對外資的依賴性。一方面,蘇加諾通過沒收和接管外資企業,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的規模,1964年國有企業數量已經增至24332 家。[5]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倡導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態度,主張國有企業應該擺脫外資依賴,以自有自然資源開發解決資金問題。“八年發展計劃”提出的方案是由印尼人擔任領導,外國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的經濟合作的形式進行,最大限度在經濟發展中保持獨立自主。[6]
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才剛起步,印尼就迎來了嚴峻的國際環境。1963年,英國主導成立了包括與印尼同宗同源的沙巴和沙撈越在內的馬來西亞聯邦,徹底激化了蘇加諾與西方國家的矛盾。蘇加諾不僅發起“粉碎馬來西亞”行動,同時宣布退出聯合國,拒絕西方國家的一切資金與技術援助。在此情形下,經濟形勢每況愈下,1960~196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僅為2%,低于1953~1959年的平均增長率3.2%。[7]
蘇哈托時期的工業發展契機得益于石油產業的繁榮。
二、不斷消磨的國家意志與依附性發展
經濟情況的惡化加速了蘇加諾政權的隕落,1965年蘇哈托發動政變,開啟“新秩序”時代。上臺伊始,蘇哈托并沒有即刻進行工業化建設,而是通過一系列財政、金融、匯率措施穩定瀕臨崩潰的經濟形勢,進一步鞏固政權。另一方面,蘇哈托一改拒絕西方國家援助的態度,不僅于1966年將國有化的外資企業歸還原主,而且于1967年頒布《外國投資法》及相關條例,通過給予外資優惠待遇積極爭取外商投資和外國援助。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成立國際開發署,以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為指南,幫助越南、印尼等國發展經濟,防止它們走向共產主義陣營。自1967年起,印尼持續從美國、日本、荷蘭等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組成的“援印尼國際財團”取得長期低息貸款。這些貸款并未立刻用于工業發展,而是注入農村人口控制項目,在農村修建節育診所、培養節育醫務人員和組織大規模移民,控制農村人口,壓制印尼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的強大影響力。[8]

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后,印尼政府放任IMF在經濟改革中居于主導地位
蘇哈托時期的工業發展契機得益于石油產業的繁榮。1973年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為印尼帶來了豐厚的資金。此后,蘇哈托期望建立印尼的自主產業,馬上調整了外資政策:規定所有的外來投資都必須與本土企業合資,且本土企業占股51%以上;限制外資進入特定產業;并限制外籍員工人數。這期間,國有企業仍然是主要承擔者,在強化基礎工業(如鋼鐵、水泥、化肥)和發展高技術戰略企業(如飛機制造、造船、國防工業、電信)發揮重要作用。在充足的資金基礎上,印尼經濟政策的重點開始轉向內需,謀求培育本國市場與私營企業。國家通過征收進口稅、限制進口額、制定本地零部件含量標準、發放許可證、政府訂單等措施,鼓勵本國私企開展進口替代,紡織業、電器業、汽車業蓬勃發展。[9]從1969年到1984年,蘇哈托政府順利實施了3 個“五年計劃”,并在20 世紀70年代經歷了制造業騰飛。1969~1978年間,印尼制造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都在13%,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8%,堪稱亞洲奇跡。[10]
但是,1982年和1986年國際石油價格暴跌導致印尼財政出現困難。工業政策不得不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在以出口為目標的國際市場上,印尼已落后于做了十余年國際代工廠的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因此被稱為“遲滯的工業化”。對外資與技術的再次依賴迫使印尼于1983年開啟經濟自由化改革,不斷簡化進出口審批程序,取消進口特需壟斷體制,降低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放開外資限制。1991年的第二輪自由化改革更是放開了港口、電力、通信、航運等重要部門的外資限制。兩輪改革直接導致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懸殊等嚴峻的經濟問題。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成為壓垮蘇哈托統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8年印尼開啟的民主改革不僅是一次政治變革,也是一場經濟轉型。亞洲金融危機在一夜之間卷走了印尼過往近五十年的發展成就。由于急需擺脫經濟危機,穩定國內政治環境,政府不得不“飲鴆止渴”,又回到了依賴國際資本與西方國家援助的道路上。蘇哈托后期制定的第二個“二十五年長遠規劃”(1994~2019)和第六個“五年計劃”(1994~1999)都在經濟危機和政治變革中被迫中斷,代之以IMF 更激進的經濟自由化改革。IMF 改革的主旨是推動印尼國內市場全面開放。經過六年時間,印尼逐漸走出經濟危機,宏觀經濟走向穩步增長。但是,伴隨民主改革而來的政治動蕩和領導人頻繁更替使得印尼缺乏長遠的經濟政策規劃,甚至放任并不熟悉印尼本土情況的IMF 在經濟改革中居于主導地位。
2004年是印尼從改革陣痛期走向平穩期的分界線,蘇西洛成為改革以來首位保持穩定期限執政的總統,這有利于印尼制定更符合國情的工業化政策。但是,工業基礎薄弱、國內市場丟失、貪污腐敗橫行、新的經濟發展政策收效甚微。2001~2016年,印尼制造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由29.05%下降到20.51%,出口份額由0.68%下降到0.56%,進口份額卻由0.54%上升至0.8%。[11]由于印尼的人均收入仍處于較低水平,因此這一制造業衰退現象被稱為“早熟型去工業化”。
伴隨民主改革而來的政治動蕩和領導人頻繁更替使得印尼缺乏長遠的經濟政策規劃,甚至放任并不熟悉印尼本土情況的IMF 在經濟改革中居于主導地位。
三、國家自主發展道路的三重陷阱
雄心勃勃的印尼國父蘇加諾,曾期望以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塑造擁有寬闊國土與海域、巨量人口基數、豐富礦產資源的主權國家,贏得國際競爭的入場券。但在向工業資本主義轉型中,自主發展的國家理性不只要面臨國際壓力,還要受制于印尼自身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困境。
印尼政府對資源的依賴給經濟帶來危機,也給政治權力帶來結構性難題。
(一)資源經濟紅利與政治不成熟
印尼是一個礦產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早在殖民時期,印尼的香料、熱帶經濟作物與礦產資源便是荷蘭政府的重要經濟來源。蘇加諾的自主性工業發展政策也高度依賴礦產資源開發計劃,“八年發展計劃”旨在以礦產資源開發獲得的收入支持國民經濟建設。[12]其中,只在礦產資源開發中接受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以最大程度減少外國資本的滲入。
盡管蘇哈托借助經濟危機推翻蘇加諾政權,但其隨后實施的經濟政策仍然沿著資源補給資金的邏輯。一旦石油出口帶來了充足的建設資金,蘇哈托便對外資進入印尼市場進行了實質性的限制,將石油收入投入廣泛的工業化建設中。1973年國際石油價格猛漲開啟了石油紅利階段,為印尼經濟政策轉型提供了契機。從1969/1970年度到1983/1984年度,石油公司上繳的稅金在印尼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9.8%上升到66%。[13]印尼政府不僅擺脫了依靠援助才能維持常態運行的被動局面,更有了充足的資金發展工業。據統計,1973年和1979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大量資金被用于發展資源提煉與石油化工等產業。[14]

石油對于印尼而言,究竟是“恩賜“還是“詛咒”?
但是,石油對于印尼而言,究竟是“恩賜”還是“詛咒”呢?[15]在資源詛咒理論看來,印尼政府對資源的依賴給經濟帶來危機,也給政治權力帶來結構性難題。首先,攫取資源的定位使得荷蘭對印尼的殖民不同于英國之于印度。作為戰備工業中心,印度在殖民時期即已建立了遠超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業化基礎和生產力水平。[16]荷蘭卻伙同英美等國將石油礦山的勘探和開發作為主要產業,怠于在印尼進行工業化建設,導致印尼在獨立后面臨基本從零開始的困境。由荷蘭殖民者統治的印尼并未培養出充足的本土行政管理和技術人才,管理的落后和技術人才的缺乏掣肘了印尼的工業化進程。蘇加諾的“八年發展計劃”在工廠層面的實施中淪為紙上談兵。
獨立后,資源經濟不僅讓印尼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更導致印尼精英集體政治不成熟。
其次,獨立后,資源經濟不僅讓印尼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更導致印尼精英集體政治不成熟。“躺著掙錢”的便利使得政治精英要么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與“虛胖”的國民生產總值,要么短視地犧牲基礎工業與技術研發能力,不顧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利益。蘇哈托時期盡管擁有高速的經濟發展數據,但第二輪自主產業發展基本還是圍繞石油產業展開。坐享石油紅利讓印尼患上了“荷蘭病”——“國家發展專注于自然資源的經營,往往排擠其他產業的發展”。[17]即使是資源下游的提煉工業,印尼也直到20 世紀90年代才開始發展。即便到了民主轉型十余年后的21 世紀初,印尼依然未將資源的下游產業發展起來,擺脫不了對資源的依賴。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占優勢的行業。但印尼在20 世紀80年代中期遭遇石油危機后,才被迫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蘇西洛在任時期,發布了禁止原油原礦石出口的禁令,卻導致數個資源型大型國有企業很快瀕臨破產,以至于后來的佐科不得不恢復原油原礦石出口。[18]
最后,印尼精英依托國際石油市場與外國資本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同樣是資源型國家,委內瑞拉依靠資源紅利建立起“蓬托菲霍體制”,精英集團與社會中下層共享紅利,從而兼得國家的穩定與發展。[19]但是,印尼長久以來只建立針對軍隊與公務員等少數特權群體的精英型社會保障體系,直到2004年才通過普惠性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法案》,并遲至2011年才付諸實施。而且,在歷次經濟危機與改革過程中,與市場開放相伴隨的是國際資本的游說、行賄與輿論,讓印尼精英階層逐步淪為尋租腐敗型社會團體。
(二)自由化改革與經濟主導權的喪失
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指出:“當印尼經濟發展態勢良好時,政府大概率會采取保護主義措施,而當經濟不好時反而會采取更為開放的政策。”[20]印尼的改革開放總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乘火打劫”。誠然,蘇哈托初上任時對外資和外國援助的開放挽救了瀕臨崩潰的印尼經濟,也穩定了這個新生國家的政權和統一。但此后在經歷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時采取的自由化改革,卻給印尼工業化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印尼在石油紅利期并沒有建立起牢固的工業基礎,國企和中小型企業基本都仰賴石油收入運營,一旦石油收入銳減,整個國家經濟體系便陷入困境。蘇哈托政府意圖通過自由化改革,開放印尼的投資市場,大力引進外資以彌補石油收入銳減帶來的危機。但這一過程極大地破壞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它們不僅在貨幣貶值中利益受損,更要面對國外消費品的強大競爭力。[21]
經歷經濟自由化改革“洗禮”的印尼已然是外資的樂園。對全球市場的依附使得國內逐漸興起了與國際接軌的利益階層。
1997年經濟危機中,蘇哈托再次寄希望于IMF 的自由化改革計劃。但是,IMF 的激進改革卻徹底擊潰了處于危險邊緣的印尼經濟。改革伊始,IMF 便在印尼策劃關閉了16 家銀行,引起銀行系統的恐慌,三分之二的銀行出逃,引發整個銀行體系的崩潰。此后,IMF 叫停了15 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并以暫緩貸款支持為威脅要求蘇哈托政府接受“一攬子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廢除小麥、大豆的進口壟斷,廢除水泥、紙的卡特爾,降低化學品、農產品的關稅,撤銷國民車計劃的優惠待遇,放寬對批發、零售的限制,撤銷對民間企業外債的政府保證等。[22]IMF 甚至出動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政要向蘇哈托施壓,要求其實施相關改革計劃。[23]可以說,IMF 強硬的激進改革計劃否定了印尼此前運行二十余年的工業體系。IMF 并未深入考察印尼具體國情,一味地推行所謂的自由化改革,不但沒有控制危機,反而進一步擴大和加劇了危機,最終成為蘇哈托政府倒臺的催化劑。
民主改革后的三屆政府為了獲得援助,仍然與IMF 合作應對經濟危機。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的努力下,政府經過數輪談判和協商逐漸從IMF 手中收回經濟改革的主導權。但是,即使重獲經濟主導權,此后的蘇西洛政府仍無力帶領印尼走出早熟型去工業化的泥淖。盡管資本能夠迅速買來技術,但是擁有技術并不等于擁有技術能力。[24]后者是靠國家政策的精心呵護與長期積累而成。印尼的自主發展政策不斷被國際局勢與國內動蕩所打斷,根本不具備內生的技術能力。這導致印尼工業產品技術更新速度緩慢,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只能將中低研發密度制造業作為主體,產業升級困難。IMF 推動的自由化改革更是擠占了國產工業產品的市場空間,直接將自主創新的技術能力扼殺在“真空”之中。
經歷經濟自由化改革“洗禮”的印尼已然是外資的樂園。對全球市場的依附使得國內逐漸興起了與國際接軌的利益階層。在石油經濟中,他們逐步形成資源型腐敗,能源礦產領域高官腐敗頻發。在自由化改革中,他們又伴隨著民主化與商業化向市場型腐敗發展。當精英階層的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相沖突時,他們常常不顧民族的未來而選擇保護自己的利益。面對集體性腐敗,蘇西洛在百日肅貪行動后也只能感嘆“新民主需要時間消除腐敗”。
(三)國家整合與政治改革陷阱
急速的現代化進程要求新生國家具備更高層次的政治整合能力。經濟、社會現代化不一定會自生自發出民主政治,后發國家往往需要人為建構有效的政治組織,以整合日益分裂的種族、階級、宗教與宗族等社會集團。[25]否則,經濟發展反而會帶來政治動亂與政治撕裂。

碎片化的地理形態,使印尼的國家建設與國族整合頗為棘手
碎片化的地理形態、多元的社會文化和分裂的歷史狀況,本就使印尼的國家建設與國族整合頗為棘手。[26]對于統一民族的塑造,印尼或是缺乏一場偉大的革命戰爭,或是缺乏強大有效的政黨組織。這讓奠定在妥協基礎上的國家缺乏必要的內聚力與自主性,經不起少數幾個軍人的推翻或少量金錢的腐化。印尼的工業化路徑和效果進一步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化以及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印尼的礦產資源大都分布在巴布亞、亞齊等外島偏遠地區,而全國的行政與工業中心又集中于爪哇主島。這就導致中央政府所在的爪哇主島必然依賴由國家財政支撐的軍隊與官僚體系來維持對邊緣島嶼的支配,蘇哈托時期的工業化正是此種“爪哇中心主義”的經濟結構表達。軍事威權反過來又鑄就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將外島資源用于爪哇的建設,石油紅利時期的基礎建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就集中于爪哇主島。“爪哇中心主義”的工業建設導致區域發展極不平衡,中央與地方關系十分敏感。
世紀之交以來的民主改革不僅無法彌補印尼的整合難題,反而消解了原有的國家意志。2004年,印尼實現總統和副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2005年起,省、市、縣級行政長官與立法機構由當地直選產生。憲法改革導致一夜之間誕生了550 個縣級“小王國”。直選進一步弱化中央統領權力,更催生了一切為選舉服務的政治生態,當權者常常將勞動福利作為贏得選舉的籌碼。根據民主改革后的勞工制度,最低工資標準由各地政府自行制定。為了在選舉中獲得高支持率,大部分地方政府首領選擇制定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且年增長幅度達到8%;對企業遣散工人的責任設定得也比較大,達到32 倍月薪。這導致企業大量雇用臨時工,以規避正式用工的高成本;缺乏穩定熟練工人的企業也怠于進行員工培訓和產業升級,難以形成強勁的競爭力。據統計,2005年后日本車廠在東盟國家進行的技術轉移與人力資源培訓時,鮮少涉及印尼,而是多集中于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27]
印尼的礦產資源大都分布在巴布亞、亞齊等外島偏遠地區,而全國的行政與工業中心又集中于爪哇主島。這就導致中央政府所在的爪哇主島必然依賴由國家財政支撐的軍隊與官僚體系來維持對邊緣島嶼的支配。
與民主改革一同伴生的去集權化改革將資源審批權和財政權下放至地方政府,地方獲得高度的經濟建設自主權。但地方分權并沒有產生因地制宜、有效發展的效果,反而滋生了尋租與腐敗、行政效率低下、中央權力式微的弊端。印尼不僅無法制定出長期有效的中央經濟政策,甚至無法統領地方貫徹實施已有規劃。一項針對佐科政府《全國性中期發展規劃(2015—2019)》的實施評估表明,脫離民間組織、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的支持,中央政策的推行舉步維艱。[28]在選舉政治的催化下,印尼甚至掉入“諸侯政治”陷阱,既難以形成共識性的全國政策,也無法得到地方政府的貫徹執行。[29]在蘇西洛時期,惠及全民的基礎建設與社會保障政策頒布后始終無以落地。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沒有因分權而改善,爪哇和巴厘島與印尼東部省份的差距與30年前一樣巨大。[30]
大刀闊斧的再工業化改革必定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佐科面臨著重重阻礙。佐科的大量改革一開始就被冠以“再集權化”“新威權主義”的惡名。
四、佐科的“工業4.0”與印尼再工業化前景
2014年,印尼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總統佐科上臺,其首份全國性戰略規劃即試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整合困境,打造一個統一的印尼市場。佐科提出的“全球海洋支點”構想以海洋為承載,致力于打造萬千島嶼間的“海上高速公路”,促進東西部經濟發展平衡。藍圖將海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擴展到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巴布亞等島嶼,建設與雅加達、東爪哇規模相當的大型樞紐港,不僅試圖打破“爪哇中心主義”的發展格局,而且具有快速連接各大群島的作用。
為了改善印尼制造業的落后現狀,佐科政府將“工業4.0”作為印尼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大舉措。2018年的《印尼工業4.0 路線圖》試圖將印尼打造為數字時代的全球制造強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2019年4月,印尼國會通過《工業4.0 預算修正案》,將財政支持總規模提高一倍,達到5.31 萬億印尼盾。2019年開始落實“工業人才4.0 計劃”,意在培養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素質工業人才,解決人才隊伍跟不上技術更新的難題。
大刀闊斧的再工業化改革必定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佐科面臨著重重阻礙。佐科的大量改革一開始就被冠以“再集權化”“新威權主義”的惡名。民主改革后,印尼的社會輿論與民意長期浸淫在西方智庫與媒體塑造的“去集權化”的意識形態之中,但凡涉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改革方案,都會上升為威權或集權的意識形態爭論。2020年10月通過的《創造就業綜合法》將散落在地方的市場審批權限統一收回中央政府,引發全國大范圍游行示威甚至社會騷亂。[31]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印尼的大批基礎建設和工業支持計劃被迫叫停,以應對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企業倒閉、民生保障不足、失業率和貧困率上升等問題。佐科的第二任期已近半,能否在剩余時間中恢復印尼經濟尚屬未知,更遑論改革的接續和效果。2024年,印尼中央政府必將迎來重組。在印尼多黨制的政治氛圍下,每個政黨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團體和打算,佐科的改革措施能否得到下一任政府的認可和繼承也是未知數。為了延續政治意志,佐科培養兒子和女婿參選地方行政長官,但這種家族政治是否會成為印尼發展道路上的又一陷阱呢?
注釋:
[1] 蘇加諾:《蘇加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 頁。
[2] 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NUS Press, 2011, pp.205~274.
[3] [4] [5] Pierre van der Eng,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onesia, 1930-1975,”in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eds.,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13,p.179;pp.188~189;p. 189.
[6] Guy J. Pauker,“Indonesia’s Eight-Year Development Plan,”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1961.
[7] [10] 黃丁蘭:《印尼工業發展戰略調整淺析》,載《南洋問題》1987年第1 期。
[8] Brad Simpson,“Indonesia’s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and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1960-1975,”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3, 2009.
[9] 布迪約諾:《歷史大變局中的印尼經濟》,龔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80 頁。
[11] 林梅、那文鵬:《印尼早熟型去工業化問題探析》,載《南洋問題研究》2018年第1 期。
[12] Guy J. Pauker, “Indonesia’s Eight-Year Development Plan,”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1961.
[13] 林梅:《印度尼西亞工業化進程及其政策演變》,載《東南亞縱橫》2011年第6 期。
[14] Jojo Jacob,“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donesia, 1975-2000,”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3, No. 3&4, 2005.
[15] Jefrey Sachs, Andrew Warner,“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in G.Meier and J.Rauch eds.,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3~208.
[16] 毛克疾:《“印度制造”的雙重困境——印度工業化的曲折道路》,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3 期。
[17] Jeffrey D. Sachs,Andrew M. Warner,“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5398, December 1995.
[18] Ari Kuncoro,“Trend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under the Jokowi Presidency: Legacies of Past Administration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 35, No. 3, 2018.
[19] 高波:《權力結構視角下的發展陷阱——基于對委內瑞拉“蓬托菲霍體制”的分析》,載《國際政治研究》2020年第1 期。
[20] Arianto A. Patunru, Sjamsu Rahardja,“Trade Protectionism in Indonesia: Bad Times and Bad Policy,”Lowy Institute,
[21] Richard Robison,“Authoritarian States, Capital-Owning Cl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1, 1988.
[22] 平田潤:《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危機與政策危機——以印尼為例》,劉曉民譯,載《南洋資料譯叢》2003年第4 期。
[23] Nicola Bullard, Walden Bello, Kamal Mallhotra,“Taming the Tigers: the IMF and the Asian Crisis,”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3, 1998.
[24] 路風:《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9 頁。
[25] 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0 頁。
[26] 孫云霄:《國族與部族:印度尼西亞的雙軌認同》,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3 期。
[27] Yin Ying、戴萬平:《由政治經濟學途徑看印尼產業發展》,載《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第六期。
[28] Kharisma Nugroho, Fred Carden and Hans Antlov, Local Knowledge Matters: Power, Context and Policy Making in Indonesia, Policy Press of Bristol University, 2018, pp. vii-viii.
[29] 孫云霄:《政治多元化與利益整合:基于印尼疫情防控政策的分析》,載《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4 期。
[30] Dirk Tomsa,“Toning Down the‘Big Bang’: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during the Yudhoyono Years,”in Edward Aspinall, Marcus Mietzner, Dirk Tomsa,eds., The Yudhoyono Presidency: Indonesia’s Decade of Stability and Stagnation, ISEAS Publishing, 2015, p. 159.
[31] 孫云霄:《印尼〈創造就業綜合法〉引發騷亂》,載《世界知識》2020年第2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