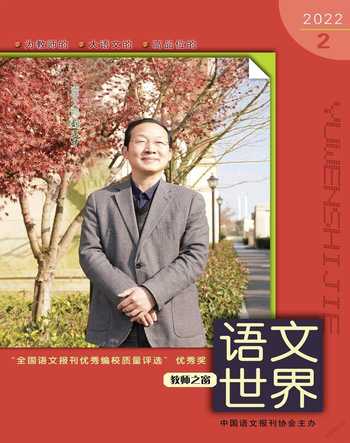審美趣味
葉水濤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賈島的《尋隱者不遇》,以簡短而樸實的話語,寫出一波三折的詩情與意趣。尋找隱者而到達 “松下”,顯見已經找到,隱者之居家近在咫尺。詢問臨門的“童子”,更是滿懷希望——與“隱者”很快能碰面。然而,卻是大失所望——“言師采藥去”——不在家,童子說,他的師父“采藥去”了。不過,接下來童子的一句話,又激起來訪者新的希望——“只在此山中”——未出遠門,就在這山中。那么,總是能夠找到的吧。但是,“云深不知處”。童子的這句話,讓來訪者完全失去了希望——山高林密,云遮霧繞,到哪里去找呢,也不知他何時歸來。于是,徹底失望。希望——失望——新的希望——完全失望,短短四句話,寫出尋訪者起伏跌宕的心理變化。簡樸的語言,雋永的情趣,電影蒙太奇式的鏡頭轉換,是這首詩最鮮明的特色。《尋隱者不遇》尺水興波,言有盡而意無窮,讓讀者領略到無窮的趣味。
顯然,無論讀詩或寫詩,都要從平易中見奇崛,領會與把握其中的佳妙,而對于這種佳妙的愛好與領略就是所謂“趣味”。藝術創作需要才能和技巧,藝術欣賞需要趣味和修養。才能和趣味、技巧和修養是一種相互對應的關系,相輔相成。西方,最早把才能和趣味聯系起來的是康德。在西方美學史上,趣味理論興盛于18世紀。法國美學家夏爾·巴德把科學和藝術相比較,指出科學訴諸理智,而藝術訴諸趣味。藝術中的趣味等于科學中的理智。理智是認清真假并把它們區分開來的能力,趣味則是知覺優劣并把它們正確地區分開來的能力。巴德把理智比作光,它可以幫助人們如實地看清對象;而把趣味比作熱,它誘使人們接近或遠離對象。用現代哲學語言說,理智發現真理,而趣味確定價值。
語言文學屬于人文學科。狄爾泰將其歸類于精神科學,他認為,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根本上的不同:自然科學研究外在于人的客觀或物質現象,而精神科學研究的則是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中心或基本內容是價值和意義的體驗、表達與理解。因此,語文教學必定是訴諸形象的,基于感覺和感性,它需要喚起更多的想象與聯想,從而讓學生有切身體驗的意趣。誠如馬克思所言,唯有人們把一切感覺能力“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覺、情感、愿望、活動、愛”都調動起來,投入其中,才能達到“對對象的全面占有”。如身臨其境那樣沉入對象世界,師生才能有發自內心的審美趣味。語文教學只有通過創設并優化情境,才能寓教于樂,讓學生像魚游水中那樣自然并陶醉,而趣味正是一種內心欣喜的美感體驗。
《文心雕龍》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趣”的基點在“情”。“情”不僅是語言的觸發點——“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而且是語文學科育人的生長點,所謂曉之以理而動之以情。李澤厚主張“情本體”。他在《論語今讀》前言中說:“孔學特別重視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視動物性(欲)與社會性(理)的交融統一。我以為這實際是以‘情’作為人性和人生的基礎、實體和本源。它即是我所謂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核心:‘情理結構’。人以這種‘情理結構’區別于動物和機器。”
審美情趣也是教師精神生活的表征。一個享有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教師,必定具有健康完善的人格和個性。教育家烏申斯基說:“在教育中,一切都應當以教育者的個性為基礎,因為教育的力量僅僅來自人的個性這個活的源泉,沒有教育者個人對受教育者的直接影響,就不可能有深入性格的真正教育。只有個性才能影響個性的發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養成性格。” 冰心說:“一個人應該像一朵花。花有色、香、形,人有才、情、趣。”教師是培育花朵的園丁,更應充溢著才華和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