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而不耀”的《老子》
郭永秉
如果把《老子》看作是中國(guó)現(xiàn)存第一部成體系的哲學(xué)家著作,那么也就可以說(shuō),我們對(duì)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思想的系統(tǒng)性認(rèn)知,是以《老子》為開(kāi)端的。一百多年前,胡適先生出版《中國(guó)哲學(xué)史大綱》,截?cái)啾娏鳎岳献印⒖鬃訛橹袊?guó)哲學(xué)誕生時(shí)代的兩位哲學(xué)家。老子的年輩高于孔子,所以,說(shuō)他是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的開(kāi)山鼻祖確實(shí)并不為過(guò)。
在老子、孔子之前,當(dāng)然也有很多稱得上思想家、政治家的人物,他們立德、立言,成為春秋以后人們效法、引據(jù)的典型;他們的言論本或有篇什記錄,但后來(lái)大多散佚,經(jīng)由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君主、貴族、政治家、學(xué)者之口援引而為我們所知。從現(xiàn)存資料來(lái)看,這些人通常是遵循殷周以來(lái)的傳統(tǒng)政治秩序、道德法則以及言說(shuō)方式來(lái)表達(dá)自己思想的。例如,仲虺(與老彭并稱的商代賢臣)、史佚(周初史官)、周任(上古良史)、臧文仲(春秋前期魯大夫)等先于孔子的著名賢人的箴言,都著眼于人倫、政治方面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的總結(jié):
·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傳·文公十五年》)
·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
· 昔史佚有言曰:“動(dòng)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
·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guó)之道也。”(《左傳·襄公十四年》)
· 仲虺有言,不穀說(shuō)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呂氏春秋·驕恣》)
· 周任有言曰:“為國(guó)家者,見(jiàn)惡如農(nóng)夫之務(wù)去草焉,芟夷蘊(yùn)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左傳·隱公六年》)
·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昭公五年》“仲尼曰”引)
·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yǔ)·季氏》“孔子曰”引)
·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jì)。”(《左傳·僖公二十年》)
· 臧文仲曰:“國(guó)無(wú)小,不可易也。無(wú)備,雖眾,不可恃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傳·文公十七年》)


雖然只是片言只語(yǔ),但從中可管窺早期中國(guó)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官所關(guān)心的主題,大致不外乎如下幾個(gè)方面:第一,國(guó)族對(duì)外的相處、壓制攻取及守備之法;第二,治官、臨民、蒞政之道;第三,君主、貴族個(gè)體的德行修養(yǎng);第四,宗族內(nèi)部的人倫規(guī)范。盡管他們有時(shí)也意識(shí)到“儉”“讓”等卑約之德的價(jià)值,但在主體給予一定克制的前提下,總體上是不否定個(gè)人之“欲”的,主張以積極進(jìn)取的態(tài)度去處理政治與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種情況—對(duì)于外國(guó)、異族要存有戒備,對(duì)于亂國(guó)危邦要侮慢以至攻取,對(duì)邦國(guó)內(nèi)的罪惡要徹底剿滅,重視選任能人、師法賢者對(duì)執(zhí)政治國(guó)的意義等。作為服務(wù)于王朝、諸侯的精英,他們創(chuàng)造、遵循并完善著既有的天下秩序、人倫規(guī)范,適應(yīng)于不斷拓土開(kāi)疆、發(fā)展生產(chǎn)、豐富物質(zhì)的歷史進(jìn)程,嘉言懿行被后世銘記。
然而,被孔子描述成“先進(jìn)于禮樂(lè)”“郁郁乎文哉”的商周古代社會(huì),實(shí)際并沒(méi)有那么美好,尤其是東周以后的歷史逐步演變成“內(nèi)廢公族、外滅人國(guó)”(錢穆先生《國(guó)史大綱》語(yǔ))的失控舞臺(tái)劇。舊有的秩序、規(guī)范、道德被打破了,但又找不到出路、看不見(jiàn)希望,弱肉強(qiáng)食、劣幣驅(qū)逐良幣的法則引導(dǎo)了社會(huì)歷史進(jìn)程的主流。
孔子說(shuō),《詩(shī)》“可以怨”(《論語(yǔ)·陽(yáng)貨》),意思就是《詩(shī)》可用以“發(fā)泄牢騷”(朱自清先生《詩(shī)言志辨》語(yǔ))。按照司馬遷《報(bào)任安書(shū)》中的看法,《詩(shī)》三百篇都是“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的,正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shī)經(jīng)·魏風(fēng)·園有桃》);《周易》《春秋》《國(guó)語(yǔ)》諸書(shū),同樣是古圣先賢因“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而作。在有資格立言的主流知識(shí)分子、貴族之外,其實(shí)還有相當(dāng)多對(duì)國(guó)家社會(huì)前途、百姓命運(yùn)懷有隱憂與不滿的人,他們多半不得遂志,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yǔ)·季氏》),所以要么是選擇做隱士逸民,要么把怨刺寄托于歷史著作、文學(xué)作品中,以抒胸中憤懣。
胡適先生《中國(guó)哲學(xué)史大綱》的開(kāi)篇,就把《詩(shī)經(jīng)》當(dāng)中所反映的時(shí)代思潮歸納為“憂時(shí)派”“厭世派”“樂(lè)天安命派”“縱欲自恣派”和“憤世派”(激烈派)。他說(shuō),這些思潮“沒(méi)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這時(shí)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這些革命種子發(fā)生出來(lái),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時(shí)代。”“老子親見(jiàn)那種時(shí)勢(shì),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產(chǎn)兒,完全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反動(dòng)。”他甚至把老子稱為“革命家”。
老子是不是一位“革命家”,也許還可以討論。我們只知道,老子與史佚、周任身份接近,是服務(wù)于周王朝的“史”(雖然他在王朝內(nèi)的職務(wù)、地位不能與史佚、周任這些地位隆崇的良史相比)。他深通古禮,習(xí)知文獻(xiàn)掌故,然而作為開(kāi)宗立派的思想家,他又呈現(xiàn)出與以往不同調(diào)的、卓立的批判色彩,不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妥協(xié)者。
老子的批判性,并非體現(xiàn)在對(duì)具體人事的形而下反思,也不通過(guò)情感濃烈飽滿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來(lái)鞭撻與控訴,更非訴諸天帝、鬼神以求安慰解脫。他抱有沉重的憂患意識(shí),結(jié)合自身職掌與訓(xùn)練,從古中國(guó)原始思想的元素當(dāng)中汲取養(yǎng)分并加以揚(yáng)棄利用,由此深刻思考終極性、普遍性的問(wèn)題與方法,向統(tǒng)治者提出自己善意的建言。這一整套主張,與前述所有主積極進(jìn)取的傳統(tǒng)治術(shù)大為不同,顯示出老子對(duì)宇宙、社會(huì)、人生深邃的觀察與獨(dú)到的智慧,是對(duì)中國(guó)古代文明高度發(fā)達(dá)時(shí)所凸顯出的各種問(wèn)題的根本性省察。他的睿智箴言雖然未必能為侯王君主所用(甚至未必能為在位者真正理解),卻在以儒術(shù)為基調(diào)的古代政教傳統(tǒng)之中,自然地形成一種巧妙的制衡力量與補(bǔ)充手段,影響至為深遠(yuǎn)。

老子思想清靜無(wú)為的一面為世人所習(xí)知,這是老子重視柔弱之德的智慧。章太炎對(duì)老子學(xué)說(shuō)中“陰騭”之術(shù)高明于儒家的地方評(píng)價(jià)不低。他在《訄書(shū)·儒道》里說(shuō):老聃著五千言,“其治天下同,其術(shù)甚異于儒者矣”。“儒家之術(shù),盜之不過(guò)為新莽;而盜道家之術(shù)者,則不失為田常、漢高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于誘人以《詩(shī)》、禮者,其廟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盜,而道猶勝于儒。”取法道家之術(shù)的政治家,往往具有更多的謀略,考慮得更透徹,比起只重虛文末節(jié)的儒生仍要?jiǎng)龠^(guò)一籌,即便從竊國(guó)者來(lái)看,也是道勝于儒。然而,機(jī)謀深刻,對(duì)于私欲膨脹的君主、政客甚至竊國(guó)者而言意味著什么,章太炎又在《訄書(shū)·儒法》中用八個(gè)字告訴我們:“道其本已,法其末已!”儒道互補(bǔ)、道法相生,在“儒表法里”的政治統(tǒng)御術(shù)主調(diào)之下,老子創(chuàng)立的道家思想從來(lái)不是可以輕忽的低音,它與另外兩者之間構(gòu)成了富有彈性的思想張力,制衡歷史車輪的前進(jìn)。

很多人都以為,主張清靜無(wú)為、柔弱謙卑的老子所設(shè)計(jì)的理想社會(huì),是最終要倒退回徹底棄絕文明、制度的狀態(tài)當(dāng)中的,因此不少學(xué)者站在進(jìn)化論的立場(chǎng)對(duì)老子思想提出批評(píng),認(rèn)為他的設(shè)想過(guò)于脫離現(xiàn)實(shí)。這其實(shí)是一種誤解。徐梵澄先生《老子臆解》認(rèn)為,老子的意思并不與進(jìn)化之理相悖:
若推其意,以人類之不齊,萬(wàn)物之相勝,皆率自然之道而返于樸,則且歸于野蠻時(shí)代,文明亦幾乎息矣,尚何“自賓”“自均”之有?老子之意,蓋不其然。或者,仍誨人以“知止”(引者按: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一句),謂此有其極限也。要之,此不失為一至高遠(yuǎn)之理想。
也就是說(shuō),侯王在“名”既已制作之后,要承認(rèn)這一事實(shí),要“知止”而不可刻意,既要守道無(wú)為,也不可能真倒退到“無(wú)名”的狀態(tài)。如果這種對(duì)于“知止”的主體的解釋合乎《老子》原意的話,那么老子本來(lái)并沒(méi)有真正徹底棄絕文明、歸于野蠻的意圖,確實(shí)是一種“高遠(yuǎn)之理想”。宋人王安石注《老子》十一章說(shuō):“故無(wú)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wú)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lè)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lè)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wú)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也。”陳柱先生《老子之學(xué)說(shuō)》認(rèn)為,“老子亦非不見(jiàn)及此也”,“老子蓋未嘗去有,特以當(dāng)時(shí)之人,皆從事于‘有之為利,而忘夫‘無(wú)之為用,故為矯枉過(guò)正之談耳”。他們的意見(jiàn),可以從《老子》十四章的一句話里得到印證:
執(zhí)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jì)。
“今之道”,傳本和北大漢簡(jiǎn)本《老子》皆作“古之道”,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長(zhǎng)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兩種帛書(shū)本《老子》都作“今之道”,文義較長(zhǎng)。可見(jiàn)老子并不無(wú)視或抵制“今之有”(也就是當(dāng)下既已存在的“有”和“有名”,文明制度、禮樂(lè)刑政這些東西都包含在內(nèi));而且,他主張用“今之道”去控御主宰“今之有”,也就是順應(yīng)既存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以因應(yīng)之法加以治理,而不是執(zhí)一成不變的“道”去應(yīng)對(duì)。但同時(shí),老子又告訴統(tǒng)治者,在這過(guò)程當(dāng)中,要把握道的根本特質(zhì),也就是“大曰逝,逝曰遠(yuǎn),遠(yuǎn)曰返”并最終“復(fù)歸于無(wú)物”的虛無(wú),虛無(wú)才是“道”之根本要領(lǐng)。因此以“自然”“無(wú)為”“清靜”的、合乎道的方式行事才能真正“御今之有”。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shuō)的:“有法無(wú)法,因時(shí)為業(yè);有度無(wú)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shí)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據(jù)同出于馬王堆漢墓的帛書(shū)《十六經(jīng)·觀》(《十六經(jīng)》或稱《十大經(jīng)》,唐蘭先生認(rèn)為即道家著作《黃帝四經(jīng)》的一篇),“圣人不朽”當(dāng)理解為“圣人不巧”,就是說(shuō)圣人不尚機(jī)巧功利,只是順應(yīng)時(shí)變行事而已。太史公曾“習(xí)道論于黃子”,這段話可稱深得黃老道家思想的精髓,是真知老子之言。
司馬遷分析儒家和老子學(xué)說(shuō)的分歧,借用了孔子語(yǔ)“道不同不相為謀”作為結(jié)論。此點(diǎn)實(shí)亦非深知孔老思想差異者所不能道。今天解讀分析《論語(yǔ)》和孔子思想,不對(duì)年輩先于孔子甚至是孔子師輩的老子的思想有比較深刻了解的話,也就很難透徹地知曉孔子和早期儒家言論的因承關(guān)系與針對(duì)性。這方面的例子,陳鼓應(yīng)先生《老學(xué)先于孔學(xué)》《老子與孔子思想比較研究》等文(收入《中國(guó)哲學(xué)創(chuàng)始者—老子新論》)有集中論述。我想再根據(jù)自己對(duì)《老子》文本的理解補(bǔ)充兩點(diǎ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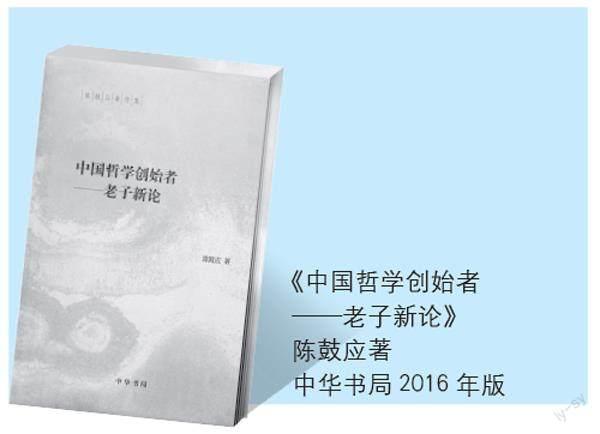
一是對(duì)待隱逸的態(tài)度。孔子從根本上是不贊成隱逸的,他與隱士、逸民大致都保持一定距離,甚至隱隱地批評(píng)長(zhǎng)沮、桀溺這一類避世之人。雖然孔子有的時(shí)候也發(fā)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的感嘆,但發(fā)完牢騷、開(kāi)了玩笑之后,便馬上說(shuō)浮海之“桴”根本“無(wú)所取材”,即明確地否定避世道路的選擇。而老子在司馬遷的敘述當(dāng)中,則正是一位曾仕于周朝的隱君子,這種關(guān)于老子身世的傳說(shu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歷史依據(jù),并非隨意編造。在《老子》中,這位思想家經(jīng)常告誡人們要自愛(ài)、自重己身,極端慎重對(duì)待自身大患。十三章是對(duì)欲取天下的侯王而言的,老子強(qiáng)調(diào)“貴大患若身”,將重視死生大患與寶愛(ài)自身放在同等地位,指出只有“貴為身于為天下”的人,才可以被托付天下、統(tǒng)治天下,也就是說(shuō),“貴身”是取天下的先決條件。但如果說(shuō)這個(gè)人過(guò)于寶愛(ài)、吝惜自身,想遠(yuǎn)避取天下為侯王可能帶來(lái)的禍患的話,老子認(rèn)為,“愛(ài)以身為天下,若可以去天下矣”(此為郭店簡(jiǎn)本,帛書(shū)甲本后半句作“如何以寄天下”,意思就是怎么能寄付天下給他呢?意思接近),其實(shí)就是贊成這些吝惜以身來(lái)為天下付出的人,離開(kāi)天下之位去歸隱。《莊子·讓王》:“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guó)無(wú)君,求王之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dú)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guó)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王子搜就是這樣一位堅(jiān)決地“不以國(guó)傷身”“惡為君之患”的人物,按照老子的看法,他既然如此不愿承擔(dān)以身為天下之任,不愿承受可能招致的大患,是可以選擇避世的,而不見(jiàn)得非要像越國(guó)人那樣千方百計(jì)地逼迫王子搜做國(guó)君。因此,孔子“鳥(niǎo)獸不可與同群”之語(yǔ),針對(duì)的或許還不僅僅是長(zhǎng)沮、桀溺這些人物,更有可能就是對(duì)早期道家關(guān)于進(jìn)退出處表態(tài)的一種反應(yīng)。
二是對(duì)待為政者卑辱處下的態(tài)度。老子因其所主張的道之弱德的特性,認(rèn)為君主本身應(yīng)當(dāng)以卑下自處,不可傲慢壓迫、高高在上,例如其自稱皆用卑賤之名而不求下民贊譽(yù)等。七十八章說(shuō):“故圣人之言云:受國(guó)之詬,是謂社稷之主;受國(guó)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此語(yǔ)與《左傳》宣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語(yǔ)“國(guó)君含垢,天之道也”有關(guān),很可能是對(duì)古語(yǔ)的引申發(fā)揮。十三章的“寵辱若驚”,也是要求侯王、君主重視“為下”的可貴,面對(duì)遭受的詬辱、卑賤要以驚喜態(tài)度面對(duì)。八章“上善如水。水善利萬(wàn)物,而又爭(zhēng)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矣”,同樣是希望統(tǒng)治者效法幾近于道的水的美德,不避污垢,甘于居之,甚至居之若爭(zhēng)。《論語(yǔ)·子張》記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這兩句話,一般認(rèn)為是表達(dá)一旦為不善就是居下流,所以不可開(kāi)啟不善之端的意思。其實(shí),“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兩句,很可能同時(shí)是針對(duì)老子要求君主受詬、受不祥、寵辱、為下而為言的。子貢的話所隱含的意思是,國(guó)君一旦受詬辱,便免不了天下之惡全歸于他的命運(yùn),商紂王其實(shí)也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樣不善,他的惡是居下流的必然結(jié)果,所以作為君主仍應(yīng)如孔子所言,像北辰那樣高高在上,“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yǔ)·為政》),決不能如道家所主張的那樣,真的去“爭(zhēng)居眾人之所惡”“受國(guó)之詬”。
儒道兩家在早期的呼應(yīng)與交鋒,以及老學(xué)對(duì)孔學(xué)的深刻熏染,只要細(xì)心去摸索,也許還能找到不少證據(jù)。雖然“道家”之名與“儒”“法”等家派名稱不同,要晚到西漢才出現(xiàn),但是老子創(chuàng)立的道家思想實(shí)際所產(chǎn)生的影響,卻可以說(shuō)在先秦時(shí)代的許多經(jīng)子著作中在在可見(jiàn),如氣體一般彌漫,是先秦思想中真正的“無(wú)冕之王”。
從一部中國(guó)古書(shū)的角度而言,《老子》也有幾個(gè)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首先,全書(shū)不出現(xiàn)具體的人物、事件、對(duì)話(縱有問(wèn)答也是自問(wèn)自答),完全是一部格言體裁的著作。然而這些格言,也并不記載說(shuō)話人姓甚名誰(shuí),仿佛空谷中回響著一位容顏模糊的曠古智者的大段詩(shī)意獨(dú)白(這種詩(shī)意,主要來(lái)自全書(shū)大部分章節(jié)嚴(yán)密用韻的特色)。日本學(xué)者福永光司解釋《老子》中的“我”說(shuō):
老子的“我”是跟“道”對(duì)話的“我”,不是跟世俗對(duì)話的“我”。老子便以這個(gè)“我”做主詞,盤(pán)坐在中國(guó)歷史的山谷間,以自語(yǔ)著人的憂愁與歡喜。他的自語(yǔ),正像山谷間的松濤,格調(diào)高越,也像夜海的蕩音,清澈如詩(shī)。
《老子》的獨(dú)白是類于呵壁問(wèn)天式的,但又不像屈原《天問(wèn)》那樣落到對(duì)歷史細(xì)節(jié)的關(guān)心上。文字所涉無(wú)一具體人事,這在古代中國(guó)著述當(dāng)中獨(dú)樹(shù)一幟,完全可以說(shuō)是前無(wú)古人。后來(lái)分章節(jié)的“語(yǔ)錄體”著作方式或許多少濫觴于此書(shū),但韻旨則皆遠(yuǎn)不可及了。

其次,因?yàn)槠 ㈨嵨挠诌m于記誦,所以《老子》在歷代流傳極廣(這種流傳必然不單單是書(shū)面的抄寫(xiě)流布);道教成立以后,《老子》又被奉為這門(mén)宗教的主要經(jīng)典,流傳的版本相當(dāng)多。李若暉先生主編《老子異文總匯》,收羅了一百余種《老子》版本,編成五百多頁(yè)的八開(kāi)大書(shū)。這在任何中國(guó)典籍中似乎都難以找到可相比較的例子。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的,《老子》的閱讀、研究因此而具有特別的有利之處。從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老子》選抄本一直到唐宋時(shí)代的《老子》文本序列相當(dāng)之完備,也許除了《詩(shī)經(jīng)》之外,先秦典籍很少可以觀察到這樣完整的文獻(xiàn)流變脈絡(luò)(有意思的是,這正好是兩種有韻的上古文獻(xiàn))。《老子》文本、思想的演變及其接受史,因此就格外具備探究的條件了。但因?yàn)椤独献印返陌姹緲O為復(fù)雜、文字上的歧異不可勝數(shù),而且異文占全書(shū)的比例相當(dāng)之高,這導(dǎo)致對(duì)它的研究舉步維艱。
第三,大凡簡(jiǎn)單的話語(yǔ),就比較容易產(chǎn)生理解上的歧義。早期的古典著作多有這方面的問(wèn)題,例如解讀《論語(yǔ)》就相當(dāng)不易,主要就是因?yàn)槠湓捳Z(yǔ)簡(jiǎn)潔、背景難曉。《老子》言簡(jiǎn)意賅、類于詩(shī)體,多義性的指向也非常突出。漢語(yǔ)本身就帶有相當(dāng)程度的模糊性,而且我們其實(shí)并不完全知道,到底老子就是將問(wèn)題看得非常復(fù)雜、不愿意把話說(shuō)得太明白,或者是因“趁韻”的考慮而把許多話講得形式美感大于表意的確切,還是他本來(lái)確實(shí)是有一個(gè)明確的意思,只是后來(lái)人在運(yùn)用、說(shuō)解《老子》文本時(shí)叢生歧讀異解(當(dāng)然,也很有可能上述這幾方面是同時(shí)交織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早已感嘆,道家學(xué)說(shuō)“其實(shí)易行,其辭難知”。學(xué)術(shù)史上從《韓非子》《莊子》以來(lái),關(guān)于《老子》文本內(nèi)容無(wú)窮無(wú)盡的解釋爭(zhēng)論、引用發(fā)揮,多半都與這方面的因素牽連。學(xué)者常說(shuō)“《詩(shī)》無(wú)達(dá)詁”(見(jiàn)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說(shuō)苑·奉使》作“《詩(shī)》無(wú)通故”。所謂“《詩(shī)》無(wú)達(dá)詁”的含義,在經(jīng)學(xué)史、文學(xué)史上頗有爭(zhēng)論,此取一般認(rèn)為的《詩(shī)》可斷章取義、沒(méi)有遍徹所有場(chǎng)合的詁訓(xùn)的意思),我想同樣也可以說(shuō)“《老》無(wú)達(dá)詁”。李若暉先生為《老子》第一章做了匯集古今解釋的工作,編成近九百頁(yè)的《老子集注匯考》第一卷,亦可見(jiàn)一斑。可以說(shuō),《老子》一書(shū),迄今仍有個(gè)別章的文句無(wú)法確解,有待后來(lái)者不斷努力。這也是《老子》一書(shū)能吸引千百年來(lái)的學(xué)者去探索、讀解的特殊魅力所在。

第四,中國(guó)古代典籍在世界上影響力最廣遠(yuǎn)的,不是《論語(yǔ)》,也不是《孫子兵法》,而很可能是《老子》。據(jù)德國(guó)學(xué)者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末統(tǒng)計(jì),《老子》西文譯本的總數(shù)在二百五十種以上;二○一九年美國(guó)學(xué)者邰謐俠(Misha Tadd)編錄《〈老子〉譯本總目》,搜集了《老子》七十三種語(yǔ)言的一千五百七十六種譯本,并稱該書(shū)是除《圣經(jīng)》以外譯本最多的經(jīng)典。我想,這不單是因?yàn)椤独献印范绦【贰⑤^便迻譯,更主要是由于《老子》“正言若反”(七十八章)的智慧、深具思辨色彩的特點(diǎn),在以軍國(guó)大事、禮樂(lè)教化、人倫日用為主要關(guān)注點(diǎn)的中國(guó)古代典籍中,尤能吸引西人目光的緣故。
最后,《老子》與一門(mén)真正的也是中國(guó)唯一本土產(chǎn)生的宗教—道教密切相關(guān)聯(lián)。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老子這個(gè)人的經(jīng)歷、風(fēng)格,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已經(jīng)是西漢流行的老壽的神仙形象,帶有神仙家的味道了,因此東漢以后的道教奉老子為道教創(chuàng)始者,奉意旨玄遠(yuǎn)的《老子》為教派最重要經(jīng)典,或者換句話說(shuō),從先秦古書(shū)中最具神秘主義玄妙氣質(zhì)的《老子》思想里孕育出希望通過(guò)得“道”而成為神仙的“道教”來(lái),是十分自然的。好像中國(guó)還不曾有其他的古書(shū),在建立一種宗教的意義上,可與《老子》相提并論,而這跟上面我們提到的《圣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倒有著相似性。如果承認(rèn)魯迅對(duì)許壽裳說(shuō)過(guò)的那句名言—“中國(guó)的根柢全在道教”不是一句錯(cuò)誤的判斷,同時(shí)承認(rèn)在儒法治術(shù)之下道家的底色與補(bǔ)充,那么也可以認(rèn)為,要真正懂得中國(guó)文化,不讀一讀《老子》恐怕也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