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青春敘事,不變的薩莉·魯尼
易揚

薩莉·魯尼(Sally Rooney)
在美國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主編的《都柏林文學地圖》中,有這樣一句極盡褒揚卻也恰如其分的評述:“都柏林創造著英語世界文學最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事實也確是如此,當我們談及愛爾蘭和都柏林文學時,談論的往往是奧斯卡·王爾德、威廉·巴特勒·葉芝、詹姆斯·喬伊斯、約翰·班維爾、克萊爾·吉根這些譽滿全球、堪稱明燈的文學大師。至于近年來被文學界盛贊為“千禧年一代首位偉大小說家”的薩莉·魯尼(Sally Rooney),雖然她絕大部分人生經歷都在愛爾蘭,但任何試圖從愛爾蘭文學傳統或是愛爾蘭前輩先賢的創作脈絡中,找尋魯尼繼承和轉化痕跡的舉動,或許都只能是無功而返。
倘若非要刨根究底,所謂的線索可能也只有寥寥幾條。比如,都柏林圣三一學院不僅是魯尼和塞繆爾·貝克特、威廉·特雷弗等前輩大師共同的母校,同時也是魯尼小說《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康奈爾和瑪麗安相約求學的地方,而在喬伊斯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兩個浪子》《死者》(均收錄于小說集《都柏林人》)中,“三一學院”也曾作為地標頻繁出現。又比如,在魯尼小說《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費利克斯演唱的愛爾蘭民謠《奧赫里姆的少女》,在《死者》中也被達西先生演唱,正如達西先生的歌聲成為葛莉塔意識覺醒的關鍵驅動一樣,《奧赫里姆的少女》也喚起了主人公艾麗絲深藏心底久未爆發的強烈感動。
一
作家塑造虛構人物,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兩者之間或多或少都會存在同構或是投射的關系—虛構人物身上無可避免都會有一些作者的影子、沾染上作者的氣味—雖然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主人公艾麗絲在給朋友艾琳的信中已經寫道:把作家和作品聯系起來“沒有為公眾帶來一點好處,還使得文學話語完全圍繞‘作者這一角色展開,他的生活和個性的諸多不堪細節勢必被人毫無緣由地翻檢審視”。但事實上,魯尼借助艾麗絲之口陳述自我的文學觀點,就已經套牢了“作家”和“作品”的關系,況且在小說“致謝”部分,當提及書中艾琳的某段思考時,魯尼也稱“如有謬誤,責任都在艾琳和我”—這也恰恰說明了虛構的“艾琳”和作為寫作者的“魯尼”本身就存在著某些必然的聯系,是無法完全撇清關系或割裂獨存的。
在魯尼先前的兩部小說《聊天記錄》《正常人》,以及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我們都能窺探出明顯的“魯尼基因”。這些基因的組成,既表現在外在的標識或身份,也體現在內在的思想和情緒上。比如,雖然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魯尼破天荒地塑造了費利克斯這個流水線上的“藍領”,但除此之外,“文學青年”的身份幾乎歸屬于魯尼筆下的每一個小說主角:《聊天記錄》里的弗朗西絲是個年輕詩人、博比熱衷于唱詩表演,《正常人》里的瑪麗安是“小說迷”、康奈爾是文學專業學生,《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的艾麗絲是小有名氣的小說家、艾琳則是位文學雜志編輯。這些被牢牢限定在文學領域的人物形象,無論如何都很難回避魯尼的人生履歷和社交圈子。又比如,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魯尼還借助小說人物之間大量的對話和通信,陳述了對于政治、歷史、文明、宗教、愛情、消費以及當下疫情的思考,這些又何嘗不是代表著魯尼自己的社會關切?況且她也曾在采訪中說過:“小說的事件可能是假的,但所有情感經歷都是真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和作家本人一樣,魯尼小說中的人物也始終處在動態成長的過程之中。在魯尼二十六歲發表的處女作《聊天記錄》中,主人公弗朗西絲和博比還都是二十一歲的女大學生;而在之后的成名作《正常人》里,小說男女主人公雖然結識于高三,但時間的軸線已經拉長到了大學四年;至于這本出版于魯尼三十歲時的《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則跨過了大學階段,把更多的敘事定格在了已經步入社會的主人公們身上。在《聊天記錄》和《正常人》里,魯尼讓主人公們的閱歷和思想都遲于自己幾年,并用回溯過往的視角審視他們失控的生活、認知的蝶變;而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除了二十九歲的艾麗絲、艾琳、費利克斯之外,魯尼還一反常態地塑造了三十四歲的西蒙—這個比自己略微年長、和自己擁有相同政治信仰的男主角,故事里西蒙所表現出來的游離、焦慮和沮喪,似乎也暗藏著作為寫作者的魯尼對于未來生活的另外一重洞察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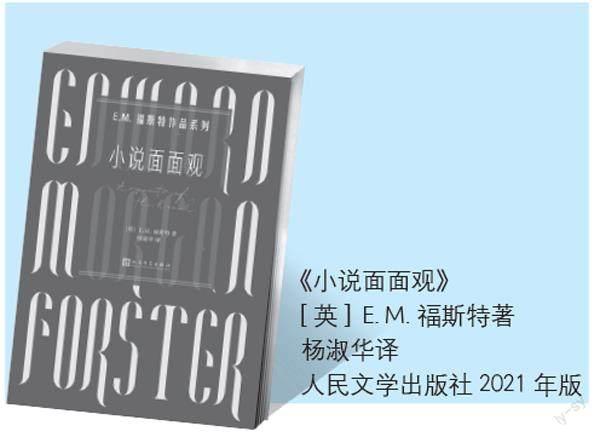
英國作家E. 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寫道:“小說的基礎是事實加X或減X,這個未知數就是小說家本人的性格。”魯尼的小說雖然絕大多數都著墨于年輕人的愛情,但之所以從未被歸類在“青春傷痛文學”的狹隘范疇,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魯尼寬闊深邃的視野。她對社會多元人群傾注了強烈的關注,這種關注也正是魯尼最為難能可貴的“X”。從《正常人》里的瑪麗安,到《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的艾麗絲,魯尼多次把目光投射到了精神病患者身上,如同凝視著真實生活中的朋友一般,魯尼凝視著她們的孤獨、厭世和無奈,給予發自心底的悲憫和共情。而在《聊天記錄》和《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魯尼還多次寫到性少數群體,他們和正常人一樣平等地參與社會事務,既沒有遭遇外界任何的異樣眼光,也從不對自身情況諱莫如深;魯尼時常展現出對“與性和解”的期待,在她看來,對性的認識應該回歸簡單和平常,任何過于深入和瑣碎繁冗的思考,都只會讓人生的困惑越來越多,疲憊的生活更加疲憊。
二
文學界對于魯尼的評價向來有些兩極分化,支持者認為魯尼的小說“從頭到尾都精彩絕倫”“令人手不釋卷”,況且年紀輕輕的魯尼,其作品早已入圍過布克獎,還一舉囊括了英國國家圖書獎、英國女性文學獎等重要獎項;而反對者則牢牢咬住魯尼的“自我重復”不放,認為她總是保守地延續著固定的主題,書寫著近乎雷同的人物形象。且不論托馬斯·哈代一輩子都在談論離奇荒誕的人生宿命,索爾·貝婁繞來繞去都在書寫知識分子形象,單是當我們環視魯尼的小說序列時,就足以驚艷于她在小說結構上的不斷探索和極具美學意義的反復重構。可以說,從《聊天記錄》到《正常人》,再到《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每一個魯尼都是新的。
和絕大多數作家的處女作一樣,魯尼的《聊天記錄》也是一部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但第一人稱的直抒胸臆并沒有成為魯尼自我禁錮的“溫室”,在接下來的《正常人》中她就開始嘗試隔章切換視角,雙主線的敘述模式猶如考究對稱的巴黎古典主義建筑,和諧而工整。而在最新出版的《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魯尼雖未在結構上“大動干戈”地另起爐灶,但也展現出既擅長“大手術”,又做得了“微整形”的敘事布局能力。不同于上部小說里類似于平行符號的絕對雙主線,魯尼讓故事結構如同甲骨文里的“大”字一樣,從“雙線并聯”到“單線串聯”再回歸“雙線并聯”,并且依舊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對稱。艾麗絲和艾琳兩個原本并行不悖的敘述對象,在小說行進到四分之三時因為相約度假而碰到一起,戲劇沖突曾一度劍拔弩張,但隨后又在理解中復歸于平靜;隨著度假結束,合而為一的敘述線再次分開,而此時曾經夾雜些許頹喪和戾氣的兩人,都已迎來久違的陽光心態。
雖然很難從愛爾蘭的文學傳統中找到魯尼繼承“衣缽”的蛛絲馬跡,但這并不等于說魯尼的創作就是無源之水。作家科林·巴雷特就認為魯尼的小說很好地承接了美國作家B.E.埃利斯“早期的那種緊湊、從容到酷的文風”,而作家安妮·恩賴特也評價《正常人》等作品是“十九世紀小說里的那種引擎”,至于魯尼作品中頻繁出現的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則更容易讓人聯想到濫觴于英國的書信體小說以及《帕梅拉》《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代表作品。雖然《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的主要敘事視角還是第三人稱,但魯尼在小說中每逢雙數章節都會插入一封艾麗絲和艾琳之間的往來信件,這些以“我”之口娓娓道來的書信,調和了小說單一的敘述模式,拓展了相對狹窄的敘事視角,讓作品兼具了第一人稱的共鳴感和代入感,也同時擁有了第三人稱的客觀性和全知性。英國書信體小說從十八世紀后期走向沒落,隨即被亨利·菲爾丁所創的第三人稱小說取代,魯尼自覺扛起了英語文學文體探索的責任,讓書信體和第三人稱這兩種曾經存在取代關系的文體,在特殊的共存交融中煥發出了新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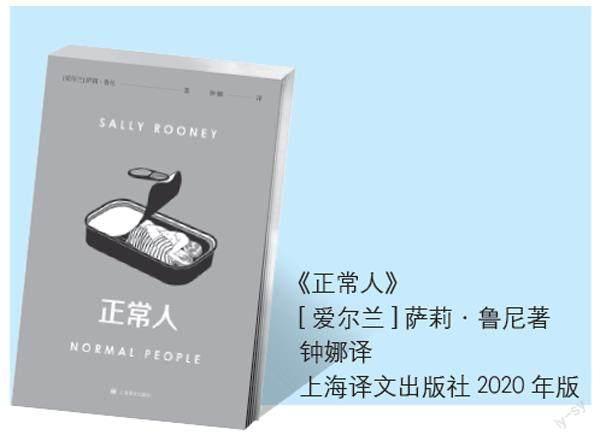
英國文學向來有關注政治歷史的傳統,以伊恩·麥克尤恩近年來的小說創作為例,《教訓》(2022)以編年史形式講述二戰后遺癥,《蟑螂》(2019)用卡夫卡筆法寫英國“脫歐”困境,《我這樣的機器》(2019)以復活圖靈為線索講述人工智能對歷史的創造。不同于麥克尤恩們將政治歷史背景雜糅于故事敘述的“毛細血管”之中,魯尼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對政治歷史的思考幾乎被限定在了艾麗絲和艾琳的書信往來之中;在和朋友聚會時,費利克斯甚至提醒艾琳,“不要一進去就開始聊國際政治什么的,人家會把你當怪胎的”,“艾琳說她本來也不懂什么國際政治”。一邊是在通信中刨根究底地探討那些事關人類社會發展最深層次的問題,一邊又是過著最日常寡淡的生活,精神的撕裂難免把主人公們推向焦灼煎熬的深淵,現實的不如意在如此對比反差中顯得更加真切。
三
相比《正常人》《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等小說所構建的絕對平衡工整的結構框架,魯尼筆下的人物設置則更多地體現了一種非對等的情境關系。“非對等”勢必帶來話語的失衡、交流的障礙、相處的困境。魯尼所要展現的正是“千禧一代”年輕人在出身、收入、形象、地位等諸多客觀因素的侵擾之下,始終揮之不去的脆弱乏力和焦慮失態。
早在《聊天記錄》中,魯尼就通過弗朗西絲和博比這對情侶、梅麗莎和尼克這對明星夫妻以及弗朗西絲和尼克的出軌戀情,展現了三段感情在非對等關系下的種種難堪。前者是性格上的差異,弗朗西絲乖巧禮貌,博比粗魯任性,兩種人設簡直天差地別;中者是角色上的倒置,妻子梅麗莎絕對是家里的頂梁柱,而丈夫尼克不過是個依附妻子的“花瓶”,這一家可謂是“女才男貌”;后者是財富上的懸殊,弗朗西絲的原生家庭寒酸窘迫,維系大學生活都堪稱艱難,而尼克的日子則過得聲色犬馬、衣食無憂。即便《聊天記錄》還只是魯尼個人風格探索時期的處女作,但魯尼小說創作的切口已經就此打開,即建構多對親密關系,并解剖這些親密關系內部的種種非對等性,或是借此扶持新的親密關系、制造新的裂痕,或是讓原本的親密關系發酵變味,在其內部滋生一重又一重的新煩惱和新矛盾。
不僅是涉身其中的虛構形象,就連旁觀故事發展的讀者,都無法不因魯尼筆下復雜難堪的人物關系而心生疲憊。不過,魯尼所要做的,似乎就是為了呈現人生疲憊的穿透性和不可變更性—無論是試圖做出改變還是努力保持不變,心力交瘁的狀態都將一如既往、難以扭轉,只不過呈現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正常人》里的男女主人公的關系,相比弗朗西絲和博比則要穩定,魯尼精妙地營造了多輪反轉,讓世俗青睞的天平忽左忽右。在小鎮里如魚得水的校園寵兒康奈爾,上了大學卻陡然變得憂傷起來;在家鄉零余孤僻的瑪麗安,來到首都求學后則搖身一變成了社交名媛,兩人處境徹底顛倒。魯尼借此討論了一個她在《聊天記錄》和《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都反復談及的問題,那就是身份地位、家庭環境這些與生俱來的因素,在非對等關系中起到的主導作用。可以說,即便康奈爾和瑪麗安最初看上去“男強女弱”,但兩人原生家庭的財富地位差異,特別是雙方父母存在的勞務雇傭關系,早已決定了瑪麗安在種種方面都凌駕于康奈爾之上;直到瑪麗安的畸形家庭暴露在康奈爾面前,康奈爾揮拳砸向家暴瑪麗安的哥哥時,兩者的非對等關系才因各有劣勢而被放緩。小說結尾處,瑪麗安向赴美求學的康奈爾的一句表白“你去吧,我會一直在這兒”,看似溫情而動人,事實上又何嘗不是男女主人公各自無奈妥協的權衡折中。
《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是魯尼三部長篇中戀愛關系建構最為穩固的,可以說,書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雖時有波瀾,但幾乎都沒什么動搖破滅的危機。然而即便如此,魯尼對身份、家庭差異下非對等關系的闡釋卻沒有半點削弱。在艾麗絲和費利克斯之間,魯尼的落筆依舊還是金錢和精神:一方面,艾麗絲的作家“光環”和頗豐收入,讓身為體力勞動者的費利克斯時常處于自尊心受壓制的狀態,費利克斯的調適方式是轉嫁壓力,先是以“施虐者”的形象搶占話語高峰,他會嘲諷性格孤僻的艾麗絲“你似乎也沒什么朋友”,也會搖身一變成為“衛道者”,詰問艾琳或西蒙“你怎么從來不來看她”,看似充滿關心,實則卻是帶著攻擊性質的先發制人;另一方面,費利克斯始終因自己微薄的收入而感到自卑,他一邊艷羨著艾麗絲的富有,一邊嘲笑著收入還不及自己的艾琳,自以為這樣就能獲得虛無的平衡。
至于《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的另一對情侶艾琳和西蒙,他們都成長在非正常的家庭。魯尼將艾琳塑造成了前兩部小說里“弗朗西絲+瑪麗安”的翻版,和弗朗西絲有個情緒失控的父親、瑪麗安有個家暴她的哥哥一樣,艾琳也有一個“算不上惡毒,就是很瘋狂”的姐姐,以及對這一切都不聞不問的媽媽。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童年決定論”所闡釋的,原生家庭的暴戾和缺愛,無疑造成了成年艾琳在感情中的過分依賴,好比瑪麗安一度心甘情愿地對杰米表明“我喜歡男人傷害我”,對康奈爾提出的“不要跟學校的人講(戀愛)這件事”的要求也毫無抵觸一樣,艾琳也一門心思地滿足于與西蒙相處中的種種被動,她有時稱呼西蒙為“爸爸”,也表明自己“很享受聽你(西蒙)指揮”,同樣,她對西蒙和別人約會、不公開她的女朋友身份也安之若素,她既害怕失去西蒙對自己從小到大的庇護,又享受著被支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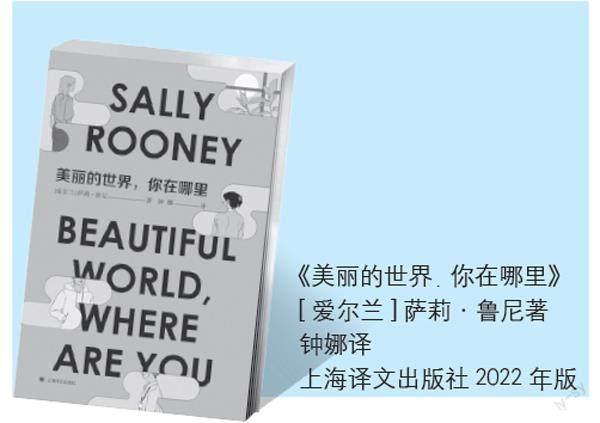
不過,正如將最新長篇命名為“美麗的世界”一樣,魯尼從來都不是一個喪失希望、沉淪頹喪的寫作者,她崇尚美國作家喬治·艾略特“女性自我喚醒”的觀點。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的結尾,魯尼交代了艾麗絲的自我提醒,“費利克斯還活著,你(艾琳)還活著,西蒙還活著,于是我就感到無比幸運,幸運得讓我害怕”;也交代了艾琳人生新的變化,“我懷孕了……他(西蒙)聽后哭了,說他很高興”,“他再次提議我們可以考慮結婚”。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萊昂納德·科恩那句盡人皆知的歌詞:“萬物皆有縫隙,那才是陽光照進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