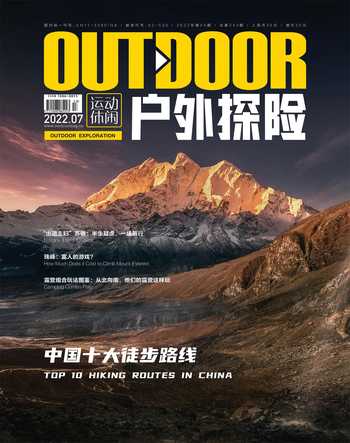“出逃主婦”蘇敏
徐時雨

媽媽真是一無所有
百年以前,魯迅曾以易卜生的著名劇本《娜拉》為引子,做了一篇關于女性自由問題的講演。娜拉不滿于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壓迫,終于離家出走。劇本到此為止,娜拉出走以后又怎么樣呢?易卜生沒有回答。
魯迅說,娜拉或許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因為如果是一匹小烏,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
如今,在中國大地上就有這樣一位女性,正如娜拉一般為自由“出走”。她叫蘇敏,今年58歲,從2020年9月24日為逃脫婚姻而離家到如今,已經1年零9個月了。
在這600多天里,蘇敏走了100多個大小城市,行程6萬余公里。在當代,“娜拉”顯然有更多可能。
她沒有墮落,至于是否會回來……
蘇敏剛剛自駕完318川藏線,抵達拉薩。這一路她開的不急不慢,路過怒江72拐,一百多個連續急轉彎,下坡的時候車頭面對著萬丈懸崖,問她:挺難開的吧?
她回答:“還可以,比219強多了!”
西藏是她熟悉的地方,她自小在這里長大,不僅有著情感上的親切,30多年后自己的肺也仍能適應這里稀薄的空氣,大概是因為當還是個小女孩時,她就曾無數次地孤身奔跑在那崎嶇的高原上。
她在西藏昌都念的小學在一座山后面,那是一個電廠的子弟小學,平時會有校車接送他們每周一次回家換取衣物,但每次放假剛好趕上蘇敏做值日時,她就會是被落下的那一個。

回家的路要翻山越嶺,還要在夜色中經過一片陰森的墳場,每次路過,她都會因為害怕而停步,等到路上有汽車經過時,才敢借著車燈的光亮,拼命往前奔跑。
“那個時候就感覺,要是能有車多好,有一部車就什么都不怕了。”蘇敏說。
汽車從此成為她心里的一種執念,車能給她安全感,也讓她“能找到骨子里的那個我”。
幼時的夢想在后來的幾十年里并沒有實現,事實上,在出走之前,蘇敏從來沒能在生活里找到實質上的安全感和踏實感,無論是從原生家庭,還是從自己選擇的婚姻中;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
出走之前的蘇敏,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失敗的、一無是處、差勁,她極盡可能挑這些糟糕的詞放在自己身上。這大概是因為,她用心地在每一個階段自己的角色里盡好責任,卻并沒有得到多少溫柔的善待,所以對自己有著深深的失望感。
18歲那年,父母帶著弟弟從昌都返回河南老家,只丟下正準備參加高考的蘇敏。父母和弟弟走的那天,瀾滄江漲水了,江水漫過堤壩沖進了學校。
“再大的水,他們還是會走,不會帶上我。”而在這之前,她是患有高原心臟病常年臥床的母親的得力助手,是那個需要照顧兩個弟弟的長姐,她常常要拖著一米四的小小身軀在午休20分鐘里奔跑著回家劈柴生火做飯,但并未得到多一點的偏愛。

高考落榜后,蘇敏聽從父親安排進了河南一間化肥廠,但每月剛剛發下工資就要按時上交。她因此想逃離原生家庭,以為進入婚姻就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熬到23歲,匆匆忙忙嫁了一個僅見過兩次面的男人,現在的丈夫老杜。
如此輕率的逃離,決定了她而后30多年的命運。和老杜的婚姻,最終讓蘇敏心中本就缺乏的安全感慢慢走向崩塌的邊緣。
蘇敏所在的化肥廠倒閉后,下崗的她曾靠老杜每月給她的500元生活費度日,那些年最讓蘇敏痛苦的是,丈夫老杜要求她每月一分一毫地匯報這筆生活費的去向。
丈夫在金錢上的刻意計較讓蘇敏感到屈辱,要強的她一邊照顧剛出生的孩子一邊打零工,做裁縫、送報紙、掃大街,但這些微薄的工資只是最終讓兩人之間徹底變成了“AA制婚姻”,另一邊,她又需要像一個免費的保姆,操持著一家人的生活。
更讓蘇敏受不了的,是丈夫在語言和氣場上對她的壓制,從無情感上的關懷,“在家里說話就像是在演講,得提前想好每一句話。”矛盾升級時,便是拳腳相加的家暴。
原生的家,不像家;丈夫的家,也不是家。

蘇敏剛剛出來時開的小polo,是2015年買的,女兒幫她付了3萬塊錢首付,她分期兩年買了這輛車。但因為自己不能辦分期,所以寫的是女兒的名字。她沒想讓丈夫出半分錢,自己在超市里打了兩年工慢慢還上。
即便算是自己的半個財產,蘇敏也一度失去了對它的掌握權,丈夫老杜說蘇敏平時用不上車,便長期霸占著。
這是加重她心里郁悶的心結,她愛開車,異常地愛。她還記得考科目三的時候,有次一個交警坐在旁邊,他看了一眼她身份證說:“這么大年紀了,學車干什么呢?”
“就是喜歡,再說了,百歲還未過半呢。”即便那時她還沒有車。
她還私下和女兒半開玩笑地說過:“以后不如買個拖掛住在你家樓下。”活了半生,房產證上是丈夫的名字,車子也不完全屬于自己,“媽媽真是一無所有,我就是咱們家最窮的一個窮光蛋。”她曾對女兒說。
逃離之前,蘇敏的人生,像是行駛在一條永無止境的黑暗隧道中,看不到光。而更準確地說,結婚30多年,她卻好像還是當年那個拼命追著車燈光跑的女孩。

把自己放在路上
蘇敏說,她很喜歡太陽,喜歡陽光。就像是當年躺在開滿格桑花的小山坡上,望著藍晃晃的天一樣,光總能給她一些安慰。
還有蒼鷹和飛鳥,在西藏的童年,被家務纏身的蘇敏也不忘抬頭看看這些極度自由的飛禽。這種像蒼鷹一樣沖向天際的爽快暢意,直到后來她在國道上奔馳,看著車窗外閃過的風景,而她可以隨意導航自己的去向時,才真正擁有。
在這之前,她怎么也舒展不開蜷縮的心靈,怎么也握不住人生的方向盤。
那是2019年冬天,一個平常的午后,在哄外孫入睡后,蘇敏像慣常一樣躺在床上翻穿越小說,她喜歡看這些,想象自己也可以如女主一樣穿越到另一個時空。
那天蘇敏沒能正常打開小說界面,卻隨手點進了一個跳出的鏈接,鏈接里是一位博主正在分享自己的自駕游經歷。蘇敏說,就是那一瞬間,她好像被擊中:原來,還有人在過著這樣的生活。自駕游視頻取代穿越小說,蘇敏用力望向“隧道”的另一頭,她好像看到了一點光的蹤跡。

“明年,等孩子們一上幼兒園,我就走。”蘇敏把出走的計劃公開擺在飯桌上,女兒沒有特別在意,默認支持,丈夫老杜則是一如既往地諷刺挖苦。
蘇敏真的出來了。
2020年春天,她將照顧了近3年的雙胞胎孫子送進幼兒園的當天,就出發了。在這之前幾天,她一鍵下單了此前一年時間里精挑細選的所有出行裝備,從車頂帳篷,到睡袋、鍋碗瓢盆、儲物柜、發電機、冰箱和柴米油鹽。這是一場謀劃好的出走,她在一如既往地照顧家人生活起居的縫隙時間里,翻看其他博主的自駕游攻略。
2020年9月24日,開著小polo駛出鄭州那一刻,她就發覺自己真的自由了。開往三門峽的路上,她穿過一個長長的隧道,那就像她的人生,但這一次她終于發現光,并追逐而去。
出發幾天后,她把車停靠在路邊,想著應該錄下一個紀念性的獨白,這也是后來最為人所知的視頻,大多數人是通過這條視頻認識蘇敏的,媒體也是在這場視頻的傳播發酵后,開始一窩蜂地跟蹤報道她。
在這條視頻里,她將自己30多年痛苦壓抑的婚姻傾吐而出,神情疲憊,眼神無光。話語之間,其實并沒有什么大的起承轉合,也沒有什么批判控訴,只是一個女人疲憊地道出自己不快樂的婚姻和失去自我的落寞。
關注她的人大多是女性,她們贊佩她擁有走出來的勇氣,但勇氣有時候只是托辭,“如果有一天你也被生活逼到了這個份上,無處可躲,除了死,就只能逃了。”蘇敏說。
在鏡頭前,蘇敏坦然撕開了自己藏得最深的傷口,那是2018年,她在和丈夫最為激烈的一次爭吵中,拿起餐桌上的水果刀,對準自己的胸膛用力一捅,留下的傷疤。丈夫總能用冷漠尖酸的言語將蘇敏逼至無助絕望的一角。女兒后來醒悟過來,父親對母親的壓制,實際上就是精神上的PUA。
自殺過就不想再死了,這次事件過后,蘇敏也得知自己患了重度抑郁,“心里的那股勁,再也扭不回來了。”
許多女性,尤其是和蘇敏一個時代的女性,生活中都有和她同樣的困境,甚至遠比她悲苦,為什么只有蘇敏真的走出來了呢?
后來女兒杜曉陽給出了合理的解釋,“就剛好她特別愛開車,又剛好她趕上這樣一個(自媒體)時代。”蘇敏追著光的方向,又借著視頻創作和身上自帶的話題站在聚光燈下。
過去30年的喪偶式婚姻,雖然讓蘇敏精神上吃透了苦頭,卻也讓她獲得了扎實的生存能力。把自己放在路上吧,獨自去生存,看看能怎樣?
“娜拉”沒有回來,一定是因為她發現自己可以活得很好。

我是被上天眷顧的人
起初在路上,蘇敏的車頂帳篷經常被圍觀,她不厭其煩地解釋著自己為什么出來,走過哪些地方,自己一個人會不會害怕。
她的車停在房車營地上,顯得特別扎眼,人們繞過一輛輛霸氣的房車走到蘇敏的小polo前,看單薄的她獨自支起比她人還高一信的車頂帳篷梯子。
“你這個車子這么小,這能撐得住嗎?”“結實得很呢。”蘇敏笑呵呵地回應。事實上,剛出發時她需要很費力有時還要在路人的幫助下才能支起那頂帳篷;也會在深夜找不到露營地,被導航導到無人的荒郊野嶺。
開始出來時幾乎所有路上的開銷,都來自于她每個月2300元的退休金,有一次,因為退休金沒到賬,她在原地停留了18天才繼續出發。
為了通過自媒體掙路費,50多歲的她認真學習拍攝,每日伴著星光耐心地剪輯。
當從家里走出來那一刻,蘇敏就覺得什么都不難了。她像是剛被放逐到荒野樂園里的孩子,一點點摸索著戶外生存能力。
這場旅行是她生命里的止疼片,她逐一推翻了那些曾經被她扣在自己身上的不正確的定義,一路上的踏實感,在拯救著她。
拯救她的,還有在路上的人們以及網絡上的粉絲給她的善意和包容。

“我們很少問及彼此的家庭,很少去問別人的過去,好也罷不好也罷,大家只想著往前看就好了,不要去想那些不高興的了。”蘇敏說。
從成都前往云南的路上,她被一個房車車隊接納,讓唯一一個開著不統一車型的蘇敏,放松且不拘謹。在進藏路上,幾輛房車會將蘇敏的小polo保護在車隊行進中間,讓她備感安心。如果不走出來,她幾乎不會知道世間溫柔還會以這樣的方式賜予于她。
如今蘇敏的軌跡,已遍布中國各大著名的公路,從前那個小心翼翼隱忍他人情緒的自己,仿若不見了。當走出那個逼仄的個人小世界,她看到了天地的廣闊和生活的美好,看到世間的人不同的活法,她的思維也跟著開闊了。
“我只是我自己,我只想我要去什么地方,去看什么風景。”
她不再忖度丈夫難猜的心思,她的心中開始流淌進大江大河,或者只是開始關心自己走過的哪條公路最美,她說:“我目前走過的最喜歡的公路應該是獨庫公路,因為它可以見到雪山,見到草原,也可以見到那些不好走的路段。”
她還會不無驕傲而興奮地說:“咱們中國最美最有名的幾條公路,219、318、315,還有331和228,我都貫穿過了!”
對蘇敏來說,目前最有寓意的一段路還當屬219,“(這條路)最挑戰的就是人心里的堅定,有的人其實走219走不遠就拐回去了,感覺沒法走下去,其實能走過來的人真的都……人家說219是勇者之路!”
“我過來之前好多人都說,你這輛小車子要是過去,這車就等于報廢了!結果我車到現在還好好的,哈哈。”
我問她,怎么可以一人應付好路上那些問題,蘇敏說:“我總感覺我是被上天眷顧的人。”

“娜拉”的第三種選擇
2022年3月2日,對蘇敏來說,是格外與眾不同的一天。這一天,或許是她人生真正意義上擁有了自己的小家。
離家出走一年半的她終于通過自己的努力買到了房車,喜提房車的那天,她拍了一段長達7分多鐘的視頻。
有了這輛房車,蘇敏終于不用再每天爬上高高的車頂帳篷,不用再害怕去寒冷的地方,她更加有勇氣和自信自己可以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這個真的是屬于我的家,以前有很多東西都不屬于我,很多東西都沒有我的名字。”她手舉著自拍桿,視頻最后激動得熱淚盈眶,哽咽著再也說不出話了。
蘇敏像對待寶貝一樣珍惜這輛房車,每天都忍不住要擦一擦。“因為它是屬于我的。”她一再強調著。
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說:“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顯然,蘇敏如今已經有了這份敢去熱烈追求自由生活的底氣。
她現在看起來很陽光,每天在直播間,都有人夸她:阿姨看起來又年輕了啊。她的臉上總是掛滿笑容,也幾乎不再吃抗抑郁的藥了。
她在自己生命中闖出的光亮,也為和她有著相似經歷的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學。在她的視頻下,總有類似這樣的留言“等我孩子大了、退休了、還完債了,我也要這樣一個人出去。”
或許其中某一個留言者,也如她當初那般,困在瑣碎的生活里,困在對丈夫的隱忍里,困在自己傳統的觀念里,其實終歸是困在自己的思維里。
而歸根到底,我們在蘇敏身上看到的最寶貴之處,莫過于她已年過50,還擁有沖破牢籠、追求自由的勇氣。
“我希望大家從我身上得到的借鑒是,對自己的生活,不管它是好是壞,都不要太去抱怨,有些東西都是自己可以去選擇的。如果你真的不堪生活的壓力,喘不過來氣,你也可以借鑒我的這種方式,我指的并不是像我一樣出來這么久在外面,你可以以你以前不曾看到的角度去規劃你的生活,看你將要怎樣去過你的生活。
生活有很多種,但是需要自己作出更正確的選擇,并不是說這次選擇錯了,就要一輩子在錯誤里生活下去,真的沒有必要,你永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路。”
至于人們對她最大的質疑:不離婚不就是逃避問題,現在的爽只是一時的,回家之后不還是要面對問題。
蘇敏自己,好像已經不太關心這個問題了。
她對這個世界有了更豐富的認識。去年,她去體驗了沖浪,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項年輕人玩的運動。當時幾個朋友開玩笑說,“我們這些人就算了,年紀大了。”
但蘇敏試了幾百次不止,喝了好幾十口海水終于站起來。問她站起來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覺?
“好爽,一定要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