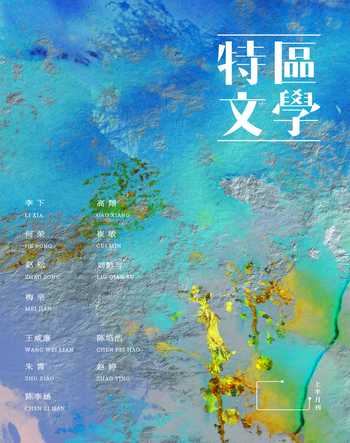夏日在雨后終結
高翔,生于1988年,遼寧人。小說散見于各文學期刊,曾獲第38屆香港青年文學獎。
他們來的那天,外面在下雨,一男一女,一人擎一把紫傘,小孩則披一件黃色的雨衣,遠遠看,如同兩朵下降的愁云和一顆明星。
雨水順著灰色的房頂淌下來,每到那種連雨季,旅館入口的棚頂就會漏雨,總是沒法徹底修好。我當時倚在旅館的玻璃門前,打算把身邊兩個裝滿垃圾的巨大塑料袋送到街對面的垃圾箱,可是雨太大了,我一手只能拎一袋垃圾,無法打傘,會被澆透。我踟躕在門邊,罕見地消磨著時間。三個人走過來。我當時沒有對他們問好,大概只是苦笑。這其實不是我分內的工作。
那對男女收起傘,對我頷首。披著黃雨衣的小孩則仰起頭,雨水順著雨衣的帽檐滑落,是個小女孩。她的父母走向前臺,說他們有預訂房間。而女孩跟我交談起來。
“這里一直下雨嗎?”女孩問我。
“也不是,最近才這樣。”我說,“你不喜歡下雨?”
“不喜歡。”女孩噘起嘴,好像很委屈。她的眼睛很細,臉肉嘟嘟。“一下雨,夏天好像就結束了。”她說。
“哦。”我應了一聲,覺得她這話很有意思。我對她說,我也不喜歡下雨,下雨讓我沒法出去倒垃圾。
“天氣預報說下午才有雨。”男人在前臺邊抱怨。他人枯瘦,黑,顯得有些焦躁,抽出一根煙想要點著。
“嘖。”女人看了他一眼,男人把煙放了下來。
“沒關系,我可以把雨衣借給你。”女孩說。我對她笑了笑,我很感激,但我告訴她,我太大了,會把雨衣撐破。
服務員很快幫他們辦好入住,女人轉過身,對女孩說:“妮妮,我們一會兒睡一覺,睡醒了,如果天好起來,我們再出去玩,好不好?”女孩點點頭,有一種對待陌生人的客氣。那對男女于是牽起女孩的手,一起走向客房的電梯。
直到中午,他們才再次從房間出來,眼睛都有些浮腫,穿戴的仍是來時的那套行裝。那對男女說要帶女孩出去吃飯,問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薦。我告訴了他們一家餐館,位置離這里較遠,俄餐,餐館二樓的露天陽臺有俄羅斯人在上面拉大提琴。他們聽后向我道謝,隨后離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去了那里。
他們離開后,我拿著門卡,第一次進入了他們的房間,里面的光景我到現在還依稀記得,因為后來我又進去過很多次,它始終沒有太大改變。
房間很暗,拉著紗簾,我把廊燈打開,屋子才亮了一些。門口的換衣鏡前擺著三雙拖鞋,其中兩雙是旅館提供的,另一雙則小小的,上面鑲著棕色的卡通熊。我把那雙鞋撿起來,拿到眼前端詳,我看到鞋里還有底部都粘著一點沙粒,有股沙灘和海洋的味道。我猜想他們來這里之前去過海邊。
房間的主人顯然還沒將它視為自己的領地。背包整齊地碼在置物架上,行李箱塞在電視柜與桌子之間的空檔,除了白色被子的一角被折疊,上面布滿褶皺,像蠕動的白色肉蟲,為房間增添了一點生動,其它全部是拒絕的姿態。它仿佛身體的免疫系統,對于一切外來物保持著警覺。
環顧一番后,我回到門口,關上廊燈,準備出去。就是在那時候,我透過紗簾后的殘光,看到一件被丟在盥洗臺下面的東西。我走過去,俯身將它撿起來。
從他們的房間退出去后,我將門把手上“請勿打擾”的牌子重新翻正過來,接著去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活計。我來到雜物間,將那只擱置許久的鐵桶拿到一樓,放在門口漏雨的地方,又拿拖布,將地磚仔細拖了一遍。地面終于不再濕漉漉。
兩個小時后,三人回來,我與他們打了招呼,像什么也沒發生。女孩對我說,她沒有聽到陽臺音樂會,音樂家們好像今天不上班。我安慰她說總會看到的,只要她在這里待得夠久。
女孩有些自來熟,接下來的幾天,每次外出回來,她都會跑來找我聊天,有時只說幾句,有時很多。我仍能記起她對我講過的話,她講她吃了兩種口味的馬迭爾冰棍兒,但她更喜歡香草味;講她在長得像面包一樣的石板路上摔了一跤,她以為膝蓋會磕破,但是卻沒有;她還對我說起美麗的教堂,鐘樓頂部像圓圓的洋蔥頭,還有廣場上的鴿子,她的父母給她買了一包鴿食,她在廣場上喂了很久。
我還是頭一次見到如此喜歡跟陌生人交談的孩子,毫無保留。我想那也許不是因為我的緣故,她應該對許多陌生人這樣做過。
他們入住后的第二天,傍晚,我正要去二樓的雜物間取東西,看到女孩一個人在走廊踱步,手里攥著一支礦泉水瓶,目光四處打量四周的空間,墻壁、地毯、樓梯,仿佛在尋找什么。我聯想到,也許她是在找我在盥洗臺下發現的東西,我將它藏在了門口的鞋柜里。我想,如果這東西對女孩來說是重要的,她應該會去找它。
因為過于專注,女孩起先沒有發現我。后來我拍拍她的肩膀,她才轉過頭。看到我的那刻,她立刻將拿著礦泉水瓶的手別在身后。
“在找東西?”我蹲下來,裝作疑惑的樣子。
女孩搖搖頭,隔了一會兒,又點點頭。她問我,阿姨,你知道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嗎?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環顧四周,想到一家漏雨的旅館能有多安全呢?我問她為什么要找這樣的地方,女孩抿抿嘴,似乎困擾了一陣子,然后將背過的手伸到我的面前。
我從盥洗臺下發現的是一枚鑰匙扣,上面綁著一只粉色的小豬,圓滾滾,戴著一頂黑色禮帽,騎著掃帚,仿佛會魔法。這枚鑰匙扣應該用了很多年,小豬原本的眼睛已被磨損,消失不見,它的主人用圓珠筆為其重新描畫了一番。它有了一雙新的眼睛,一只是藍色的,一只是綠色的。我把它藏在了門口鞋柜的深處。
空瓶里爬著幾只蜘蛛。一只看起來大一些,剩下的兩只體型較小。因為女孩的動作,三只蜘蛛各自沿著瓶壁爬行了一段。女孩看我沒什么反應,似乎松了口氣。她說她以為我也討厭蜘蛛。我搖搖頭,問她,為什么要撿這些蜘蛛回來。女孩回答我,因為它們很危險。
女孩說,蜘蛛是她在游船的時候看到的。那時候她坐在靠近船舷的一個座位上,她的頭頂上架著一盞小小的燈籠。那艘船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懸掛著一只,船上別的燈籠都亮了,只有她頭頂的這一盞沒亮。女孩很沮喪,她希望自己頭頂的燈籠也亮起來,于是不時抬頭看,希望它只是暫時壞掉。可直到游船結束,她都沒能看到它亮起來,倒是意外發現幾只在燈籠架附近隨風飄搖的蜘蛛。
“外面風很大,它們的網被吹壞了,只能在一根蜘蛛絲上走來走去,它們可能會被吹到水里,會被淹死。”女孩說。
“所以你想給它們找個安全的地方,是這樣嗎?”我問。
女孩用力點點頭。我站起身,試圖幫助女孩找到一個她所說的安全的地方。
“那邊是什么?”女孩用手指向走廊盡頭的那扇窄門。我看到那是雜貨間的位置。
我將女孩領到那間雜貨間前,點上燈,小小的屋子立刻亮起來。屋里面緊湊地擺著兩排置物架,上面堆滿清潔工具和一些很少用的雜物。朝東有一個小小的窗戶。女孩立刻喜歡上了這里,她對我說,這里很安全。她走到那個小小的窗前,將瓶蓋擰開,試圖把里面的蜘蛛傾倒出來,但它們緊緊地趴在瓶子里。沒辦法,我只好用剪刀把瓶子裁開,將蜘蛛們抓出來。
“別弄傷它們。”女孩叮囑我。我將自己的動作幅度放緩,將蜘蛛一一放在窗臺上。它們在窗臺上停留片刻,便立刻四散逃竄,有的鉆進柜架與墻壁的縫隙,有的順著墻向上爬去。
“這下你可以放心了,”我說,“它們很安全,這里只有我和另外幾個女工會來。它們無聊的時候還可以看看窗外。”
“嗯。”女孩高興地答應著,說謝謝阿姨。緊接著,她給了我一個擁抱。
那是一個小小的擁抱,女孩的手只夠環著我的腿,頭則勉強貼在靠近我腰部的位置。我微微躬著身子,一時手足無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姿態非常古怪。
上個擁抱是多久之前?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去年八月的時候,我辭掉旅館的工作,離開老家,來到這座邊境城市。我有個親戚在這邊的一家物業公司做副經理。我只帶了少量的行李,其中之一是從那個女孩的房間撿來的小玩意。
一開始我被安排在酒店工作,后來公司承包了政府業務,我又被調去政府大樓。都是做保潔。政府大樓是日本人建的,幾十年了,外面是磚紅色,后來被漆成了墨綠,它的里面像個迷宮,有很多房間。除了保潔人員的休息室和衛生間,其它的我一間也沒進過。
在旅館工作之前,我沒上過班,在家帶孩子。我的兒子有自閉癥,三歲的時候去醫院檢查出來的,情況比較嚴重。醫生說你就養著吧。回家后,我向我男人復述了醫生的話。我男人說,那就養著吧。
兒子長到七歲,看起來已經很老了。有時候我看著他,就像看到未來的自己,我想我最終也會得那種癡呆的病,這是遺傳吧,兒子發病早點,我發病晚點。
像全天下的母親一樣,我不能完全了解他,他經常獨自縮在床上,目光呆滯,怔怔地看著墻角,忽然嚷一句什么。
世界在此后的每一天都收縮一點,如同敏感的軟體動物,在觸碰之后,變瘦,變小。我巴掌大的生活,只有兒子和那間西偏的舊房。那里夏季悶熱,冬季陰冷,日子望不到頭。出門就像放風,回去則像越獄犯人被重新逮捕。墻上布滿糞便、尿液、彩筆、醬油的痕跡,我沒再粉刷過,我以為還會有新的痕跡。
我不是沒想過逃離這種生活,我也會設想新的孩子,新的家,房子的墻壁要粉刷成雪白。這令我慚愧,因為它如此自然。但我太粗心大意,一直以來,我從沒想過,舊日子會以何種方式結束,一次也沒有。等到它終于戛然而止,我才知道,生活跟想象、直覺、預感,一點關系也沒有,它是突如其來的旋風,到來時只管將一切席卷。
終結的那天傍晚,我從母親家回來,她摔斷了腿。濃重的煤氣味像鬼魂一樣纏住我。我捂著鼻子,打開門,看到餐桌上擺著空酒瓶,半碟花生米。里屋的床上,兒子乖巧地躺著,丈夫仰在沙發上。他們都像睡著了一樣,神情淡漠。我把煤氣關掉,把他們拖到大門口,隨后像個咿咿呀呀的聾啞人,將一些自己都聽不懂的音階從嘴里吐出來。那一刻我失去了語言。我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后來,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誰打開了煤氣。兒子,丈夫,還是,我?我出門前曾燒過一壺開水。我想不明白。這是生活留給我的另一個謎團。在夢里,有時候我會變成我的丈夫,在那個煤氣環繞的房間,一切墮入沉沉睡意前,他已預感到危機,生命行將結束,卻不想呼救,只是把原本閉上的眼睛,閉得更緊一點。
他們死后,我來到那家旅館,老板給了我一間屋子住,在旅館二層,我不必再回到原來的住處。我一直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遇到那個小女孩和那對男女。
因為蜘蛛的緣故,女孩常來找我,讓我帶她去雜物間,仿佛那些蜘蛛是她的寵物。我們不總見到它們,它們會爬上窗戶,也會藏在各種堆積物之間,叫我們無法找到。有時候,我去晾曬床單、被罩,女孩在一旁幫忙。真是一個乖巧的孩子。我將床單的一頭交給她,另一頭攥在自己手里。我告訴她,我們要把這張皺皺巴巴的床單拉扯平整。她點頭,表示明白,她愿意做我的助手。可當我們真的開始抻床單的時候,她卻總不可自抑的大笑,仿佛這個行為觸發了她身體的某個穴位。她小小的身子蹲下來,因為怕床單掉落弄臟,手還拽著那頭,笑得咯咯咯咯,我于是也開始跟著她笑。我們樂此不疲,不斷重復。“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問她。她說她一抻床單的時候,就覺得渾身癢癢,手立刻沒勁了。“阿姨,我費了好大勁才沒讓床單掉下來!”“那我還要感謝你嘍?”我笑著說。等晾曬完床單,我們會在院子里待一會兒。院子的角落,有一輛廢棄的白色吉普車,不知道是誰的,輪胎早就完了,座椅也變形的厲害,但我們總會到里面坐一坐。她坐駕駛位,我坐副駕駛。我從兜里掏出糖果或者瓜子遞給她。她便一本正經地說她在開車。有時候,在半夢半醒之間,我真的以為自己在一條公路上,女孩開車載著我,我們一起去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地方。“你愿意跟阿姨單獨出去旅行嗎?你敢嗎?”有一次,我問她。她說,那有什么不敢的,阿姨是好人。
院子里傳來女人的聲音,她在喊女孩的名字。我原本以為時間被上帝點了穴,它已經停止了呼吸,但那聲呼喊讓我意識到它仍在流動。有時候,我們誰都不會吭聲,仿佛在跟女人做一個游戲,假裝我們真的開車去旅行了。我又變成了我丈夫。
我將車門打開,然后拉著女孩的手,將她帶出廢棄汽車。女人看到我們,立刻跑過來,將女孩的手扯過去,隨后,她給了我一個難看的微笑,笑容消失時,眉頭立刻蹙了起來。
我總時不時想起那孩子,不管是現在,還是當時。那時候我躺在旅館的床上,眼前就會浮現出她那張圓嘟嘟的小臉,她的笑容足以驅走夏天的溽熱,我感到幸福、寧靜、滿足,好像重新活過來。我自己的兒子始終抗拒與我交流,甚至對視。我知道他不是故意這樣做,但那確實會傷害我。我有時候會在別人的孩子那里尋求一點安慰,地鐵、市場或者公園,那些孩子靜靜注視著我做鬼臉,看我將自己隱藏在一尊雕塑或者一棵大樹后,然后再次出現。他們的眼睛微微放大,隨后嘴巴咧開,爆發一陣口齒不清的笑聲。我也對他們回報微笑,然后轉身離開。與陌生孩子的互動令我滿足,卻意味著對兒子的背叛,我因愧疚而從不讓這種互動過久。只有他死后,我才能稍微放縱自己。
從那時開始我不斷進入女孩的房間,試圖尋找她的影子,吮吸她的味道。那個房間自始至終掛著“請勿打擾”的牌子,它和衣而臥,一派拘謹,物品擺放的位置也沒有太大變化,只多了一些速食商品和一些零碎的渣滓。每次進去,我都會查看那枚鑰匙扣的位置,看到它仍在原來的位置,我便很放心。我想我注定無法帶走這個女孩,但有天他們離開,我會把這枚鑰匙扣裝進自己的口袋,作為紀念。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將那女孩作為了某種替代品或者是安慰劑,與那女孩相處的短暫的日子,令我感到愉悅,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她父母的反感,他們似乎對我與孩子的接觸很介懷。二樓的走廊上,或者院子里,一度充斥他們呼喚女孩的聲音。他們戒備女孩和我親近,故意將呼喚的聲量放大,做出焦急的情態。他們明知道女孩跟我在一起。我不是不能理解他們的反應。即出于安全考量,會想要替孩子提防陌生人的無故接近,或者擔憂孩子跟我這樣的人接觸,會生出什么可怕的陋習。我與女孩只能見縫插針地見面。有一天,走廊又傳來那個女人的呼喊。女孩忽然對我說,他們不喜歡阿姨。我裝作鎮定,但應該臉色十分難看。我對女孩說,沒關系,我不能讓所有人喜歡。那時候我才意識到,也許事情要比我想的嚴重。
后來發生的事,證實了我的預感,我本該在我們假裝開車的時候就從女人的神色上有所察覺,并且及時收斂。
男人找我談話那天,我正清理一間剛剛辦理退房的房間,他單獨朝我走過來。沒有女人,也沒有女孩。他先對我打了聲招呼,然后對我說,他很感謝我的好意。
“什么?”我放下手中剛剛拆卸下來的床單。
“我們知道你對我們額外地照顧,你幫我們照看妮妮,還幫我們收走屋里的垃圾,更換浴巾,我們很感謝,真的。但我想,你應該沒注意我們門把手上的門牌。我們一直掛著請勿打擾。”男人說。
“很抱歉我沒有注意到門牌,你知道,有時候我會注意不到這些細節。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這些都是我分內的。”
“我只是提醒你,我知道你做這些對我們有益,也很辛苦,一天之內,你會清理我們的房間不止一次。”男人干笑了聲,“有些事情我們不說,不證明我們不知道。所以還是不麻煩你費心了。如果你再這樣,我保不準我會干什么。”
我注視著男人的眼睛,對他說:“好的,下次我會注意。”
我在那間被退掉的房間里坐了一會兒,男人的話讓我汗流浹背,不得不思考他話中的含義。我擔心他發現了什么。他們也許是那種會在旅館自行安裝偷拍設備的住客。我在網上看到有人這樣干過,一些不負責的清潔工,將擦完馬桶的抹布擦拭杯子,被他們偷拍后,曝光于網絡。他們也許同樣看到了我,獨自在房間中逡巡。我想他們也許已經掌握了我的證據。
我得說,旅館的工作我一直干得不錯。在保潔方面,我擁有其它旅店的員工所不具備的自覺。這一自覺源自我的服務意識,它聽起來沒什么了不起,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做到,但很少有人真的愿意為之—在打掃房間時,我一直盡最大可能消除保潔人員作為人的痕跡。這么說有點別扭,我是說,我會盡力在保持房間原樣的基礎上做清潔工作,如同罪犯離開作案現場前清理罪證。我盡量不讓房客在回到房間后,發現這里像一片新天新地。
我預想的場景是這樣的:當住客們回到房間,第一時間還來不及發現什么,他們感到一切如同他們出門前一樣。他們將在房間里放松下來。隨著與這間屋子發生更多互動,比如換衣服、洗澡、丟垃圾……他們又會發現房間有所不同地面被拖過,桌面的垃圾被一掃而空,旅館配備的物品被歸位……往往他們注意到這一切后心里會相當舒適,而且感到自己的隱私仿佛從未被打擾過。他們認為我叫他們賓至如歸。
“真是麻煩你了。”他們說。
但我并非完美無瑕,我有小小的癖好,你可以因此否定我的人品,認為我下作、卑劣、手腳不干凈。不過這就是我—我喜歡從住客的房間帶走一些東西,一些在我看來無關緊要的東西。最初的時候我能夠克制這種欲望,可后來這成為一種習慣,到底為什么會這樣,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些被我從房間帶走的東西,包括奶嘴、跳繩、夾在雜志里的楓葉、舊郵票和貝殼手串……還有,那枚鑰匙扣,我因無法衡量它對女孩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歸女孩所有,所以暫時沒將它帶走,而是藏了起來。這些東西大多來自住客們敞開的行李箱、沒有拉上拉鏈的背包,或者被直接擱置在床鋪的表面。它們的姿態像是一種邀請,一切暴露在空間的事物對我都構成一種誘惑,仿佛希望我把它們帶走。它們與各自的主人了斷,卻又保留著主人的印記,記載了他們的音容笑貌。所有一切都將成為回憶,再長久的,也會成為回憶。我試圖把它們留下來,成為他們新的主人,僅此而已。
雖然這在我看來無傷大雅,可如果公之于眾,我想那會對我的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我不僅會成為罪犯,更會成為一個別人眼中的瘋子。我不想坐以待斃,如果他們手中真的掌握著我的一些證據的話,那我必須做些什么來挽回,而不能因為那個男人幾句不咸不淡的話便自行遠離,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得干干凈凈—那等于承認自己犯下了錯誤,陷于更加被動的地步。
那次談話之后,我想到一個方法,或者說策略,那就是,我將以更加殷勤的態度面對他們,以此顯示我的坦蕩和磊落。在接下來的日子,我確實一直按照這一策略行事,我照舊與他們接觸、攀談,毫不退讓。男人一開始對我的這番態度抱有敵意,充滿懷疑,也許他更希望我會對他們敬而遠之,不過后來我想他欣然接受了,我看出他有所緩和。
城市進入汛期后,那對男女和女孩基本沒有外出,一直待在房間內。雨水不僅讓旅館前廳原本漏雨的棚頂更加難以為繼,甚至還淹沒了外面的街道,行駛的車輛猶如船只。不過那對男女在這里似乎有朋友,總有人冒雨前來旅館看望他們,有時候是一對夫婦,有時候只是一個人。他們那些出入賓館的朋友,都不太喜歡登記,讓他們出示證件似乎是一件為難的事。我有時會幫著疏通一下,將他們放行。我對他們說,我跟他們的夫妻朋友很熟。我想我的這番舉動應該會讓他們得知。而我也適時增加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幾率,碰面后神色如常地與之打招呼,自然、溫和。與此同時,我減少與女孩的交談,也不再踏入他們的房間。
有幾次,女孩想找我說些什么,也許是希望向我傳達新見聞,我都借口有工作,躲避了,或者只說很少的幾句。最令她失望的一次,是她在雜物間的門口碰見我,央求我帶她去里面看望她的幾只蜘蛛朋友。我沒有答應她,因為我看到她的父親站在不遠處。我只能當著她的面,將雜物間的門上了鎖。看到她小小的、落寞的背影,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恐怕傷了那孩子的心,不過我告訴自己,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天終于放晴,是三人登島的那天上午。雨水退去后,陽光兇猛,熱氣沸騰。那座小島位于沿江對面,它此前被新建成一座公園,上面不僅有長頸鹿、鴕鳥之類的動物,摩天輪、旋轉木馬等游樂設施,還有一片俄式的建筑群落。坐船或者搭纜車,十分鐘就能到。
那天上午,我正在大堂打掃衛生。女人自己站在前臺,正詢問服務人員那座島的情況,她本不想去,并且顯得很不耐煩。“沒什么意思,估計會有很多游客。我們不喜歡人多的地方。”服務員聽后,連忙推薦了另一處自然景區,但女人嫌太遠了,她將手中的墨鏡不斷敲打著前臺的桌面。
我試圖再一次表達我的善意。我停下手中的活計,告訴女人,那個島上有個地方,人少,他們也許可以去那里。女人立刻表現出興趣,讓我把話說下去。我發誓我說那些話的時候絲毫沒有想過它可能帶來的后果。
“是個濕地,平時很少有人去,上面有許多夏季遷徙過來的候鳥,我以前去過,可以告訴你位置。”我說。
“太好了。”女人說,她認為那個地方妮妮會喜歡。我將位置畫在一張便簽紙上,交給她。女人看后,塞進包里,又傳了簡訊,叫男人和女孩下樓。至于她自己,則率先走出旅館大門,她撥通了一個電話,交談起來。
因為天難得放晴,老板在當天找了一位做防水的師傅來,漏雨已經讓門廳前的棚頂略微有些發霉,被水洇濕的部分,像一塊不大干凈的尿布。可我們從上午一直等到快中午,也沒見到那位師傅的蹤影,倒是那對男女帶著女孩回來了。我以為他們會回來得更晚,因為那個島很大,可以玩賞的地方很多。
女孩被男人抱著,頭埋在男人的肩膀,發絲凌亂,看起來仿佛病了,病得很重。
“這附近哪里有藥店?孩子不舒服。”女人對我說。
“她怎么了?”我問。
“熱傷風吧,”女人一頭汗,“孩子心情不好,她說她丟了幸運符。”
“那是什么?”
“一個小豬,鑰匙扣,之類的東西,我之前見孩子拿過,現在找不見了。孩子非要鬧著回來找。”
我忽然感到一陣輕松,一根看不見的繩子仿佛從我身上松綁。他們沒能找到鑰匙扣,或許證明了,沒有人發現我將鑰匙扣從盥洗臺下拾撿起來,又藏在了鞋柜。他們沒有我行為的記錄,或許也壓根沒有針孔攝像頭那類東西。一切都是我自己杜撰,自己嚇唬自己的把戲。
“你們找過了嗎?什么時候丟的?”我還是問了一句,以防萬一。
“我也不知道,孩子也不知道。也許是今天,也許是昨天,也許早就丟了。說不清。誰能告訴我藥店在哪兒?”女人問,旁邊的幾個服務員湊上來為女人指路。
我告訴她別著急,我知道藥店在哪兒,讓他們先把孩子送上去,我替他們買退燒藥。
“在旅館很容易丟東西,你們找找床與床墊之間的縫隙,垃圾箱,還有,”我說,“鞋柜,人們經常把東西落在鞋柜里。”女人點點頭,對我千恩萬謝,她說她會好好找這些地方。
“也許你能再幫我買一點安眠藥。”女人說。
去買藥的路上,我懸空的心終于放下。我既輕松,又有些沉重。輕松是因為危機解除,而沉重,則因為畢竟那孩子的發熱有我一半的原因—我把她的幸運符藏了起來。而我最近對她的態度,也一定讓她失望透了。我想著一定要盡力彌補一些,也許給她買幾根香草味的馬迭爾冰棍,或者多帶她去看看她在雜物間的蜘蛛朋友。
再次站在那對男女房間的門口,我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我沒有掏出卡片徑直進入,而是叩響了房門。
那對男女一起出現在門口,他們并排站立,入口因此顯得十分擁擠。我將藥品交給他們,他們表現出一副感激的樣子,但并不打算讓我進去。
“妮妮怎么樣?”我問他們。
“睡了,等會兒我叫醒她,喂她點退燒藥。讓你費心了。”女人說。
“別客氣,這孩子我也很喜歡。對了,東西找到了嗎?之前我說了幾個地方,鞋柜、床頭……”
“都找過了,找不見,我們想可能是丟在濕地了。沒關系,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女人說。
“怎么會?如果是丟在旅館……”我下意識說下去,但立刻制止了自己。我看到地面上停著幾個紙團,上面一團紅色,仿佛是血。
那對男女似乎并沒有聽出什么,他們堅持說,應該是丟在了濕地。我只好點點頭,將身子向后退了退,告訴他們,如果有需要,隨時找我。男女倆人連連點頭,隨后將門緩緩關上。
在517房間的門口,我站了一會兒,我沒辦法解釋地面上紅色的紙團是什么,女人為什么要我買安眠藥。我只能懷著莫名的心情離開房間。隨后我去雜物間待了一會兒,試圖尋找那幾只被妮妮放生的蜘蛛,但是我一只都沒看到,它們似乎知道我來,都躲了起來。
下午一點,維修棚頂的師傅才匆匆趕來,我們為他找了一個梯子,讓他爬上去,打開棚頂的蓋子。他查看了一番,認為這工作很棘手。
“得弄很久,我后面還好幾個活兒呢。”他啰啰唆唆,試圖增加一點費用。我們沒吭聲,老板不在,我們沒有辦法擅自做主。他見沒人回應,便從梯子上下來,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打起了電話,一會兒聯絡找人,一會兒又叫人帶一些工具和材料。
“你們這管飯嗎?我中午沒吃飯。”過了一會兒,他說。
早餐時間雖然早就過了,但廚房還剩一些米粥、煎蛋、香腸和面食。服務員問他嫌不嫌棄,他便站起來,說:“在哪兒,我得先吃飯。”
服務員讓我領著那位師傅去餐廳。我打開門,將他讓進餐廳,那時,正好看到那對男女穿戴整齊,重新抱著妮妮來到大廳。
“抱歉,我們這兒維修,你們躲著點走。”旅館的服務員對他們說,“這是要出去?”
“對,上午在島上丟了東西,我們再去找找,你們忙吧。”女人說。
女孩正趴在男人的肩頭,眉目低垂,仿佛仍在熟睡。既然孩子病著,為什么還要帶出去?我正想出去問問,卻被維修的師傅叫住。他沖我嚷,你瞅啥呢,還讓不讓人吃口飯了?我向他道了幾句歉,隨后跑去后廚幫他要吃的,等我熱了飯菜,重新回到餐廳,男女倆人已經不見。
棚頂維修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那位師傅此后又叫來兩個人,三人合力,才勉強做好了上面的防水,將棚板扣好。至于到底做得怎么樣,只能等下一次雨天才能驗證。幾個人怨聲載道,覺得收錢少了,第一個來的師傅問我們旅館晚上有沒有飯,他們在這對付對付吃了。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們悻悻離開。
我將掉落在地面的碎片、殘渣清理干凈,又拖了幾遍地,才結束工作。我無心吃飯,心臟悶得厲害。外面氣壓很低,似乎又在憋著一場大雨。我于是回到樓上的房間休息。
其間,我睡著了一會兒,仿佛還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和女孩一同坐在江邊的觀光船上,外面下著小雨,頭頂的燈籠隨著波濤搖搖晃晃,我們也搖搖晃晃。可是沒過一會兒,那盞燈籠嗞嗞啦啦響了幾聲,忽然熄滅了。
“阿姨,燈籠上的蜘蛛哪去了?”女孩在夢中問我。
我醒過來,發現自己的對講機在響,服務員的聲音從里面傳來。
姐在嗎?517退房,你過去給看一下。
我從床上坐起來,將床頭的對講機拿過來。收到,我馬上過去。我說。
講完我才意識到,517是女孩和那對男女的房間,他們要退房了。我連忙跑過去,刷卡,開燈,發現房間里一片凌亂。行李被帶走了,床上堆滿浴巾、塑料袋、衣架。地板濕漉漉的,有明顯雜亂的腳印,帶泥。衛生間的門開著,那里懸掛著女孩那件橙黃色的雨衣。我又去檢查鞋柜,發現那枚鑰匙扣,還靜靜地躺在那里,騎著掃帚的小豬,將臉對著我。眼睛一只藍色,一只綠色。
“你們太大意了,妮妮的東西忘記帶了。”下樓后,我對那對男女說,語氣一如往常,親切、自如,說完,我將女孩黃色的雨衣遞過去。
“沒關系,幫我們處理掉吧,”男人說,“外面不下雨了,這種一次性的雨衣穿幾次就夠本兒了。”
我對他笑笑。他們正在辦理退房,我沒看到女孩的身影。“妮妮呢?”我問他們。
“妮妮被她媽接走了,知道孩子病了,她媽下午趕過來了。現在他們應該到火車站了,一會兒我們也過去跟他們匯合。”女人說。
“啊,我以為你們就是妮妮的父母。”我感到驚詫。
“是親戚。”男人說,說完立刻將目光從我身上收走,重新看向前臺的服務員。
我點點頭,將手伸進口袋:“對了,妮妮的幸運符……”
“那個我們下午在濕地那里找到了,就掉在草叢里,之前著急沒看到。妮妮高興壞了。謝謝你還記得。”女人對我說。
我原本伸進褲袋的手,在聽到女人的話后,只得緊緊攥著。那枚鑰匙扣,差點被我捏碎。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形同此前某一時刻我突然的失語。
辦理完退房手續,女人掏出一百塊錢,說是還給我此前為妮妮墊付的藥費,見我沒說話,將錢塞進我的口袋。男人這次終于點上了一支煙,女人沒有責怪他。他們的心情似乎都不錯。
我離開旅館的時候,棚頂還是沒修好,雨天時依舊向下淌水,仿佛無休止的哭泣。我將妮妮的那只騎掃帚的小豬,還有那件遺落的、橙黃的雨衣塞進行李箱里,那些來自其它房間的、不屬于我的物品。我都把它們拿了出來,放進前臺遺失物品存放處。我查詢了那對男女的住房登記,他們都姓喬,身份證信息顯示他們所在的城市是一座邊境城市,對面就是朝鮮。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在那里見過他們。
后來我回過一次老家,在母親去世的時候。下葬那天,我跟家人一起吃了頓飯,我吃得很飽。飯后,我想出門走走,就出了門。那天天又下雨了,我在地鐵站出口買了一把傘。我不知道要去哪。我先是走到了我原來的家,之后又走到旅館,接著又不知怎么地走到了江邊。我很久沒來這些地方了,它們還是老樣子。我在江邊坐了一會兒,上空的觀光纜車正沿著軌道,緩緩下行,它們在雨中閃著五色的光,像一簇簇小小的煙火。
一艘大船正慢慢在岸邊停靠,一批游客下了船,新一批又上了去,即使下雨,他們的興致依舊很高。售票員在船上喊著,“游江,游江,十塊錢一位,還有座兒!”我想了想,站起來,對女人說,我沒有零錢,能找嗎?她說多少錢都能找,上來吧。我于是登上觀光船。船篷雕龍刻鳳,上面還掛著古香古色的燈籠,我看到其中有一盞不亮的燈籠,走過去,坐下來。
船客滿了之后,大船緩緩開動,它先靠著江岸行駛,之后又轉了一個彎,向對岸的燈火靠攏。是那座小島。我手里攥著那枚鑰匙扣,注視著江面,江水被江浪攪擾,又被砸落的雨滴激起水花,雨在水面上留下了自己的形狀。這讓我想到那個夏天,一個在雨中消失的夏天。
不知道旅館里的那些蜘蛛怎么樣了,剛才路過的時候應該進去看看,我想著。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即使是毫無用處、微不足道的東西,也不該由我評判。我不是它們的主宰。我應該盡早明白這些,我為此深深懺悔,在許多夜晚夜不能寐。
一個波浪,船震動了一下,身邊的人們發出陣陣喊叫。我一驚,鑰匙扣從我的手中滑落。
“咕咚。”
周圍的大人和孩子再次爆發一陣叫嚷,似乎在為自己剛才的驚慌失措感到可笑。我看到那只小豬在水面留下自己的形狀,之后轉瞬下沉,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和那個消失在雨中的夏天一樣。
(責任編輯: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