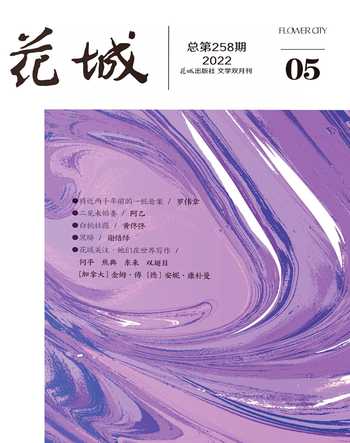小事件
劉鵬艷
30分鐘前
30分鐘前老姚還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他只是接了一單外賣,地址是東流北路原東市區糧食局宿舍2單元501室。當時他還挺高興,剛剛跟兒子通了電話,這小子說新談了個女朋友,五一就帶回來給老子瞧瞧。當老子的難免有些手舞足蹈——兒子快30了,前面談了幾個對象都沒戲,正經往家里帶的,這還是第一回。接單的老姚按捺不住雀躍的心情,就那么喜氣洋洋地跨上電驢子,往糧食局小區方向奔去。
老姚的笑容綻出成堆的褶子,顯得有些滑稽,一張國字臉皮松肉弛,五十出頭的年紀,看起來倒有六十。他這一輩子都活得皮粗臉糙,沒空計較時光帶給他的那些滄桑和沉淀。早些年還是小伙子的時候,他就比同齡人略顯老相,這幾年風里來雨里去,老得更快了,但只要掙錢的速度能趕得上,他倒也欣然接受。
迎面騎過來一個年輕人,和老姚一樣,紅色勾金邊的電驢子,夸張的紅馬甲、紅頭盔。兩人錯身而過時點頭示意,老姚快樂地喊:“逆行了啊!”年輕人嗖一下過去,不忘回頭丟一句:“你也不比我守規矩!”老姚看著風馳電掣絕塵而去的同行,心想到底是年輕,逆行還敢這么快。可是,誰不趕時間呢?
在路上跑的騎手都比他年輕,他有時候想起自己的年紀就有些氣喘吁吁,但真跑起來也沒那么矯情,畢竟跑一單是一單,鈔票落袋為安。這是最實際的動力學因素。出來跑不為錢,難道還為了那些大人物說的什么“情懷”不成?他從來不關心時事政治、經濟趨勢什么的宏觀問題,有時間不如刷刷抖音快手,哈哈笑幾聲。他不過是個隨處可見的小人物,是這座地級小城市里頂不起眼的草根,混口飯吃,就這么簡單。什么政治經濟環境還不讓小老百姓吃飯?誰發明的“草根”這詞兒?是草,還是根,聽著就自帶一股子泥土腥氣,鞋底下踩來踩去的那種。老姚覺得這詞兒貼切,用在自己身上最合適不過。他從不敢高看自己一眼,沒有這個資本,草根就挺好,服服帖帖地生在地上,土頭土腦,不拉風,不惹眼,本本分分的。
他是個本分人,靠自己的一雙手,先把老婆娶上,然后又生下兒子,一手一腳養活一家老小,連個偷奸耍滑的機會都沒有。到了兒子這代,好像娶媳婦沒那么容易了。首先是兒子心大,不愿在家里待,北上廣又待不下,只好跑到省城去落了草。省城的房價也不低,老姚為了湊首付,跑得一雙腿都快斷了。就那也還差一截,不多,十萬塊。十萬也是個數,俗話說,一個子兒逼倒英雄漢,況且老姚又不是個逞得起英雄的主兒。那就借么,周圍親戚,一家借個兩三萬,能湊十萬塊錢也是不容易,這年頭,能借錢的都算是至親了。
但借下的賬得還,老姚皮再厚,不能拿自己的臉當草紙;再加上房貸,月供也是不小的一筆開支,這都得老姚出面,親力親為。兒子是不可能擔這筆賬的,也擔不起,照老姚老婆的說法,兒子的肩還嫩,不能剛入社會,就讓萬惡的房貸給壓趴下了。兒子不能趴,那么只有老子往地上趴了。老姚苦笑,好在他本就是地里土生土長的,犁田耙埂,風吹日曬,練就了一副好腰腿,后來進了城,也是各種粗活累活都扛過,騎上電驢子就能跑,跑得還不比年輕人慢。
現在他正騎著電驢子跑在路上,4月的風擦著粗糙的臉皮刮過去,臉頰上干燥的皮屑好像簌簌動起來,和額頭、眼周、嘴角的溝溝坎坎一起,在這個溫柔多情的春天里可著勁兒地放風。他心里測算了一下距離,15分鐘的車程,規定半小時送達,綽綽有余,不過現在是晚高峰,多少受點影響。
老姚要去的老糧食局宿舍,早些年是個條件不錯的小區,后來糧食企業關停并撤,小區就有點年久失修的意思,好多房子都租出去了,修車的、洗頭的、販菜的、開鎖的、美容的、健身的、通下水道的、推銷保險的,各色人等都有。租客有一半是單身小青年,到了飯點兒,小區里來去橫豎都是跑外賣的,老姚早就熟門熟路了。有時候老姚也搖頭,兒子在省城,怕也是這樣對付三餐。年輕人嘛,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是懶,不愿做飯,省得洗碗,一個電話,外賣就送來了,倒退回去20年,可想得到?這一大批點外賣的,催生了一大批送外賣的。說句大白話,老姚還得感謝人家夠懶呢。
先前看大門的是個瘸老頭兒,薄唇,短髭,三角眼,面相雖看著凌厲,倒還好說話。老姚跑得勤,光是同一個小區,有時一天得跑好幾趟,進去出來,老姚點個頭,瘸老頭兒也點下頭,像是對暗號。久而久之,老姚竟有了錯覺,以為老糧食局宿舍的大門形同虛設,至少,對他老姚是不設防的。
老姚心情不錯,騎得就有些生猛,到路口拐彎,也沒顧上減速。這幾年路上跑得熟了,車技說不上好,總歸差不到哪里去,這一點老姚還是有自信的。沒想到路口那兒有個新手上路的女司機等著他呢,你風馳電掣,可把她給嚇壞了。老姚這個彎,拐得就不大順當,原本可以挨著邊兒擦過去,現在變得險象環生,前轱轆巧不巧地擦過去,后轱轆卻擦不過,搖搖晃晃地,哐當摔地上,火紅色的頭盔也從腦袋上掉出去,骨碌碌滾出幾尺,像是一顆明晃晃的人頭。
路口當即就堵上了,這個點兒,南來北往的,車流量本來就大,哪里經得住一點栓塞?老姚的好心情給摔得稀碎,車禍現場瞬間就變成了圍觀展示區,他被亂七八糟的車和七嘴八舌的人困在當中,像條溺水的魚。那出師不利的女司機怕被訛住,連車都沒下,直接打電話報了警。好嗎,光是等警察就用了10分鐘。待交警騎著摩托閃著警燈嗚哇嗚哇地趕到,老姚已經心焦得不行,急忙忙地搖搖手自認倒霉。警察說你認倒霉不管用,既然報了警,就得走程序,身上有什么零部件摔壞沒有?要上醫院檢查不要?還有賠償的問題,雙方可以協商。女司機立刻皺著眉說她有保險,老姚想怎樣就去跟保險公司談,反正她是一個字也不打算跟老姚“協商”,否則也不會第一時間選擇報警。雖然女司機是全責,但從身架到口氣都是相當的理直氣壯,全程不看老姚一眼,生怕老姚像塊狗皮膏藥粘上她似的。
老姚胸口憋著氣,不過這可不是賭氣的時候,況且倒下去那一刻,他心里清楚并不是女司機的車“撞”了他,多半還是因為失去平衡,自己沒把住。倒地的時候他腳下還稍稍帶了點勁兒,半邊身子搪了一下,因此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傷,不過是右手掌撐在地上擦掉一塊皮而已。最幸運的是外賣包裝盒的密封性不錯,吃的喝的一點兒沒灑。他皮糙肉厚的,原沒把這當回事。要不是女司機報了警,非得等警察看現場,他都打算拍拍屁股走人了。警察這么一說,老姚覺得自己孬好得表個態,就耷拉眼皮伸出一根手指頭,也不看女司機,對著警察說,叫她給一百塊錢,他去藥店拿瓶跌打酒就算了。警察看看女司機,女司機沒想到問題解決得這么容易,臉上頓時呈現出如釋重負的表情。看來出了事找警察是對的,如果不是警察在場,這個送外賣的迫于人民警察的威懾力,肯定不會這么輕易罷休。女司機揣著這句潛臺詞剜了老姚一眼,把一張粉紅色的鈔票遞過去。
老姚接過錢,把滾到地上的安全帽撿起來,套在腦袋上扶正,跨上電驢子就開拔了。時間不等人,他還趕著送外賣呢,咋也不能落個差評。權當讓狗咬了一口。老姚心里罵句娘,車把上攥了把勁兒,轟一下躥出去,耳聽身后毒舌的女司機還在跟警察碎碎地念叨:“您瞧吧,就這種危險駕駛,早晚掛在路上。剛才他就是這樣趕著投胎似的,我躲著躲著沒躲開……”
風一吹,話就亂了,老姚頭有點暈,心里膈應得慌,又犯不著再折回頭去吵一架,就這么盛著一肚子氣,氣鼓鼓、暈乎乎地往糧食局小區去。原先的高興勁兒早沒了,真是人有旦夕禍福,眨個眼的工夫,好的變成壞的,香的變成臭的,餑餑直接變垃圾。老姚心想我低人一等是怎么著?我他媽還就低人一等了!想想那女司機的腌臜嘴臉,老姚就來氣,仿佛是,他身上有病毒,他看她一眼都有故意散播致命病毒的作案嫌疑似的。
一路騎過去,4月的風擦著老姚粗糙的臉皮,頰上一層干燥的皮屑簌簌地顫動,和額頭、眼周、嘴角的溝溝坎坎一起,把這個郁躁的春天填滿了。不冷不熱的天兒,老姚竟騎出一身汗。到糧食局大院門口,老姚的心思還在路上劍拔弩張地飄著呢。
電動車不準進小區,老姚下來,把車支在一邊。一個穿保安服的中年男人虎著臉過來:“嗨嗨嗨,你車停這兒,人還怎么走路?”老姚抬頭看看,面生,心想瘸老頭兒呢?那保安一臉認真地指手畫腳,讓老姚把車移開,老姚只好捺下性子,配合他的工作。
車移了二尺,老姚高低不愿動了,人沒有那么胖的,身形再怎么寬也過去了,這能擋誰的道兒?老姚不再配合保安工作,提了外賣就打算移步進小區。
“哎哎哎,我說你,送外賣的不讓進啊!”保安攔住老姚,嚴肅的樣子有些嚇人。
“怎么不讓進?我昨天還進去呢。”老姚也有些惱了,“昨天可不是你看大門。”
保安臉上掛了霜:“少跟我來這一套!墻上貼著小區管理制度呢,外賣、快遞一律不準進小區。怎么著,還想硬闖哇?”
30分鐘后
30分鐘后,東流路派出所的小周給老呂做筆錄,耳里只聽老呂哭得哇哇的。小周抬起頭,拿簽字筆不耐煩地敲敲坑洼不平的桌面:“現在知道哭了,當時干嗎呢?”眼前這張老式條桌很有年代感,隔著小周和老呂,像是隔著一整片的滄海桑田。小周心想所里早該把這張桌子換掉,領導辦公室的家具都換多少茬兒了。
老呂的兩只手埋住自己的臉,胡蘿卜似的又短又粗的十根手指頭,把他那原本就不大好看的塌鼻子、腫眼泡揉搓成皺巴巴的一團。淚水從指縫里滲出來,看著又可氣又可憐,小周索性把筆錄往前一推,身子卸了勁兒,靠在椅背上,從鼻孔里重重出了口氣,聽起來像是一聲嘆息。
五分鐘前所里接到電話,說是剛剛從糧食局宿舍小區送到醫院的那個人沒搶救過來,已經證實死亡。小周解開脖頸上的風紀扣,又從頭上摘下大蓋帽,對著頭臉直扇乎。這鬼天氣,到了晚上更燥得慌。頭頂上盤著一架蒸籠似的,小周的耐心和身體里的水分一起流失得差不多了。
從上午開始,小周一直在外面出警,連口水也沒顧得上喝。先是幫人逮貓,后來跟一個丟包的年輕女孩到失竊現場走了一遭,再后來接到報警電話,說東流北路原東市區糧食局宿舍出了嚴重狀況。小周他們馬不停蹄地趕過去,把橫著身子臥在地上的那位老兄送進醫院,又把抱頭蹲在一旁瑟瑟發抖的這個家伙帶回派出所。
被帶回派出所的是老呂,小周放下電話,一句“出人命了啊”,老呂就開始哭。小周說你現在知道哭了,當時干嗎呢?老呂回答不上來,他腦子還沒轉過彎兒,一會兒工夫,人就沒了。剛才那人還跟他橫呢,他和警察同志都交代了,那個送外賣的無視小區規定硬往里闖,他無奈之下才出的手。
“怎么個出手法兒?”小周皺著眉頭問老呂。一把年紀的人了,兒女成行,兩鬢見霜,下手還沒輕沒重的。小周乜斜著愁眉苦臉的老呂,心里滿是不屑。
那根被定性為“兇器”的黑膠皮棍兒早就主動上交給警察了,老呂戰戰兢兢地等候著處罰決定。遠親近鄰都說他是個老實人,打小聽媽的話,后來聽老婆的話,在單位也是夾著尾巴做人,領導罵他,再怎么難聽的話,他都縮著腦袋夾緊了,連屁都不帶放一個。就這么個老實人,剛才把一根小孩兒手臂粗的膠皮棍敲到了另一個人的腦袋上,竟然,還把人家敲死了!聽聽,這得是多大的怨仇哇?
可是,往日無冤,近日無仇,警察一問,老呂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不認識,不認識。”這就奇了怪了,警察一拍桌子:“不老實!”老呂嚇得一哆嗦:“確實是不認識,我第一天上班……以前在南七里塘的金鷹大廈當保安,這才調過來。”他們保安公司的經理后來也證明,確實是這么回事兒。黑膠皮棍是根據工作需要由公司統一配發的安全裝備,理論上不算有預謀的作案工具。經理還出于人道主義精神替老呂說了幾句好話,大概意思是老呂是他們的老員工,工作上還是很負責任的,出了這么大的事,任誰也想不到,絕對是個意外。
誰也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么,讓素不相識的兩個人拳腳相向,還鬧出了人命。問老呂,老呂說是送外賣的老姚蠻不講理,無視管理規定,硬闖小區,他為了維護小區的秩序和業主的安全,挨了老姚幾下子,一時怒火攻心,從小區門崗的凳子下面摸出黑膠皮棍,鬼使神差地給了老姚一下子。老呂特別強調老姚打了他“幾下子”,而他只打了老姚“一下子”。因為急于表白,他全然顧不得體面,唰一下把衣襟掀起來,給警察看他瘦骨嶙峋的肋下那片青紫的瘀痕。“就一下子,我……哪知道會這樣……”老呂委屈地豎起一根手指頭,又很快地彎下來,迅速地藏到了大腿之間,拼命絞著,大概恨不得將這根指頭立刻處理掉。
這起案情極其簡單的殺人案,差點讓小周背過氣去。
人間四月天兒,怎么就這么燥得慌,小周扇著大蓋帽,舔了舔發干起皮的嘴唇。他起身去飲水機接了杯水,又給老呂帶了一杯。老呂慌忙站起來,受寵若驚地躬身接了,嘴里像螃蟹吐泡似的往外禿嚕:“謝謝警察同志,謝謝,謝謝!”他還沉浸在突如其來的恐慌中難以自拔,以為討好警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不可饒恕的錯誤,又或者,他50多年的人生經驗告訴他,在權力者面前表現出順從和謙卑可以降低某種風險。
可惜今天的這場“意外”也太讓人意外了,小周搖搖手,讓老呂坐下,告訴他處理決定沒那么快出來,他可以考慮請個律師了。
老呂像是沒太聽懂似的,茫然地坐下來,空洞的眼神里滿是惶惑和無助。他是個老實人,遠親近鄰都這么說,他一輩子也沒機會攤上這么大的事,把人打死了,叫誰能信?天色早暗下來,要不是在燈下,早就有一團一團的墨涌上來了吧?他忽然覺得冷,抱住雙臂縮在椅子里,原本就瘦小的身體一下子塌陷下去。
小周支著下巴,有幾分同情地看著他。剛才小周要給老呂老婆打電話,老呂慌慌張張地攔住了:“別,別……她……有病哩……”老呂堅持讓小周給他們領導打電話,理由是,他是在工作時間因為工作理由出的事,公司得管他。小周哭笑不得,說你們領導的電話要打,你老婆的電話難道就不打了?出了這么大的事,無論如何也瞞不住。遠的不說,近期你肯定是回不了家了。一個大活人突然不見了,你老婆不找?老呂埋著頭,軀體僵硬地深陷在自責和懊悔當中,像顆萎縮的棗核似的嵌在沼澤里,安靜而又絕望地等待著滅頂之災,半天憋出一句:“再說吧。”
等保安公司那位姓毛的經理過來,小周才知道老呂的老婆患有精神分裂癥。“還是暫時不說的好,他老婆那人……唉,不要這邊‘葫蘆沒按下去呢,那邊‘瓢又起來了。”身材矮胖的毛經理從褲兜里掏出紙巾,擦著額頭冒出的汗,有點氣急敗壞。他接到電話就著急忙慌地趕過來,路上差點追尾。這鬼天氣,讓人沒點準備就熱起來,毛經理的白襯衫像水洗過似的緊貼在后背上,胳膊彎里卻搭著條西裝褂子。派出所門口沒有停車的地方,他從幾百米外的停車場小跑過來,穿了一整條巷子。原以為晚上涼,特意披了件上衣,誰知晚上比白天還燥。
毛經理痛心疾首,說他認識的老呂脾氣不錯,“平時同事之間有點摩擦,他都禮讓三分”,“工作上也肯吃虧”,不是那種為一點小事就動手的人,更何況殺人這么沖動。小周點著頭,不置可否,旁邊,早一年分來派出所的大劉卻不以為然:“就這種人,平時蔫巴巴的,你以為他干不出來,結果一出事就是大事,有沒有?”
立刻就有人附和,都說大劉說得對。所里幾年沒出這么大的事了,平時處理的案子,也就盜個電動車什么的,老呂的事一出來,一時間成為熱議的焦點。大家伙兒你一言、我一語的,倒把老呂晾在一邊。那倒霉的事主,現在愁眉苦臉地蜷在一個角落里,膽戰心驚地等著懸在頭頂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掉下來,給他一個痛快。他想毛經理會為他說幾句好話。他平時見了毛經理都畢恭畢敬,點頭哈腰,偶爾還會殷勤地把口袋里的好煙讓出來。他本人不抽煙,別人給他根好煙,他就存在兜里,遇上毛經理便遞上去。雖然毛經理從不抽他的煙,但對他的態度還是相當認可的。不過眼下,毛經理的話好像并不能使他脫罪,他心神凄愴地隔著遙遠的距離聽到了自己的命運,頹然癱坐在地上,從幾乎是匍匐的身體里生出一陣悲涼。
毛經理一臉同情地把老呂家的情況一說,警察都直嘖嘴: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妻子、80歲的老娘,還有一對上高三的雙胞胎女兒,都靠老呂的一副肩膀硬扛著呢,這下塌了天。可殺了人就是殺了人,誰也沒這個權力把老呂放回家去,那一家子,唉,就那樣吧。毛經理搖頭,小眼睛在金絲眼鏡后面,配合著夸張的表情眨巴眨巴。前胸后背的汗收了些,說了半天話的毛經理覺得涼,反手把西裝褂子套上。這時候聽見羈押室里老呂的哭喊聲隔著門傳過來:“毛經理,我是因為認真執行崗位責任制度才被抓進來的,你要幫我呀……”
毛經理尷尬地搓搓手,油光光的胖臉對著小周他們:“我剛才見他的時候已經和他說了,這個,設立崗位責任制,是為了把工作做好,不是鼓勵員工殺人嘛,哈,怎么能拿這個做借口呢?荒唐呀,荒唐!”毛經理又覺得熱了,兩手拉住西裝外套的兩片前襟,最大限度地敞開懷。“這鬼天氣,穿上熱,脫掉冷。”毛經理咕噥一句。大劉湊趣兒似的跟著來了一句:“也是,這工作吧,認真也不好,不認真也不好。您說上哪兒說理去?”毛經理雙手不自覺地摸著凸起的大肚腩嘿嘿笑,小眼睛瞇起,一副憨厚模樣。
當時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呢?
根據幾位目擊者的證詞,當時送外賣的老姚和新上任的小區保安老呂,先是因為外賣能不能進小區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口角,然后發展到肢體碰撞,在幾個回合的推搡之后,雙方的拳腳功夫開始升級,最終老呂使出了公司派發的奪命追魂膠皮棍,讓老姚一命嗚呼。整個過程不超過三分鐘,看熱鬧的人甚至沒看過癮。有人拿手機拍下了老呂施暴的那一擊重棍,不斷“哇噻”的話外音讓視頻更加生動鮮活,幾乎是在事件發生的同一時刻同步上傳到云端,呈指數級傳播的網絡發酵就此帶火了沒落多年的糧食局小區。
那個4月的黃昏云淡風輕,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老姚騎上電動車的一剎那,心情還是有幾分雀躍的,因為兒子正經八百地談了個女朋友,讓這個做父親的感到未來可期。趁著浩蕩的東風,他一路愉快地騎行在送外賣的路上。這份工作雖然辛苦,卻能夠給他帶來相對豐厚的報酬,并讓他扛在身上的債務顯得不那么沉重。但在東流路與紫湖路交口和一輛私家車發生剮蹭之后,他的好心情隨即被破壞殆盡。他幾乎是有些氣急敗壞地重新跨上電動車,往糧食局小區方向騎去。一路上他感到頭暈、氣悶、燥熱難當,扣著安全帽的腦門上滲出豆粒大的汗來。
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他一把摘下了安全帽,支起電動車,拎上外賣就往小區里鉆。他和看門的瘸老頭兒打了幾年照面,熟門熟路,況且他是遵守小區規定的,電動車留在了小區外面。他沒想到有人埋伏在這兒刁難他——突然冒出來的小區保安攔住他,橫眉豎眼地挑他的理兒。他一下子就火了,你奶奶的,那些有錢有權有地位的人看不起老子,老子認倒霉,怎么你一個小保安,也比老子高一頭不成?說到底,不就是個看大門的!老話怎么說的,看門狗,看門狗,穿上老虎皮,也強不過一條狗。保安老呂在老姚眼里,忽然就生出狂吠亂叫的惡犬形象來,再加上客戶一個電話一個電話地催,“超時,差評”的脅迫感讓老姚登時橫下心來。
新來的保安老呂對小區環境還不是很熟悉,但“外賣、快遞一律不準進入小區”的規定他是知道的。“規定”就白紙黑字地張貼在保安崗亭的外墻上,既是一種對外廣而告之的宣示,也對老呂自己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他一向是個安分守己的人,從國家的法律法規到單位的規章制度,他絕不敢有秋毫觸犯,況且初來乍到,工作上不說做出什么驕人的成績,認真負責還是能做到的。這么一說,大家伙兒大概就了解啦,老呂其實是個膽子特別小的人。因為膽小,所以做事特認真,特仔細,生怕出一絲紕漏。他可不敢胡亂出紕漏,一家老小都指著他呢,他有什么膽子出紕漏呢?
這個春風浩蕩的日子,老呂第一天上班,認認真真地,仔仔細細地,認真、仔細到近乎偏執的地步,讓老姚誤以為是一種刁難。
“哎哎哎,我說你,外賣不讓進啊!”老呂伸手攔住老姚,嚴肅的樣子有些嚇人。
“怎么不讓進?我昨天還進去呢。”老姚一臉不服氣,“昨天可不是你看大門。”
老呂臉上掛了霜:“少跟我來這一套!墻上貼著呢,外賣、快遞一律不準進小區。怎么著,還想硬闖哇?”
老呂是有身份的人,一身保安制服就是最好的憑證。認真履行崗位職責的老呂認為,這保安呢,擱在小區門口,就得有門神的架勢。他攔老姚攔得有理有據。
老姚可不這么想。一個看大門的,還跟老子跩得二五八萬,老子不吃那一套!
兩人當場就戧起來,你看不上我,我瞧不起你,相互指認對方是“鄉里頭的”。其實進城都沒幾天,面對張牙舞爪的對手,卻跟坐穩了江山的帝王似的,霸氣側漏地滲出一種滑稽的自我高級感。先是嘴上不干凈,“替人跑腿的”罵“給人看大門的”,“給人看大門的”氣不過,回罵“替人跑腿的”。罵得不過癮,嘴炮不斷升級,各種難聽話砸過來扔過去,像是鍋爐里沸騰起來的開水,唰唰地冒白汽,那閥呢,咕嘟得實在關不住,漸漸就動上了手。也不知誰先使了一膀子力氣,叫對方搖搖晃晃,接下來就跟啟動了引擎開關似的,停不了手腳咯。不一會兒,呼呼啦啦圍上來一圈兒看熱鬧的。
光看,熱鬧么。大家伙兒熱熱鬧鬧地看老呂和老姚撕起來,你一拳我一腳的,雖沒有電視里的功夫好看,但落個實在,拳拳到肉。大家伙兒沒有不愛看的,有的還拿起了手機,對準了拍,估摸著網上也有人愛看。
老呂個頭矮些,又生得精瘦精瘦,論塊頭不是老姚的對手。有人就在一邊說:“那保安要吃虧。”另有人說:“也不一定,拳怕少壯,我看那送外賣的怪老相……”都只歪歪嘴,并沒有上前拉架的。
這邊老姚和老呂撕得更兇些,老呂肋下吃了老姚一拳,痛得還了一腳,無奈腿不夠長,倒顯得老姚騰挪功夫了得,差點沒惹看熱鬧的人喝一聲彩。老呂也是昏了頭,盛怒之下貓腰進崗亭摸出黑膠皮棍來。
老姚原以為老呂吃了虧,定是落荒而逃了,誰曉得老呂一磨身子,呼地上來給他一棍。老姚哼都沒來得及哼一聲,就軟軟地癱在地上了。眾人一陣驚呼,把看熱鬧這事兒推向高潮。老呂這下穩準狠,也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堪堪敲在老姚的腦袋上。老姚到死也沒明白,這一下的速度和力度,怎么拿捏得那么恰到好處。要是生命也和電影一樣能夠回放,他大抵會后悔剛才因為嫌熱摘了安全帽。在倒地的最后一秒,老姚瞳孔里映出掛在電動車把手上的那個紅色安全帽,搖搖欲墜,如一團冰冷的火……這幀畫面那么驚悚,好像平白又出了一場車禍。這回,比上回慘烈得多。
外賣盒子骨碌碌滾了一地,仍是滴水不漏。老呂呆了一呆,無端地想,待會兒老姚爬起來,會不會把外賣撿起來接著往里送。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想得多余,因為老姚一動不動,不像是打算繼續跟他作對的樣子。老呂慌了神,這才想起來,剛剛那一棍子敲得不是地方。我的天,敲人腦袋上了!
哎,出大事兒了!眾人這才恍然而悟似的,收起瞧熱鬧的那股子熱鬧勁兒,報警的報警,幫忙的幫忙。等到警察來,一問,都說,誰想得到呢!前后沒有三分鐘。
是想不到,一個送外賣的和小區保安打架,把命給送了,憑誰也想不到。
就沒有哪個上去勸勸的?
誰想得到呢!前后沒有三分鐘。
照那些目睹了大事件的人的說法,都以為是尋常打架呢。這小區里人多且雜,相互之間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多是擦肩而過。有時若擦上了,便生出口角事端,動手動腳的也不在少數。打架實屬尋常,在旁人看來不過是個樂子。誰想得到呢?若是廝打得厲害,時間一久,該有人上去拉架,偏偏兩個半老頭子,又不像能打出什么名堂的,還以為扇兩巴掌就完了。后來有人看那保安摸出黑膠皮棍,心想,嚯嚯,使家伙了!可還沒夠得上看清楚身形步法呢,只一下子,那送外賣的就倒在地上。
小周問了一圈,大概就這么回事。進,還是不進,是個問題。圍繞這個問題,保安老呂和送外賣的老姚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據理力爭,拒不妥協,終于聚沙成塔地釀成了一起重大案件。那一顆顆粗糲的沙子,是4月燥熱的風,是黃昏掉落的日頭,是馬路上刺耳的喇叭,是人來人往的喧囂,是催單的電話,是銀行的貸款,是墻上的規章制度,是四周異樣的眼光,是日復一日的庸常和辛苦,是一家老小的生計,是心底冒出來的一簇小火苗,是神經叢上跳動的那聲命運的獰笑……老呂揮出黑膠皮棍的時候聽到了一聲悶響,他沒在意,那種鈍物與鈍物之間親密而猛烈的接觸,聽起來像是噗的一聲屁。
這么多年,老呂也變鈍了,什么都挑不起他的興趣似的,缺乏對周遭事物的感知力。要是他足夠敏銳,哪能忍受得了經年累月鈍刀子割肉的痛呢?老婆發病時的歇斯底里,要吃要喝、要上補習班的一對雙胞胎女兒,還有老娘的慢性病,哪一樣都讓他煩惱不已,又不得不按捺下厭煩之情。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假裝咳嗽一聲,缺什么、少什么,就有人主動送到面前來。他什么都要自己觍著臉去掙,缺這少那的,夠他累上半輩子。他這半輩子都在為雞零狗碎的生活打工,因而也就活得雞零狗碎,上不了臺面。最驚天動地的一次,怕就是今天這樣的“高光”時刻了,一棍子把人給敲死,嚯,多大的事體!老呂貼著羈押室冰涼的墻面簌簌發抖,熱乎乎的4月天兒,竟然抖得上下牙齒咯咯打架。
小周把羈押室的鐵門當地帶上,先自打個激靈,這是他分來東流路派出所之后,接手的第一個大案。大劉說,這案子很簡單。他卻不這么認為。此案實在是太復雜了,復雜到一目了然的驚悚。涉世未深的他像是卷入了一個避無可避的旋渦。看似偶然的結果,竟使他和關在羈押室里的老呂一樣,驚覺背后一涼。他無端地感到心情低落,那種被有背景的同學頂替身份的郁悶之情,又陰云似的涌上了心頭。
他不知道接下來老呂會受到什么樣的法律懲罰,也不想知道。雖然那段“保安揮棍打死外賣大叔”的視頻還在不斷發酵,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對這種大事件的熱情不會持續一周。要不了一周的時間,網上的舊聞就會被新的大事件覆蓋,輕飄飄地泯然于眾,任誰再也想不起那個猥瑣的小保安和死去的外賣大叔。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一天結束了,好像生活才剛剛開始。小周搖搖頭,晚上還約了女朋友去酒吧。春夜無邊,明晃晃的燈光下,臉上暈染著幾分落寞的小周走到派出所入口處那面碩大的衣冠鏡前,正了正頭上的帽子,然后,默默地朝更衣室走去。
責任編輯 李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