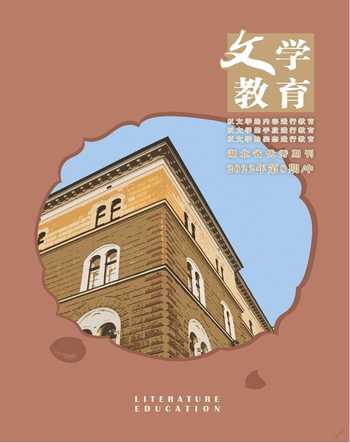論《熱帶癲狂癥患者》中的東方形象
毛伊揚
內容摘要: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因其猶太人身份而遭受迫害,他的作品對20世紀西方社會現實進行深刻分析,宣揚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在他的《熱帶癲狂癥患者》中,描寫了一些東方男女,他們大多身份卑賤,愚鈍、順從、落后,與西方男女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類東方形象的塑造既是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結果,同時也加深了西方對東方人的刻板印象。這種情況反映出茨威格受到歐洲社會集體想象的制約和霸權主義與二元對立經驗模式的影響,凸顯了作家內心世界里“歐洲情結”與猶太人身份的尖銳矛盾。
關鍵詞:茨威格 《熱帶癲狂癥患者》 東方形象 社會集體想象
斯蒂芬·茨威格是二十世紀奧地利著名猶太裔作家,出生于維也納一個富裕的猶太資產階級家庭。《熱帶癲狂癥患者》的故事發生在遠洋客輪上,白人醫生對“我”講述其在馬來西亞殖民地的經歷:一位富商妻子與一位年輕軍官有染懷孕后求助于自己,而醫生與這位太太在交談中產生矛盾,她選擇在華人區進行墮胎手術卻不幸死去。最后,醫生和她的靈柩一同沉入海底,用自己的生命保守住了這個驚天秘密。
一.東方他者形象
茨威格作品中多次出現了東方他者形象,《熱帶癲狂癥患者》中刻畫了中國、印度與馬來西亞的他者形象,多被描寫成愚昧、落后、卑賤的負面形象。
1.中國地域
歷史悠久的天朝上國以其富饒的物質文明與獨特的東方魅力吸引著西方,如同一曲西方人魂牽夢繞的遙遠歌謠。近代以來,西方資本的肆意擴張使得東方逐漸淪落為殖民地,西方人不再將中國捧于圣壇,而是將其視作低人一等的野蠻國度,茨威格對近代東方形象也充斥著負面評價。
在白人醫生眼中,華人的居住地不堪入目:“小車離開了坐落在海濱的歐洲人聚居地區,進入下城,繼續向前,一直進入中國人居住區的那些人聲嘈雜、彎曲狹窄的街道。”[1]這與坐落于海濱的歐洲人聚居地區截然不同,華人區在醫生看來破舊、落后、骯臟,所見之處盡是污穢,仿佛賊窩一般讓人唯恐避之不及。
除此之外,作家對中國接生婆和黃種仆人的描寫也毫不客氣:“那可惡的中國女人兩手哆哆嗦嗦地端來一盞直冒黑煙的煤油燈……我得壓住滿腔怒火,不然我會跳上去卡住那個黃皮膚無賴的脖子……”[2]中國接生婆在醫生眼里不是迎接新生命的形象,而是長著獠牙的惡毒巫婆,看似是以手術拯救人的生命,實則在以非人的手段折磨著白人女士。
2.東南亞地域
醫生曾于七年前到過印度,熱帶風景帶來的新鮮感很快被消磨殆盡,那里的人們日漸頹廢,只好用酒精來消磨望不到盡頭的日子。馬來西亞使醫生的生活也充斥著空虛與寂寞,只能在煙酒慰藉中懷念在歐洲時的舒適生活,并宣稱自己染上“熱帶病”:“不僅是癲狂……這是一種瘋病,一種狂犬病……直到人家把他像條瘋狗似的一槍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3]這是對馬來西亞的一種鄙夷,將自己生活不適歸咎于馬來西亞的骯臟與落后,以“熱帶癲狂癥”來命名,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他對馬來西亞領地中的黃種人更是鄙夷至極,將黃種男仆攔住自己看作是十分放肆的行為,而自己可以在大庭廣眾下對他拳打腳踢,并用各種負面詞匯:“狗一樣的目光”、“遲鈍的黃皮膚的動物”、“黃種混蛋”羞辱他。
二.社會集體想象
“異國形象應被作為一個廣泛且復雜的總體——想象物的一部分來研究。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集體想象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4]這里的他者不是客觀事實的再現,而帶有凝視者的主觀看法。西方確立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后,牢牢掌握著話語霸權,以排異性目光審視東方。茨威格的歐洲人身份也使他受到社會集體想象制約,對東方同樣持有一定的偏見。在茨威格筆下,西方人以文明、高尚、智慧形象出現,東方人則被用野蠻、低賤、麻木等負面詞匯描述。
1.霸權主義下的東方奴仆形象
《熱帶癲狂癥患者》中的東方奴仆從未被視作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喪失話語權、被任意差遣與羞辱的沉默者。“歐洲的東方觀念本身也存在著霸權,這種觀念不斷重申歐洲比東方優越、比東方先進。”[5]西方對東方的認知中便將這種霸權意識體現得淋漓盡致。
東方奴仆卑躬屈膝、怯懦卑賤,無論是唯唯諾諾的黃種聽差,還是膽戰心驚來送信的中國小男孩,以及被刻畫成巫婆一般的中國接生老太婆,他們都沒有為自身言說的機會。在女主人病危之時,聽差一直盡心盡力協助白人醫生,并且為女主人虔誠祈禱著。即使醫生曾經當街羞辱過自己,他依舊對醫生充滿感激之情。而醫生即便被聽差的忠誠感動,也不過用些輕蔑的話語來“贊賞”,這實際上是歐洲人對東方殖民地人麻木愚鈍的奴性感到不可思議。
小說中的東方是被看的他者,西方作為注視者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心理審視他者時,“異國現實被視為是落后的”。[6]失去話語權的東方被西方以各種含有貶義性色彩的套話形容,這里的東方是歐洲人在霸權主義下對東方的集體想象物,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東方的狹隘認知。
2.二元對立觀念下的東方女性形象
當歐洲資本主義進行殖民擴張而邁向世界前列,東方逐漸落后于世界發展潮流,東西方勢力的日漸懸殊使得歐洲文化形成了“東方/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歐洲將東方置于自己的對立面,東方形象也就淪落為異類或他者。
茨威格將英國太太塑造成美麗、高貴的形象,她與醫生第一次見面時,醫生便為她神魂顛倒。當醫生提出以占有她作為條件時,她十分高傲地拒絕了他,而醫生仍舊追隨她至舞會,所見是“她薄薄的嘴唇四周漾起的討人喜歡的、彬彬有禮的微笑。這笑靨又重新使我心醉神迷。”[7]此外,作家并沒有譴責英國太太的婚外情有違道德標準,反而以豐富的情節將其塑造地合情合理,博得讀者的同情。茨威格對“輕佻下作”的東方女人的描寫與對“高貴體面”英國太太的刻畫形成了諷刺性對比。小說中,醫生對東方女人的描述無不滲透著歧視,用“順從”、“奴性”之類的套話將其丑化,而東方女性的勤勞、溫婉、智慧等正面形象卻沒有在小說中體現。
醫生不但震驚于身份如此卑賤的中國接生婆竟然敢觸碰貴族太太的身體,并且憤怒于她寧愿讓這么一個“魔鬼似的老巫婆”對自己身體任意宰割卻不愿意依賴自己。在醫療不發達的年代,中國確實有接生婆代替專業的醫療人員來為孕婦進行手術。茨威格在富裕的歐洲環境中長大,自然無法理解這種行醫方式。這同時也是歐洲對注重傳統的東方的輕視,歐洲將自己視為“權威”與“科學”,而東方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視作“歪理”與“邪術”。
茨威格在《熱帶癲狂患者》中對東方他者形象的描述始終離不開歐洲集體想象。他懷揣著身為歐洲人的優越感,以先入之見將東方他者描繪成愚鈍、卑微的形象。
三.作家創作動機
茨威格生于奧地利維也納,關于歐洲的情結深深植根于他的內心之中,在東方之旅中以偏概全地認為整個東方都充斥著原始與蒙昧。但是,兩次世界大戰迫使他流離失所,作家內心理想的歐洲大廈轟然坍塌,昔日美好的歐洲一去不復返,而猶太人的血統讓處于身份困境中的作家民族意識覺醒,與猶太人的“流亡”苦難史產生遙遠的共鳴,對殖民地人遭受奴役的生活更加感同身受。歐洲理想身份與猶太民族精神在其身上共存,這也使得茨威格創作中的東方形象更加復雜化。
1.幻想破滅的東方之旅
茨威格的創作動機直接體現在他的東方旅程。茨威格在自傳里提到,他曾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地區。作為旅行者,當踏上去往印度的游船,他沒有被這座古老神秘的東方土地所折服,而是感慨:“印度給我的印象比我想象中的險惡的多。骨瘦如柴的身影,黑眼球流露出的沒有絲毫歡愉的目光,及其單調的景色使我感到震驚。更使我吃驚的是其嚴格的種族和等級制度。”[8]作家在游船上邂逅了兩位迷人的歐亞混血姑娘,她們沒有被眾星捧月般優待,反而被其他人刻意回避。因為這是一艘開往印度的船,種族偏見滲透進船上每一個人的毛孔之中,他甚至將其與可怕的瘟疫相提并論。作家頭腦里“涂著一層粉紅色彩”的瑰麗土地不見了,取之而代的是一座“充滿警戒氣味”的冷漠之城。經歷這趟東方之旅,茨威格目睹到野蠻、貧困的叢莽之地,便以偏概全地認為整個東方都充斥著原始與蒙昧,斷定現代文明從未踏足于這片土地。
小說中醫生對東方的看法也就是作家頭腦中的映射。初來東方,熱帶的異域風情深深吸引著他,想要將自己的全部熱情揮灑于這片古老的土地。但很快他的熱情便被消磨殆盡,逐漸在對歐洲的懷念中空虛度日。同時,醫生還將殖民侵略美化成文明的傳播。實際上,殖民擴張不可避免地讓現代人成為物質的附庸,逐漸被社會邊緣化,在精神上淪落為漂泊無依的流浪者。茨威格借醫生的情感轉變來訴諸自己對東方美好幻想破滅后的失望,以及對歐洲執著于殖民擴張卻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痛惜。
西方的二元對立經驗模式使西方將自己置于中心,而將東方置于邊緣地帶。“旅行者帶著這種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上路,尋找并發現異域與本土的差異,并將這種差異極端化為對極或對跎想象,世界與他鄉呈現在自我面前的樣子,正如他虛妄的世界觀念秩序中期望的那樣。”[9]作家在旅行中發現了歐洲與東方的差異,茨威格對東方即便有美好的想象,也始終難以掙脫西方二元對立經驗模式的藩籬。
2.“歐洲情結”與猶太人身份
茨威格出生于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這是一座具有兩千年悠久歷史的藝術名城。在繁榮昌盛的氛圍中,維也納人每日醉心于文化生活的消遣,他們以極大的熱情和近乎苛刻的標準追尋著藝術,將藝術等同于維也納的集體榮譽。維也納璀璨奪目的藝術成就、“兼容并蓄”的藝術精神滲透在社會各階層觀念之中,也哺育了茨威格的童年與青年時光。維也納既是茨威格的成長搖籃,也是他朝思暮想的精神樂園。
茨威格的自傳《昨日的世界》副標題為“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不難看出他想以理想的歐洲人身份去回憶他的一生。維也納獨特的氣質也使得歐洲意識很早就烙印在茨威格腦海中,他想從維也納走向歐洲、邁向世界。文化之間的碰撞不僅堅定了茨威格以文字捍衛自己作家身份的目標,更培養了他作為世界公民的歷史責任感,致力于追求全人類的精神自由。“即使歐洲,我心中選擇的故鄉,在同室操戈的戰爭中第二次自相殘殺地將自己撕成碎片后,也從我心中消失了。”[10]茨威格內心理想的歐洲大廈轟然坍塌,戰爭使茨威格猶太民族意識覺醒,更加冷靜地審視自己的世界主義理想價值。
猶太民族是一個優秀且苦難的民族,猶太人的“流亡”既是地理上的顛沛流離,更是心理上的居無定所。即便猶太教的選民觀賦予了他們上帝選民的特殊身份,讓流浪的猶太民族獲得了一定的精神支柱,但在殘酷的現實中,許多猶太人一生都在尋找精神家園卻受盡排擠,臨死前都無法采摘故土之花告慰自己的靈魂。漂泊使每一位猶太人都懷有憂患意識,并且格外重視自己的身份,猶太人想要通過對文化藝術的追求提升自己的精神層次,他們努力去認同歐洲文化,在與歐洲文化的融合中淡忘自身氣質,試圖獲得歐洲的身份認同。猶太民族的苦難使茨威格對殖民地人懷有惻隱之心,同情他們遭受奴役的悲慘生活。
面對東方殖民地時,茨威格的內心也十分復雜。一方面,歐洲人的理想身份使他認同歐洲的主流文化,對東方投向輕蔑的一瞥。而兩次世界大戰使他心中理想的歐洲大廈轟然倒塌,身為作家的歷史責任感促使他以文字宣泄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猶太民族顛沛流離的苦難史與無法解決的身份危機使茨威格對自己身份的認識產生了動搖,面對遭受奴役的殖民地人他心生憐憫卻無可奈何。即便以最理想的方式追尋精神的慰藉,他仍然會因為找不到兩全其美的方式而迷茫。歸屬感的缺失形成了茨威格矛盾的思維方式,他既存在于自我認定的身份中,又處于始終被拋棄的境遇中。歐洲理想身份與猶太苦難血脈在他體內共生,對歐洲主流文化的認同與對殖民地人的共情在他筆下并存。因此,《熱帶癲狂癥患者》中對東方形象的負面描述也是作家掩飾自己復雜情緒的一種無奈方式。
茨威格在《熱帶癲狂癥患者》中塑造了帶有負面性色彩的東方形象,其筆下的中國不再是富饒美麗的天朝上國,而是骯臟蒙昧的國度。位于熱帶的東南亞也不再披上異域風情的面紗,而是由內而外都滲透著作家對殖民地的鄙夷,這顯然離不開歐洲社會集體想象的制約、霸權主義與二元對立經驗模式的影響。此外,茨威格對東方形象的偏見也與自身旅行經歷、復雜的“歐洲情結”和猶太民族意識有關。茨威格的東方之旅使他想象中的瑰麗土地破滅了,身為維也納人,茨威格想從維也納走向歐洲、邁向世界,渴望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追尋全人類的精神自由。作家痛惜于歐洲財富大肆擴張導致的現代人精神文明的衰落,而猶太民族的苦難歷史又使得茨威格在面對東方殖民地時心生憐憫。他渴望獲得歐洲身份的認同,在歷史厚重的歐洲精神文明中扎根。但是,戰爭導致的猶太民族意識覺醒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自我認同的懷疑使他的心靈失去庇護。作為知識分子,他筆下的偏見語言既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白描,也是對自己復雜情緒的無奈掩飾。
注 釋
[1][2][3][7][奧]斯蒂芬·茨威格.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選[M].張玉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194,195,196, 188.
[4][6]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21,175.
[5][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10.
[8][10][奧]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M].汀蘭,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179,2.
[9]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707.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