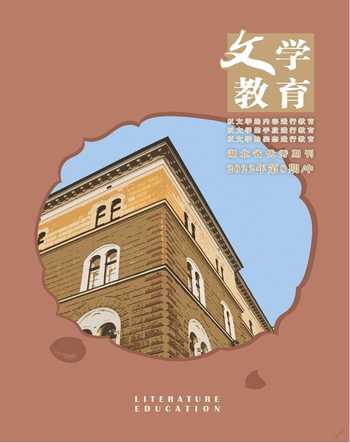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霧津紀(jì)行》中的距離控制失衡與朦朧性
潘春澎
內(nèi)容摘要:距離控制作為小說中重要的宏觀修辭技巧之一,在作者表達(dá)主題思想,讀者理解接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朦朧性則作為曲折含蓄的表現(xiàn)形式,充分體現(xiàn)了文學(xué)含蓄蘊(yùn)藉、韻味無窮的特點(diǎn),具有豐富的審美價(jià)值。筆者通過結(jié)合《霧津紀(jì)行》的話語文本與篇章結(jié)構(gòu),分析小說中出現(xiàn)的內(nèi)在距離過大的失衡現(xiàn)象,以及因迷霧的象征性、霧津—首爾對立空間的模糊性、以及小說思想主題表達(dá)的多重性等因素而產(chǎn)生的小說朦朧性特征,同時(shí)注重文本所映射的現(xiàn)實(shí)要因。本文通過考察距離控制和朦朧性在具體文學(xué)作品中的審美構(gòu)建及思想映射,為研究《霧津紀(jì)行》及韓國作家金承鈺的思想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
關(guān)鍵詞:《霧津紀(jì)行》 距離控制失衡 朦朧性 時(shí)代要因
《霧津紀(jì)行》是韓國作家金承鈺于1964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其憑借著感性的語言與深刻的幻想成為韓國60年代文學(xué)的重要作品。目前,韓國學(xué)界成果層出不窮,但國內(nèi)現(xiàn)有研究資料數(shù)量較少,其主要集中在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作者思想意識研究等方面,本文將從小說宏觀修辭背景下,從距離控制和朦朧性兩個角度切入,具體分析《霧津紀(jì)行》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運(yùn)用的手段、策略與技巧。
一.距離控制
小說中的距離,籠統(tǒng)地講,它是指小說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之間,在時(shí)空、情感、道德、認(rèn)識等方面的間隔、差異、認(rèn)同或拒斥。一部小說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如何通過設(shè)置距離關(guān)系,從而影響并引導(dǎo)讀者對小說人物及主題表達(dá)的反應(yīng)。一般來說,每部小說中都會存在兩個距離體系:一個是與小說形象體系的外在距離相對應(yīng),另一個是與小說意義世界的內(nèi)在距離相對應(yīng)。外在距離要求作者通過直接而客觀的刻畫,使得作品中的場面和人物與讀者直面而對,使得讀者獲得最貼切的感受和體驗(yàn);而內(nèi)在距離則要求作者適時(shí)適度地介入其中,通過各種形式對小說人物、情節(jié)進(jìn)行評價(jià),使得作品想要表達(dá)的思想情感能夠被讀者所認(rèn)知到。兩種距離是相互矛盾統(tǒng)一的,任意一方過于強(qiáng)勢,必然會導(dǎo)致另一方的失衡。而在小說距離的控制上,主要涉及場景描繪和概述敘述兩種手法。前者是典型的展示表現(xiàn)手法,具有客觀性;后者是典型的講述表現(xiàn)手法,具有主觀抽象性。在一部小說中,作者應(yīng)當(dāng)從整體上與讀者保持一種和諧的距離關(guān)系,即從情感距離的角度上看是可接受的,從認(rèn)識距離的角度則是可理解的。
在《霧津紀(jì)行》中,作者通過少而精煉的概括描述對霧津的整體形象與主人公霧津之行的原因進(jìn)行了詳細(xì)交代。其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霧津不是沒有特產(chǎn),我知道那是什么,霧津的特產(chǎn)便是霧”、“然而那為數(shù)不多的霧津之行,卻總發(fā)生在我想要逃離失敗的首爾生活,或者想要重新開始的時(shí)候”等描寫話語中。正如塞米利安所說,“概述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讀者可以通過概述的導(dǎo)引,從個別形象到場景,以至普遍意義,對作品將有一個普遍的理解”。作者通過主人公,對霧津的特點(diǎn)及霧津之行的原因進(jìn)行簡潔凝練的敘說概括,為讀者理解霧津這一迷惘形象及其對主人公的影響等方面提供了理性認(rèn)識的線索和價(jià)值判斷的依據(jù)——即我們由此明確了霧津所代表的頹敗性意味,明確了主人公逃離首爾是因?yàn)樯钍《胍匦麻_始,明確了小說對當(dāng)時(shí)人們迷茫徘徊,不明生命意義進(jìn)行批露的主題。
但除上述明顯的幾處概括敘述之外,作者在小說中運(yùn)用大量筆墨于主人公的自身獨(dú)白,與他人的對話(尤其是與“樸”、“趙”、“河”三人之間的對話),以及主人公所進(jìn)行的空間移動等場景中。
其中,以主人公所進(jìn)行的空間移動為例,《霧津紀(jì)行》作為旅行紀(jì)文,作者采用主人公所處霧津的四個不同場景作為文中小標(biāo)題,層層遞進(jìn),環(huán)環(huán)相扣,背后暗含著主人公不斷變化的心理狀態(tài),同時(shí)小說開頭放棄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背景鋪墊,直接開門見山般地引出第一個空間——“巴士”里的情節(jié)敘述,作者通過設(shè)置農(nóng)夫之間的對話,將讀者迅速拉入“霧津”主題之中,節(jié)省讀者融入故事情節(jié)的時(shí)間。并且在第三小節(jié)中,也就是主人公邂逅“河老師”之時(shí),作者詳細(xì)刻畫了其發(fā)生的內(nèi)心波動——有感受到蛙聲變成繁星的復(fù)雜與混亂,有回家后深夜被笛聲消納干凈的思考與沖動,在讀者遨游主人公的內(nèi)心世界之后,對于主人公矛盾的內(nèi)心便有了更為強(qiáng)烈而真實(shí)的觀感。縱然“靠妻子過得風(fēng)生水起,內(nèi)心卻痛苦掙扎,自卑羞愧”的這一主人公形象鮮活在我們面前,我們也不過是洞察了他內(nèi)心的復(fù)雜與混亂,不過是感受到他對于現(xiàn)有生活狀態(tài)的強(qiáng)烈不滿,但是越過這一人物形象本身,我們無法明確主人公亦或是作者究竟為了什么而“掙扎”。因?yàn)樽髡咴谛≌f中沒有以概括敘述的形式加以總結(jié)或引導(dǎo),使得我們難以從主人公的直接經(jīng)歷迅速剝離出來,難以從主人公及其所處場景的直接刺激而引起的沉悶、疲累和混亂感中得到緩和。
杜夫海納認(rèn)為,“不管表現(xiàn)手法多么精巧,它總是為一種意義服務(wù)的”。評價(jià)技巧表達(dá)效果的根本依據(jù),便是看它是否表達(dá)清楚作者的意圖與作品的意義。客觀上講,雖然作者在小說中有涉及到概括敘述,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文中大多筆墨是為主人公的內(nèi)心活動及其進(jìn)行的場景對白服務(wù),雖然這成功刻畫了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給予了讀者當(dāng)時(shí)韓國整體層面上的有關(guān)民眾與社會的真實(shí)寫照,但作者過多地將焦點(diǎn)放在了主人公混亂無序的內(nèi)心中,一定程度加大了我們理解作品的內(nèi)在距離,使得作者所蘊(yùn)含的思想呼聲難以短時(shí)間內(nèi)被讀者認(rèn)知。
二.朦朧性
“朦朧”又可釋為“含混”或“模糊”等意,本指模棱兩可,容易引起歧義的表達(dá),但隨著英國作家威廉·燕卜遜在《朦朧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中對其重新詮釋之后,“朦朧”漸漸受到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燕卜遜指出:“當(dāng)我們感到作者所指的東西并不清楚明了,同時(shí)即使對原文沒有誤解也可能產(chǎn)生多種解釋的時(shí)候,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品該處便可稱為朦朧。”由此可見,朦朧不是讀者對作者及其原文本意的歪曲或捏造,而是基于原文的更多的合理化解釋。以下,將從三個方面具體考察《霧津紀(jì)行》中體現(xiàn)出來的朦朧美感。
首先,作者在小說中巧妙地使用了象征性修辭,通過設(shè)定“迷霧”這一意象,給作品整體披上了一層模糊而神秘的面紗。從自然形成上來講,霧是空氣中所含水蒸氣凝結(jié)成的小水點(diǎn),飄浮在地面上,反射光線從而呈現(xiàn)的白茫茫的自然現(xiàn)象。聯(lián)想到該意象所具備的客觀特征,便不難誘發(fā)一種朦朧的審美感覺。并且結(jié)合小說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通過“霧仿佛是今生有恨、夜夜出沒的女鬼突出的氣息”、“雖無法用手抓住,卻又分明存在。將人們包圍,又將其與遠(yuǎn)方之物分開。”等話語描寫,用霧若即若離,忽隱忽現(xiàn)的象征特點(diǎn)來暗示主人公未來目標(biāo)規(guī)劃不清晰明朗,內(nèi)心尚處于混沌與彷徨之中的現(xiàn)狀。如此一來,作者便使得霧的朦朧形象與主人公的迷茫心境相互契合,進(jìn)一步烘托出整篇小說的迷失基調(diào)。在這種撲朔迷離的意象刺激之中,讀者已有或想象出來的經(jīng)驗(yàn)和感知被進(jìn)一步喚醒,去探尋主人公背后的故事。
其次,作者在文中設(shè)定了霧津這一幻想性世界,使其作為首爾的對立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并賦予明確的中心內(nèi)涵。不同于首爾——作為主人公失望頹敗的現(xiàn)實(shí)處地,霧津作為主人公本應(yīng)放空身心,進(jìn)行自我拯救的精神樂園,象征著一個自由世界。但霧津與首爾的對立性是難以明確界定出來的,霧津作為拯救主人公墮落心靈的治愈空間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相當(dāng)有限的。正如黎千駒所說,“我們認(rèn)識模糊概念,一般從概念的外延入手,因?yàn)槟:跃褪侨藗冋J(rèn)識中關(guān)于事物類屬邊界或性質(zhì)狀態(tài)方面的不明晰性,也就是中介過渡性。”在文章頭尾兩處,作者設(shè)定“前往霧津的大巴”與“您正駛離霧津,一路順風(fēng)”的呼應(yīng)結(jié)構(gòu),觸發(fā)了首爾與霧津之間的空間對立,但始終未涉及兩地之間的具體距離、霧津的詳細(xì)位置等信息,可以說霧津相對于首爾來說,是一個模糊化、虛擬化的位置概念。同時(shí)作者通過增設(shè)崇拜主人公的“樸”、阿諛奉承的“趙”、及迷戀首爾生活的“河”三位勢利人物,進(jìn)一步暗示了霧津這一幻想世界的欺騙性,從而也為霧津難以作為首爾的對立結(jié)構(gòu)存在增加了合理性依據(jù)。在霧津中,主人公并沒有完全得到精神上的放松與凈化,如同“忘我地唧唧喳喳,仿佛不知道一會走出那旋渦后,將會感受到怎樣的空虛”一般,霧津中的人們也是毫無意外地落入俗套與空虛,這里爾虞我詐、物欲橫流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與主人公的理想期待是不相符的,首爾的陰暗面在霧津依舊清晰可見,最終霧津也只能成為主人公短暫的精神駐地,最后主人公不得不再次回歸現(xiàn)實(shí)。從以上幾點(diǎn)可以看出,雖然霧津存在與首爾形式之上的對立,但從邊界性質(zhì)上來看,兩者是有著極大相似性與過渡性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將霧津看成是首爾的外延。即作者在刻畫霧津這一空間時(shí),難以避免地呈現(xiàn)出了與首爾的相似性,也就使得小說整體層面上產(chǎn)生了環(huán)境空間上的模糊性與朦朧感。
再次,不僅由于迷霧的象征性、霧津與首爾空間對立上的模糊性,而且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小說中過大的內(nèi)在距離——蘊(yùn)含于主人公復(fù)雜內(nèi)心背后的思想主題表達(dá)——也為小說籠上了一層厚厚的朦朧感。從主人公以半睡眠狀態(tài)乘車來到霧津,到在霧津期間頭腦里時(shí)常充斥著一些天馬行空的臆想,再到因“樸”、“趙”、“河”三人而產(chǎn)生的情感變化波折,以及最后對現(xiàn)實(shí)屈從的整個過程中,主人公的精神斗爭我們是難以清晰認(rèn)知到的,只能依靠作者在小說中的客觀概述和特定的環(huán)境對比來感知。例如,我們可以理解為作者筆下的主人公對于自己的現(xiàn)狀和未來沒有明確清晰而具有主動性的反省思考,在霧津所經(jīng)歷的一切是被環(huán)境及人物所影響,所牽引向前的結(jié)果,因?yàn)樗麧撘庾R上深知自己無法放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只寄希望于霧津這一客觀存在能夠打破藩籬拯救自己;亦或是我們也可以將主人公的妥協(xié)看做是殘酷現(xiàn)實(shí)所產(chǎn)生的巨大吸力,把主人公牢牢困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結(jié)果,縱使他主觀意識上想要逃離首爾這個“圍城”,卻在客觀上難以實(shí)現(xiàn)。并且就算逃離首爾,來到霧津,這對于主人公來說只不過是權(quán)宜之計(jì),他內(nèi)心深處本質(zhì)的想法和追求又是什么呢?除此之外,還有那主人公遇到的,與自己極其相似的“河”老師。作者運(yùn)筆下的主人公究竟是將“河”老師視作一個僅僅起到慰藉內(nèi)心作用的過客呢?還是將她視作命運(yùn)般出現(xiàn),點(diǎn)醒自己的救命稻草與愛人呢?我們難以定論,因?yàn)橹魅斯膬?nèi)心世界是一定程度上作者內(nèi)心世界的反映與體現(xiàn),而小說過大的內(nèi)在距離面前,任何自我性解讀都會顯有很強(qiáng)的主觀性與不確定性,并會隨著我們對作者內(nèi)心世界于不同時(shí)期,不同程度的理解不同而有所不同。而這種感覺便如同縈繞在我們心頭的那一團(tuán)迷霧,揮之不去,使得我們愈發(fā)感覺到小說中的部分內(nèi)容有著因人而異的模糊性審美價(jià)值。
我們可以將以上這一點(diǎn)視作燕卜遜所提到的第四種朦朧——“一個陳述的兩層或更多意義相互不一致,但結(jié)合起來便會形成作者的更為復(fù)雜的思想狀態(tài)。”朦朧性是具有自身的反傳統(tǒng)性和創(chuàng)新性的,能夠體現(xiàn)出小說這一文學(xué)作品在表達(dá)思想感情,反映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可塑性與包容性。同時(shí)它也能刺激我們的想象力,誘導(dǎo)我們從自身的理解出發(fā)去品味,推測作者的思想和意圖,從而感受到一種豐富的審美情趣。正如譚善明所提到:“文學(xué)的審美性要求文學(xué)作品用一種曲折含蓄的形式來展現(xiàn)生活的真實(shí),一切使語言變得含混、富有張力的形式都可以運(yùn)用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含混的文學(xué)語言更能夠讓讀者體驗(yàn)到美的事物、美的情態(tài),因?yàn)樯钪械拿辣揪褪菗渌访噪x的。”雖然對于主人公朦朧模糊的內(nèi)心世界與認(rèn)知心智,我們可能會產(chǎn)生不同程度上的讀解,但是作為作者筆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產(chǎn)物,也難以否定說這種模糊性不是作者的有意所為,并且在一定程度下,作者所體現(xiàn)出來的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也不失為對當(dāng)時(shí)韓國文壇與社會的一個真實(shí)寫照。
20世紀(jì)60年代可以說是韓國社會極度混亂與動蕩的時(shí)期,在經(jīng)歷政治巨變,經(jīng)濟(jì)貧窮與迅猛發(fā)展,社會階級與貧富差距變大之后,人們儼然置身于客觀環(huán)境劇變的混亂與生活困難之中,一時(shí)間難以找到穩(wěn)定的物質(zhì)歸宿與精神歸宿,他們彷徨不安,輾轉(zhuǎn)反側(cè),從而轉(zhuǎn)向?qū)ふ易陨韮?nèi)心的價(jià)值認(rèn)同,人與人之間的疏遠(yuǎn)程度進(jìn)一步加深,缺少現(xiàn)實(shí)中的溝通交流,陷入了深深的虛無與頹敗之中,這便是作者在小說中專注運(yùn)用大量筆墨于場景描繪和主人公內(nèi)心刻畫的重要現(xiàn)實(shí)因素之一。作者復(fù)刻私欲橫流的內(nèi)心世界,可以說深受20世紀(jì)60年代韓國社會下的價(jià)值觀與世界觀的影響。但雖然小說來源于現(xiàn)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的寫照,可小說同時(shí)也具有改造社會現(xiàn)實(shí)的重要功能,我們不可否認(rèn)的一點(diǎn)是作家可以充分發(fā)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去創(chuàng)作一些超越時(shí)代,不局限于當(dāng)下時(shí)代特點(diǎn)的作品,比起在當(dāng)下時(shí)代中受傷,在美好的世界中暢游,不也失為一種自我發(fā)掘,自我治愈的好辦法。
參考文獻(xiàn)
[1]金承鈺.金承鈺全集(第一卷)[M].文學(xué)村(? ? ),1995.
[2]黎千駒.模糊修辭學(xué)導(dǎo)論[M].光明日報(bào)出版社,2006.
[3]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M].二十一世紀(jì)出版社集團(tuán),2018.
[4]利昂·塞米利安.現(xiàn)代小說美學(xué)[M].宋協(xié)歷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
[5]呂玉銘.小說創(chuàng)作修辭論[M].吉林出版集團(tuán)股份有限公司,2015.
[6]米蓋爾·杜夫海納.美學(xué)與哲學(xué)[M].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5.
[7]譚善明,楊向榮.20世紀(jì)西方修辭美學(xué)關(guān)鍵詞[M].齊魯書社,2012.
[8]威廉·燕卜遜.朦朧的七種類型[M].周邦憲,王作虹,鄧鵬譯,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6.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