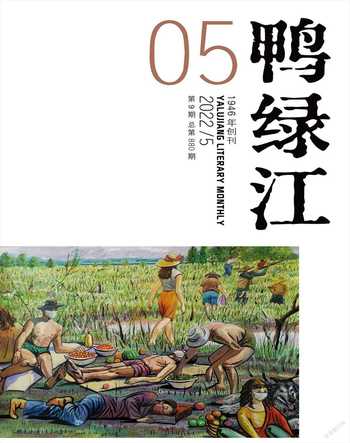一個故事的N種講法(短篇)
年假來了,我作為公司最后走的一名員工,關上了電腦,拉下了所有的電閘,鎖好了公司大門,在公司群拍了照片報備,然后趕往火車站,坐上最后一班回老家的火車。
坐在彌漫著煙酒氣味和腐爛味道的綠皮火車里,我靠著窗戶,數著向后奔跑的樹,它們跑得并不快,從農村奔向城市,和我的方向正相反。經過了七八個小時,我抵達了離家鄉最近的火車站,北方的太陽早就貓到了夜里,我搭乘朋友的老捷達奔向老家。
“半年不見了吧,福子。”何浩說,車里充斥著老捷達的異響。“福子”是我的小名,這個名字只屬于我出生的村子,我一聽到這個名字就感覺我也屬于這里。雖然我好久才回來一次。
“噢,上次是‘十一’回來的。”我應著說道,看著沒有路燈長滿雜草的小路,我有點慌張,明明熟悉每一棵樹,卻陌生得像個旅客。
“今晚你先回家吧,明天咱們再一起出去玩,明天好好喝點兒,哥兒幾個都挺想你的。”何浩幫我搬著車上的行李,在凜冽的北風中順手關上了后備箱,他幫我拎著兩個口袋,向家門走去。
“送到這兒吧,明天早點兒來找我,今晚上我先回家陪陪我爸媽。”我告別了他,并期待著明天和他再次相聚,期待著明天中午和少年時期的幾個發小把酒言歡,回憶那些又傻又可笑的往事,然后就著啤酒咕咚咕咚地灌下肚去,再一起打出一個嗝,看著彼此傻樂。
“妥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上午來找你。”說罷何浩關上車門,猛地踩一腳油門,腳力大到快要將他的捷達踩漏,一股濃煙竄出,他和他的野性座駕便消失在夜里。
與家人在年前團聚,是家庭的重要時刻,和母親聊聊她這一年在鄉村學校工作的日常,和父親喝點他珍藏的泡了亂七八糟的我不認識的東西的白酒。炕燒得很熱,我坐在炕頭有點燙屁股。午夜將至,我們熄了燈,開始做夢。
天亮是三十兒。
冬天的北方天亮得很晚,我看看墻上掛著的陳年老鐘,現在才剛過八點,急促的敲門聲就響起來了。我父母早早出門去后街大姨家了,那么這個時候能來的就只有何浩了,但他來得也太早了些。
“耗子,你來得也太早了。”我睡眼惺忪,看著他在我家的門外焦急地扒著門往里看。我不緊不慢地打開門閂,這家伙卻真的像個耗子似的一下子溜進來。他眼里有慌張、不安、局促,看了我一眼,又看向地上,又看向屋里,又看向我。
“沒人,我爸媽去我大姨家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渾身發抖,像是出了很多汗,絕不可能是熱的,因為這天氣都能把人凍死,他出的是冷汗,他開始哆嗦了。
“我殺人了。”
我蒙了,他這句話我從沒想過會在現實生活中聽到,這句熟悉的話會出現在電視劇里、小說里、新聞里,但是不會出現在我身邊的現實世界里,更不會出現在何浩的嘴里。但他真真切切地說出了這句話,對著我。
“你開什么玩笑?大過年的,說點正經的!”我心里已經有些不好的預感,因為有些東西是裝不出來的,他現在的狀態如同我在城市中的那些演員朋友,我去看過他們演的戲,很真實但并不是生活,現在在我面前的何浩如果是演的,那么他配得上世界上任何表演獎項。
“等我鎖一下門,你先進屋暖和暖和。”我也一下子緊張起來,不知道該怎么辦,但是這一瞬間我想到的是讓他先冷靜下來,把話說清楚。
“我沒開院子門,我是從后邊跳進來的。”他說話還是有些哆嗦,我把他扶進了屋里,然后摸著炕沿靠著墻邊坐在炕頭,他靠自己已經根本站不住了。
我走到掛在墻上的棉襖邊上,翻了翻我的棉襖口袋,摸索出一盒芙蓉王,抽出兩根,我先把一根煙叼在嘴里,再把另一根煙塞進他顫抖的嘴唇里。他差一點兒就把煙抖掉了。我拿出打火機給他點上,再給自己點上。我們倆坐在炕邊,吞吐起來。
煙霧繚繞下,何浩緩和了一些。他來找我,我并不意外,從記事起我倆就是最好的朋友,我倆一起偷過他媽媽錢包里的錢,一起摘過別人家的果子,一起逃過課,一起打過架。我上大學的時候,他因為沒能考上,去附近的鎮子上賣水泥,這幾年也賺了點小錢。他說二十八歲之前一定要在鎮里買上二層小樓,今年他二十七了。
“別著急,實在不行下午去自首,也判不了幾年。”煙已經剩下一個屁股,我說出了這句話。
“操。”他這個字雖然簡短,但是配合著眼里的淚水和哭腔,讓我不能直視他的表情,就好像他心里的整片海洋裝在杯子里,這個杯子被這一聲震開了一個小口,然后整片海洋從小口泚出來。
“說說吧,和我,萬一沒啥事兒呢?”我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碾了一下,讓它在白色的瓷磚地面上劃出一道黑線,像是把一塊瓷磚劈成兩半。
“萬玲玲,我那個嫂子。”何浩顫抖的手拿著煙屁股,靠手的抖動就能將煙灰抖到地上。
“啥?你把玲姐給……”我有點驚訝,但還期待著他下邊的陳述。
“不是,我從頭給你講。”我又給他點了根煙,他深吸一口,表面看起來冷靜了下來,講起今天早上發生的事。
今天早上,天還沒亮,何浩去他家的大棚幫著摘菜。大棚,是東北農村種植蔬菜的地方,它一面是保溫的土墻,一面是采光的塑料。無論冬夏,這里都是植物生長的天堂。在他家前邊的大棚是他哥家的。他哥何勇今年三十出頭,沒念過什么書,在家靠著大棚種菜生活。何浩剛走到自家大棚門口,就聽到前邊的棚子里傳來女人的叫聲。那聲音何浩熟悉,那是鎮里的洗腳城二樓包房里才會傳出來的聲音。那是他嫂子萬玲玲的聲音。他湊近了一些,大早上就開始整這個,我哥可真牛啊,他想著。但一句話讓他瞬間渾身發冷。“李冬,你別這樣。”這句話清晰透明,穿透了薄薄的塑料大棚,穿透了冷冰冰的空氣,穿透了何浩的身體。
何浩也沒想太多,順手抓過一塊磚頭,爬上大棚的墻頭,破開薄薄的塑料膜跳將下來,仿佛神話之中的天神下凡,手持一塊赤紅寶磚,身著靛青夾襖,出現在兩人面前。
對面的倆人都還穿著衣服,但是沒穿褲子,萬玲玲的手正扶著土墻,李冬的腰正頂在萬玲玲的屁股上。倆人愣了,不對,是三個人都愣了。
何浩憤怒地罵了一句后就將手中的奪命法寶發射出去,直奔李冬的面門。僵直在原地的李冬根本來不及躲閃,紅磚綻放出紅光,紅點噴射到各個方向。
李冬不再愣在原地,他直挺挺地倒下,向后。萬玲玲直接哭了出來,一個女人,面對這種電光石火的變化,用哭來應對也情有可原。何浩呢?何浩慌了,他沒想到眼前這種情況該怎么處理,他也沒想到自己會遇到這種情況。他選擇跑,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跑到一個讓他信任的地方,跑到我這里來。
太陽漸漸出來了,但是轉身又躲進烏云里,聽說過年這兩天有大雪,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開始下,這里的天氣預報永遠不準,所有人都只能隨機應變。
說起來,李冬也是我們的同學。我想了半天,在腦海里刻畫他的容貌。上次見他應該還是初中的時候,那時候他是個混混頭子,帶領著學校里的一幫混小子干些混蛋的事情。他家承包著村上唯一一個魚池,在經濟上有點實力。他長得挺高的,還有點瘦,看起來挺狠的,實際上狠不狠我不知道,沒什么交集。
窗外的雪花開始飄落下來,很大,像是從天上往下掉瓷碗。
“我出去看看。”我站起身,準備出去。
“你嘎哈去?”何浩依舊很緊張,我一動就破壞了原本安靜和諧的環境。
“我去看看外邊什么情況了。”我安慰著他。
“行,你去看看李冬死沒死。”何浩開始說出一些理智的話語,讓我感覺這個人已經恢復正常的狀態了。
“他要是沒死,你就給我打電話,我們給他送到醫院去,然后我去自首,或者怎么都行。”我看他已經有主意了,也就沒多說話,只是問了一句,“要是他死了呢?”
“也先告訴我一聲,然后報警,來抓我。”他淡淡地說道,好像已經看開了,看懂了一些事情。
“你就在這兒待著?”我問。
“對。”他說。
“要不要換個地方?”我又問。
“不,這炕上挺熱,我暖和暖和,我不走。”
“把煙給我扔下。”他說。
我便也不再問下去,給他拿了幾根煙,轉身出去,推開門走入一片雪中。
這世界的變化來得太快,本來還約好了今天一起喝酒的人現在正因為自己可能殺了人而坐在我家的炕頭,我感到有些緊張,我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殺了李冬那么我算不算電視劇里的包庇罪犯,窩藏逃犯,直接給我扣上一個從犯的帽子。但他也說了,如果李冬死了,讓我報警抓他,那這樣來說我于法于德也都過得去,我心里一下就好受了起來,繼續向雪的更白處走去。
小小的村莊本就不大,家家戶戶都離得很近,所有的大棚都在居住區的東北面。我走了大概五六百米,就看到了一片片整齊的大棚,躺在一片白色里,在白色的更深處有一團黑色,雪越下越大了,甚至看不清什么東西,前幾天剛下的雪還沒化,新的大雪又續上了。更靠近那團黑色,我發現那是一群人,團團圍住的人,大概有二十到三十人,圍成一個圈。在圈里躺著一個人,跪著一個人,站著一個人,我看得清楚,正是李冬,雪蓋在他身上,省了白布,他死了。跪著的是他媽,站著的是他爸,他媽哭得震天動地,他爸哭得聲嘶力竭。周圍的人議論紛紛,都是熟悉的面孔,都是附近的叔叔阿姨、大爺大娘在這兒議論著。我爸媽也在其中,看到我在人群里還拉了我一把。
“福子,你嘎哈來了?”我爸低聲說道。
“我溜達到這兒了。”
“別上這兒溜達了,李冬死了,不知道誰整的,但是被砸死的,臉都砸爛了!別看了,睡不著覺,回家吧,回家!”
“好。”
“有人報警了,我們在這兒等一會兒,一會兒警察來了就都散了。”我爸接著和我說道。
我爸把我推向人群的外圍。但他還在黑色的旋渦中,隨著人群議論著。
最近的派出所到這里也要一個小時,我應該還有些時間來和何浩說些事情。
我拿出了手機,想給他打電話,卻突然感覺這里并不是能給他打電話的地方,于是給他發了一條信息“死了”。然后我點了支煙,在離人群幾十米的地方,聽著由遠及近的警笛聲,伴隨著那根芙蓉王慢慢化成煙灰落下。
我沒想到這個世界的變化來得如此快,人在一瞬間變成尸體,要好的朋友在一瞬間變成罪犯,本來是歡天喜地的年節,在一瞬間變成了漫天飛雪的葬禮。真是無常。
警車在我附近停下,因為再往里就開不進去了。車門打開,從副駕駛下來一個熟悉的身影,我聽說她在鎮里當警察,卻沒想到巧合又一次發生,她一下車就站在我的面前。
“好久不見了,林警官。”我嘗試和她打趣,畢竟她是我的初戀,在學生年代給我留下了無數美好的回憶,在上了不同的大學后我們才分道揚鑣,她去了警校,我去學了計算機。
“一會兒再聊吧,王福,我先辦案。”她冷冰冰的,像是嘴里也下著雪。
后邊的車上也陸陸續續下來幾個警察,畢竟命案是大案,整個派出所的民警估計都出動了,有十來個人,向黑色的人群旋渦走去。我一把拉住了林雪說:“我有線索。”
我本來不應該這么說的,說出這句話有點不妥,不說更不妥。或許是想和她搭話而突然言語不受自己控制,也或許是對自己知道的事情負責任,讓我拉住了她,并說出了這句話,
“我有線索。”我又說了一遍。
“什么線索?”她轉過頭來,看向我,上次她這么看我應該已經是七八年前了,我們分手的那天。
“能上車說嗎?我單獨和你說。”我腦海中還在組織語言,渴望有點時間來緩和一下我腦海中的信息海嘯。
“上車。”她拉開副駕駛的門,一把把我推了上去,手勁可真大。之后她從車頭繞過去,到駕駛位上坐下,把車門關上。
我拿出一根煙,塞到嘴里,準備掏出打火機點燃它。
“這是警車,你注意點兒。”林雪斜了我一眼,我趕緊把煙又拿在手里,放回煙盒里也不是,夾在耳朵上也不是,這根煙和我都有點尷尬。
對講機響起來,“現場發現被害人面部受到多次重擊,兇器也找到了,是一塊磚頭。”
我愣了,這和何浩和我說的并不一致,他說他用磚頭把李冬砸倒了之后跑了,但是現在對講機里說的卻是多次重擊。
“不對。”我說。
“什么玩意兒不對,王福你是不是逗我玩呢?我沒時間跟你在兒玩,我走了。”林雪說完就要開車門下車,又被我拉了回來。
“別走,事兒不對。”我說。
“人是何浩殺的,又不是何浩殺的。”我接著說。何浩讓警察抓他,我覺得直接讓警察把他按了也是對他好,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又有變化了。
我把何浩所說的一字一句都重復給了林雪,我完成了何浩對我的囑托,讓警察來抓他。但是我又違背了他的意愿,我現在想讓警察查明白這件事再去抓他。
“何浩,萬玲玲,先找到這兩個人。”林雪冷靜地說道。對講機里還在傳出嘀嘀的聲音,我思維有點混亂,如果何浩把李冬打倒了沒有殺他,但是李冬卻因為連續受到重擊而死,那一定是萬玲玲殺了他。
是何浩在撒謊,還是什么其他的地方出了問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面前的大雪已經沒過了腳踝,耳畔的哭聲還縈繞著。這個世界真的很混亂。
我撥打了何浩的電話,沒有人接,但是我相信他會在我家等我,等我帶著警察回去抓他。何浩是個好人,也不對,他算不上好人,但并不是壞人。他至少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值得信賴的朋友,我能確定這一點。
“他應該還在我家,幾個人去就行,別嚇著他。”我說完這句話,好像又有些不妥,在林雪面前,我經常做一些不妥的事情,這讓我更不安了。
“一隊,一隊。”林雪拿著對講機說話。
“一隊收到,請講。”
“一隊來三個人到車里,剩下的人保護現場,疏散群眾。”
“收到。”
“二隊,二隊。”林雪接著拿著對講機說話。
“二隊收到,請講。”
“二隊去找一個叫萬玲玲的女性,三十歲上下。”
“收到。”
她拿著對講機說話的樣子和當年與我玩用紙杯加毛線做的土電話說情話的樣子完全不一樣了,這副容貌下裝的好像已經是另外一個靈魂,相同的蠟燭點燃兩次就已經是不同的火焰。
一輛車上,五個人,沒什么話,我只是將何浩和我講的東西又大概重復了一遍,媽的,說了好幾遍了,真煩。
到了我家,推開大門,何浩并不在屋里。我們五個人都不太驚訝,他在這種狀態下做出什么決定、想到什么事情都并不奇怪,但我們要做的就是第一時間控制他,然后查明真相。
何浩去哪兒了?我想不出。
“走,去萬玲玲家。”林雪說道。
“哦。”我應答著,和他們一行人往外走去。
“你還跟著干什么?你提供的線索我們已經了解了,回家待著吧。”林雪看著我說。
“不行,何浩是我兄弟,我得找他。”我有點和林雪較上勁了,以前我們也總是在一起較勁,像現在一樣。
“別耽誤我們辦案,別的隨你。”她扔下這么一句就鉆上了車,關上車門,把我拒之門外。
“還跟以前一樣。”我嘀咕著。
我掏出手機,又給何浩打了個電話,還是沒有人接,也沒有人掛斷,我想到會是這種結果,卻也有些失落。于是我給他發了條消息:“人可能不是你殺的,我聽到說是多次重擊致死。”還是沒有回應,希望他能看到。
手機震動了兩下,我拿起來一看,居然是何浩給我發回了消息:“帶警察來后山,秘密基地。”
內容很短,秘密基地也很近,那是小時候我們幾個小伙伴的秘密地點,說白了,就是一個小山洞,矮矮的山上有一個小小的洞口。如今,我們都快三十歲了,這個秘密基地依然存在。
我跑出去,這么大的雪,警車開得也很慢,我幾步就攆上了警車,跑得一身是汗。
“干嗎?”林雪沒開車門,搖下車窗對我說。
“開門,何浩他上后山了,這地方只有我能找到。”
“好,上來吧。”
我又爬上了警車,帶著一車人向后山進發。
雪太大了,車有點走不動,我和林雪以及三名警員下車,在雪地里步行。剛才沒腳踝的雪現在已經到了小腿深,有點兒見小了,從白瓷碗變成了白鵝毛。我們往山上去,我走在最前邊,林雪和三名警員踩著我的腳印前行,五個人只有一排腳印。
“到了,那兒就是。”我指著半山腰的小小洞口,和身后的幾人說道。洞口里還閃爍著微弱的火光,看來是何浩點了火,我們小時候也經常在這個山洞里生火,燒東西,感覺燒點什么東西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后來我明白,那是無法創造就去毀滅的快樂,是我們年少的天性。
“耗子,我來了。”我遠遠地喊。
“你喊什么?別喊!”林雪用胳膊撞了我一下,生怕我把何浩嚇跑了。
“沒事兒,他讓我帶著警察來的。”我有點無奈。
探進洞去,其實洞很小,這些人根本站不下,更何況洞里本來就有兩個人。
一個是何浩,一個是萬玲玲。倆人圍著一團火焰,也不作聲。
我有點蒙圈,身后的幾個人倒是沒猶豫,上去就把兩個人給按住了。
“放了小浩吧,和他沒關系。”萬玲玲先張嘴了。
“都別扒拉我,我自己能走。”何浩推開了身邊的警察,站了起來。
“行,那都和我回警察局吧。”林雪環視了一周,冷冷地說道。
對講機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一隊二隊,收到請回答。”
“收到。”
“天氣原因,所有路段都封閉了,今天無法離開平安堡子了。”
“收到。”
“那就不著急了,先在這里說說吧,到底怎么回事兒。”林雪聽完對講機里傳來的聲音,也沒什么變化,蹲坐在了火堆旁。
“都別緊張,事情已經發生了,大家都坦白了,對所有人都好。”林雪接著說。
我也蹲在一旁,用火堆里的火焰點煙。
“人是我殺的。”萬玲玲低著的頭又抬起來,對著我們說道,然后她開始講述她的故事。
李冬早就對萬玲玲有意思,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身邊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萬玲玲是何浩大哥何勇的媳婦,何勇為人踏實內斂,身體結實,一米八多的個子,一身干農活兒練出來的腱子肉,也不是好惹的茬子。于是李冬對萬玲玲這個事兒一來二去也沒什么下文,村子里的人也就沒當回事兒。
但何勇最近這兩年不光開始扣大棚,也研究上了蔬菜運輸。開著他買來的二手三輪車,把自家大棚里的菜運到鎮里的集市上去賣,收入上來了,但在家的時間更少了。何勇和萬玲玲結婚快三年了,還沒孩子,倆人的感情也出現了波動。李冬就乘虛而入,在何勇去鎮上賣蔬菜時,進入萬玲玲的生活。
今天早上,何浩發現了倆人的茍且之事,一磚頭將李冬放倒。萬玲玲怕事情敗露,一時起意,痛下殺手,用那塊磚頭朝著李冬的面門狠砸下去,三五下之后,李冬徹底沒了呼吸,整張臉都沒了。她本想著李冬死了之后可以栽贓給何浩,但當她冷靜下來之后還是決定自首,于是她給何浩打了電話,倆人約在了這里。
就是這樣,萬玲玲述說得很平靜,也很真實,但我總感覺有點不自然。何浩在旁邊不知何時也點起了一根煙,到目前為止,他沒發表過什么意見。
倆人戴上了銀色的銬子,有了點兒犯人的樣子。
“你走吧,沒你事兒了。”林雪看了我一眼。
“沒我事兒了?”
“對,你還在這里干嗎?”
“這么大的雪,剛才不是都說了嗎?今天你們出不去了。”
“我們出不出去和你有關系嗎?”
“和我沒關系?”
“對,沒關系。”
“我和你沒關系?我和耗子也沒關系?”
“何浩現在是嫌疑人,我們必須把他帶走,咱倆就更沒關系了。”
“行,我走。”
環視了一圈小小的山洞,大概五平方米的地方人擠人,警察同志把嫌疑人保護在中間,中間圍了一團小小的火焰。
耗子看著我,沒說什么。萬玲玲也看了我一眼,也沒說什么。林雪看了我一眼,像是在和我告別。
太平靜了,讓我感覺有些不對勁,一個女人殺了一個她出軌的男人,現在還能平靜地坐在火堆旁邊烤火?她伸出一雙白皙的雙手,靠近火焰,右手的無名指上金色的戒指反射著火焰的光芒,我突然想起了剛剛聊起何勇被大雪隔離在了村莊之外。太不對勁了。
我走出山洞,往高處爬。這座小山是我和何浩小時候的樂園,我們曾經騎著自行車從小山包沖下去,摔得人仰馬翻。我們也曾經藏匿一些小物件當作寶藏,幻想著自己是尋寶的勇士。如今這里變成了我把他交給警察的最后地點,我覺得有些恍惚。雪還在下,仍舊不小。我漫無目的地走著。
我不能去耽誤警察辦案,也無法和何浩聊天,另外幾個兒時的小伙伴聽說出了這檔子事兒都避之不及,我只能在這里漫無目的地走。這里是唯一一條出村的路,在山的另一面,積雪很少,所以相對要好走一些。在白茫茫的雪里,我看到了另一個身影,有些蹣跚,有些猶豫,好像在回頭看什么。他好像看到了我,步伐加快。
我快速追上去,正常來說這條路不會有人的。這是屬于孩子們玩耍的小路,前面快速在走的人明顯是個成年人。我又加快了速度,前邊的人開始奔跑,我也開始奔跑。雖然是山的背面,但是積雪仍舊很深,每一步都沒到小腿,跑起來很累,兩個人在如此深的雪地上奔跑著,帶起兩道雪浪。我逐漸縮短了和他的距離,在雪中我已經能夠聽到他的喘息聲。更近了,我伸手就能觸碰到他。他回過頭來看我,竟然是何勇!他神色慌張,我更慌張,我之前感覺到的不對在這一刻全部應驗,我奮力跳起,將他壓在雪地上,壓出一個人形。
他當即哭了出來。
我有點不知所措,他的哭聲很大,像個孩子。他也三十多歲了,不再是孩子了。我從他身上起來,撲了撲身上的雪。小時候,我和小伙伴經常玩這種游戲,在雪地里撒歡兒、摔跤、打雪仗。更狠的就是拉開伙伴的衣領,把雪團扔進對方衣領里。最高禮儀則是把人放倒之后,大家圍成一個圈,用雪將他掩埋。
過了十幾分鐘,或是幾十分鐘,他漸漸平息下來。我給他點了根煙,又怕他嗆著了。聲音斷斷續續,他開始對我訴說,對我懺悔,對我祈禱。我像個神父,像個佛陀,像個警察,但我都不是,我不清楚現在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只是一個在雪地里和他抽煙的人,他弟弟的朋友。
于是我聽到了第三個故事。
何勇很愛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很愛他。雖然沒有一兒半女,但是兩個人依舊非常相愛。去年開始,何勇不僅扣大棚種蔬菜,而且開著三輪車去鎮上的市場賣菜,家里的收入翻了一番,倆人開始研究著去市里的大醫院做試管嬰兒。這個時候另一位主人公出場了。李冬其實這么多年一直覬覦萬玲玲的美色,很多年了,雖然差了好幾歲,但是李冬經常說他是真心愛著萬玲玲的,路上遇到了要說幾句葷話,沒事閑聊時也要扯上幾句。他還經常在背地里說何勇不行,何勇忍了,但他又騙了何家的錢。李冬的父親說要把養魚池轉給何勇,三萬塊。這是何勇和萬玲玲想要下一代的錢,不過養魚池收入可觀,何勇和萬玲玲研究了一宿,決定承包養魚池。但是錢出去了,池子沒包回來。老李家耍起了無賴,何勇一氣之下,決定綁架李冬要錢。
他和萬玲玲商量好,由萬玲玲把李冬引到自家大棚里,埋伏的何勇跳出來,將李冬劫持。這是他們本來的計劃。
誰也沒想到,何浩神兵天將,一板磚將李冬掀翻在地。何勇傻了,直到何浩跑遠,才出來和萬玲玲面面相覷。此時李冬卻醒了,指著何勇威脅說:“我要你全家死,我馬上回去告訴我爸。”何勇慌了手腳,拿起那塊磚頭朝著李冬面門砸下去,一下,兩下,三下。他心中的憤恨、不滿、不安、痛苦、煩躁全集中到這一塊磚頭上。他把李冬的臉都砸爛了。
萬玲玲已經哭成了淚人,何勇卻異常冷靜。他讓萬玲玲先聯系何浩,讓他別緊張,然后讓她去自首,就說她是被強奸合理反抗,不會重判。
但何勇說他后悔了,因為何勇說他很愛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很愛他。
所以我聽到了這個故事。
我在想如果何浩沒去找我的話,或許這件事還真就這么過去了。
天已經見黑了,冬天的北方黑得早。何勇和我一起返回了村子,他要去自首。
我給林雪打了個電話。
“你在哪兒呢?”
“審犯人呢。”
“我問你在哪兒呢!”
“我說我審犯人呢!”
“別他媽審了,犯人換了!”
“你跟我說話別總帶臟字行嗎?”
“行,你在哪兒呢?”
“村委會。”
“我帶何勇過來找你,他要自首。”
“嗯,我這邊也了解了。”
看來林雪審問也不是白審的,好像一切都明白了,我卻依舊云里霧里。
雪已經停了,天也徹底黑了。走了十幾分鐘,我們到了村委會。這是一排小平房,屋里點著爐子,還算暖和。村里的幾個干部也在。何勇走進了里邊的小屋,我在大廳里站了一會兒,然后找了個椅子坐下。我應該回家嗎?還是在這里繼續待著?我也不知道。
窗外有禮花炸裂,崩得漫天開花,過年了。
電話響起,是我媽叫我去二大爺家吃餃子,今年一起在二大爺家過年。
“媽,我今年就不去了吧。”
“嗯,也行。”
我今年不沾喜氣,我這么一說,家里人也都懂。
“媽,今晚家里是不是沒人啊,你和我爸都在我二大爺家吧?”
“對,晚上不回去了。”
“好,我知道了。”
“你小心點啊,兒子。”
“啊,我沒事兒,也沒我啥事兒。”
掛斷了電話,我剛叼起一根煙,林雪就從小屋走了出來,把我的煙搶走了,塞到了自己的嘴里。我便又抽出一根煙,拿起打火機點著,林雪也將頭湊了過來,我們倆在一團火下點燃兩根煙,然后坐在村委會的長凳上。
“你怎么還不走?”林雪問我。
“抽完這根煙就走了。”我說。
“根據幾個嫌疑人的證詞,事情有些變化,我想了想,還是要告訴你。”林雪吐出霧氣,她并不熟練,也不生疏,看來她確實經歷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有所改變。
“還能有什么變化?難道李冬是自殺的?自己把自己的臉捶爛了?”我實在想不出事情還有什么變化。
“萬玲玲和李冬確實是有事兒。”林雪低下頭接著說。
“啊?”我一下陷入了恍惚,反應了一會兒,才聽到林雪把整個故事講給我。我已經記不清這是今天聽的第幾個故事了,我真渴望它是最后一個。
萬玲玲和李冬,確實是有事兒。倆人在大棚里正折騰得熱火朝天,何浩路過給了李冬一板磚,把李冬拍暈了,何浩就跑了。萬玲玲也慌了,這個時候她給何勇打了電話。按理說她怎么也不應該給何勇打電話,但是她確確實實第一時間打給了何勇。何勇很快趕回來,還是用那塊磚,把李冬殺了。后來的事,和何勇說的差不多,但其實那些事兒他早都知道。
林雪的故事講得精簡而準確。
“但我感覺……”林雪講完之后看向我。
“你感覺什么?”
“我感覺啥地方有點不對。”
“哪里不對?”我實在不想再去思考這漫長一天里的任何一秒。
“萬玲玲和何勇愛得挺深的,你說是不是?”林雪扭著頭看我,雪花映著炸裂的煙花,透過村委會的窗戶讓她的臉呈現出迷幻而絢麗的色彩。
“那肯定的啊,我今天唯一能肯定的就是這件事。”對此,我真的無比堅定。
“那你說,愛得那么深的人,會背叛嗎?”林雪的煙灰掛在煙上,搖搖欲墜,仿佛彈一下就會變成雪落下。
“我覺得不會,相愛的人只會為彼此承擔。”
“比如呢?”她問我。
“命?”我反問她。
“對了,何浩和何勇關系怎么樣?”她終于抽完了一支煙,把煙蒂放進煙灰缸里。
“很好,特別好。”我已經心不在焉。
“在我看來并非如此,兩個人各自的表述里對彼此都不太友好。”
“你還能比我了解何浩?”我們兩人對視著陷入了沉默,我頭腦炸裂,無數的狂風裹挾著雪暴沖擊著我的毛孔,我快要窒息。
“如果何浩騙了你呢?”她問。
如果何浩騙了我呢?我想。
我腦海中有了我自己的故事。何浩和萬玲玲有事兒,倆人在大棚內熱火朝天的時候,李冬不巧經過,倆人怕事情敗露便用磚頭砸死了李冬。何浩慌亂之中來找了我,和我說的那些話故意留下錯誤的線索讓我為他開脫,即使最后發現是何浩殺了人,也不會懷疑他和萬玲玲有那種事兒。
萬玲玲本想說李冬強奸她,她在拼死反抗之下正當防衛殺了李冬。但沒想到何浩直接跑到我家來和我說了那些話,倆人只能再次約到后山的山洞里,商量了那樣的說辭,這樣何浩和萬玲玲的罪就都沒那么大。
那么何勇呢?何勇為什么要把這些東西扛在自己身上?或許是那些事兒比罪、比命更重。為了那些事兒,他能不要命。
我想透過那小屋的玻璃看看三個人的眼睛,我想知道這故事到底有沒有結局,這無底的洞到底能不能到底。
窗外煙花炸起,絢爛的煙火啃噬著無邊的黑色,宣告著時間的結束與開始。
我和林雪坐在長凳上,煙霧彌漫,周遭是永恒的變化和相對的規律。
【責任編輯】安 勇
作者簡介:
王冠楠,1994年出生于鞍山市臺安縣,畢業于沈陽大學中文系,從事過新聞編輯、文案、演藝等行業。有小說、詩歌、散文發表于《鴨綠江》等刊物。出版小說合集《盛京四俊》。現供職于沈陽市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從事宣傳教育及編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