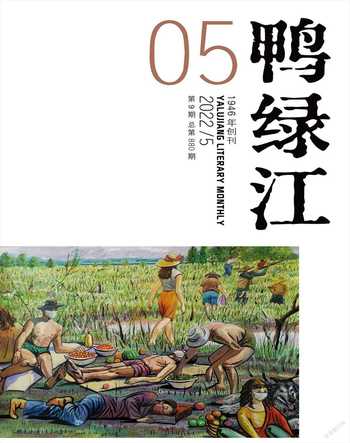“中國氣派”的藝術創造:20世紀30—40年代的馬健翎
論及文藝創造的目的和意義等重要問題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兩次提到民歌劇《小放牛》: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于被普及者,則普及還有什么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群眾所接受的教育,他們的接受能力比群眾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于當前的和群眾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滿足于《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于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①
《小放牛》作為一種文藝現象出現在《講話》中,原因無他,乃是時任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團長的柯仲平參與座談會討論時,提及這部作品,以說明新作品在群眾中的較大的影響力:“我們說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卻很歡迎。你們要在那些地方找我們的劇團,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路走,就可找到。老百姓慰勞我們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吃不完,裝滿了我們的衣袋、挎包、馬搭子。”柯仲平的說法引起了較多參會人員的共鳴,但毛澤東在高度肯定之余,也特別提醒:“你們要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②
自20世紀30年代末至20世紀40年代初的歷史語境看,《小放牛》的成功不僅關涉文藝的社會學影響這樣的顯在的問題,還關涉文藝的立場、道路等更為宏大和復雜的問題。在文藝為什么人、怎樣發揮其經世功能和實踐意義這些重大命題上,《小放牛》及其彰顯出的民眾劇團的創作理念,自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的時代和現實意義。本乎此,有論者認為,“毛主席的思想、觀點,是從群眾中來的,經過綜合、提煉,形成科學的理論,反過來又到群眾中去,指導群眾的革命實踐”。其中,“柯仲平同志和民眾劇團的藝術實踐”,對“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素材”③。不僅如此,民眾劇團在20世紀30年代末至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在戲曲現代戲上的實踐,不僅為《講話》若干觀念的形成貢獻了藝術上的素材,也在處理傳統與現代、藝術和生活等重要問題上,做出了至今仍有啟示意義的藝術探索④,其中尤以馬健翎的創作最具代表性。
《小放牛》的作者,便是時為民眾劇團劇作家的馬健翎。《小放牛》并非他的第一部作品。此前他還創作了在彼時影響極大的現代戲《一條路》《查路條》等作品。而以《講話》為界,將這一時期馬健翎的創作略作分期,則其《講話》前的作品可以《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十二把鐮刀》等為代表,《講話》后作品計有《血淚仇》《大家喜歡》《一家人》《窮人恨》等。如將《講話》前作品視為《講話》所闡發之文藝觀念提供了重要的藝術實踐的素材甚至“問題”的話,《講話》后的這一系列作品,自然可以解作是在《講話》精神指導下的創作實踐。其在這十余年間的藝術實踐,極為廣泛地關涉戲曲藝術的新舊之變,以及其間所包含的更為復雜的時代和現實問題。此問題關聯內容頗多,遠非簡單的藝術實踐所能概括。《講話》反復申論文藝的立場、觀念和方法,出發點和落腳點皆在文藝的時代價值和社會意涵。所謂的“藝術問題”固然緊要,卻仍需退居其次,因為相較于藝術的獨特創造,更為迫切和緊要的問題是如何發揮文藝戰線的作用,以更為有力地配合軍事戰線,從而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勝利,是為《講話》的核心要義和根本邏輯:“《講話》處理的顯然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而是完全、直接在政治空間內部,在思想和組織上厘定革命文藝的位置、作用、功能,提出黨對革命文藝和革命文藝人的期待與要求,并為后者滿足和達到這樣的期待和要求指出具體的努力方向。在毛澤東看來,革命作為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高表達形式,本身為中國文藝規定了方向,提供歷史經驗、思想內容乃至形式創造的可能性。”⑤是為在“政治內部思考文藝”與“在文藝內部思考政治”根本分野所在⑥,此后近80年對《講話》精神理解的不同,原因泰半源出于此。《講話》中“經”(經常之道理)與“權”(權宜之計)的辯證⑦,亦需在此一語境下得到較為妥帖的理解。
1938年,在《講話》所面對的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成立并開始了最初的創作實踐。正因充分意識到傳統戲曲(尤其是秦腔)在群眾中的巨大的影響力,民眾劇團的藝術實踐遂以“舊形式”(秦腔、眉戶等地方戲曲的藝術表現形式——曲牌、唱腔等)表現“新內容”的戲曲現代戲創作為主。《講話》前馬健翎的作品,無論在故事核心結構,還是藝術表達方式上,使用了較多傳統戲曲的藝術成規⑧。這些切近緊迫的現實問題的新內容,當然也可以話劇的形式演出,但缺少了戲曲曲牌和唱腔自身的影響力與感染力,其藝術效果則要大打折扣。也因此,借用在老百姓中間有極大影響的固有的戲曲藝術形式表達全新的觀念和生活內容,是馬健翎及民眾劇團這一時期創作的基本方式。此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題中之義:“而今看大戲班的戲,就看個紅火,娛樂娛樂罷了。看你們的戲,教我們娛樂,還叫我們知道打日本的事情。看你們的戲不止看紅火,還要看個情節。”——此為老百姓所言。“你們來唱三天戲。比過我們做三五個月的宣傳教育工作。”——此則為地方干部的評價。如此,足以說明“以中國民族特有的作風為主,將西洋藝術的適用的優良作用融合起來,那高度的創造性也才能充分發揮,這種新創造,是不要脫離中國藝術傳統的。它是中國藝術傳統的一個否定,同時是一個很好的繼承。”⑨
“新”(內容)與“舊”(形式)的辯證取舍,是民眾劇團此一時期藝術創造所面對的重要問題。既深知沿用舊形式之重要性,亦須傳播全新的觀念和生活內容,故而視野需要向兩個方面敞開。此如長安畫派的創作觀念所示,“傳統”和“生活”(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缺一不可。無傳統則所謂之創造即成無根之木,無生活則極易流于凌空蹈虛、不著邊際的顧影自憐。二者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延安文藝界皆不乏具體例證。自創建之初即有極為明確之目的的民眾劇團自然與此兩者皆不相同。⑩也因此,充分利用民間藝術形式,開拓現代戲的影響力和藝術表現力,是其時柯仲平等核心成員思考的重要問題。故此,民眾劇團現代戲創作史上,眉戶藝人李卜有著幾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李卜身世坎坷,卻在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中習得了超乎常人的藝術能力。其在眉戶現代戲創作過程中,對民眾劇團的創作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李卜參加民眾劇團的過程頗具傳奇色彩,丁玲、任國保相關文章考證甚詳,此不贅述。而因李卜的加入,民眾劇團在借鑒傳統戲曲的表現方式表現全新的現實內容上,可謂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自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今,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現代戲作品中,眉戶現代戲占據半壁江山即是明證。在此探索過程中,李卜無疑貢獻甚大。而在李卜引入眉戶唱腔之前,民眾劇團的戲曲現代戲皆為秦腔現代戲。相較于其時流行的如李卜常演出的舊戲《張連賣布》等作品,《一條路》《查路條》顯然已包含全新的生活內容。此為李卜甘愿加入民眾劇團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前的戲也有很多是勸善,只是沒有說出一條路。其實么,老百姓就沒有壞人。就拿我一個舊戲子來說,抽洋煙,該是老毛病么,可是并不打人搶人。你們這個戲我說的是大大的好戲,你們告訴了老百姓一條路,唉,我50歲了,這是第一次才看到的呢!”然而精通眉戶并在鄉村演出多年且深知群眾喜好的李卜,對民眾劇團的戲的缺點也有自己的認識:“戲是好戲嘛,這是新戲舊演。勸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功把式顯次點,沒啥,要是改唱眉戶就更好,吐音清楚,更聽得真。”!當然,眉戶唱腔的優點并不僅止于“吐音清楚”,其音樂細膩婉轉,長于表達更為復雜柔婉的情感,也是此后民眾劇團眉戶現代戲多出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對并不宏大的生活主題的表現上,眉戶有著較為鮮明的特點。馬健翎先后創作的《十二把鐮刀》《大家喜歡》是其中典范,即便在這兩部作品所涉之具體的現實問題已成“陳跡”的新的時代語境下,其中若干重要唱段仍在廣為流播,音樂之美恐怕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十二把鐮刀》《大家喜歡》皆為眉戶現代戲。前者所涉為其時影響甚大的大生產運動,后者則更為具體地涉及大生產運動背景下的“二流子”改造問題。如果說《十二把鐮刀》用意在于先進分子對落后分子的觀念勸勉,《大家喜歡》重心則在于以新的勞動觀念轉變游手好閑者的舊觀念,二者皆涉及思想觀念的改造問題——此亦屬該時期文藝作品發揮其經世功能的要義之一。但毋庸置疑,這兩部作品當時之所以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力,與其采用的鮮活生動的舊戲傳統密不可分。王二對其妻桂蘭的勸告,在具體的勞動生活實踐中逐層展開,不唯勞動自身的力和美在該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由勞動之美所引發的對全新的生活內容的想象則構成了文藝的世界想象的重要部分,包含了極大的感染力和精神創造力。該劇結尾處夫妻二人的對唱生動活潑,極富民間生活質感,觀者為之心動。《大家喜歡》亦是如此,劇情雖不復雜,但唱腔柔婉細膩,極富感染力。此中足見馬健翎借鑒傳統戲曲藝術形式及其所包蘊之民間傳統,書寫新觀念、新生活和新心理的藝術探索的重要價值。
前述兩部作品雖有較為具體的生活內容,但題材并不宏大,故而可以較為充分地發揮眉戶音樂靈動、鮮活的特點。但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所涉多為宏大而緊迫的現實問題,故而如《血淚仇》《窮人恨》這樣的規模宏大的作品亦不可或缺。《血淚仇》《窮人恨》皆格局宏大、情節復雜且人物眾多,是從更為宏闊的層面對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具體的現實問題的藝術處理,其間包含著創作者極為濃重的現實關切。劇中人物無論王仁厚、王東才(《血淚仇》),老劉、滿倉(《窮人恨》)等正面形象,還是田保長、郭主任、孫副官(《血淚仇》),胡萬富、高順、馮鎮長(《窮人恨》)等反面角色,皆入木三分,極具時代的典型性。而前者所面臨的具體的生活困境,亦屬那一時期身處底層的小人物的普遍境況。他們身在舊時代,被迫面對被欺凌、被侮辱、被損害的艱難境遇卻無由解脫,唯有同心協力、奮起反抗,創造屬于自身的新世界一條路而已。由此,《窮人恨》在“新區”的演出受到普遍歡迎的根本原因可做如下總結:“作者寫出了窮人的一般痛苦,刻畫了壓在窮人頭上的剝削者的惡和罪孽”“新區的群眾,受過了長期的獨裁反民主的統治,在政治上沒有地位,在經濟上受到剝削,他們心里的千辛萬苦,無處可訴,而《窮人恨》這個劇本,正把他們心里的話講出來了”@。此正說明馬健翎作品在20世紀至20世紀40年代較大的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原因,是其對宏闊的、緊迫的現實問題的獨到的藝術處理。其間不僅包含他對具體的生活世界根本問題把握的高度、廣度和深度,還包含著對藝術影響力的深入考量。一言以蔽之,乃是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
如《講話》所論,“普及”與“提高”,關涉其時更為復雜的現實問題。不僅文藝作品的接受者的基本狀況需要藝術創作者考量,如何不斷感應時代問題的新變化并將之高度融入藝術作品的創造也頗為緊要。其間必然涉及內容與形式的辯證。故而述及《血淚仇》的創作經驗,馬健翎特別強調民眾劇團若干嘗試的重要性。“我們在這六七年當中,運用舊形式寫新的內容的劇本,大小有幾十個了,有秦腔,有曲子小調,每次從寫劇本、導演,一直到演出后的不斷地改正,為了加強現實性,不時和舊形式肉搏斗爭。”《血淚仇》《窮人恨》更為宏大的主題,對現實問題更為復雜的藝術處理,皆表明寫作者自身觀念的“提高”,以及為了將這種“提高”表現到作品中,從而促進觀者“提高”的用心。在創作《血淚仇》的過程中,“近情近理,紅火熱鬧,叫人看得懂,受感動;看完了,明白世事,懂得道理”#成為“指揮”和“糾正”他的重要因素,原因蓋出于此。
但形式問題并不能僅在形式的意義上得到充分的闡釋,它必然涉及更為復雜的社會觀念問題,也唯有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其蘊含的復雜能量方能得到充分的釋放。20世紀50年代后,除《兩顆鈴》《雷鋒》等作品外,馬健翎的大部分精力皆轉移到對傳統經典的改編上,這當然有賡續傳統藝術的充分考量,但更多彰顯的卻是時代氛圍之變引發的創作觀念和主題的自然調適。將其作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作品并作一處看,則更能體會其在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創作之用心及其現實意涵。他在其時“中國氣派”的藝術作品的獨特創造上的探索和積累而成的經驗的意義也在此處。20世紀40年代前后,關于民族形式和中國氣派的討論呈一時之盛$,但其所包含的復雜問題仍需在論者的如下視野中得到理解:“民族形式并不被看作已經固定的東西(‘瓶’),而是一種新的中國構想,其內涵與社會主義、抗日、新民主主義密切互構,同時又超越諸種政治內涵而具一定的穩定性。”因是之故,“這里的‘民族形式’不僅早就超出了‘文學(的)形式’的一般內涵,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內容’的附屬品,毋寧說,正是民族形式本身在決定著文學如何具有‘中國氣派’以及政治內容如何具有中國的合法性”%。亦如柯仲平1939年所論,“中國氣派”乃是由“民族的特殊經濟、地理、人種、文化傳統”歷經千百年而逐漸形成的。這種氣派,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民族文化的精神氣質,一種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韻味,一種足以代表和彰顯中國文化的重要調性。當然,這種氣派也因長期扎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為他們“喜聞樂見”。也因此,使用和創造“中國氣派”,必然要植根其時宏闊的社會現實,表達藝術家對時代的緊迫問題的深度感應和藝術化處理能力。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面臨貞元之會、絕續之交,緊迫的現實問題在多重意義上決定了有社會擔當意識和責任感和藝術家的藝術創造的精神選擇。在此過程中,雖未必有暇從容判定“歷史中國”與“當下中國”的內在連續性,但如柯仲平等人所論,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精神和中國氣派的“傳統”仍在,雖面臨“新”與“舊”的鼎革之變,仍以其充沛的生命力和不息的創造力作用于新的歷史和時代語境,并成為其時藝術創造者可以依憑和借鑒的重要的精神和藝術資源。而在全新的歷史和時代語境下重解“歷史中國”與“當下中國”的連續性問題,且在突破古今中西之爭所開顯之狹窄視野中重新理解中國古典傳統之于當下現實意義和精神效力,是不容回避的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命題。也因此,《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并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
時距《小放牛》初演的1939年已有80余年,戲曲現代戲創作在此期間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但如《小放牛》及馬健翎的《血淚仇》《窮人恨》等切近具體的現實問題、以文藝作品的獨特創造極大地發揮經世功能和現實意義的作品卻日漸稀少。這里面不僅包含了創造藝術的年代之間巨大的分野,也包含了扎根具體的歷史和現實語境在融通中國古典及域外藝術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屬于自己的時代的藝術形式的重要命題。因為在多重意義上,“民族形式”抑或“中國氣派”,既關涉文藝審美價值偏好,亦內在于時代和現實問題的深層變革,乃是兼具內容與形式的雙重意涵。明乎此,則馬健翎的現代戲創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參照意義,有觀念和藝術經驗的累積,同時也包含著“未盡之意”和“未竟之處”,有待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做進一步的賡續和發揮。以之為參照敞開的觀念和藝術路徑,不僅有助于更為深入地理解《講話》闡發的文藝觀念及其現實意義,亦有助于打開更為開闊的藝術視野,以創造屬于我們時代的秉有中國氣派的藝術作品。
本文系陜西省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項目“‘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字媒介時代的文藝批評研究”(19ZDA27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16—17頁。
②康濯:《<講話>精神要代代傳(節錄)》,《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532頁。
③林默涵:《柯仲平與民眾劇團》,《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④民眾劇團的藝術探索的源起,也和毛澤東的文藝觀念密不可分:“1938年4月在一次邊區工會組織的舊戲曲晚會上,當聽到毛澤東同志提出可不可以用民族形式和新內容結合的問題,柯仲平同志便自覺而勇敢地把這一個責任承擔在自己肩上。”參見秦川:《要為民眾劇團唱贊歌》,《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關于毛澤東與民眾劇團創立之關系,任國保有更為詳細之說明,可一并參照:“1938年4月間,毛主席在邊區工人代表大會組織的戲曲晚會上,看演出秦腔《五典坡》和京劇《升官圖》等戲時,群眾很歡迎。毛主席當場對工會負責人毛齊華同志說:‘你們看群眾非常歡迎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但是內容太舊了,應該有新的革命內容。’齊華指著坐在毛主席身后的柯仲平同志說:‘這是文協的老柯,他是專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轉身親切地問柯仲平:‘是不是應該搞呀?’‘應該,應該。’柯仲平同志肯定地回答了毛主席的提問,并堅決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參見任國保:《五十年足跡: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大事記》,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⑤張旭東:《“革命機器”與“普遍的啟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語境及政治哲學內涵再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⑥楊輝:《總體性與社會主義文藝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
⑦劉奎:《有經有權:郭沫若與毛澤東文藝體系的傳播與建立》,《東岳論叢》2018年第1期。
⑧如辛雪峰所論,其時較多作品是對傳統秦腔的套用,“馬健翎按傳統戲《反徐州》仿寫的《好男兒》,張季純按《牧羊卷》仿寫了《回關東》”。其他如《雙投軍》仿寫自《柜中緣》,《抗戰三回頭》仿寫自《三回頭》等等。辛雪峰:《從<秦腔音樂>看延安民眾劇團的秦腔改革》,《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⑨柯仲平:《介紹<查路條>并論創造新的民族歌劇》,《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頁。
⑩柯仲平為民眾劇團創作的團歌,即充分體現其全然不同之觀念和藝術追求:“你從哪達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又要往哪達去?/到老百姓中去。/我們是來學習老百姓的寶貴經驗,/你看老百姓已活了幾千、幾萬年。/我們是來動員老百姓抗戰生產,/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無底、大無邊。/我們是來吃老百姓的奶,/我們是來為老百姓開墾荒山。/在民主的邊區,/我們自由地走去走來。/我們要叫勝利花開遍,/花開遍,在荒山。”柯仲平:《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團歌》,《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頁。
!丁玲:《民間藝人李卜》,《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頁。
@鐘紀明:《<窮人恨>在新區的演出反映》,《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頁。
#馬健翎:《<血淚仇>的寫作經驗》,《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藝術紀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可參見李瑋:《重新發明“中國”——1930—1940年代中國的“民族形式”問題》,《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
%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5頁。
^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2月15日。
作者簡介:
楊輝,文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表論文近百篇,著有《“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陳彥論》等專著多部。曾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年度優秀論文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柳青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