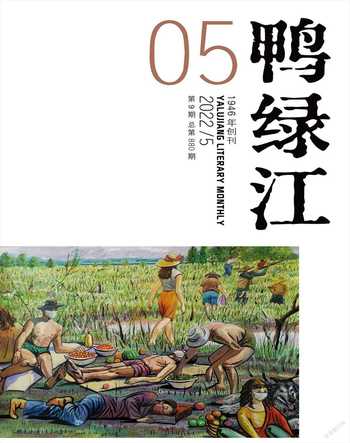“對不變的藍天白云做深呼吸”
沙克自稱“老資沙克”已經多年,究竟他“老資”的含義是什么,我也說不清楚。只是想,大概是為了區別于所謂的小資。因為小資一般會顯得膚淺些,有小情小調,卻不會深刻,而這是沙克看不上的。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不論老資還是小資,顯然都帶了文化或美學上的追求,有自來的“資”。這自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資,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資歷的資、精神資質的資、寫作資本的資、可資用途的資……且什么東西一旦“老”,皮就厚些,也不怕別人嘲諷,與其被人視為“資”,不如干脆自詡,且直接升格為“老資”。
以上純屬我的瞎想。上海人有個說法,叫作“老克臘”,大意指老上海的一種有格調的男士,不一定有特別不尋常的身份,但一定會有特別不一般的格調。這個詞,要么是來自英文“colour”,要么是“classic”,是顏色,或者層級之意,都可以引申為情調或者格調的意思。不知為何,我時常把沙克想象為一個類似于“老克臘”的身份,一個有不同尋常品位的、有著追求別致生活方式的人——他的履歷,與上海那座老資扎堆的城市或許有些連帶關系,或者毫無關系,卻應有時空上的微妙感應。
說了這么多,當然是為了談沙克的詩,弄不準他的身份,便不會準確解讀他的作品。反過來,如果讀不懂他的詩,也大概不會明白他為什么叫老資沙克。
沙克的這組詩,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用比較輕松和輕便的口語表達其沉浸和深入的文化思考,或者生命態度。他刻意讓自己的語言脫離華美的不及物,而落地于日常性與細節化的宣敘,連描述都很少用,更遑論象征與隱喻。這大概是他從年輕時代作為“第三代詩歌”運動的卷入者身份那里繼承來的,是一種相當定型的文化態度,或者是由詩歌觀決定的。怎么寫和寫什么,以什么樣的風格調性來寫,他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規。
但是沙克有非常自覺的精神與文化方面的“人設”,他不會允許自己的詩歌真的僅僅成為日常性的敘述,必然在其中有各種深度設置。因為他是老資沙克,所以必然有其別致的、沉浸和內在的東西在。
這組非洲主題的詩是怎么來的,我拿不準。從朋友的角度,我好像并沒有聽說沙克有在非洲工作或較長期的旅居。從作品看,比較大的可能是他有一次或多次的旅行史,至少到了北非和東非的許多地方,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亞以及東非高原的肯尼亞等,到了那里的城市、草原、叢林和沙漠,或許是一次純粹的“紙上旅行”也未可知。但從詩中看,絕對是充滿了細節意味與現場感的。
這個當然很重要。我在想,沒有現場經歷,沒有身臨其境,很多感受是不會產生的,產生了也不會真正感人,所以這更像是一場浩大的旅行,是多個情境下悉心的觀察與思考,那些自然、歷史、現實的城市風情,沒有身臨其境的體驗,很難寫出如此豐富的感受。
而且就地理差異而言,北非的埃及和摩洛哥,與歐洲文明與文化的關系非常深。而東非高原的肯尼亞,則是非洲的高原與叢林,與前者差異巨大。
都不管了,我們姑且設想作者是用了相當漫長的時間漫游了這兩大區域,而且還由此以歷史與文明的觸角,思考了更多更遠的問題——比如他還寫到了納爾遜·曼德拉,那位為南非獨立而斗爭了一生的黑人總統。
讓人吃驚的是,他一會兒是在馬賽馬拉草原,一會兒就來到了搖曳著地中海風情的卡薩布蘭卡,一會兒還站在河馬和鱷魚的前面,一會兒就來到了四千年前的盧克索。這一切都被他整合為一種黑色的或者褐色的文明,它們有著自古至今的連貫性和某種總體意味,是一塊有著莽野的自然蠻力,又有著久遠的古老文明的巨大陸地,至少我在讀這些詩的時候產生了這樣一種整體感。
依照我個人的趣味,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組詩中的《卡薩布蘭卡》。如同電影史上的那部名片一樣,這首詩把一個風情萬種的城市的諸般側面生動地再現。“忽閃忽閃/三種美人魚擺動尾花/名字好聽/白里透紅的卡薩布蘭卡//王宮,綠,清真寺,綠/五官偏藍的尼格羅—歐羅巴/融進大西洋的風和景/頭巾隨時散落/綻開曲身長腿的三個她”。將城市的主調與標志性的建筑,以印象派繪畫的方式斑駁交錯地點染出來,并與那部著名的電影的形象進行了暗自的接通與對應。
里克咖啡館,烤魚香
游在窗外的白魚,乳溝深
混血魚的臀,翹向一月的迷情
英格麗·褒曼還在扮演一只躲閃的貓
懷舊的敏感兩世通達
這種蒙太奇式的印象疊加,如同一幅地中海風格的風情畫,讓人流連忘返,浮想聯翩。
當然,最壯觀和最令人震撼的,還要數開篇的一首《馬賽馬拉草原》。這塊非洲大陸最生氣勃勃的土地綻放著地球上最動人的生命史詩。沙克以疊加刻寫的筆法,濃墨重彩地描畫出了這一史詩場景,寫出了“比胸懷大十倍比視野大百倍的馬賽馬拉”。仿佛一只鷹或帶著廣角鏡的攝像機飛過草原上空,他注視著這生命世界中的弱肉強食,注視著叢林中固有的生存法則,它的血腥和殘酷、壯美與永動。他用刻意冷靜的目光與對生命世界中生存斗爭的沉思,將我們帶入了一個充滿悖謬與感動的境地:“遼闊嗎,壯麗,野蠻嗎,靜謐/比胸懷大十倍比視野大百倍的馬賽馬拉/對一只獅子撲倒角馬無動于衷/對一群鬣狗撕碎羚羊……/一只獵豹咬斷斑馬的脖子無動于衷”。
這就是生命世界的真相,生命史詩中永恒的倫理與悖謬。“眼神空茫的馬賽馬拉站在原地/遍體草茬,碎骨零落/對不變的藍天白云做深呼吸。”
作為《馬賽馬拉草原》姊妹篇的,還有《藍天邈遠如飛》《奈瓦莎湖畔之夜》《原野上的傘》《夜雨后的清晨》《這一角人類》諸篇,它們分別從不同視角續寫這個生命世界的不同側面。有安詳的靜謐,有飛翔的舒展,有星夜的柔情想象,也有烈日下的風景變幻。它們都可以視為沙克對一首生命史詩的反復展開與變奏,正如《夜雨后的清晨》這樣寫出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背后一個個溫馨美好的靜謐時辰:
織巢鳥起得早些
叼著草葉細麻飛到合歡樹的枝杈間
就著旭日的柔順光線
搖晃腦袋,編織可舊可新的一天
危機四伏與萬象叢生中,生命的曙光照常升起。實在是太美了,這才是史詩的主題,雖然沒有史詩的規模與長度,卻有史詩的靈魂與意義。
除了自然部分之外,便是歷史文化的尋訪了,《卡薩布蘭卡》是其中之一,而《踩點內羅畢》《納爾遜·曼德拉》《入埃及》《碎瓷公主》都屬于這一部分。這是時間之維、歷史之縱深的部分,前者是空間與自然的世界,這是對文明的理解與造訪。平心而論,我對這一部分沒有什么資格評論,因為在我個人的履歷中,非洲這塊大陸,我只到過埃及,且只限于尼羅河終點處的開羅和亞歷山大,對于上埃及的盧克索那些古文明之地還沒有去過,所以很難做出有意義的判斷。但是在筆者的寫作履歷中,也寫過一首《曼德拉》,是紀念他去世的一首,與沙克詩的立意大概也很像,是對于他半生坐牢,為非洲的獨立與尊嚴奮斗的一生的追祭。沙克所寫,可謂深得我心。
埃及是寫不盡的,沙克寫出了他的埃及觀感,仿佛是沿著尼羅河順流而下,他一路感嘆緬想,把埃及的歷史與現實交織在一起。這感受與我去埃及時的觀感很像,這古老的國家,經過了四次文明的斷裂,依次被希臘、羅馬帝國、阿拉伯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和統治,剩下來的,便只有金字塔、木乃伊和偉大的古代傳說了。這謎一樣的文明,甚至難以為今人做出解釋,沙克寫出了這復雜的感受。
總體上,沙克的這組詩是當代詩歌中比較罕見的文本,書寫非洲的自然與歷史文明,對中國的詩人來說,是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沙克算是一個大膽的試水者。需要交代的是,沙克近期出版了一部書寫域外地理歷史與人文風情的詩集《憶博斯普魯斯海峽》,而在我讀這組非洲主題詩時還沒見到它,或許可以猜測它作為關聯深厚的人類文明的認知背景,能夠為非洲組詩的必然生成而非偶然出現做堅實的托底。作為朋友,我對沙克兄有著深遠的閱讀期待。
【本欄目責任編輯】林 雪
作者簡介:
張清華,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兼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出版學術著作15部,詩集和散文集7部,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批評家獎、省部社科成果一等獎、北京市教學成果一等獎、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獎、北師大教學名師獎等。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等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