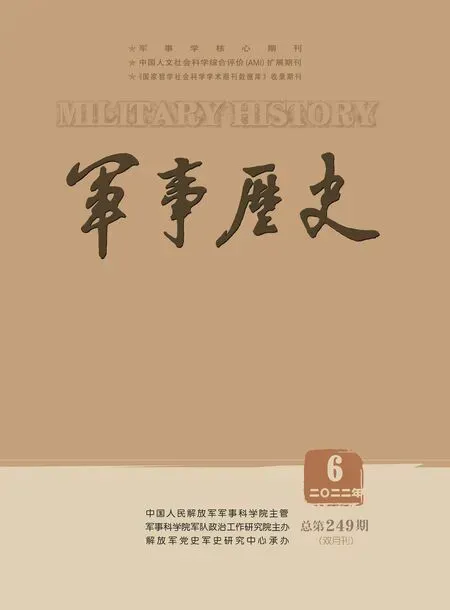抗戰時期山西聯莊會的發展態勢及其命運走向 *
★ 于 飛
聯莊會是清末華北地區興起的民間自衛武裝組織,當時主要分布于河南、山東、河北等平原地區。華北平原地區的聯莊會不僅分布廣泛,其規模亦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漸惡劣而愈發膨脹,抗戰時期更是出現了超縣域級別的聯莊會。但聯莊會在山西僅有少許分布,總體上呈現出“寥若晨星”的局面。
聯莊會是一種臨時性的武裝自衛組織,多興起于社會大規模動蕩之際。抗戰全面爆發后,日軍對華北的軍事入侵直接影響了該地區的社會穩定,導致聯莊會大規模地復蘇。抗戰初期冀魯豫三省的聯莊會是華北社會環境惡劣的表現,也是政府權力失序和統治力動搖的體現。隨著中共進入華北平原并逐步開展根據地建設,聯莊會在這一過程中為中共所消化,并成為中共早期武裝來源的重要部分。而在山西,基于歷史問題和政治形勢等因素,抗戰初期聯莊會呈現出勢微的態勢。
從時間上看,山西聯莊會組織的歷史淵源不遜于平原各省。目前學界關于抗戰時期聯莊會的研究多集中于河北省,且多聚焦于冀中地區①如張洪祥、王璇:《略論抗戰初期冀中區的聯莊會和會門武裝》,《南開學報》1993 年第2 期;[韓]宋在夏:《三四十年代華北農村傳統武裝組織的演變》,《歷史教學》1999 年第8 期;鄭立柱:《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冀中聯莊會工作述論》,《保定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第1 期;張同樂:《1940 年代初期河北省淪陷區聯莊會研究》,《安徽史學》2014 年第6 期;鄭立柱:《華北抗日根據地社會問題及其治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并未涉及山西的聯莊會。歷史研究不能僅僅著眼于宏大現象的存在及其原因,對于式微的現象和為什么“不存在”的問題亦要關注。因此,本文不僅浮于對晚清以來山西聯莊會發展態勢的敘述,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季節性的組織來反映晚清以來至抗戰爆發后山西社會歷史變遷的獨特面相,最終落腳到抗戰爆發后山西特殊的抗戰形勢。
一、“寥若晨星”:從華北區域看清末以來山西聯莊會的發展態勢
自晚清聯莊會出現以來,華北各省的聯莊會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態勢和路徑。縱觀整個華北區域,聯莊會主要分布于平原地區,山地地區相對較少。從時間來看,晚清咸同之際與抗戰初期是山西歷史上聯莊會出現相對較多的兩個主要時段。聯莊會為非常設之組織。每遇地方不靖,獨力難持時,村莊才會依靠“團結”的力量來對抗各種外來因素的侵害。因此,聯莊會的出現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社會環境的惡化。
(一)晚清至抗戰全面爆發前
清咸同年間,太平軍北伐和捻軍席卷華北平原各省,威脅直逼京師。咸豐三年(1853),面對江南叛亂,文宗未雨綢繆,下令“各直省仿照嘉靖年間堅壁清野之法,辦理團練”。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3 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108 頁。隨后,河南基于事態蔓延逐步興辦團練。在這其中,由民眾自發組織而起的聯莊會成為國家平叛與地方反叛活動中的重要角色,但部分聯莊會不僅未能契合清政府實行地方自衛的預想,甚至一度“火上澆油”,加劇了國家與叛亂群體的矛盾沖突。
晚清的興辦團練大潮,山西亦參與其中。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諭令山西巡撫“體察情形,各飭所屬勸諭紳民,認真團練”②《清實錄·文宗實錄》卷95,咸豐三年五月癸丑。,是為晚清山西團練武裝的制度化起源。山西相對遠離太平軍和捻軍的活動中心,處于起義影響的邊緣地帶。因此,上述兩股勢力并未對山西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承辦的團練并不普遍。”山西興辦團練的勢潮要晚于河南等省,“不僅時間較晚,而且時辦時停,形勢緊張時,就積極提倡、催辦;形勢緩和時,即予裁撤”。團練承辦較多的區域,“主要是靠近河南、陜西的晉南、晉東南和晉中的一些州縣”,“北部各州縣辦團練的為數甚少”。③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卷36“軍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470 頁。
如河南一般,山西團練的試辦中亦有聯莊會的身影。同治元年(1862),西捻軍自陜西逼近山西,清政府督促山西辦理團練。晉省內亦有地方人士呼吁倡辦。《壽陽縣志》載,該年有人以“壽陽地處衛途,兵差絡繹,恐有逃兵滋擾,強盜竊發”為由具稟行保甲團練事,主張各村聯合,“請令各村團長于編聯本村之后更與鄰近諸村互相約定,一村有警,或放炮,或鳴鐘,數村實時赴救。如有約而不赴者,或私相議罰,或公稟究治,此即所謂連莊會也”④《壽陽縣志》卷11《藝文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839、840 頁。。雖未見聯莊會的確切案例,但聯莊這一原則應為鄉村團練所接受。叛亂事畢,聯莊會隨著團練的陸續解散而瓦解。
清末時期山西也出現過聯莊會。《臨晉縣志》載,光緒三十一年(1905)時有哥老會匪“費蛋娃之亂”,擾亂民眾。為了應對此事,知縣賴慶榮“改里為團,仿直省聯莊之法,村自為守計,全境分設十六團,團各有長,分轄各村,藉收指臂之效”⑤《臨晉縣志》卷1《區村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34 頁。。由此來看,山西聯莊組織的出現受到了直隸以及周邊省份的影響。此外,新絳縣亦曾辦過聯莊會,“系連結數村合力防匪。遇有警時,凡有契約之村,俱招集壯丁執械往捕”⑥《新絳縣志》卷3《兵防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288 頁。。受八國聯軍侵華影響,毗連河北的大同靈丘縣,“逃兵集縣境為患”。對此,舉人杜上化聯絡53 個村莊,創辦聯莊會,“南到大地,北到銀廠,東到糟伯,西到川嶺”,以上寨為中心,分5 個分團,同匪兵搏戰,最終“匪潰敗,再不敢入境”⑦《杜上化事略》,《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55 輯,1998 年,第719 頁。。山西境內平陽府西一帶,“有武生聯合鄉村七十座”⑧《紀聯莊會之關系》,載《清議報》1901 年第87 期。,成立聯莊會,并欲聯合河南義和拳民對抗八國聯軍及漢奸。民元以后,聯莊會在山西銷聲匿跡。晚清山西聯莊會的浮現如蜻蜓點水,曇花一現。
(二)抗日戰爭時期
抗戰全面爆發后,華北平原尤其是以河北冀中為主,出現了大量的聯莊組織。冀中平原出現了多種雜色武裝,大體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國民黨軍人組建的抗日武裝,有萬余人;第二類是土匪武裝,有6000余人;第三類是地主豪紳以“保境安民”名義組建的“聯莊會”“民團”“自衛團”等,有2 ~3 萬人;第四類是會門武裝大刀會、紅槍會等,約萬人左右。①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審編委員會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3 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 年,第21 頁。可見抗戰爆發后冀中平原的混亂局面,但其中關于聯莊會數量的估計仍有很大程度的保守。1938 年春中共方面統計的冀中聯莊會人數達9.5 萬余人。②參見張洪祥、王璇:《略論抗戰初期冀中區的聯莊會和會門武裝》,《南開學報》1993 年第2 期。此表根據中央檔案館藏1939 年《冀中區發展概況》整理而來,“但并不完全準確,因為當時安新、安平、蠡縣、深縣、深澤、肅寧等縣也都有聯莊會組織,沒有統計在內”。
侵華日軍的鐵蹄踏到山西,這是近代以來山西首次遭到大規模、長時間的武裝侵入。這不同于晚清太平軍在河南、山東等以南省份引發的動亂。抗日戰爭爆發后,與以往聯莊會只出現于晉南、晉東南等地區的情況不同,靠近平津并成為日軍入侵山西的起始區域的晉北地區亦出現了聯莊會。
盧溝橋事變之后,山西河津縣的嚴慎修③嚴慎修(1878—1945),字敬齋,山西河津縣里望鄉上井村人(今屬萬榮縣)。清末曾由山西大學西學專齋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回山西發展,深得閻錫山賞識。1931 年曾與梁漱溟、晏陽初等人一同推行過“鄉村建設運動”。從上海回到家鄉,組織抗日武裝。嚴慎修同梁漱溟、晏陽初等“鄉建派”代表人物一同推行過“鄉村自治建設運動”,因此對“鄉建派”中以聯莊會為組織的鄉村保衛體制設想有一定接觸和認識。基于時局與自身經驗,他“將西廟埝八村四社的賽會官款全部買了槍械,組織保衛聯隊,各村均制定專人負責,分別在本村成立自衛隊”④山西省《萬榮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萬榮縣志》卷36《人物》,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年,第799 頁。,開展抗日斗爭。晉北地區也因日軍侵華引發的社會動亂而組織有聯莊會。抗戰甫一爆發,應縣受戰爭波及,散兵游勇、地痞流氓趁機作亂。應縣南河種鎮西崔莊的趙徹趁機糾合百人進行搶劫,對此,縣周邊“有許多村莊便組織鄉丁購置機械實行武裝自衛”,其中羅莊的袁悅、楊順等人購買武器,并與上寨的賈秘、董高品等秘密約定,成立聯莊會相互照應,以對抗趙徹匪幫。次年又同喬日成的聯莊相聯合,進一步擴大聯莊對抗土匪的實力。⑤《羅莊成立聯莊與保甲隊始末》,應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印:《應縣文史資料》第8 輯,1995 年,第60、61 頁。
抗戰中后期,沁水地區受日偽的影響也成立了聯莊組織。1942 年,沁水馮村偽村長李奪元依靠日軍宣撫班為后盾建立馮村民團,“強令張村、馮村、蘆坡各個村莊,凡18 歲以上,40 歲以下的男性公民,全部入團”⑥《馮村“民團”被殲記》,沁水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沁水文史資料》第1 輯,1991 年,第111 頁。,足有千余人。團員分骨干隊和普通隊,骨干隊有武器。團部設在馮村三官堂,團下設大隊、中隊、分隊。除訓練外,民團每天結隊到張村南嶺、西鄉東文興、西文興、譚河一帶進行活動。
以上是筆者目前所見的歷史上山西聯莊組織僅有的幾個案例。雖然近代史料浩如煙海,難以窮盡,但總體而言,無論是著眼于晚清以來的較長時段還是聚焦于抗戰時期,山西聯莊會的數量、規模與活動程度皆遠遜于華北平原的省份。究其原因,尚需進行多方面考量。
二、自然環境與社會民風:影響山西聯莊的隱性因素
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提出的“三時段理論”成為目前學界分析歷史發展過程的常用套路,也代表了學界對其理論的認可。該理論最突出的特點是對地理環境演變之于人類社會的影響這一“長時段”的觀察。“時間”是“長時段”理論的基本內容之一,任何歷史事物的發展都有著潛在而漫長的演化過程。此外,生態環境作為歷史發生的土壤亦不可忽視。裴宜理在研究中國的地方叛亂時基于生態史視角指出,自然環境是淮北形成高風險經濟系統的重要因素,并為土匪和紅槍會的興起提供了條件。⑦[美]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池子華、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第24、25 頁。“長時段理論”和生態史的研究角度為分析山西為何沒能出現聯莊會的隱性因素提供了方法論和視角上的借鑒。
聯莊會的興起與演化受當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惡化的綜合影響。同理,聯莊會的兵微將寡亦受當地環境的潛在影響。歷史上,山西為何沒能出現大規模的聯莊組織?從潛在長遠的因素來看,可從自然環境和社會民風兩個方面分析。
(一)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對聯莊會的規模、分布有著重要的影響。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聯莊會多集中于平原地區而少見于山地地區。相較于華北地區的平原地形,山西為山地省份,地勢起伏較大且坡度陡峭崎嶇,不利于民眾聚集與交流,也并非同平原一般村莊密集且分布廣泛。閻錫山推行村政時,曾考慮到“晉省僻處山隅,村莊零落”①邢振基:《山西村政綱要》,太原:山西村政處旬刊社,1929 年,第16 頁。,為此于各村特設村長副加以輔助。村莊的零落與空間間隔使得各村之間難以產生緊密聯系,同時也導致村際間交通與信息交流的通暢度遜于平原地區。
不同的地理形勢導致各區域間的民眾防衛策略呈現差異。在面對社會環境的大規模惡化時,一望無際的平原使得一般民眾避無可避,逃無可逃,相互團結是其僅存的生存方式,通過“人多勢眾”來保衛自身生命財產安全。而山地地區民眾應對危機的方式較為保守,即采用“躲進山里”的方式來避免沖突與對抗。山西太原赤橋村士紳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曾提到,在日軍逼近太原時,其三子劉珦于凌晨時“即起呼喚眾收拾一切,俾其妻及四媳奉其繼母史竹樓入明仙峪避難”,其他子嗣亦分別逃進山中,“四孫吉忠隨其嫂入柳峪,長孫全忠亦于昨晚引導四男之兩女入明仙峪,到瓦窯村賃屋而居,為闔家避亂之所”。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7 年11 月6 日),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65 頁。崎嶇荒涼的深山為民眾逃避禍患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場所,也塑造出民眾在面對災禍時偏保守的行為邏輯。同時,崎嶇的地形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匪幫勢力的擴張,削弱了地方不安定勢力的大規模聚集流動和民眾自衛的發生機制。
自然災害是導致社會環境惡化的外部因素。地形地勢不同,承載和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也不同。以水患為例,水患對平原地區的影響要大于山地地區。相較于其他災害,水患更容易導致民眾流離失所,增強民眾的流動性,加劇社會不穩定程度。
歷史上的華北平原受黃、淮等河水患侵蝕嚴重,富集而居的民眾為此多被災蒙禍。以淮河為例,近代的淮河水患頻發,且每次大型水患發生時,流域內受災人數皆在百萬人以上,嚴重時甚至達兩千余萬,是1912 年山西省人口數的兩倍有余。③陳橋驛:《淮河流域》,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 年,第31 頁;[美]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第24 頁。山西省1912 年人口為1081896 人,參見葛劍雄:《中國人口史》卷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120 頁。黃河下游地區亦受災嚴重,自1855 年至1948 年的94 年間,黃河共決溢70 次,其中1933 年決溢口門多達104 處。④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志》總編輯部編:《黃河志》卷2《黃河流域綜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152 頁。而山西的水患多發生在黃河、汾河、沁河等沿岸河谷地區,河谷以外地區受水患直接影響較小甚至無水患影響。復雜迥異的自然條件造就了(自然因素只是原因之一)各省民眾流動性和社會穩定性的差異,亦成為塑造民眾生存策略的潛在因素。
平原地區是華北地方叛亂多發的核心區域,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大規模的民變,如清末白蓮教起義、捻軍起義等。山西則多為流經波及的“邊緣”區域。面對平原地區的叛亂,位于晉冀豫之間的太行、中條兩條山脈削弱了山西同冀魯豫三省的物質、人員流動,避免了大規模叛亂力量直接進入山西。同時山西西側于華北平原,屬中國的中部地區,并非是叛亂者進攻的重點。晚清太平天國、捻軍等反清勢力直搗京津,從華北平原肆虐至山西界邊時,經兩條山脈的阻擋,猶水之就下,向北而去,山西社會未遭受其長時間大規模的騷亂。總之,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形勢作為先天性的因素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山西聯莊會屈指可數的歷史態勢。
(二)民眾性格
民性是某一地域內民眾性格的整體性表現,代表著民眾的行為與處事邏輯。受地理環境、生存條件的影響,不同地區的民眾性格亦呈現出顯著差異,影響著民眾的處事風格和行事決策。冀魯豫一帶向來“民風彪悍”,民眾多有習拳之風,甚至部分地區曾是秘密會社的發源地。《東華續錄》載,“河南等處民風強悍,平時結捻械斗”①[清]王先謙:《東華續錄》第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117 頁。。袁世凱曾上奏說:“臣查直隸南境各屬,民情強悍,盜賊素藩。”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17 頁。轉引自黎仁凱:《聯莊會與景廷賓起義》,《景廷賓起義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57 頁。因而,歷史上如白蓮教、義和團、聯莊會等民眾自發性運動多發于冀魯豫一帶。盡管同屬于華北地區,但兩兩相較之下,山西民眾在性格上更加溫和,歷史上的斗爭規模和次數亦遠不及平原地區。《山西風土記》載:“山西民風素弱,右文左武。”③石榮暲:《民國風土記·職業篇第三·兵勇》,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舊志二種》,任根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119 頁。1938 年3 月中旬,中共晉察冀省委在遼縣召開建立太行山根據地會議時對晉冀兩省的民眾性格和斗爭情況作過簡要分析,認為:
河北民性強悍,山西民性溫和易于統治,但同為農民性質,如領導不好,或缺乏領導,極易走上土匪主義的道路。在晉東,存在的政權都是原有的,人民生活雖極窮苦,過去缺乏斗爭經驗。冀西多偽政權,有自發的、武裝的、非武裝的,公開的、非公開的組織,如會門紅槍會等,他們有極高的警覺性,不容易聯合,可是群眾所受壓迫厲害,斗爭經驗豐富。④《關于建立根據地的基本工作問題(節錄)》(1938 年3 月20 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七·群眾運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94 頁。
雖說以上論述的范圍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兩省交界的太行山地區,但對于這一區域民眾性格和斗爭情況的分析恰如其分,大體上可以反映晉冀兩省的整體情況。在論述中,雖然明顯強調的是地方政權與民眾斗爭的關系,并非直接強調民風因素,但以民性起筆,無疑證明了民性在民眾斗爭中的潛在影響。
由上可知,自晚清以來山西民眾性格較平原地區溫和確是事實。本節無意于討論各省民性之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僅就實際意義而言,山西民眾骨子里的溫和使其不善于組織自衛武裝或發動民變,缺乏“斗爭經驗”。民性是民眾行事方式的情感表現,深刻影響了區域內民眾的行為。不同的環境條件造就了不同區域間民性的分化與差異,塑造了民眾之間不同的行事邏輯。
三、地方權力與社會秩序:閻錫山對山西的維護
民初至抗戰前,山西聯莊會已不可見;全面抗戰爆發后,聯莊會的身影再次出現于山西大地。相較于自然等因素,山西聯莊會這一發展趨勢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因素的主導與影響。或者說,聯莊會的興起與政府的地方統治力有直接的關系。
(一)閻錫山的軍事組織
1917 年,閻錫山統攝山西軍政大權后,主管山西直到內戰結束之際。從整個民國戰爭環境來看,在閻錫山的經營下,抗戰之前山西境內并未受戰爭嚴重波及,即使是1930 年的中原大戰也并未直接影響到山西。但是深入分析,近代山西內部的社會環境之惡化程度并不遜于華北各省。以土匪為例,朱新繁提及山西土匪的情況時指出:“土匪之多,比之各省,有過之無不及。”⑤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及其特質》,南京:新生命書局,1930 年,第312 頁。有學者曾粗略統計過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國各省匪幫數量:

20 世紀20 年代各省匪幫的人數和規模(節錄)① [英]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40、41 頁。表中“最大匪幫的規模”,數字只是粗略的估計。
盡管各省的土匪統計數目皆不完整,而且相比之下,山西的土匪數量和規模遜于山東、河南兩省,但山西土匪的絕對數量亦是相當龐雜,且大匪幫的規模不亞于山東、河南兩省。
已知聯莊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家護院、防匪防盜”,而且近代山西的土匪數量并不亞于平原地區,那么為何山西沒能出現聯莊組織來抵御土匪?除了上述討論的自然因素,閻錫山的政治統治發揮了主要作用。
近代以來,閻錫山對山西的地方治安可謂是下了很大功夫,也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劉大鵬曾在其日記中站在地方民眾的立場上多次對閻錫山“保境安民”的成果做過良好的評價,“中國無亂之省,山西為第一”,“各省皆有亂事,土匪充斥,惟吾晉治安”,“晉民雖受苛政之虐,卻無兵匪之害,斯亦為亂世之大福矣”。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稿本),民國七年七月初一日、民國十年四月初一日、民國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山西省圖書館藏。雖然劉大鵬對山西的苛政抱有不滿情緒,但在劉大鵬看來,治安良好的山西成為了全國的一片凈土,是“亂世之大福”,百姓雖食不飽穿不暖,生活條件不僅沒能得到改善,反而因閻錫山參與軍閥混戰而日趨貧困,但不至于受到土匪所施加的生命財產威脅。據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中統計,山西土匪多集中于邊界地區,這一現象也從側面印證了近代山西社會治安的相對穩定。
土匪的抵御分政府主導和民眾自發兩種模式,且政府主導優先于民眾自發。民國以來山西方面的防匪策略以政府為主導,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采用軍隊鎮壓與戍守。劉大鵬在日記中記錄過山西官軍抵御土匪一事:
盧占魁糾眾數百,橫行晉北、歸化城一帶,奸淫焚掠,無所不為。初名獨立隊,陸軍至則散處山谷,退則任意滋擾,民受其害,已覺不堪。今春就撫,現又嘩變,改名為“靖國軍”,攻打包頭鎮等處,聲勢猖獗,銳不可當,將有窺我晉弊之消息。日來省城發兵向北,防杜北鄙之關隘。③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17 年12 月9 日),第233 頁。
盧占魁是民國時期晉北有名的匪首。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對土匪的描述雖然帶有傳統儒家的嫉惡色彩,但在土匪入侵與山西方面應對問題上所言不虛。當盧占魁僅僅是“窺我晉弊”而并非已經進入山西時,山西政府方面已經做了應對,“發兵向北”,而且次日就防匪一事進行了募兵:
募兵一役,各縣皆有省兵辦理,募集二三十人即送至省,湊成一營遂遣戍北,赴戍扼守晉北緊要關隘,防杜盧占魁之兵竄入晉北也。但所募之兵多系貧窮,恐不濟事耳。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17 年12 月10 日),第233 頁。
兵差的來源是分攤到各縣的,這顯示了山西政府對地方各縣的基本控制。這一情況在中原大戰前亦有體現。朱其華(即朱新繁)指出,1929 至1930 年山西負擔兵差數遍及山西各縣,共達105 個,而河南、山東等省份則出現兵差縣數小于總縣數的情況。②朱其華:《中國農村經濟的透視》,上海:中國研究書店,1936 年,第253 頁。僅從數據來看,閻錫山對山西的統治從形式上看頗為穩固。回到防匪一事,盡管政府方面通過募兵手段進行防匪,一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夕仍是如此③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6 年12 月10 日),第453 頁。,但劉大鵬從基層旁觀者的視角觀察到“所募之兵多系貧窮”的情況,因而對此事并不看好。而且劉還提到山西土匪受地形之便,“陸軍至則散處山谷,退則任意滋擾”。因此官兵防匪一事的效果恐并不太好。此外,由劉的記載可知,政府方面還曾對盧占魁進行過安撫,但最終由盧嘩變一事可知此法并無長效。
或許是鑒于政府方面防匪效果的不力,因此由政府主導組建地方自衛組織成為山西防匪的重要方式。這是第二種方式。為抵御匪兵騷擾、緝捕盜賊,20 世紀20 年代,山西省頒布《保衛團施行細則》《改訂地方保衛團施行細則》等條例,勒令各村建立保衛團,以加強民眾自御能力,達到“一村保住一村,一縣保住一縣”④《保衛團之需要》(1925 年3 月),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處編印:《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6 冊,1937 年,第31 頁。的設想。在地方上,1926 年偏關縣受災嚴重,匪軍侵擾,“所至各村無不劫掠一空,貧富無能幸免。惟老營堡南山一帶村民團結或壘石為人以俱敵,或塞路作險以阻匪,巡查會哨,前后獲敵九名,卒使匪眾畏不敢前……嗣后各村皆覺悟自衛之當急,雖集貧之民,亦無不樂于辦理保衛團。其請愿出資購買置槍械者,不下數十起……蓋重創之后,人人同有覺悟”⑤山西村政處編:《山西村政匯編》卷2《令文》,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214 頁。。1933 年12 月25 日,劉大鵬半夜夢醒時,聽聞西南方向有連綿槍聲,下意識認為是“盜賊放槍搶劫”,而后想到是保衛團丁放槍警夜,遂在日記中感嘆:“現在因世面不靖,村村皆設保衛團,每村有團丁十人、八人、五六人,晝夜在外梭巡,以防盜賊。”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3 年12 月25 日),第434 頁。制度推行與現實困境加快了保衛團的創設進度。截至1933 年,山西省全縣保衛團人數約54 萬人。⑦此數據統計自《山西民政刊要》(民國22 年),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 年,第225 ~242 頁。
抗戰爆發前,閻錫山為了“防共”曾組建“防共保衛團”再次動員民眾,時人稱“第二次之保衛團”⑧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6 年2 月21 日),第449 頁。,本質上依舊是保衛團政策之延續。保衛團是山西政府管轄下的鄉村自衛自治組織,其制度設計相對于20世紀30 年代后期國民政府普遍推行的保甲制來說,自治色彩明顯重于控制色彩。⑨劉娟:《民國山西村治研究》,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7 年。
(二)政治權力的基層滲透
閻錫山極為重視農村和農民問題,一心設法將散漫的山西民眾置于嚴密的組織之中。⑩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于抗戰爆發前后雙方在晉東南關系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1 期。對此,他在政治方面推行“村本政治”,實行編村制,擬組織全省民眾并加強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結果,須先從作極密之政治網起。鄙人現在亟亟于編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網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論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網能密到此處,方有政治之可言。”①《官吏必要之覺悟——應增添之新知識》,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處編印:《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1 冊,第83 頁。1922 年4 月,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滲透,山西在村一級實行了村—閭—鄰三級管理體制,進一步加密和下沉行政統治網。②董江愛:《山西編村制度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1 期。
1935 年,中共進入陜西建立革命根據地,同山西一河之隔。為防備中共向山西發展,閻錫山在政治上設立“主張公道團”,意圖通過“主張公道”思想,強化對民眾的規訓,以此加強對民眾的掌控。“主張公道團”并非是武力組織,其除了對“防共”進行政治宣傳外,還有檢舉消除地方不平的任務。《退想齋日記》載:“晉祠人及公道團控告黃總監修造別墅,侵占土地,黃總監因之拆毀所修之物,已經動工,予于昨日請暫停止,再行會議。”③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6 年8 月3 日),第451 頁。可見,“公道團”對消除地方不平一事具有一定效果。此外,“公道團”還對工人的權利進行過援助,幫助工人反廠長之壓迫。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6 年8 月25 日),第452 頁。“公道團”通過檢舉消除了一些社會不平,整頓了吏治,取得了部分民眾的擁護,在客觀上鞏固了閻錫山政府在地方上的統治。⑤關偉:《閻錫山特殊組織“主張公道團”的多面相》,《求索》2016 年第11 期。
據統計,截至1936 年,“主張公道團在總團部之下有縣團部105 個,村團部11152 個,團員1007094 人,團員都是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一下的青年”。⑥山西省主張公道團總部編印:《山西省主張公道團總團部訓練縣村干部人員紀念冊》,1936 年,第16 頁。“公道團”將大量的山西青年民眾牢牢地納入閻錫山的統治系統下,“如此山西省主張公道團如網狀在各地擴散,閻錫山一個人的意志通過百余萬團員宛如手足般地自由行動”。⑦關偉:《閻錫山特殊組織“主張公道團”的多面相》,《求索》2016 年第11 期,第161 頁。
(三)閻錫山的“排外”統治
國家與社會的疏離是社會動亂產生的重要原因。⑧[美]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增訂本),池子華、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譯者前言”,第8 頁。相反,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避免了社會動亂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衛組織的出現。除基層社會控制外,閻錫山政府時期的排外統治有效地避免了山西社會受到外力的侵擾,進而阻礙了山西聯莊的出現。閻錫山主政時期一直拒絕其他政治勢力進入山西。全面抗戰爆發前,除中共外,無論是各路軍閥還是國民黨中央勢力,抑或是日偽方面都未曾強行進入過山西。1935 年,日本發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欲強迫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獨立自治。閻錫山方面拒絕參與華北“自治”活動,反而應蔣之邀請南下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與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因此事對閻錫山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百川到京表示共赴國難之決心,其晚節自勵,殊為可慰。”⑨《蔣介石日記》(1935 年10 月26 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在日軍的壓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 年12 月18 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兩省實際置于中國行政區域之外。對此,蔣介石曾承認:“老實講,現在中央的權力已經不能在華北行使,事實上華北已經不是受中央統治的地方了!”⑩《論“政略”與“戰略”之運用》,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 卷,1984 年,第558 頁。轉引自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第1 卷《局部抗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343、344 頁。由此,兩省呈現出不同的命運走向,河北被日偽所滲透,山西則依舊掌握于閻錫山之手。
四、中共與閻錫山的合作根除了民眾自衛武裝出現的契機:特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訖至1935 年,陜甘革命根據地尚處于蔣介石武力“圍剿”的包圍之中。在1935 年擊退第三次“圍剿”后,東征山西成為毛澤東打破紅軍在陜甘根據地困境的首要策略。東征之后,中共在積極深入山西發展力量的同時,因整體局勢的變化,政策更加注重構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此同時,閻錫山鑒于抗戰復雜形勢,也認識到“日可抗,紅軍不可抗”,開始尋求同中共合作,以達到強化自身實力的目的。①王奇生:《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1 期。
1936 年9 月18 日,中共與閻錫山聯合領導的“犧牲救國同盟會”于太原成立,以“不作漢奸亡國奴的人們聯合起來”和“組織百萬民眾武裝”兩個口號開展抗日組織工作②石賓:《從犧盟會看山西民眾運動》,濟南:黃河出版社,1939 年,第13 頁。,并于12 月初組織1080 位“臨時村政協助員”③關于“臨時村政協助員”的人數有不同的記載,本文不重于此,在此不做贅述。下到鄉村開展抗日救國宣傳鼓動工作。主要有三個任務,其中兩個“一是廣泛地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二是宣傳犧盟會的綱領,建立基層組織,在全省發展一百萬會員”。經過為時3 個月的抗日宣傳工作,山西鄉村建立了眾多犧盟會組織,發展了60 余萬犧盟會員。④王生甫、任輝媛:《犧盟會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13、114、117 頁。閻錫山的“村政”措施與同中共的合作強化了抗戰爆發前山西基層社會的穩固,尤其是對鄉紳和富戶的管理,杜絕了其自我組織武裝的機會。
日軍開始全面侵華,河北首當其沖,山西亦岌岌可危。對此,中共、閻錫山雙方繼續以犧盟會為媒介深入農村,敦促民眾成立自衛組織。中共通過犧盟會組織,派遣黨員以犧盟會特派員的身份到各地加緊開展革命運動,穩定社會秩序,發展人民武裝,并在此基礎上建立黨組織。⑤《潞城早期革命活動的開展》,長治市政協文史處編印:《長治文史資料》第9 輯,1991 年,第82 頁。人民武裝以各城村的自衛隊為主。“自衛隊是由不脫離生產的民眾所組成的,是動員城鎮鄉村十六歲至四十歲的男女,依其住在地區有指揮系統地編為民軍”。⑥《抗日自衛隊三個基本任務》(1937 年12 月7 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三·地方武裝斗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28 頁。例如平順縣在犧盟會平順分會的倡導下成立人民武裝自衛隊。自衛隊初設兩個中隊,隊員300 人,兵源由各村選送。此時自衛隊的主要任務是防御匪患,維持社會治安⑦山西省《平順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順縣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 年,第265、266 頁。,穩定當地社會和民眾生活秩序的穩定。
1937 年8 月,閻錫山接受中共建議成立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連同犧盟會一起開展民運工作。根據晉冀區和薄一波的指示,決死隊將民運主力從知識分子轉變為青年農民。對此,決死二總隊立即組織干部和隊員成立民運工作隊,到黎城、襄垣、武鄉和榆社等縣發動群眾參軍,“只一個多月的功夫,就動員了大幾百青年……還組織了一個警衛部隊,成為不久以后建立的游擊大隊的基礎”。⑧《在犧盟會和決死隊工作的片段回憶》,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山西文史資料》第15 輯,1983 年,第107 頁。決死隊在犧盟會的幫助下得到了長足發展。至1939 年底,決死隊已發展成為9 個旅,轄50 個團,共計7 萬余人的抗日武裝,⑨《回憶山西新軍》,《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西新軍概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第353 頁。“變成了與閻錫山過去依賴的晉綏軍有明顯區別的一支山西‘新軍’”。⑩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于抗戰爆發前后雙方在晉東南關系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1 期。
為了組織動員山西淪陷區的民眾,1937 年9 月20 日閻共雙方聯合成立了以續范亭為主任委員,中共方面以鄧小平、彭雪楓等為代表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在“晉察綏戰地動員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回顧抗戰初期戰動總會的武裝斗爭》,《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西新軍概況》,第393 頁。。雙方以是否為淪陷區為劃分標準開展戰爭動員工作。戰動總會成立后,立即派出工作隊到雁北、晉西北、晉中等地區的38 個縣建立縣、區、村各級動員委員會,在民眾中開展動員工作。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發展游擊隊上,將“原有自衛隊中的好分子,吸收他們加入游擊隊,尚未成立自衛隊的縣份,便馬上改為發展游擊隊”。①《戰動總會一年半工作概述》(1939 年9 月),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總論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81 頁;《回顧抗戰初期戰動總會的武裝斗爭》,《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西新軍概況》,第395 頁。在很短的時間內,戰動總會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就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1938 年1 月,戰動總會直轄的抗日游擊武裝共25個支隊,計21000 余人。②《回顧抗戰初期戰動總會的武裝斗爭》,《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西新軍概況》,第396 頁。
1938 年6 月召開代表大會,重新將中心集中到自衛隊的發展工作,使之“負擔起放哨、檢查行人、破壞道路、偵察敵情、幫助實行堅壁清野以及幫助游擊隊、正規軍作戰的種種任務”。③《戰動總會一年半工作概述》(1939 年9 月),《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102、103 頁。在此之后,又承擔起將人民武裝自衛隊改編為抗敵自衛團的任務。④《戰動總會一年半工作概述》(1939 年9 月),《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108 頁。除上述外,戰動總會還承擔幫助落伍士兵歸隊,號召群眾回家、肅清土匪,開展群眾工作,組織農救會、青救會、婦女工作團等工作。⑤《戰動總會一年半工作概述》(1939 年9 月),《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86、101、102 頁。戰動總會的武裝自衛口號深得民心,根據晉西北14 個縣的統計,在戰動總會成立的短短半年里,“自衛隊就發展到65000 多人”,甚至兩年內在晉西北還動員了7 萬多人參軍抗日。⑥《回顧抗戰初期戰動總會的武裝斗爭》,《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西新軍概況》,第401、402 頁。戰動總會的一系列動員舉措促進了山西社會的穩定和民眾動員工作持續推進,為穩定民眾和抗戰的順利進行提供了組織上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是,犧盟會、決死隊等組織短時間內動員民眾工作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犧盟會領導人早期對統戰工作的簡單認識和粗略開展導致民眾空有組織架構,缺乏對抗戰嚴酷性的深刻認識。以至于日軍侵入晉南時,“犧盟會工作完全暴露了是空架子,決死隊雖然打過不少小仗,但未能‘如八路軍活躍’(所謂不是‘有聲有色’),且有些不打自散(如十一總隊)”⑦《楊尚昆關于晉西南黨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況向劉少奇的報告》(1938 年6 月3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第104、105 頁。。由此可見,雖然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山西的統戰活動廣泛深入農村,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尚有不足之處。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同閻錫山聯合抗日,共同領導犧盟會、決死隊和戰動總會進行民眾動員和統戰工作,第一時間將民眾置于雙方共同領導的官方抗日組織之下。盡管這一戰線形成之初的工作難免存有缺陷,但總體來看,這一舉措使得山西民眾成為軍隊抗日的重要力量來源,并杜絕了民間自衛武裝出現的契機。
五、結論
華北各省受晚清地方自治與興辦團練風潮的影響,都曾出現過程度不一的團練組織。在河南、河北等平原省份,受多種因素影響,團練組織相互聯合演變為聯莊會,成為地方民眾發動叛亂、抗糧抗差的重要角色。民國以后,隨著地方近代化進程的推進,地方自治進一步深化,社會環境因災害、軍閥混戰導致的的間歇性惡劣,華北平原各省的聯莊傳統得以保留與延續。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書中以紅槍會為例分析了淮北地區地方自衛武裝的歷史發展態勢,通過生態史的角度解釋了淮北地區為何經常發生農民叛亂這一問題。惡劣的自然環境、緊缺的社會資源、長期戰亂與地方政府統治力薄弱等因素共同塑造出民眾自衛組織這一地方性歷史圖景。抗戰爆發后,在日軍侵華這一背景之下,包括淮北地區在內的華北各地都出現了較多數量的以聯莊會、紅槍會為代表的民眾自衛組織,而山西截然相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聯莊自衛組織,是為抗戰背景下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
聯莊會作為平原地區的季節性自衛組織,抗戰初期廣泛出現于華北平原各省,在山西省內則呈現出一種“貧瘠”的狀態。究其原因,地形的復雜和地理位置的邊緣化是山西聯莊勢力薄弱的先天性因素。不同于冀魯豫地區長久以來的彪悍民風與習拳結社的傳統,山西民眾的溫和性格間接影響了民眾大規模的“聯莊”自衛行為。政治方面,近代以來,閻錫山秉持“保境安民”和“村本政治”的施政理念,借助以自衛團、編村制等基層軍事組織與政治制度牢牢地將山西民眾納入自身的統治與管理之中。抗戰爆發后,進入山西的中共方面同閻錫山聯合抗日,以犧盟會、決死隊和戰動總會等組織組成特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于第一時間將山西民眾“組織起來”,使其納入閻共領導下的官方抗日組織。基于以上眾因素的綜合,抗戰時期的山西民眾得以迅速且組織化地投入到抗戰中去,而并非像華北平原各省民眾一般經歷通過聯莊會等民眾自衛組織來保家抗敵的松散的斗爭過程。
進而言之,同華北平原大規模聯莊自衛組織的盛行相比,聯莊會在山西近乎“消失”的狀態反映出抗戰初期同為華北地區的山西和平原各省抗戰形勢的不同。聯莊會作為社會動亂的“預警器”,反映著社會秩序的惡化程度。其在山西的“寥若晨星”的態勢反向證明了抗戰爆發后山西社會秩序處于相較穩定的狀態。
同華北平原地方社會的混亂失序相比,山西省的抗戰統戰工作進行的井然有序,直到全面抗戰開始,在山西以聯莊會為代表的民間自衛武裝始終未能大規模出現。民眾層面的抗戰活動直接從閻錫山的統轄過渡到由中共、閻錫山雙方組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之中,始終依附于地方政府的指揮下,為官方抗日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員輸送,并為山西塑造了穩定的抗日社會環境,加快了中共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全面抗戰爆發后基于穩定的社會秩序與官方組織動員工作的迅速開展,山西呈現出與華北平原各省相比更為井然有序的政治與抗戰局勢,山西在抗戰初期華北戰場的中流砥柱作用得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