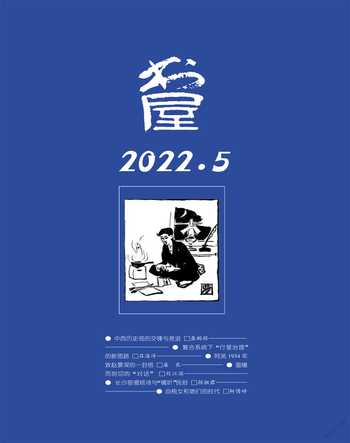自梳女和她們的時代
柯倩婷
順德騰沖鄉,有何翁者,家頗小康,有子年二十,娶某氏女為妻。孰知女子嫁后,數年不落家,何翁抱孫心切,因翁誕辰,女不得已到家慶賀,何翁遂與子謀,強留之不許返婆家。女抵死不從,何并將女子與鎖禁房內,不料女子于更深時懸梁縊死。女家謂翁父子謀死其女,糾纏官署,卒判何翁賠償五百金作了。
這一則刊載在1929年的《廣州共和報》的故事頗具代表性。女子結婚后不落夫家的風俗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持續了幾百年,翻閱珠三角各地的縣志、風俗考、文人筆記,不落夫家的習俗引起不少爭端和爭議,但習俗根深蒂固,且促使自梳儀式的出現。
不落家的第一步是新娘拒絕與丈夫同房。因為一旦同房就算是認可了婚姻,若再懷孕,就必須到夫家生活了。弱勢的古代女子如何能夠拒絕婚姻生活呢?她們大抵依靠的是娘家的支持和姐妹團體的力量。要對抗夫家的落家要求,起碼家人和族人不極力反對,她們才能成事。婚姻通常是家長訂下的,但婚后女兒回門即不再到夫家,若無父母家人支持,必難以持續。而父母或疼愛女兒,不愿讓女兒過早到婆家操勞;或需要勞動力,希望女兒在家里幫手。
姐妹支持的力量也很重要。金蘭姐妹聯合起來,相約不嫁,協助彼此逃避婚姻。如果有姐妹被父母逼婚,無奈成親,她們也要求結婚的姐妹不與丈夫同房。她們的團體有檢查、監督的職能。胡樸安記載:“女子嫁期有日(粵語謂之知日),必召集一群女子(粵謂之花枝群),作秦庭七日之哭,如喪考妣,其金蘭友亦在焉。臨過門之夕,嫁者必被帶束縛,其狀若死尸之將入殮,復飽喂以白果等物,使小便非常收縮。及歸寧后,其蘭友必親自相驗,若其束縛之物稍有移動,是為失節,群皆恥之,其女必受辱不堪。”一般歸寧是婚禮后第三天,算來起碼兩整天不能上廁所,這對新娘的意志已是挑戰。此外,她在夫家還要應對眾人勸飲食,并拒絕丈夫的要求。可以推想,新娘在這幾天如果沒有強烈的抗婚意識,是很難堅持的。歸寧之日,姐妹們會嚴格檢查,如果發現衣服打開了,會受到嘲笑,被排斥,甚至受到打罵、責罰。金蘭契、姐妹會是支持的力量,也是規訓的力量。
歸寧之后,女方以各種借口留在娘家,拒絕到夫家生活,一拖三五年是尋常,十幾二十年的也有。學者們通常的解釋是,女方逃避作為媳婦的辛勞和凄苦,自梳女接受采訪時也常常這樣解釋。但即使嫁到中上等人家,有仆人可使,也會拒絕落家,如開頭引述的故事中,何家是小康之家,女方也不愿落家。這些女子抗拒的是婚姻,而不是婚姻生活的艱辛。面對妻子不落家,丈夫家通常不會坐視不管,比較溫和的是以長輩生病為由,請媳婦回門,但媳婦知道是借口,就以要給姐妹送嫁為由拒絕。俗語云:“家婆多病痛,新婦多嫁送。”其實,家婆沒病痛,新婦也沒嫁送,都是借口。也有些夫家候著女方出門時搶回家,有些則“誘捕”。《越華報》就有“話劇”描繪“誘捕”的場景:一男子清明回鄉掃墓,派人告妻子家人,說丈夫在船上中痰而死,請妻子去哭喪,妻子上船,向披麻蒙面的“尸體”哀哭盡禮,麻布下的人突然坐起,女子大驚,知道受騙,但船已經離岸,只能隨丈夫回家。這樣的“巧智”故事,多有所聞。
逢年過節或重要日子,女方需要回夫家,這是禮數。何家就借何翁生日之機,設計強留、囚禁媳婦。不少夫家認為,婚姻已經締結,既然占著道理,便悍然采取強硬措施。然而,這樣往往導致兩敗俱傷,因為不落夫家的女子多抱持貞烈觀念,寧死不與男子親近。為此,官府也不得不經常處理這些訴訟,然而,不管官府怎么判,都難以平民憤。何翁與兒子預謀強留并監禁,導致媳婦自殺,只需要賠償五百金,女方會認為不公正,而何家又何嘗不是人財兩失?此外,一旦出了人命,結金蘭的姐妹們會結伴到夫家興師問罪,俗稱“鬧人命”。不落家風俗導致傷亡和沖突,官府遂采取各種方式來改變習俗。
官府常常四處張貼告示,聲明禁止女子結拜金蘭和不落家。一些文人士紳撰文抨擊,道光年間,曾在廣東任職的翁心存批評道:“粵東地方,地處邊隅,尤失交道……其女子以生死相要,亦有十姊妹之拜。維爾生童,固不容有此敗類。”番禺一名鄉紳頡云公,與鄉民聯名為丈夫一方打抱不平,要求認定抗婚的女子自殺死亡,夫家無須承擔責任。然而,官府卻難以簡單地判定夫家無須承擔責任,怕夫家仗著法律而逼迫過甚。當然,也有嚴厲的地方官。例如,順德知縣李沄就出臺“若女子以死抗婚,夫家免責”的法律。《順德縣志》記載他的嚴苛法令:“自是凡有訴者,亟逮其父兄至,墨涂其面以辱之,不以門第恕也。一時民俗警動,以被迫橫死告,遽令殮埋不詣驗。婦女知徒死無益,三十余年來,不復有自棄其生者。”李沄是浙江人,于嘉慶十八年(1813)任順德知縣,從外地調任來,對順德習俗缺乏了解與同情,或是他采用強硬手段來治理的原因。而且,這縣志的記錄有為李沄歌功頌德之嫌。黃芝就提到,官府的干涉導致更多女子以死相抗:“此等弊習,南〔海〕、順〔德〕兩邑鄉村居多。昔賢縣令曾禁之,眾女聞知,以為閨閣私事揚之公庭,殊覺可恥,一時相約自盡無算,弛其禁乃已。”不落家習俗已成,行政手段也難以革除。
問題是,女子何以要以死來抵抗婚姻呢?學者通常認為,是貞潔觀念和嚴苛的父權制婚姻所致。民國初年番禺鄔慶時曾談道:“鄉間婦女視貞潔二字最重,足稱節婦、烈婦、貞女者,隨處有之。間有過激者,因不愿與夫同室,或仰藥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積蓄為夫置妾。視居室為大辱,等生命于鴻毛。”胡樸安也提及番禺的不落家習俗中的過激行為:“因不愿與夫同室,或仰藥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積蓄為夫立妾者,視男女同室為大辱,等生命于鴻毛。”這些文字相似,都認為是貞節導致她們不愿落家。
然而,貞節的道德要求未必導致不落夫家和金蘭契。例如,貞節禮教嚴苛得多的地域如安徽、河南、西安都沒有這些風俗。反倒可以說,是女子借著貞節的名義來爭取不落夫家,借以延續、鞏固不落夫家這一習俗。當社會標舉貞節,警戒女子成親前不要接近男子,女子就可能以貞節為名,拒絕結婚或婚后的親密生活。
不落家與金蘭契相互依仗,成為主流婚姻制度里的另類形式。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結婚而不落家,即推遲進入實際的婚姻生活,是女子爭取到的一些時間與空間。到了晚清,自梳儀式興起后,不落家和金蘭契依然存在,并延續到民國末期,可見其扎根之深。可以說,沒有不落家和金蘭契的習俗基礎,自梳儀式不可能成為那么普遍的實踐。
較早的自梳女記載見于張心泰的筆記,那是同光年間:“若婢女不愿嫁,積資自贖開臉傭工者,廣俗謂之自梳妹,實為物色尚未有屬也。”這個記錄的意思是,廣東風俗,未嫁女留辮不梳頭。自梳,就是女子請人將頭發由辮式改梳為髻式,以示決志不嫁。
然而,那時華南地區的婚姻制度有很多規則要遵守,例如不能“阻頭”“跨頭”。所謂“阻頭”,即兄姐不婚娶致誤弟妹之婚期者;所謂“跨頭”,即弟妹嫁娶先于兄姐者。“阻頭”和“跨頭”多為世人所惡,“阻頭不便,跨頭不祥”。所以,家中女兒成年后,還不想出嫁或還沒找到意中人,但又不想耽誤弟妹的婚事,自梳即兩便,因為梳起就相當于出嫁,弟妹結婚也不算“跨頭”了。也有些因為兄長未娶,妹不能“跨頭”出嫁,等到兄長結婚后,自己年歲也大了,嫁人不容易而自梳。咸豐三年《順德縣志》載:“男女婚嫁又多愆期,蓋欲循長幼之序而遞及之,如諸兄諸姊或因姻家有喪服事,故不得嫁娶,弟妹雖年長亦必俟之。”婚禮擇日有諸多禁忌,男女一方家中有喪事,年內都不宜辦喜事,這些客觀事件也會造成“阻頭”。
再者,有的女子因為父母早喪或體弱,弟妹年幼,而決意梳起,協助家計。在這些情況下,女兒承擔起兒子的責任。明萬歷十三年《順德縣志》載:“鄧六娘者,宋上舍鄧夢槐女也。夢槐生子伯瑜,早卒。有女六人,六娘最小,嘆曰:‘父無宗屬可后矣。’矢不適人,乃取姊子李元為其父后,改名履元。”這位鄧六娘不是招上門女婿,而是留在家中,把姐姐的兒子過繼來作為宗屬的后代。番禺東北部的大嶺古村則有“姑嫂廟”,是紀念陳氏一位姑婆和她的寡嫂,這位叫“娃姐”的姑婆知書達理,由于母親早逝,她為了照顧年幼的弟弟而終身不嫁,侍奉老父,為陳氏宗族延續香火。可見,一些女性是為了家族的利益而放棄婚嫁。
更普遍的不婚是為了幫補家庭的勞動力和經濟收入。自梳女爭取到不婚的自由,既能于鄉間務農,也可以靈活地選擇工作。早期的自梳女主要做女傭,繅絲廠發展起來之后,她們成為絲廠最受歡迎的女工。宣統三年《南海縣志》卷二十六曾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機器繅絲創于簡村堡:“每間絲偈大者女工六七百位,小者亦二三百位……三四年間,南、順兩邑相繼起者多至百數十家。”這些工廠招收大量女工,有些女工一人收入即可維持一家生活。機器繅絲的產業促使更多女性梳起不嫁,絲廠更樂意招募單身女工,當時工廠有所謂“三不請”規矩,“已婚不請、有仔不請、訂婚不請”,自梳女自然最受歡迎。
這樣的盛況持續了半個世紀,直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由于國際市場絲價猛跌,珠三角地區的繅絲業受到了重創,“約四分之三的絲廠倒閉,三點六萬絲業工人失業”,從此一蹶不振。那時候的報紙充斥著悲觀情緒,對自梳女的遭遇落井下石,片面報道自梳女如何急于嫁人,從標題即可見一斑:《自梳女廉至無價》《自梳女減價平沽》《自梳風氣日減的原因:生活逼人,難善其身》《漸歸消滅之鳳城女子陋習:環境壓迫,打破了自梳夢》。事實上,很多繅絲女工轉入家政行業,當起了媽姐或梳傭。自梳女需要獨立謀生,生存的緊迫感促使她們到廣州、香港、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經濟更發達的地方求職,而不是改志出嫁。
自梳女在廣州主要是做梳傭,類似于私家美發師,以滿足那些雇主的時尚與社交需求。較粗重的工作是做奶媽和幫廚。到東南亞工作的女工也通常能夠到上層社會的家庭打工,她們自律、專業的精神以及可以持久工作的身份,使她們更容易得到雇主的信賴。以新加坡為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新加坡男多女少,女性傭工工資不菲。然而,也由于性別比例失調,一些女性被引誘去做性工作。為了避免這樣的陷阱,很多女性在出洋之前就梳起,或者到新加坡之后加入自梳女團體,從中得到照顧、保護和歸屬感。
很多自梳女十來歲外出工作,常年支持父母、兄弟乃至侄輩的生計。從米面糧食、日用品到建房資金、做生意的成本、學費等大項支出,自梳女都盡其所能。“特別是遇到水旱天災,農業歉收時,無論家庭開支、地租交納,都要靠她們來支持。”紀錄片《自梳女》中,東莞的自梳女倫松勝十幾歲到新加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回國時帶回二十萬元,支持侄兒做生意。也有自梳女支持哥哥建房子,為侄輩供書教學,并不計較回報。如《自梳女贊》寫道:“農家散腳聰慧妹,梳起勤儉為后輩。青春獻與家計事,碌碌操勞不知悔。勿論漂洋留鄉居,振作奮發志無回。英雌豪氣賽男兒,諄諄精神真純粹。”自梳女普遍認為自己對父母的家庭負有責任,她們心理上與原生家庭是一家人,不分彼此。
工作的經歷也塑造了自梳女的社群意識。自梳女到外地工作,會結成團體,相互幫助,她們在新加坡等地的姑婆屋,往往是集體租賃或購買。姑婆屋也接待其他姐妹,逢年過節一起拜祭、休閑,像親戚一般往來。例如,冰玉堂約定:“該堂建成后,凡本鄉旅外姐妹回到家鄉,沒有依托或不想與兄弟子侄同居的,可申請入住,不收費用……”該堂建成后,入住最高峰時曾達三十多人,設有大飯堂。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出資的自梳女,也可以申請入住,這就使得冰玉堂具有公益性質。可見發起者有社群意識和前瞻性,她們不僅為自己籌建未來的居所,也為其他姐妹提供住宿與活動場所。自梳女的親友關系,很大程度超越了血緣維系的家庭形式。此外,她們以自梳女的身份做善事,為家鄉捐資捐物,抗日時期更是出錢出力:“聞近以寇難日深,該處自梳女子愛集同人,發起捐資救國,并協力組織救護隊,擔任救護事宜,以盡國民天職。”她們主動請當地醫生傳授救護知識,以備家鄉戰事所需。
自梳女以梳起的形式,得以獨立于婚姻之外,不必像不落家的女性那樣與夫家進行各種拉鋸戰。梳起是嚴格的婚姻制度下的靈活形式,它以契約形式爭取到新的身份,使得不婚的女性可以獨立謀生,持續與原生家庭的關系,并尋找替代的方式來處理生活、親情、歸屬、身后事等諸種關乎生存與人生意義的問題。
珠三角鄉間習俗,逢年過節,已婚或已梳起的女子不能在父母家居住。不落家女子有婚姻作為屏障,節期到夫家住幾天,死后葬在夫家的墳墓,沒有后顧之憂。自梳女則除了要解決日常的住宿,還要規劃死后的歸宿,這就有了姑婆屋。為了與父母家區分開來,建造姑婆屋的選址一般是在村外。
自梳女外出打工,經濟獨立,也為自梳女外出居住提供了條件,一些絲廠女工在廠區附近或合適的地方租房住,獨租或合租。也有自梳女添置物業,出租給有需要的自梳女。《自梳女與不落家》所言,“居住在姑婆屋的自梳及不落家婦女,除在生計上相互提攜以外,在生活上亦互相關懷”。生有所居,死有所祭,姑婆屋因應需求,功能逐漸完善,具有居住、親密情感庇護、宗教信仰、死后放置牌位等功能。
以冰玉堂為例,它由旅居海外的自梳女合資建造,各方面考慮周到,可謂姑婆屋的典范。冰玉堂是一座兩層樓房建筑。一樓是廳堂和神殿,廳堂可作聚會、聚餐、休閑之用,神殿內供奉著觀音、關帝以及已去世的姑太的神主牌。二樓以前是姑太們的臥室(現在用作自梳女文化展示廳)。前面還有庭院,側面有廚房。這些房屋布置使得自梳女可以在這里生活、休閑、拜祭,舉辦各種儀式。如早年的報紙記載,自梳女們“居于是,食于是,終于是,不須依賴父母,具有獨立性質,此等屋中,有若旅店,房榻繁列,群雌粥粥,歌談玩笑,通宵達旦,其樂何極”。姑婆屋里的姐妹們儼然一家人。
自梳女一起生活,難免會有親密伴侶產生,她們類似上契姐妹,情感濃烈,肌膚相親。胡樸安記載:“二女同居,雖不能具有男女之形式,實具有男女之樂趣。”《廣東婦女風俗及民歌一斑》記載:“當女子成年的時候,她們結了幾個‘相知’……而且立誓后的她們,就儼然夫妻一般,食、住、睡、游玩都必在一處的。”詩文《十二時辰》描述她們的愜意生活:“記得與娘游月下,或吟或詠共同夸。清閑無事問枝瑤仙卦,吹枝橫笛弄琵琶。個晚與娘花下灑,賞完花景又烹茶。”《夜諫金蘭》描述她們的恩愛:“日與同裙言笑語,夜來同睡一張床。悠游快活無拘束,勝過池邊寶鴨一雙。”濃烈的情感往往是獨占而排他的,若有一方破約,就會遭到糾纏、攻擊。《五想同心》嘆道:“指望多嬌存正性,聽耷人講話爾敗壞堅貞……爾咁樣立心神吟報應,故此新交朋友總契唔成!”這首方言歌的意思是,你既然不守貞節背叛我,就別想結交新朋友。為報復而打鬧的現象也偶有所聞。
姑婆屋里最熱鬧的是舉行自梳儀式。立志自梳的女子擇定日期之后,提前一晚到姑婆屋住下,用黃皮葉煮水沐浴,與自梳女們聊天,聽取誡命,熟習規矩。吉日的凌晨早早起來,拜過觀音,回到姑婆屋等候梳起時辰。關祥曾記:“‘自梳’的儀式是非常隆重的,親友和相好的姐妹都來祝賀,其熱鬧程度與正式結婚無異。自梳的少女穿起華麗的衣裙,先祭告天地祖宗,然后自己對鏡親手把辮子盤起來,梳成髻子,簪花鳴炮,再一次拜祭天地祖宗,隨后請親友吃一頓飯。”梁應沅、羅永安介紹順德的自梳儀式:“要擇定吉日良辰,邀集親朋觀禮。到時,燃點香燭,禱告神靈祖宗,特請‘從嫁’替自梳者裝飾打扮,當著神靈前梳起大髻,然后向神靈祖宗及父母尊長獻茶及接受親朋祝賀,最后燃放鞭炮,入席飲宴。至此,禮節完成了,也即是說從此成為合法的自梳女了。”自梳等于是宣告了一個新身份的誕生,這個身份使得女子可以獨立生活,而不受家庭和鄉親歧視、排擠。她們像已婚人士一樣,有了成年人所具有的自主權。
自梳女信仰佛教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教派。例如,她們拜觀音、天后,也過七夕節,姑婆屋的佛堂供奉阿彌陀佛、菩薩、道教諸神、濟公、關公、財神等。冰玉堂后來在附近加建了華帝廟,肇慶的觀音堂設有佛堂。然而,宗教解決了自梳女的精神信仰問題,卻并未能夠解決身后事。死后安葬在哪里?牌位在哪里?誰為你祭祀?為此,自梳女租用佛堂或籌建姑婆屋來解決牌位的安放問題。一般而言,姑婆屋有放置牌位的專門廳堂。在冰玉堂,自梳女的名字牌掛在廳堂的墻上,健在的用紅布蒙著,死后有人為她們揭去紅布。肇慶的觀音堂設有祖堂,用于祭祀先人、停放離世的自梳女,祖堂的后壁設有三級靈臺,中央供奉肇慶自梳女們的師祖何妙乜和歷代自梳女“老大”的牌位,左右座即放置已故自梳女的牌位。
為了解決安葬的問題,一些自梳女沿用“不落家”的守清、買門口等習俗,通過靈活的形式婚姻來解決這個問題。買門口原本是不落家女子的妥協方式,付錢給夫家納妾,女子依舊是正妻,但不回去居住,只在病危時才到夫家,殯葬開支均由女方支付,女方只需要夫家的墓地。若丈夫先死,女子回婆家主持家務,是守清;若訂婚后未辦婚禮男方死亡,女方亦要守清,即俗稱的守活寡。康有為所言:“守寡不已,則有守清;守清不已,則有代清者,余鄉比比皆然。”意思是,要嚴守風俗,反而逼迫人們想出各種替代的辦法,如代清、買門口等。在當代喪葬風俗改革之前,自梳女不能安葬在父母家,為了尋求墓地,有些自梳女與未婚死亡的男子舉辦個形式婚姻,以獲得安葬之地,類似于冥婚。自梳女的遺產可以給男方,也可以留給自己擇繼的自梳女,并由繼女來主持自己的喪葬。
沒有夫家,生養死葬的事務又不能由父母家人承擔,自梳女社群就需要承擔起來。這就促使自梳女擇繼,以便獲得更親密的后輩為自己送終善后。關于擇繼,梁應沅、羅永安記道:“每個自梳女年紀老了,都選擇年輕的自梳女作下代接班人。擇繼儀式是十分隆重的,必須選擇吉日良時,邀齊親友,當眾介紹自己的繼承人。繼承人要置備表示吉祥的豐盛禮物,作為認親的孝敬。入門時,屋內燃起香燭,大放鞭炮,繼承人先祭告神靈祖先,然后叩見‘親娘’及至親長輩。所謂‘親娘’,就是擇繼人;所謂至親長輩,就是擇繼人的金蘭姐妹。叩見完畢,繼承人照例接受‘親娘’的紅封包……最后自然是大排筵席,宴請親朋。以后擇繼人與繼承人就母女相稱,共同生活。繼承人對擇繼人負生養死葬責任,享繼承遺產權利,這是當時社會所公認合法的。”擇繼的儀式作為補充,使得自梳女更接近已婚女性,她們借此獲得為人母的身份,并贏得尊敬,提升其社會地位。
自梳女在嚴格的宗族文化制度中尋找到一個裂縫,爭取到獨立的空間,也付出相應的代價。她們因襲不落家、金蘭契的風俗及其所堅守的貞節,立誓不嫁,不近男人。她們獨立謀生,承擔家庭生計,獨自安排身后事。她們既獨立特行,又遵守地方的風俗習慣。一些學者尋找自梳女習俗的原因,分別提出是母系社會遺風、守貞節、逃避婚姻壓迫,都難以充分解釋自梳習俗的成因。應該說是傳統地方習俗、宗教信仰、貞節規范、婚姻禁忌、經濟文化等各種要素相互激發,使得珠三角逐漸發展出自梳的儀式,而不是單一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