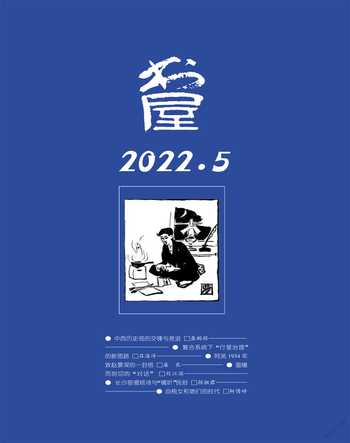抗戰時期重慶的粵菜館
周松芳
抗戰時期,國統區有一句流行的名諺,叫“前方吃緊,后方緊吃”,也就是說前方在打仗,緊張得要死,士兵衣食都無著,國民黨官僚則在后方歌舞升平,大肆吃喝。這是有事實根據的,尤以重慶最為典型。
一
1943年7月28日,卸任駐美大使尚未歸國的胡適在日記中說:“費孝通教授來談,他談及國內民生狀況,及軍隊之苦況,使我嘆息。他說,他的村子里就有軍隊,故知其詳情。每人每日可領二十四兩米,但總不夠額;每月三十五元,買柴都不夠,何況買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紀律那〔哪〕能不壞?他說,社會與政府仍不把兵士作人看待!”著名社會學家陳達寫于1945年1月28日的一篇文章更寫到士兵餓死的情形:“由廣西柳州運兵入云南,曾派某軍官押運,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里許黃土鋪住宿,該地保長負招待之責,據其自述,一路餓死或病死的兵頗多。押運官到昆明市后,即向負責機關領糧,但減價出售款歸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飯,難得一飽。士兵夜間許多人共宿一房,無床和被,少數人能坐,多數人站立。次晨開門,有人依墻而死。過此往楚雄交兵,據估計自廣西柳州至交兵地點,死亡的士兵約占一半。”士兵的這種慘狀,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早有親錄,1941年6月5日,他自重慶乘船去瀘州途中,看見“房門外兵士坐臥滿地,出入幾無插足之處,且多顯病態,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瘡,四肢頭頸皆可見到,坐立之時遍身搔抓。對此情景,殊覺國家待此輩亦太輕忽,故不敢有憎厭之心,轉為憐惜矣”。梅貽琦等旅客“船上三餐皆為米飯,四盤素菜,略有肉丁點綴”,但“兵士早九點吃米飯一頓(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門外有二兵以水沖辣椒末飲之,至天夕又各食萬金油少許,用水送下。豈因肚中餓得慌而誤以為發痧耶”。
至于后方的緊吃,雖然蔣介石開展新生活運動及給酒席限價,且本人平日只喝白開水,生活也可謂儉樸,但自鄶以下,無復論矣。從國民政府行政院負責總務及人事的參事陳克文先生的日記中,我們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證。他上通行政院長甚至蔣介石,下及很窮困的公務人員,所見所聞,自然堪為典型。比如1938年8月19日他在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處吃飯喝法國紅酒,自覺有些過分,但也認為不算啥,因為奢靡之風遍及重慶:“重慶有名廚‘姑姑筵(系商標之名)者,筵席費因受節約運動之限制,僅取八元,惟另取酬勞金:登門卅元,出門城內六十元,城外二百元,迎者仍不絕,可謂豪矣。”以至于“汪先生聞此,對目前之節約運動,深致懷疑”。
其實焉用懷疑,行政院長孔祥熙一直就在帶頭搞奢靡之風,而且一直主動違反新生活運動之規定。早在南京做行政院副院長時期,一次(1937年11月4日晚)各部會長官歡宴他,那奢華氣派就讓陳克文瞠目:“主人十五人,客一人,共費一百九十余元,僅煙酒一項便是五十元左右。富人一席宴,窮人半年糧,真不虛語。際此國難萬分吃緊,前方浴血搏戰,國土日蹙之時,最高長官對于宴會所費,仍毫不吝惜,無一不以最上等者為標準,亦可嘆也。”到了重慶,做了院長,雖然遵令制定了一些生活規則,比如行政院不宴請參政員,但別人不敢請,孔院長卻親自來請,而且親自安排大超規格事宜,“(1938年10月27日)孔院長忽然要宴請參政員駐會委員”,仍宴必求奢,“新生活運動規定每桌八元,我們可以要每桌十二元的”,“事實上庶務科定的菜饌每桌還是十六元的”,超了一倍。又有一次(1940年1月12日)請行政院各部會的部次長、委員長、副委員長到嘉陵江畔山上新落成的外賓招待所吃晚飯,吃得在座的許多人都大發感慨:“有些人望望堂皇的飯堂氣象,望望豐富的肴饌和不可多得的黃色牛油,很有感慨的〔地〕說,到底我們中國偉大,打了兩年多的仗,居然還可以建造這樣的新式建筑,居然還有這樣講究的西菜可吃,英法和德國打仗還不到半年,已經要計口授糧了。”中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的奠基人李先聞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受農林部派遣赴美接受善后復員訓練,則以親身經歷描述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情形:“初去美時,吃得尚稱無限制。整塊牛排,有二寸厚,半尺見方,館子里都可買得到。但到1945年春天,到館子就只能買碎牛肉餅和雞雜了。好的部分都送到前線給士兵享受……”1945年6月回川以后,見在成都的世家豪族還大魚大肉,“歌舞升平,酣醉通宵,哪像戰事正殷景象”。
當然,假公濟私是常有的。孔祥熙有多少私人宴請是假公之名?“(1940年4月13日)核了一批院長機密費開支的賬目。孔院長請客的開銷最大,每個月總在二三千元,每一次請客每桌筵費多者七八十元,少亦四五十元,水果煙酒還不在內。今日接到國防委員會蔣委員長的命令,限制公務員宴會:此后非機關核準,認為公務上必要者,不許宴客;經核準的,每客所費亦不得超過二元五角。將來各機關和公務員是否能切實奉行自然很成疑問,長官如不能以身作則,更行不通。孔院長這種請客能受限制嗎?我想決不會有所變更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許多法令之所以行不通,這也是一個原因。”如此“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使孔祥熙遭到了社會部長谷正綱的公然譏刺:“(1943年5月27日)本星期二院會席上,提到公務員生活補助費事,孔院長說,公務員生活困苦,余所深悉,但國庫負擔過重,一時想不出好辦法;社會部長谷正綱說,安得無辦法,有錢的人多出些錢可矣,還說了些其他的話。所謂有錢的人,其意即指孔院長。孔含怒說:‘谷部長你常在外罵孔某人有錢,革命黨并不是人人皆系窮光蛋,有錢人參加革命的也不少,孔某人并不是參加革命之后才做生意賺錢的。你一言,我一語,形勢殊嚴重。此殆半年來院會之最可記錄之一事矣。”真可謂貽笑大方的丑聞了。
他們那些小公務員有多苦呢?陳克文日記中也寫道:“(1940年11月7日)經濟部的人說,某科員子女五六人,只能用鹽拌飯吃,買不起蔬菜,更買不起肉類。”“(1943年1月17日)唐文爵從青木關來,訴說物價高漲,生活困苦。看他消瘦如野鶴,公務員的苦狀已畢露無遺矣。”且不說這些小公務員,即便清廉的高官,也同樣是清苦的: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日常生活主要靠“每三個月分配到面粉一袋,每一個月分配到菜油七十二兩,都不足用”,“她(蔣廷黻夫人)的幼子四寶患肺炎初愈,勸她買點豬肝給他吃。她說,價錢太貴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在陳克文日記中也有所反映。比如1939年4月7日:“徐公肅邀晚飯于飛來寺外交賓館,客人有《中央日報》的社長程滄波,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總編輯陳博生,此外為鑄秋、公琰和初次見面的朋友,共十一人。餐是每客兩元的西菜,酒卻是每瓶五十元的洋酒白蘭地。白蘭地喝了一瓶半,差不多一百元。酒是外國來的,牛油也是飛機從香港帶來的。在這時候我們居然能夠喝到洋酒和﹝吃到﹞香港的牛油,不能不說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這些東西自然是為外賓預備的,我們不過揩油而已。但問良心總是不安的。”這是抗戰初期的公宴。及至抗戰后期的私宴,也同樣追求豪奢:“(1944年5月24日)鄭道儒假鑄秋寓請吃晚飯,席中均系行政院同事。廚子是有名的顧家廚(顧祝同的廚子),菜品有蝦蟹、青魚、鰍魚、田雞,都是目前不容﹝易﹞得的珍饈,耗費總在一萬元以上。公務員生活雖苦,這種宴會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享受的。”而與粵菜有關的則是:“(1940年11月19日)曾養甫和甘乃光請我和之邁到他們那里吃乳豬。曾養甫自詡他的廚子是一個數一數二的能手。菜確很不錯,難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說乳豬只不過幾元的價值,可是燒烤的用炭卻費幾十元,這也是一件怪事。”曾氏的豪奢,陳克文覺得怪,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則覺得愧:“(1941年10月13日)晚曾養甫請客在其辦公處(太和坊三號),主客為俞部長,外有蔣﹝夢麟﹞夫婦、金夫婦及路局數君。菜味有烤乳豬、海參、魚翅;酒有Brandy,Whisky;煙有State Express。飲食之余,不禁內愧。”按:曾養甫(1898—1969),廣東平遠縣人,1923年天津北洋大學畢業,后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深造,與陳立夫同學,1924年獲礦冶工程碩士學位,1925年初回國,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后方總政治部主任、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廣州特別市市長、廣東省政府財政廳廳長等,1938年后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督辦、交通部長兼軍事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此肥缺,自然豪奢無憂,但也實在過分。不過他也做了件“大好事”,就是高薪禮聘蔣夢麟為顧問,據《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42年4月2日)孟鄰﹝夢麟﹞師相告,曾養甫聘其為滇緬局顧問,月薪一千元,生活問題差可解決。師每月所入不足三子讀書,月有虧空。近來全校人人不得了,然其尤甚者,莫師與月涵先生若。日前月涵先生女公子得西人家館,月入可千元,今師亦得此,可稍免張羅之勞矣。”
二
重慶食風,必得外江相助。重慶是歷史文化名城,古巴郡、江州和后來的渝州、重慶府治地,而且早在1890年中英《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確定為通商口岸,1895年《馬關條約》又使重慶成為中國第一批向日本開放的內陸通商口岸,因之英、日、法、美、俄、德總領事館陸續設立,但真正的現代化城市建設和商業的全面繁榮,則有待于1929年重慶正式建制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省轄市,從商埠向都市轉型,特別是1937年之后,五方輻輳,始底于成。餐館業尤其如此,大作家張恨水即有及時敏銳的觀察:“客民麇集(重慶)之后,平津京蘇廣東菜館,如春筍怒發,愈覺觸目皆是。大抵北味最盛行,粵味次之,京蘇館又居其次,且主持得人,營業皆不惡。其理由如下:冠蓋云集,宴會究難盡免,一也。入川之人,半無眷屬,視餐館為家庖,二也。莼鱸之思,人所俱有,客多數日一嘗家鄉風味,三也。餐館就地取材,設置較易,四也……廿七年十一月廿日晚,密霧籠山,寒窗釀雨,書于棗子嵐埡寓樓燈下。”
為我們留下記錄最多的恐怕非顧頡剛先生莫屬。顧氏是當紅的大學者,也是著名的學術領導者,故每至一地,無不詩酒流連,應酬頻繁,以致他小學的同窗好友葉圣陶先生在1938年都連連感嘆說:“頡剛真是紅人,來此以后,無非見客吃飯,甚至同時吃兩三頓。彼游歷甘肅、青海接界之區,聆其敘述,至廣新識。不久彼即離此往昆明,云擬在郊外覓居,以避俗事。然恐避地雖僻,人自會追蹤而至,未必便能真個坐定治學也。”他的詩酒流連之地,當然少不了粵菜館;這多少也與其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等職有關吧。
在列敘顧氏重慶粵菜館生涯之前,我們不妨先簡單介紹一下他抗戰期間的行止。抗戰軍興,學校和學人均紛紛南遷,顧氏則于1937年獲中英庚款管理董事會之聘,任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前往甘、青、寧考察教育。1938年10月始赴昆明云南大學任文史教授,兼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歷史組主任。1939年秋轉任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1941年赴重慶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史雜志社副社長(葉楚傖任社長,顧主持社務)。1944年秋再回任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1945年又任復旦大學教授并兼任北碚修志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國出版公司總編輯。1946年2月離渝。自到重慶任職后,期間雖曾離渝赴蓉,但因為文史雜志社職始終未辭,還有其他諸多重慶的政學兼職,故始終在重慶時間為多。他曾自謂流連詩酒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比如每月四千元的《文史雜志》主編費,便基本用于跟作者見面談稿子了。
顧氏在重慶第一次上粵菜館的記錄是1941年1月31日:“飯于大三元……今午同席:予(客)、張姑丈夫婦、子豐夫人、珍妹、子豐二女(主)。”而1月29日他還在日記里說:“米貴至三百元以上一石矣,肉貴至三元以上一斤矣。大家覺得生活煎迫無法解決,一見面即談吃飯問題。今年如不反攻勝利,許多人將干死。”大有即使飯吃不上,館子還是要上的味道。
大三元是重慶著名的粵菜館,早在1938年9月24日,《中央日報》即有大三元酒家招待新聞界月餅的報道。《宇宙風》1938年第六十九期滄一的《重慶現狀》,羅列各商家,粵菜館可只提到大三元一家呢:“商家呢,有滬杭的綢緞店,有冠龍、大都會等照相館,有大三元、小有天等吃食店,有蘇州、南京等處的種種老招牌……”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梁寒操赴貴州宣慰,兩廣同鄉會在貴陽大三元酒家設茶點歡迎,梁說貴陽大三元比重慶大三元還大,并題寫了“貴陽大三元酒家”的招牌,也從側面反映出重慶大三元的地位。或許因為大三元的名聲,顧頡剛是屢屢與席的:
1942年8月27日:唐京軒邀至大三元吃飯,晤傅秉常。
1942年9月10日:訪唐京軒、龔仲皋,與同到大三元吃飯。
1943年10月6日:到都郵街大三元吃茶。
1943年11月2日:回聚賢處,與諸人同到大三元吃飯。
1946年4月2日:到大三元吃飯。
大三元也真還勝流如云。國民政府行政院主管總務及人事的廣西岑溪籍參事陳克文,在重慶期間上粵菜館的總次數雖然不如顧頡剛,但上大三元的次數則不相上下,而且更有故事:
1939年1月8日:學生劉宗立邀晚飯于大三元,到內政部司長陳屯……皆農所學生。
1939年2月8日:晚間劉建明請晚飯于大三元酒家。除了著名﹝的﹞怕老婆的國府委員鄧家彥和林翼中兩人之外,其余都是不相識的。
1939年12月6日:陳樹人夫婦請到城里大三元午飯。甘乃光夫婦、馬超俊夫婦、劉蘅靜均在被請之列。
1940年11月21日:因為有便車進城,和之邁、鑄秋同到林森路訪出名的女詩人徐芳小姐。后來同到大三元吃午飯。
1943年6月15日:上午和鑄秋同車進城,邀律師陳廷銳夫婦吃茶于大三元酒家。
1944年8月16日:因事到市中心區,吃午飯于民權路大三元。
著名史學家劉節先生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據說生活極為清苦,但仍多上粵菜館,其中兩上大三元:“(1939年2月1日)仲博亦來,即與一同至大三元午餐。”“(1939年7月9日)仲博臥病數日,人覺稍瘦。同至大三元飲茶,談至十時左右。”
顧頡剛去粵菜館最早的是大三元,去得最多的則是嶺南館和廣東酒家,日記中分別錄得九次。陳克文去廣東酒家也不少,并且說:“那里的風味和廣州的茶居早市相差不遠,有各色的廣東點心。”又說:“物價雖貴,茶客依然滿座。”
葉圣陶1942年去了一趟桂林,途經重慶,也特別來喝過一次早茶:“(1942年5月5日)晨起茗于廣東酒家,進點。”
當時重慶最大最有名的粵菜館,非冠生園莫屬:“在每個星期日的早晨,重慶冠生園的熱鬧情形,恐怕是孤島人士想像不到的。桌子邊,沒有一只空閑的椅子。許多人站立在庭柱旁邊,等候他屁股放到椅子上去的機會。有人付賬去了,離開椅子,不過十分之一秒鐘,就被捷足先登,古人說席不暇暖,這里的卻有‘席不暇涼之概。”并因著“座客完全是上流人”而想象全國的冠生園莫不如是:“從清早七時到十時,全國展開著這樣一幅圖畫。”(畫師《重慶冠生園的素描》,《藝海周刊》1940年第二十期)如此名店,著名的顧頡剛先生自然也有多去。
陳克文關于他自己在重慶上冠生園的最后一條記錄,彌足珍貴:“(1939年7月12日)中午應劉昌言、郭松年約,和鑄秋同到城內冠生園午飯。五月三日空襲以后,到城里吃館子這還是第一次。城內的館子,現在只有兩家,每日十一時以后,便關門不做生意,情況殊為凄寂。城內經過五月六月的空襲和最近兩次夜襲,差不多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子了。”也即是說,在敵機狂轟濫炸得幾無一間好房,別的餐館都不敢或不愿營業的情況下,冠生園成為碩果僅存的兩家開門營業的店家之一,而且可以說是大餐館里唯一的一家。如此敬業精神,焉能不成為重慶粵菜館乃至重慶餐館業的標桿?
葉圣陶先生則將冠生園作為其宴飲生活的重要參照:1942年5月5日夜,“祥麟以開明﹝書店﹞名義宴客,至冠生園。久不吃廣東菜,吃之頗有好感。一席價三百元,以今時言之,不算貴。”1938年1月11日的一封信中說:“李誦鄴兄之酒棧已去過,二層樓,且買熱酒。設坐席八,如冠生園模樣,頗整潔。”也以冠生園為參照來介紹朋友的酒棧。1938年10月8日在致洗、丐、伯、調諸先生信中,說到重慶有名餐館生生花園,則拿上海冠生園來作參照:“規制如上海冠生園農場,本月二日曾與頡剛、元善、勖成前往聚餐,為卅二年前小學四友之會。”由此,可見冠生園酒樓在他心目的地位。
粵香村也是葉圣陶去過的酒家:“(1942年5月7日)吳朗西來訪……君知余能飲,邀往一家售綿竹大曲之店。自菜館不許飲酒以來,酒店之生意大好,客恒不斷,幾如茶館。例不許售葷菜,只備花生豆腐干。各飲酒二兩,遂飯于粵香村。”
粗略統計,顧頡剛在重慶期間,至少上過大三元、廣東大酒家、廣東酒家、冠生園、嶺南館、廣東味、粵香村、廣東館、廣東人家、珠江食堂、南國、廣東第一家等十二家粵菜館,這不僅超過所有其他人的紀錄,也超過所有的重慶指南書的紀錄。如此看來,對于我們今天考察粵菜的向外傳播,特別是在重慶的發展,顧氏真是功不可沒。
可惜當時重慶還有幾家有名的粵菜館,顧頡剛沒有提到,或者忘了記錄。比如南園酒家,陳克文先生曾于1939年1月9日應甘紹霖之邀在此晚飯。劉節先生也曾兩度前往,而且初到重慶第一頓飯就是在那兒吃的:“(1939年1月31日)宿處既定,乃與仲博同至新川旅館洗澡理發,晚至南園酒家晚餐。”“(1939年8月17日)晚上戒嚴,余方在南園晚餐。”此外,還有國民酒家、國泰飯店、陶陶餐室。
這樣,依筆者寓目的文獻材料,當時重慶知名的粵菜館,如果說名流眷顧的粵菜館至少有十六家,再加上時人記述不及而各指南書涉及的醉霞酒家、南京酒家、廣州酒家、大東酒家、清一色酒家、四美春酒家,則達二十二家,如果再加上冠生園的另兩家支店,則有二十四家了,這明顯超過了除川菜之外的所有下江菜系。粵菜的向外發展,不避治亂,均粲然可觀,委實值得我們珍視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