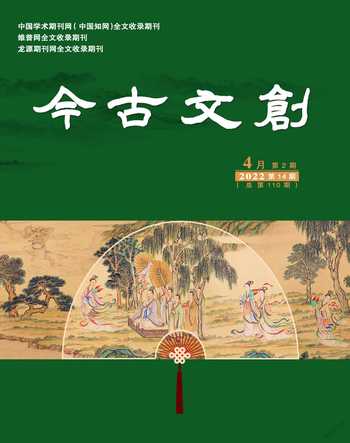論薛福成的西學(xué)中源說
【摘要】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早期維新派代表人物。“西學(xué)中源說”是其在洋務(wù)實(shí)踐過程中形成的極具特色的思想,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關(guān)鍵詞】 薛福成;西學(xué)中源;晚清
【中圖分類號】G04?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4-005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16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早年以洋洋萬言的《上曾侯書》得曾國藩青睞,入其幕府,人稱“曾門四弟子”。后以《應(yīng)詔陳言疏》一夜成名,被李鴻章招入麾下。自此期間,籌防浙東,抵抗法軍,出使四國,展現(xiàn)出卓越的政治才能。相較于傳統(tǒng)知識分子,薛福成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不斷地接觸、了解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了解較多。薛福成也在此過程中不斷思考中西文明間的關(guān)系,最終形成“西學(xué)中源”這一極具特色的思想。
西學(xué)中源,顧名思義,認(rèn)為西學(xué)來源于中學(xué),西方文化的先進(jìn)是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但是該學(xué)說并非薛福成獨(dú)創(chuàng),關(guān)于該說法的最早提出者眾說紛紜 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說法最早伴隨著明末清初大量西方傳教士來華而產(chǎn)生的。伴隨著傳教士到來的西學(xué)推動了中國思想的演變,給當(dāng)時思想界帶來動蕩,西學(xué)成為明清思想家走出中世紀(jì),走向近代的重要思想來源。[1]這一時期的思想動蕩被胡適認(rèn)為是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四次文藝復(fù)興之一。當(dāng)時的士大夫感嘆西方文化的先進(jìn),又不愿承認(rèn)自己的落后,于是提出“西學(xué)中源”的說法來安慰自己。在這種自我安慰心理的麻痹下,士大夫并沒有進(jìn)一步探索外部世界,“西學(xué)中源”思想也日漸式微。
“西學(xué)中源說”曾在清康熙帝時有過短暫的復(fù)興。康熙帝本人對西學(xué)比較感興趣,他曾在《庭訓(xùn)格言》中提及:“朕幼時,欽天監(jiān)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于午門外九卿前,當(dāng)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 因自憤而學(xué)焉。”[2]在康熙帝的大力提倡下,“西學(xué)中源說”逐步臻于至善并曾風(fēng)行一時。這一時期最大的貢獻(xiàn)就是梅文鼎對于“西學(xué)中源”的途徑的補(bǔ)充,隨后阮元、江永和戴震等學(xué)者研究的深入,經(jīng)世之風(fēng)日盛,“西學(xué)中源”學(xué)說也日臻完善。但隨后發(fā)生的中西歷法之爭及其引發(fā)的百年禁教②,使清政府封閉國門,在將傳教士拒之門外的同時也將先進(jìn)的西方文化拒之千里,繼而導(dǎo)致傳統(tǒng)思想體系日益僵化,也使“西學(xué)中源說”在中國逐漸沉寂。近代以來,西方的堅(jiān)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各種西學(xué)相繼涌入,不斷地沖擊中國傳統(tǒng)思想體系。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被迫再次思考中西文化間的關(guān)系。而薛福成就是其中一員。此時,中西文化交流已成為大勢所趨,如何做到中西文化貫通成為當(dāng)務(wù)之急。至此,“西學(xué)中源說”再度流行。
首先,薛福成與其他主張“西學(xué)中源”的思想家一樣,認(rèn)為西學(xué)來源于中學(xué),西方先進(jìn)的文明是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關(guān)于西學(xué)源于中學(xué)的例子,薛福成認(rèn)為是很多的。“如(《墨子》)第九卷《經(jīng)說下》篇,光學(xué)、重學(xué)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魯問》《公輸》數(shù)篇,機(jī)器、船械之學(xué)之所自出也。第十五卷《旗幟》一篇,西人舉旗等以達(dá)言語之法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則所見大,景亦大遠(yuǎn)中,則所見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鏡、顯微鏡者,皆不出此言范圍。”[3]
除自然科學(xué)外,西方的宗教也能在中學(xué)中找到依據(jù)。他認(rèn)為“余常謂泰西耶穌之教,其原蓋出墨子,雖體用不無異同,而大旨實(shí)最相近。”[3]甚至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在中華傳統(tǒng)中找到源頭。“余觀泰西各邦治國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則其擅強(qiáng)盛之勢亦較多。”[3]191薛福成認(rèn)為西方的議會制度的設(shè)立就與《管子》中重視“民意”的觀點(diǎn)有關(guān)。《管子》認(rèn)為,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無不成。不強(qiáng)使人民干他們厭惡的事情,欺詐作假的行為就不會發(fā)生。不貪圖一時僥幸,人民就不會抱怨。不欺騙人民,人民就擁戴君上。那么君上如何才能了解“民力”,知曉百姓心中所想呢?西方議院的設(shè)立就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薛福成曾在日記中記載一位隨行出使官員在談?wù)撐鞣礁粡?qiáng)的原因是,把“通民氣”放在首位。人民選舉產(chǎn)生議員組成上下議院,為民眾表達(dá)意見建立一個通道。議員就好比民眾的代言人,凡是對百姓不利的,一定想辦法改變。議院成為君上知曉百姓想法的一個渠道。薛福成本人對該觀點(diǎn)也是頗為贊同。
其次,在對中西文化進(jìn)行比較之后,薛福成承認(rèn)當(dāng)時西方較之中國是先進(jìn)的,并主張向西方學(xué)習(xí)。雖然西方當(dāng)時更加強(qiáng)盛,但只要向西方學(xué)習(xí),“安知數(shù)千年后,華人不因西人之學(xué),再辟造化之靈機(jī),俾西人色然以驚,睪然而企也?”[3]68薛福成以暹羅為例,暹羅從一個受緬甸挾持、甚至一度被滅國的弱小國家,在短短數(shù)十年間,發(fā)展成為“國勢尚稱完固”的自立之國,最大原因在于“西法有以輔之”,最終得出“今之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墊使然也”[3]170的結(jié)論。但是自從中西開始頻繁交往之后,中國的士大夫拘于成見,在對待西方的問題上甚是倨傲,不屑于西人打交道。而精通洋務(wù)這又多為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的商人,目光狹隘,因此近代中國在中西交往中往往落于下風(fēng)。薛福成提議設(shè)立專門的職位,從新進(jìn)舉人中挑選精于洋務(wù)的,按其擅長分配工作。久而久之,士大夫們定能摒棄成見,改變空談,腳踏實(shí)地辦洋務(wù)。朝廷也定能發(fā)現(xiàn)辦洋務(wù)的奇才。洋務(wù)辦得好,國家強(qiáng)盛了,中國之“天朝上國”的地位才能無人可撼動。
為了使深受“天朝上國”自滿心理影響的士大夫接受西方學(xué)習(xí),薛福成解釋道學(xué)習(xí)西學(xué)是為了“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4]同時又提出了“西法為公共之理說”。西人的科技、制度等并非西人獨(dú)有,是“公共之理”,我們中國人也可以追求。并且中國士人的智力和能力是不遜于西人的,中國暫時的落后是因?yàn)橹袊闹R分子未能“專攻有用之學(xué)”[5],只要國人自此虛心學(xué)習(xí),奮起直追,定能青出于藍(lán)而勝于藍(lán)。
再次,薛福成在比較中西文化的過程中,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做了深刻的反思。為什么中國古代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輝煌的成就,而在近代卻日漸衰弱呢?薛福成在思考后得出結(jié)論:中國的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專事一事。薛福成認(rèn)為,治術(shù)學(xué)術(shù)的關(guān)鍵在于“專”“精”二字。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有限的精力全部傾注在一件事情上,專心致志鉆研,才能達(dá)到“精”。薛福成以齊國為例,認(rèn)為齊國強(qiáng)盛、成為一方霸主的原因就在于采取職業(yè)的世襲制,以“士之子恒為士,農(nóng)之子恒為農(nóng),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4]160。家族世世代代專攻一事,必然能做到“精”。
而中國自宋、明以來逐漸衰弱的原因就在于放棄了這種做法,“取士專用時文試帖小楷,若謂工其藝者,即無所不能;究其極,乃一無所能。仕于京者,忽戶部,忽刑部,忽兵部,迄無定居;忽治河,忽督糧,忽運(yùn)鹽,亦迄無定官。”[4]160古代圣人專注一事數(shù)十年尚且不敢說自己做出成就,現(xiàn)如今的官員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又如何對業(yè)務(wù)精通、做出成績呢?官員尚且如此,國家又如何能強(qiáng)大起來?較之西方,“泰西諸國,頗異于此。出使一途,由隨員而領(lǐng)事,而參贊,而公使,洊升為全權(quán)公使,或外部大臣,數(shù)十年不改其用。軍政一途,由百總而千總,而都司,而副將,洊升為水陸軍提督,或兵部大臣,數(shù)十年不變其術(shù)焉。”[6]西方國家正是采用了這種分業(yè)的方式才逐漸強(qiáng)盛起來。
除此之外,薛福成還認(rèn)為中國衰弱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4]162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在于不能更新,更重要的在不能守舊。中國要想富強(qiáng),趕上他國,就要學(xué)習(xí)西方的“新”的知識,以開放的態(tài)度面對和汲取西方先進(jìn)文化。而西方這些所謂“新”的知識正是在“舊”的中華文明的影響下形成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發(fā)掘自身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成果,在此基礎(chǔ)上向西方學(xué)習(xí),實(shí)現(xiàn)自我更新。古代黃帝、周公造出了指南車,民間尚且能受其啟發(fā),發(fā)現(xiàn)造針之法。而后來的“暨公輸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杜預(yù)之河橋,早已盡失其傳。”[5]424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忘舊”,進(jìn)而阻礙了其“更新”。
此外,薛福成還認(rèn)識到不論中華文明抑或西方文化皆各有其“新”“舊”,“西方的器械制造所以能參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闡之學(xué),屢言而益進(jìn)爾,并非一旦超然豁悟,驟得無上之秘訣也。即如中國上古之世,繼天立極之圣人,應(yīng)運(yùn)迭興,造卦畫,造市場,造網(wǎng)罟,造耒耜,造舟車……能使洪荒氣象,變?yōu)橛钪嬷拿鳎w新莫新于此矣。”[5]424所以薛福成得出了“宜考古,毋厭舊;宜知新,毋鶩新”的結(jié)論,這也使其得以區(qū)別于守舊派與其他維新派。因此,薛福成在處理中西文化關(guān)系時更強(qiáng)調(diào)融會貫通。
薛福成的“西學(xué)中源說”的提出,是近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面對中西文化碰撞過程中所發(fā)出的時代呼聲,也是其對于如何挽救民族危機(jī)問題的答卷。該學(xué)說在理論上使西學(xué)成為中學(xué)的一部分,“以弘揚(yáng)民族文化的形式,將西方文化納入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體系之中,協(xié)調(diào)了民族自信心與危機(jī)感”[7],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深受“夷夏之防”影響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西學(xué)的抗拒,為西學(xué)在中國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此外,薛福成極力推崇《墨子》,認(rèn)為西學(xué)的源頭大多都在《墨子》,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儒學(xué)在近代思想界的獨(dú)尊地位。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思想界呈現(xiàn)百家爭鳴的燦爛局面。而在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后,儒家思想一家獨(dú)大,其他非儒家文化被視為“異說”而逐漸沉寂。近代以來“西學(xué)中源說”的再度興起,使知識分子的目光從儒學(xué)轉(zhuǎn)移到《墨子》《管子》等非儒家文化,沖擊了儒家思想千年來的獨(dú)尊地位,對解放思想起到了推動作用。薛福成也將其對于《管子》的認(rèn)識應(yīng)用于“夷務(wù)”之中。在論及籌辦海防問題時,薛福成指出:“防之之策,有體有用。言其體,則必修刑政,厚風(fēng)俗,植賢才,變舊法,祛積弊,養(yǎng)民練兵,通商惠工,俾中興之治業(yè)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戰(zhàn)態(tài)以螫我中國;言其用,則籌之不可不預(yù)也。籌之預(yù)而確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長有二:一則火器猛利也;一則輪船飛駛也……彼之技藝可學(xué)而能也……若是,則彼之所長,我皆奪用之矣。”[8]這種“管”為西用的主張與洋務(wù)派“中體西用”思想不謀而合,推動了洋務(wù)運(yùn)動的開展。
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薛福成的“西學(xué)中源說”產(chǎn)生于距今百余年的晚清,其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薛福成本人出身于傳統(tǒng)的書香世家,自小接受的是傳統(tǒng)儒家教育,文化優(yōu)越感是深深扎根在骨子中的。比如在談及耶穌教經(jīng)典《圣經(jīng)》時,薛福成甚是鄙夷,認(rèn)為連中國的《封神演義》《西游記》都不會淺俚至此。將耶穌教義與儒家學(xué)說相比,就好比拿水晶和玉比較。同時將西方取得的一切成就歸因于中學(xué),甚至其在日記中對于英國進(jìn)步的肯定也是為了佐證中華文明西傳的成果。“昔軒轅氏見飛蓬而作車,見落葉而作舟,即中國構(gòu)造機(jī)器之始。風(fēng)車水碓,相傳亦久。至于雙碇紡車,提花織機(jī),則愈變愈巧也。然則機(jī)器之用,始于中國,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機(jī)器也,即化學(xué)、光學(xué)、重學(xué)、力學(xué)、醫(yī)學(xué)、算學(xué),亦莫不自中國開之……所謂西學(xué)者,無非中國數(shù)千年來所創(chuàng),彼襲而精究之。分門別類,愈推愈廣。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藍(lán)也”。[5]620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國人的文化自大心理。再加之其對西方的了解多來源于書本或出使四國的經(jīng)歷,因此對西方及西學(xué)的一些理解難免片面和偏頗。
薛福成認(rèn)為西方“貴女賤男”,并認(rèn)為“其夫婦一倫,稍微圣人之道”。[3]211此外,“西學(xué)中源說”還混淆了古代科技與近代科學(xué)間的差異,阻礙了國人對西學(xué)的真正認(rèn)識。薛福成在日記中引用的《請派員游歷外洋疏》中道“夫外洋測算,衍自中法;制器相材,源自《考工》。營陣束伍,乃古者司馬法步伐進(jìn)退之遺;開采五金,仿于《周禮》礦人之職;測繪地輿,亦晉人裴成秀之法。”[3]107他一方面主張向西方學(xué)習(xí),一方面又認(rèn)為西學(xué)的一切都能在中學(xué)中找到依據(jù),難免使其他知識分子陷入學(xué)習(xí)西方是否有必要的困惑之中。頑固派也可以西學(xué)之精中學(xué)固有之為由,反對洋務(wù)派的洋務(wù)活動。
綜上所述,固然薛福成的“西學(xué)中源說”有很多的局限性,但在當(dāng)時來說能承認(rèn)西方的先進(jìn)、并倡導(dǎo)向西方學(xué)習(xí)已經(jīng)是鮮有的先進(jìn)之聲。薛福成在處理中西文化時融會貫通的原則雖未在當(dāng)時取得預(yù)期效果,但也給現(xiàn)今處理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鑒。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當(dāng)今,文化交流無法避免,大家要以正確的眼光對待外來文化,既不要故步自封,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中華文化在新時期煥發(fā)出新的光彩。
注釋:
①江曉原在《試論清代“西學(xué)中源”說》(《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提出該說法發(fā)端于明之遺民,并認(rèn)為最先提出“西學(xué)中源”思想的是黃宗羲。而李兆華在《簡評“西學(xué)源于中法”說》(《自然辯證法通訊》1985年第6期)中從數(shù)學(xué)發(fā)展的角度提出“西學(xué)源于中法”的說法最早是由康熙提出的。
②嚴(yán)格來說,禁教政策是從雍正朝開始,康熙時期只是驅(qū)逐了未領(lǐng)票的傳教士。
參考文獻(xiàn):
[1]張西平.明清之際西學(xué)東漸的歷史反思[J].中央社會主義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1,(3):178.
[2]康熙.庭訓(xùn)格言[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40.
[3](清)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0.
[4]薛福成著;徐素華選注.籌洋芻議——薛福成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90.
[5](清)薛福成著,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98.
[6]馬忠文,任青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薛福成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4:290.
[7]安宇.晚清“西學(xué)中源說”論綱[J].徐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3,(4):84.
[8]馬忠文,任青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薛福成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4:19-20.
作者簡介:
吳雨,女,漢族,河南新鄉(xiāng)人,鄭州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xiàn)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