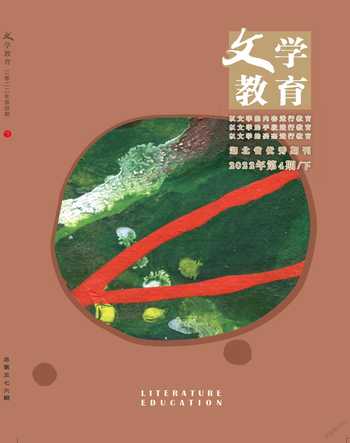許淵沖翻譯思想對翻譯審美再現的啟示
龔智鵬
內容摘要:許淵沖的“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打破了傳統翻譯理論中以“真”為尊的理念,在翻譯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兩個理論與翻譯美學理論有著不小的共通之處。本文通過對許淵沖“優勢競賽論”“再創論”與劉宓慶有關翻譯美學理論的研究,考察兩位學者各自翻譯理論間的內在聯系,并通過具體的翻譯案例探討“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對于翻譯美學視域下翻譯實踐的啟示。
關鍵詞:優勢競賽論 再創論 審美再現
20世紀末21世紀初,我國偉大的翻譯家許淵沖根據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已提出的“三美”論等翻譯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受到翻譯學界的廣泛關注,在強調譯者主觀能動性,提升譯者地位等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不僅如此,源于譯詩實踐的“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翻譯美學理論的發展也有不小的啟發意義。因此,本文將探討“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如何應用于翻譯美學視域下的翻譯實踐,并以具體的翻譯案例進行論述,探究許淵沖翻譯思想對翻譯審美再現的積極意義。
一.“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
許淵沖最早在1982年《譯文能否勝過原文?》一文提出翻譯“優勢競賽論”,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甚至是兩種文化的競賽,在競賽中,要青出于藍而勝于藍[1]。“優勢競賽論”可以分為“優勢論”和“競賽論”兩部分。許淵沖的“優勢論”基于中西方文字差異性較大,翻譯時難以達到對等的語言表達效果。以往的翻譯理論多注重原文與譯文之間是否是對等的。但許淵沖認為在譯詩時,對等的翻譯未必就是好的翻譯。而“競賽論”假設表達形式對等的譯文等同于原文,那么原文就能與采取其他表達形式的譯文比出孰優孰劣[2]。許淵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看來,創作也可以算是一種翻譯,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翻譯成為文字。而中外翻譯則是把作者的思想從一種文字轉化為另一種文字。既然兩種文字都在表達作者的思想,那就有一個高下之分, 這就是兩種文字在競賽了。”[3]
關于“再創論”,許淵沖提出“創造性翻譯應該等于作者用譯語的創作。”“再創論”的內容主要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1)翻譯要忠實于原作的意圖;(2)要發揮譯語優勢,創造性地傳遞原作的美感;(3)詩詞翻譯要創造性地傳達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4)發揮創造性并不是隨心所欲,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4]。“再創論”是基于文學文本的開放性、模糊性和多義性等特征提出的。若譯者僅從語言表層去把握原文的含義,很可能只能領會其皮毛。唯有不拘泥于原文表達形式,將自己想象成作者,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原文的核心內涵。
“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的核心思想是“發揮譯語優勢”。文學翻譯最終是使譯文成為翻譯文學。因此傳遞原文的意義只是最基本的功能,更高層次的目的是使讀者在閱讀譯文的過程中獲得良好的審美體驗,這包括了意境美、音韻美和形式美。以“美”為標準,通過發揮譯語優勢,在原語(或稱之為與原文表達形式對等的譯語)與譯語的不同表達方式中,尋求最優解,以追求與原文神似的審美效果。
二.翻譯美學理論
翻譯美學是揭示譯學的美學淵源,探討美學對譯學的特殊定義,用美學的觀點來認識翻譯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并運用美學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譯不同文體的審美標準,分析、闡釋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美學問題[5]。劉宓慶在《翻譯美學導論》一書中詳細論述了翻譯的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審美再現等問題。
劉宓慶認為審美主體(譯者)受制于原文可譯性、雙語文化差異、藝術鑒賞的時空差異等因素,同時又具有主觀能動性,可以能動地表達、創造與原文相對應的審美效果。翻譯審美客體(原文、譯文)應依附于原文的審美構成,對應原文的審美效果。同時,翻譯審美客體容許審美主體感應的靈活性與歷史發展對其審美價值產生的可變性。翻譯審美客體的審美構成分為形式系統與非形式系統兩部分。形式系統包括語音層、文字層、詞語層、句與段的審美信息。非形式系統包括情志、意旨、意象與意境等。
有關于翻譯實踐層面的翻譯審美再現問題,劉宓慶提出了模仿與重建兩種類型。劉宓慶將模仿分為以原語為依據的模仿、以譯語為依據的模仿和取前兩者之長的動態模仿。重建則是擺脫原語形式束縛,按照目的來安排體式,達致譯者預期最佳優化的方式[6]。
三.“優勢競賽論”“再創論”對審美再現的啟示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優勢競賽論”“再創論”與翻譯美學理論之間存在密切的共通性。首先,許淵沖提出的“再創論”提倡譯者不拘泥于原文的表達形式,將自己想象成原文作者,“將心比心”地再創作。這與劉宓慶提出的重建是一致的。其次,“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的核心在于“發揮譯語優勢”,這本身就是翻譯審美主體,即譯者主觀能動性的體現。
此外,許淵沖的“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對翻譯美學理論指導下的翻譯實踐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為了更好的闡述這一啟發意義,本文將通過具體的翻譯實例進行論證。首先,“優勢競賽論”中的“競賽”提倡譯者在包括原語(或稱之為與原文表達形式對等的譯語)在內的各種語言表達形式間相互比較,尋求最佳譯法。而劉宓慶在論及翻譯審美再現時,提出了三種模仿與重建,共四種再現方式。若將兩位學者的觀點結合,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分別采取上述的幾種或全部四種方式翻譯后,相互對比得出最優譯法,比單一采取其中某種方式,更能保障譯文的審美效果和藝術性。
例1
原文:雪のなかで糸をつくり、雪のなかで織り、雪の水に洗い、雪の上に曬す。[7]
譯文1:在雪中繅絲、織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曬,......[8]
譯文2:雪中績麻,雪中紡織,雪水漂洗,雪上晾曬。[9]
譯文3:在雪中績麻、雪中紡織、用雪水漂洗、在雪上晾曬。[10]
描繪景色的句子是翻譯美學理論天然的發揮場所。例1的原句出自日本現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國》中有較多描繪自然風景的語句,意境豐富、唯美。譯者的審美體驗與審美再現方式對譯文帶給譯語讀者的審美體驗有直接影響。例1是中的三個譯文分別出自葉渭渠、高慧勤、林少華三位譯者的譯本。原文采用了排比的修辭手法,并且具有極強的節奏感。然而要譯出“音美”,前半句中兩個「雪のなかで」成為了難點。譯文1將前半句合譯,直接破壞了原文本身排比修辭的形式美。譯文3雖然沒有采用合譯的翻譯技巧,保留了原文四個排比的結構,但“在”“用”等忠實于原文的譯法,仍舊難以體現原文的“音美”。相比之下,譯文2發揮了中文里四字詞表達的語言優勢,將四個小句全部翻譯為四個漢字,不僅保留了原文排比的修辭手法,也體現出了一定的節奏感。這里,譯文1與譯文3可以說是采用了以原語為依據的模仿,而譯文2采用了以譯語為依據的模仿。通過兩種語言表達方式或兩種審美再現方式的對比,可以發現發揮了譯語優勢的譯文2相對而言更能體現出原文的形式美與節奏感。
例2
原文:露の世は露の世ながらさりながら。
譯文1:露水的世呀,雖然是露水的世,雖然是如此。[11]
譯文2:露水消逝終不歸,落花不再返枝回。兒女消逝難斷念,人生亦如此奈何。[12]
上述的這句俳句是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里記錄他女兒去世時寫下的,通過露水的滴落、無法回流指代生命的消逝。既表達了對女兒逝世的悲傷,也透露出了對人生無常的哀嘆。自然風物的枯榮、流失常常觸發日本人對于“好景不長”“人生苦短”的哀嘆,使他們體會到雖與自然風物同根同源卻不能同體同歸的無常感與孤寂感。譯文1基本上保留了原文“5-7-5”表達形式,從字面含義上講的確是做到了忠實。然而,如果不是對日本文學有較多了解和體會的讀者,是很難體會到這當中透露出了的日本植物美學觀與“空寂”的審美情趣。相比于譯文1,譯文2將其翻譯為中國的七言詩,相比于譯文1的散詩形式,更具形式美和音韻美。不僅如此,通過后兩句的加譯,既補全了該俳句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解除了中文讀者的理解障礙,又符合中國古詩詞“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的審美習慣。第二句中加譯的意象“落花”與第一句的“露水”聯系起來,讓人很容易形成“落花流水”的畫面感,從而體會到一股衰敗之感。這種通過運用譯語的語言和文化特征創造性翻譯的方法就是所謂的“發揮譯語優勢”。
其次,當譯者面臨很難實現翻譯對等,或形式對等的譯文審美效果不佳時,就需要在忠實與美感之間進行取舍。關于翻譯中忠實與美感的關系,許淵沖在《新世紀的新譯論》一文論述“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前有所闡述。許淵沖認為翻譯中“真”與“美”二者兼得是最理想的結果。若二者不可兼得,則允許一定程度的“失真”以達到“求美”的目的。而劉宓慶則認為譯者在審美再現時不能脫離原語固有的審美構成,應避免“美言不信”。面對兩位學者不同的見解,筆者更傾向于前者。對此,筆者將以下面的例句進行論述。
例3
原文:裸の天の河は夜の大地を素肌で巻こうとして、直ぐそこに降りて來ている。[7]
譯文1:茫茫的銀河懸在眼前,仿佛要以它那赤裸裸的身體擁抱夜色蒼茫的大地。[8]
譯文2:光潔的銀河,似乎要以她赤裸的身軀,把黑夜中的大地卷裹進去,低垂下來,幾乎伸手可及。[9]
譯文3:無遮無攔的銀河徑直垂降那里,要把夜晚的大地用裸膚卷裹起來。[10]
從「素肌」一詞可以看出,原作者在此處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縱觀三個譯文,三位譯者在翻譯時都選擇保留這一修辭。然而,在處理「巻こうとして」一詞上,譯文2、譯文3都選擇了直譯,但“卷裹”一詞通常是把東西彎轉裹成圓筒形,“用身體卷裹”在中文里并不是特別形象,不符合我們對身體結構的普遍認知,容易在讀者腦海中生成一種較為扭曲的人體姿勢,導致審美體驗的效果不佳。相比而言,譯文1選擇用“擁抱”一詞代替原文“卷裹”的含義。“擁抱”通常給人溫暖、溫柔、熱情等感受,更容易引導讀者產生唯美的審美體驗。雖然用“擁抱”替換“卷裹”在擬人的動作表達上與原文有所出入,但卻符合大多數中文讀者的邏輯思維和審美習慣,更容易在中文讀者腦海中形成“天地相擁”的美好畫面,獲得良好的審美體驗。
例4
原文:山茶花に犬の子眠る日和かな。
譯文1:山茶花正香,小狗花下入夢鄉,甜甜浴斜陽。
譯文2:山茶花下狗仔眠,小陽春里晴和天。
例4的俳句描繪的是一幅晴空下小狗在山茶花旁睡覺的美好畫面。譯文1保留了原文“5-7-5”的語言表達形式,而譯文2則翻譯為了七言詩,二者都注意到了押韻,且兩種表達形式都能被中文讀者所接受,因此在表達形式上只能說各具特色。但從“意美”的角度而言,譯文2只翻譯出了原文的字面意義,在意境的營造上稍有欠缺。譯文1加譯的“香”字使讀者能通過聯覺感受到一種環境的美好,而“夢鄉”能讓人聯想到“美夢”,比起單純的睡眠,又增添了一種閑適之美。譯文1美中不足的是第三句的“斜陽”一詞。根據《廣辭苑》釋義,「日和」為「良い天候。晴天」,而“斜陽”多指傍晚西斜的太陽,會給人一種夕陽西下,走向衰落的感覺。這與前兩句的美好意境形成了沖突。筆者認為可將譯文的“斜陽”改為“暖陽”。如此一來,譯文1雖然增添了“香”“夢鄉”“甜”等原俳句中沒有的詞,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但本質上卻與原俳句試圖營造的意境一致,甚至將原文的意境美營造得更加美妙。
“真”與“美”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保持“真”是為了防止譯者過度創造,徹底與原文背道而馳,但追求“美”才是翻譯美學視域下的翻譯目標。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對譯者的創造性有一定的包容度才能為譯文讀者呈現出更加優質的譯文。但是強調發揮譯者的創造性不是允許譯者背離原文,肆意創作。任何事物都應把握一個度,發揮譯者的創造性并非否定翻譯的忠實性。正如上文所述,譯者的創造性也須基于原文的美學元素,換言之譯文必須符合原文的基本意義。譯者的創造性是作用于于對“美”的呈現方式,即語言表達形式,而并非原文的內在含義。
綜上所述,許淵沖的“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與翻譯美學理論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優勢競賽論”試圖在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中尋求翻譯的最優解。“優勢競賽論”與“再創論”打破了傳統翻譯理論中以“真”為尊的理念,是翻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對于翻譯美學理論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譯者對原文美感的傳遞必須經過譯者積極的、建設性的解讀才能完成,而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譯者的主體性因素。翻譯美學視域下,譯者的翻譯重心應是表達和創造“美”,但也并非是完全脫離原文的憑空描繪。“真”與“美”雖是一對矛盾體,但也具有同一性。“美”以“真”為基礎,“真”以“美”為目標。翻譯實踐中,可以采用劉宓慶所述的幾種或全部四種審美再現方式對同一原文進行翻譯后,相互比較各種譯法的優劣,從中選出審美性最佳的譯法。同時,譯者在審美再現時需要在“真”與“美”之間有所取舍,尋求一個適當的平衡點。許淵沖有關“真”與“美”關系的論述,對于翻譯美學視域下以“求美”為目的的翻譯實踐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許淵沖.譯文能否勝過原文?[J].教學研究.1982(02):39-47.
[2]許淵沖.譯學要敢為天下先[J].中國翻譯.1999(02):4-9.
[3]許淵沖.新世紀的新譯論[J].中國翻譯.2000(03):2-6.
[4]王厚平.美學視角下的文學翻譯藝術研究——許淵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0.
[5]方夢之.譯學詞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6]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M].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
[7]川端康成.雪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8]川端康成,葉渭渠譯.雪國[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9]川端康成,高慧勤譯.雪國[M].沈陽:沈陽出版社.1990.
[10]川端康成,林少華譯.雪國[M].青島:青島出版社.2011.
[11]周作人.周作人自編集:雨天的書[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40.
[12]李曉旭.《俳句》翻譯實踐報告[D].哈爾濱:哈爾濱理工大學,2018:17.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