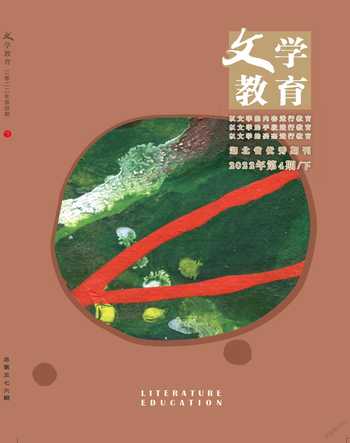雙域型概念整合下的狄金森詩歌研究
汪虹
內容摘要:狄金森詩歌風格獨特、想象力豐富,卻常讓人感到含混難解。將雙域型概念整合運用于狄金森詩歌解讀,能讓讀者從認知視角解析詩歌中的深邃涵義。
關鍵詞:狄金森 概念整合 雙域型
概念整合是一種思維認知方式,通過概念整合,人們可以更科學地解讀抽象概念、理解語言意義,也能更合理地解釋人類創造性思維和豐富想象力背后所蘊含的奧秘。從心理空間組織框架的角度進行分類,概念整合網絡模型可分為:簡單型、鏡像型、單域型和雙域型。四種概念整合網絡模型里,雙域型最為復雜,是一種較為高級的概念整合網絡模型,將雙域型概念整合網絡模型應用于狄金森詩歌解讀,必然能讓詩歌的鑒賞變得更具全面性和深入性。
一.雙域型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網絡通常會包含四個抽象空間:類屬空間、輸入空間一(源心理空間)、輸入空間二(目標心理空間)和合成空間。[1]雙域型概念整合網絡的兩個輸入空間的組織框架各異,且常有沖突,兩個輸入空間都有部分結構被投射至合成空間,并在合成空間里進行整合。由于雙域型概念整合的層創結構(兩個輸入空間的部分成分和結構選擇性投射到合成空間,通過組合、完善和擴展三種整合操作形成層創結構)具有和輸入空間完全不同的組織框架,因此,此網絡里的概念整合最具創造性。[1]
二.雙域型概念整合下的《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
狄金森運用豐富的想象力對“生”、“死”的真諦進行了各種探尋,寫下眾多有關“死亡”的詩歌,《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是其最為出彩的一首“死亡”詩歌。此詩里,“死亡”不再令人恐懼,它是一場與“死神”相約的浪漫出行。那么,詩人是如何將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變得如此愜意的?運用雙域型概念整合理論進行解讀,答案自會揭曉。
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他便好心地停車把我接上——/馬車里載的只是我倆——/還有“永生”為伴。║我們徐徐前行——他知道無須匆忙/而我已經撂下/勞作與閑暇/只為他的儒雅——║我們經過學校,孩子們正在嬉鬧/正逢課間休息——他們圍成一圈——/我們經過莊稼彌望的田地——/我們經過西下的夕陽——║或許可以說——是他從我們身邊經過——/露珠使我們渾身顫抖冰涼——/因為我的長裙,薄似蟬衣/我的披肩——只是絹紗——║我們在一幢房子前停步/它仿佛是地面隆起的小丘——/房頂幾乎模糊難辨——/屋檐——埋在地下——║自那以后——幾百年過去了——然而/卻覺得比那一天的時間更短/我第一次猜出那馬頭/原來是朝著永恒——[2]
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的兩個輸入空間分別為:“與‘死神’的旅行”和“死亡的過程”。“與‘死神’的旅行”輸入空間屬于具體事件,“死亡的過程”輸入空間屬于難以言表的抽象概念,盡管兩個輸入空間在組織框架上存在差異,但還是能夠在兩個輸入空間里找到一定的映射關系,如:“馬車”對應“靈柩”,“學校”對應“人經歷的少年階段”,“豐收的莊稼地”對應“人經歷的中年階段”,“夕陽西下的暮色”對應“人經歷的暮年階段”,“地面隆起的小丘”對應“墳墓”等。類屬空間體現了“與‘死神’的旅行”輸入空間和“死亡的過程”輸入空間的共享元素“旅途”。合成空間在“與‘死神’的旅行”輸入空間和“死亡的過程”輸入空間提取的部分組織框架為“具化的浪漫之旅”和“抽象的‘死亡’過程”,并在認知常識完善下得到層創結構:“與‘死神’的旅行和‘死亡’的過程具有相似性”。最后,通過擴展,也就是運行合成空間所產生的層創結構得出:“死亡”并不可怕,“死亡”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與“死神”邂逅的一場浪漫之旅。”正是詩人把“死亡”的過程具化成了一次另人心動的浪漫旅行,讀者對“死亡”不再心存恐懼,因為這里的“死亡”體驗不到任何的痛苦之感,也看不到任何的悲戚之景,連令人畏懼的“死神”也化身成為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他駕著馬車,在輕松、浪漫的氣氛里,帶著他的應邀者踏上生命最后的旅途。因此,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毛骨悚然的“死亡”成為一場愜意之旅是完全可行的。
三.雙域型概念整合下的《一條漸漸消失的路》
狄金森對“死亡”有著濃厚的興趣,對“大自然”也充滿了熱愛之情。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四季美景、浩瀚海洋都是狄金森筆下的詠頌對象,對“大自然”里居住的小動物們,詩人更是無比喜愛。“狄金森一生喜愛動物,她時常生動細膩地描述那些被她親切地稱為‘大自然居民’的幼小生靈。即便是一些在現實生活中不為人們喜愛的生靈,她也滿懷愛心地把它們看作生活的伙伴、叢林中美麗的居民”[3]。《知更鳥是加百利》《蜘蛛好似藝術家》《一條漸漸消失的路》等,都是狄金森詠頌“大自然居民”的名篇,而《一條漸漸消失的路》更是這些名篇中的經典。詩中,蜂鳥是詩人的詠頌對象,但全篇卻沒有“蜂鳥”二字出現。詩人是如何做到不著一字,卻又傳神地將蜂鳥意象展現給讀者的?通過運行雙域型概念整合,疑惑不復存在。
一條漸漸消失的路/有一只飛轉的車輪——/一聲祖母綠的反響——/一陣胭脂紅的奔騰——/灌木上的每一朵花/都擺正碰歪了的頭——/突尼斯來的郵件,或許/一次清晨騎馬閑遛——[4]
通過運行雙域型概念整合,“人的感官感受”和“蜂鳥的閃現與飛逝”成為《一條漸漸消失的路》的兩個輸入空間。“人的感官感受”是人通過視覺所看到的實物、通過聽覺所到的聲響;“蜂鳥的閃現與飛逝”是蜂鳥的行為。因此,兩個輸入空間都是具體事物。兩個輸入空間雖然都是具體事物,但“人的感官感受”和“蜂鳥的閃現與飛逝”在組織框架上的差異性是顯而易見的,兩個輸入空間里的映射關系主要表現為:“一條漸漸消失的路”對應“蜂鳥的飛行路線”,“飛轉的車輪”對應“蜂鳥的飛行速度”,“一聲祖母綠的反響”對應“蜂鳥的顏色和鳴叫聲”,“一陣胭脂紅的奔騰”對應“蜂鳥的顏色和速度”,“灌木上的每一朵花/都擺正碰歪了的頭”對應“蜂鳥飛過”,“突尼斯來的郵件、清晨騎馬閑遛”對應“蜂鳥的飛行”。類屬空間體現了“人的感官感受”輸入空間和“蜂鳥的閃現與飛逝”輸入空間的共享元素“蜂鳥”。合成空間在兩個輸入空間提取部分組織框架分別為“人在視覺和聽覺上的感官感受”和“蜂鳥的飛行過程”,并在認知常識完善下得到層創結構:“人在視覺和聽覺上的感官感受”就是“蜂鳥的飛行過程”。最后,通過擴展,也就是運行合成空間所產生的層創結構得出:人們看到一條逐漸消失的蜂鳥飛行路線。蜂鳥毛色艷麗,飛行速度極快,所到之處,完全看不出有它來過的痕跡,它的到來有如“突尼斯”般遙遠,也如“清晨騎馬閑遛”般平常隨意。可見,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詩人完全可以做到不著一字,卻能細致傳神地把蜂鳥的意象展現于讀者眼前。
四.雙域型概念整合下的《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
無論是探尋“死亡”的真諦,還是詠頌“大自然的居民”,狄金森的詩歌總是極具想象力,以致讀者對其詩歌的解讀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爭議性,最具代表性的是詩歌《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統計出對‘我的生命——一桿實彈槍——’的不同解讀多達79種”[5]。那么,這些見解各異的解讀是否都有其合理性?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答案是肯定的。
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在墻角里——直到有一天/主人經過——認了出來——/把我扛上肩——║現在我們在皇林漫游——/現在我們在把雌鹿捕殺——/每當我代他發號施令——/群山便立即響應回答——║我粲然一笑,熱烈的光輝/頓時照得幽谷燦爛——/就像維蘇威的面孔/讓它的歡樂涌現——║一到夜晚——我們美好的一天結束——/我守護著我主人的頭——/這勝過深深下陷的/鴨絨枕頭所得到的享受——║對于他的敵人——我就是死敵——/我的一只黃眼要是把誰瞄上——/或者要對誰痛下狠手——/誰要再動一下,休想——║雖然我比他——也許活得久/他一定比我——壽命更長——/因為我只有殺傷的本領,/卻沒有——去死的力量——[4]
“查爾斯·安德生認為,‘我的生命——一桿實彈槍——’以一個絕妙的玄學奇喻開始,全詩融合了民謠、吟游抒情詩、荒誕故事及格言詩的不同風格,表現了某種具有傳奇色彩的愛情、對愛義無反顧的忠貞、為愛而迷失自己的狂喜,同時也刻畫了世俗愛情的局限以及對永恒之愛的渴望” [5]。雙域型概念整合下,查爾斯·安德生的解讀不無道理。這里,“實彈槍”和“世俗愛情”為詩歌的兩個輸入空間。“實彈槍”是具體事物,“世俗愛情”是抽象概念,兩個輸入空間組織框架差異較大,但也存在一定的映射關系,如:“實彈槍”對應“戀愛中的女子”,“槍的主人”對應“愛慕之人”等。“實彈槍”輸入空間和“世俗愛情”輸入空間的共享元素體現在類屬空間的是——“忠誠堅定”。合成空間從“實彈槍”輸入空間和“世俗愛情”輸入空間提取的部分組織框架分別是“實彈槍的使命”和“義無反顧的愛情”。通過組合、完善和擴展得到的層創結構是:“(戀愛中的女子)‘我’甘愿為愛慕的對象付出一世忠誠,并傾盡全力為他效力。”由此可見,通過運行雙域型概念整合,查爾斯·安德生將《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解讀成一首愛情詩是有其可行性的,畢竟詩中“實彈槍”為“槍主人”誓死效忠的表現與陷入愛情且迷失自我的女子的行為如出一轍。
“保拉·貝內特認為,‘一桿實彈槍’象征著女性作者的創作力,它具有‘維蘇威’火山的力量,其破壞力對父權價值觀有著潛在的威脅”[5]。很明顯,保拉·貝內特是從女性主義角度對《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進行解讀,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這一解讀也是合情合理的。此解讀里,“實彈槍”仍然是其中一個輸入空間,但另一個輸入空間變成了“女性作者的創作力”。同樣,兩個輸入空間在組織框架上有差異性,“實彈槍”輸入空間是具體物體,“女性作者的創作力”輸入空間則是抽象概念。兩個差異性的輸入空間存在的映射關系是:“實彈槍”對應“女性作者”,“維蘇威火山”對應“巨大顛覆力”等。類屬空間展現了“實彈槍”輸入空間和“女性作者的創作力”輸入空間的共享元素“巨大威力”。通過組合、完善和擴展得到的層創結構是:“女性作家具有巨大的顛覆能力,她們通過作品創作,挑戰父權社會里的各種不公平。”基于此,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保拉·貝內特對詩歌的女性主義解讀是成立的。
“克勞迪婭·尤克曼認為‘我的生命——一桿實彈槍——’表現的是詩人、作品與讀者的關系。在她看來,狄金森以‘主人’作為詩人的象征,而‘我’自比‘實彈槍’則代表了詩歌作品”[5]。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克勞迪婭·尤克曼的解讀有其合理性:“實彈槍”依舊是兩個輸入空間中的一個,另一個輸入空間則是“詩歌作品”。“實彈槍”和“詩歌作品”雖然都是具體事物,但組織框架仍有差異性,“實彈槍”屬于殺傷性極強的武器,“詩歌作品”卻是抒情言志的文學作品。但不可否認,兩者間仍然存在一些跨空間映射關系:“實彈槍”對應“詩歌作品”,“槍的主人”對應“詩人”等。兩個輸入空間在類屬空間所表達的共享元素是“影響力”。合成空間從“實彈槍”輸入空間和“詩歌作品”輸入空間提取的部分組織框架分別是“實彈槍的威力”和“詩歌作品的影響力”。通過組合、完善和擴展得到的層創結構是:“像實彈槍般有威力的詩歌作品是得到詩人自己認可的作品,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會對讀者產生影響力”。
查爾斯·安德生、保拉·貝內特和克勞迪婭·尤克曼對《我的生命佇立——一桿實彈槍——》的解讀只是眾多解讀中的代表,還有許多獨到的解讀未能列舉,雖然不能說這些解讀都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雙域型概念整合下,查爾斯·安德生、保拉·貝內特和克勞迪婭·尤克曼三位批評家的解讀是完全可行的,他們讓讀者從不同認知視角體驗到了狄金森詩歌的多樣魅力。
雙域型概念整合的層創結構極具創造性,能產出原輸入空間沒有的信息、意義和知識,它是整個概念整合的核心結構。因此,通過運行雙域型概念整合,讀者能更好地解讀狄金森詩歌,讓看似含混難解的詩歌變得極具哲理性。
參考文獻
[1]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131-134.
[2]劉守蘭.英美名詩解讀[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512-513.
[3]劉守蘭.狄金森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212-213.
[4](美)艾米莉·狄金森著,蒲隆譯. 狄金森詩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151,226-227.
[5]劉曉暉.狄金森與后浪漫主義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56, 54,55,56.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優秀青年項目“認知詩學視角下的狄金森詩歌藝術風格研究”(20B5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邵陽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