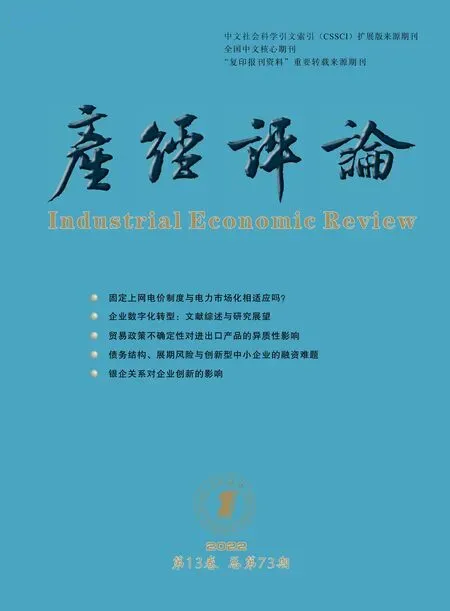數字時代物流業的服務轉型:基于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視角
陳 曦 丁 旭 馮 濤
一 引 言
產業生產要素投入中主導生產要素的變遷反映出產業結構的轉型。進入數字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生產要素不再限于傳統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成為新興的重要生產要素(于立和王建林,2020)。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在提升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對部分勞動力產生替代作用(唐波和李志,2021)。近年來,人工智能設備和大數據生產要素的廣泛應用,推動著物流業進入智能時代,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著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技術對人力的替代。技術發展史上的重大變革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自此機器開始大規模替代手工勞動(Yin et al.,2017)。從工業文明進入信息文明,技術進步產生的替代效應逐漸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傳遞(David和Dorn, 2013)。技術對人力的替代呈現出日益加速的發展趨勢。隨著智能化手段的大范圍運用,信息技術是否會對勞動力就業造成破壞引起了廣泛討論。雖然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就業既有負向的破壞效應,也有正向的創造效應(王君等,2017);但在勞動力的不同層面和領域,技術影響不同(邵文波等,2018)。一方面,智能支撐系統提高了人的勞動生產率(朱巧玲和李敏,2017);另一方面,智能化也在一些領域開始替代人的工作崗位(張慧,2018)。雖然一些來自宏觀經濟系統的證據顯示技術進步并未造成太大的就業問題(Autor et al.,2003;Dauth et al.,2017; Graetz和Michaels, 2015),但在不同產業和企業層面,信息技術與勞動力的關系猶待深入分析。
傳統物流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數字時代,物流業成為智能化服務轉型升級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信息技術廣泛運用提升了物流業的績效(李丫丫等,2018),物流業的生產服務模式從人力主導轉型到智能控制,在集人工智能、物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以及信息處理等技術為一體的智能物流系統支撐下,無人機、無人車、倉儲機器人及智能快遞柜等設備被廣泛運用到物流的各個環節。生產服務方式的轉型重新定義了物流業中人與技術的關系。本文基于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視角,分析數字時代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構性變遷,以及中美代表性物流企業智能化的現狀,進而探討物流業生產服務過程中信息技術對勞動崗位的替代和互補效應,并提出數字時代物流業服務轉型的實施路徑。
二 數字時代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構性變遷
生產要素是生產過程的投入資源,是來自上一生產階段或生產過程的產品(于立和王建林,2020),主要包括勞動、土地、資本、信息等,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信息技術也作為獨立要素投入生產。不同產業發展階段核心要素投入不同(李剛和何煉成,2005)。一方面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受到技術進步影響,技術進步能降低相對價格較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比例;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會改變資源結合方式,從而提升生產效率。
(一)理解數字時代信息技術與勞動力的關系變遷
計算機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驅動著產業進入數字時代。計算機信息技術對于組織運營的滲透呈現自底向上、從手到腦、由物及心的歷程,從低層到高層、從執行層到戰略層的發展。具體體現為信息系統的迭代更新。如圖1所示,從事務處理系統(TPS)、管理信息系統(MIS)到決策支撐系統(DSS),信息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關系從替代體力,到替代腦力,智能系統已經日益接近于人的本質。隨著智能決策支撐系統日益成熟,信息系統的應用達到社會智能系統階段,在這個階段機器開始替代人的心智模式,計算機信息系統相互聯通融合成為連接全人類的社會信息系統,具備閉環反饋、自動適應、主動響應三個社會信息協調控制機制(陳曦,2017)。

圖1 企業信息系統演進視角下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過程
智能化的深度運用引發關于信息技術與勞動力關系邊界重構的廣泛討論,按照替代性和互補性的偏重方向,衍生出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吞噬取代四種范式(陳春花和梅亮,2019)。雖然互利共生是一種最為理想的人機關系,但在復雜社會系統中,鑒于信息技術與勞動力的關系在不同領域存在差異,在相對長遠的時空范疇,四種范式將會并存。特別是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將成為產業升級進程中難以回避的陣痛。
(二)物流業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的時間臨界點
生產要素的成本隨著技術進步和時代發展而演變。當一種要素的單位使用成本高于另一種要素時,就存在用價格較低的要素取代價格較高要素的激勵,此時替代性開始顯現。社會發展演進趨勢表明,技術進步使生產設備成本持續下降,而教育投入增加導致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金三林和朱賢強,2013)。因此,企業出于對生產要素投入成本效益的權衡,在同等產出效率的條件下,會使用單位成本較低的生產要素去替代單位成本較高的生產要素。從現實情景來看,一方面近年來中國人口紅利下降,人力成本逐年上升,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外遷(原新和金牛,2021);另一方面工業4.0戰略廣泛推廣,國家和企業層面大力投資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智能化設備的應用成本逐年降低(Karel et al.,2021)。
本文通過建立物流機器人成本函數和物流勞動力成本函數,描述兩種生產要素成本隨時間的變化軌跡與趨勢,以找出替代效應開始顯現的時間點。兩條曲線相交時的交叉點是替代臨界點,臨界點所對應的時間就是勞動力單位價格超過物流機器人單位價格的時間點,即替代效應開始產生的時間臨界點。基于對成本函數的描述與估計,物流機器人成本及物流勞動力成本曲線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

圖2 物流機器人成本及物流勞動力成本曲線變化趨勢圖
當前物流機器人每臺成本約70萬元,而機器人成本在未來十年內會下降一半。內資企業固定資產殘值比例為5%, 新企業所得稅法固定資產折舊年限中規定,飛機、火車、輪船、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折舊年限為10年,飛機、火車、輪船以外的運輸工具為4年。目前業界對物流機器人的所屬類別仍存在爭議,因此分別按照10年和4年對物流機器人的采購成本進行折舊。若對物流機器人進行10年折舊,物流機器人成本曲線將和物流勞動力成本曲線在2016年附近相交,此點為物流機器人對物流勞動力產生替代效應的近期臨界點。若對物流機器人進行4年折舊,物流機器人成本曲線將和物流勞動力成本曲線交于2023年左右,此點為物流機器人對物流勞動力產生替代效應的遠期臨界點。替代時間臨界點的到來意味著自該時點開始,物流機器人的平均使用成本將低于勞動力,企業隨即產生激勵,對智能設備進行更多投資,以替代勞動力。隨著時間推移,激勵將逐步增強,使得信息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作用日益顯現。
現實表明,自2016年以來,物流機器人日益頻繁地出現于公眾視野,智能物流設備成為各大物流企業爭相投資的領域。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倉儲類智能機器人的增長率明顯提升。2017年中國物流AGV機器人(一種移動運輸設備)銷量達到1.35萬臺,與2016年同比增長101.6%;隨著AGV機器人在其他領域的滲透,2018年中國AGV機器人銷量已達到2.96萬臺,與2017年同比增長119%。此外,2017年,順豐員工總人數及操作類崗位員工數均呈現不同幅度的下降,京東倉儲崗位員工數量下降,進一步提供了替代臨界時間點到來的事實證據。
三 中美代表性物流企業的智能化
產業要素投入結構的變革改造了企業的生產或服務行為。作為廣泛應用智能化的行業,信息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物流企業中均有體現(Ahmad et al.,2018)。本部分從物流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和物流企業的具體做法兩方面詮釋數字時代中美代表性物流企業智能化發展的現狀。
(一)代表性企業的替代彈性估計
生產函數可以反映不同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要素替代彈性描述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性質和替代能力的大小(Robinson,1953)。在物流企業中,信息技術和智能化生產設備的投資,主要表現為智能產房、計算機設備、物流機器人等固定資產購置(王洪艷,2013),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企業資本要素投入變動中。物流企業中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表明了資本和勞動力的關系屬于替代性還是互補性,進而可以作為反映物流企業服務轉型的一項表征。
以不變替代彈性生產函數模型(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Arrow et al.,1961),該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影響(陳登科和陳詩一,2018)。原函數模型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即產出與生產要素的投入等比例增加,未考量企業規模報酬的實際特征。因此,在CES函數模型的基礎上引入規模報酬參數m
,當m
=1(<1,>1)時,表明研究對象是規模報酬不變(遞減,遞增)的。京東和順豐均是我國現階段最為消費者耳熟能詳的物流服務企業,兩家企業同在香港上市,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5月28日,順豐和京東分別為我國市值排名前兩位的物流上市公司;UPS則是全球領先的物流服務企業。因此,本文選取中國京東(JD)、順豐(SF)以及美國的UPS(United Parcel Service)三家代表性物流上市企業的數據進行分析。1.計算模型。測度物流業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時,采用固定資產和勞動力變動衡量投入,使用企業營業收入衡量產出。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于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年報,對應科目如表1所示,數據不存在因分類標準和統計口徑不統一所帶來的估算誤差偏大問題。

表1 指標、數據來源及計算方法
首先構建計量模型:

(1)
通過數據整理及分析發現,中國樣本企業中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具有共同的向上變化趨勢,為了避免虛假回歸,對變量進行一階差分,使之成為穩定序列,再建立差分模型式(2); 而美國樣本企業不存在上述趨勢,因此采用計量模型式(1)。

(2)
再構建回歸模型:
Y
=β
+β
X
+β
X
+β
X
+ε
(3)
其中被解釋變量Y
=lnY
,解釋變量X
=lnK
,X
=lnL
,X
=(lnK
-lnL
),進而得到參數估計值:A
=e
(4)
m
=β
+β
(5)

(6)

(7)

(8)
最終可根據式(8)得到替代彈性σ
的估計值。其中,待估參數A
為效率系數,m
為規模報酬參數,δ
為分配系數,ρ
為替代參數。選擇在ρ
=0處展開Taylor級數,當ρ
=0時要素替代彈性σ
=1,即模型退化為C-D生產函數,因為C-D生產函數具有普遍適用性,所以假定ρ
為接近于0的數,當參數估計完成后,根據ρ
的估計值是否接近于0,以檢驗此方法的可用性。2.數據說明。本研究收集了京東、順豐及UPS 2016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1季度財務報表的相關數據,對小部分存在缺失的數據進行舍棄。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企業原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中國代表性物流企業呈現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特征,配送和倉儲環節的勞動力占比最高,以京東為例,近五年來,配送和倉儲崗位的員工人數占比分別達到員工總數的54%和20%。相對于中國企業,美國UPS員工總人數近幾年保持穩定。
3.估計結果。基于計量模型,分別對三家物流案例企業進行實證數據分析,并計算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具體如表3所示。

表3 三家物流企業中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
(二)案例企業的智能化程度
1.領先者:美國物流企業UPS智能化程度較高。美國物流企業UPS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數值顯著大于1,處于替代關系。UPS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遞承運商與包裹遞送公司,同時也是運輸、物流、資本與電子商務服務的領導性提供者,自2016年前后開始引入AI人工智能物流運輸服務系統,并著力打造智慧物流科技,利用現有的龐大數據庫,支撐經營決策,UPS每年投入超過十億美金用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利用智能技術整合供應鏈,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2.后進者:中國物流企業順豐智能化相對落后。順豐物流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顯著小于1,為0.795。2019年初,順豐開始籌資進行物流智能化和數字化建設,新增近4億元研發投入以布局下一代物流信息技術,將智能物流布局分為三個方面:自動分揀、無人機應用以及客戶體驗。順豐優勢在于高效的運輸網絡,但相對于其他兩家企業,其大力發展智能化起步相對較晚,因此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處于相對低值。
3.追趕者:中國物流企業京東加速智能化進程。京東物流持續向著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其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為1.001。2008年京東建成首個自動化倉庫,逐步在存儲、揀選、包裝、輸送、分揀等環節投入自動化技術;2016年,開始探索智能物流,自主研發智能化物流技術設備,此后,京東無人倉、無人車、無人機不斷出現;2017年,開始致力于數字化和智能化的供應鏈改造;2019年,京東物流全國首個5G智能物流園區正式投入運營,涵蓋智能園區、智能樞紐、智能倉儲三大領域;同年,京東物流全面投用亞洲規模最大的一體化智能物流中心——東莞亞洲一號,在各個環節均大規模應用了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自主研發的“智能大腦”具備調度、統籌、優化以及數據監控全方位功能,利用京東物流十幾年來積累的復雜訂單處理能力和算法優化,提高了各環節的運轉效率和服務質量。未來,京東物流還將持續向著運營“無人化”的方向發展。這些事實從客觀上印證了京東物流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近年來的持續上升。
圖3呈現了近年來中美三家主要物流企業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的演化情況。我國物流企業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京東由小于1,逐步上升,至2019年超過替代臨界點1。美國物流公司UPS亦在2018-2019年跨越了彈性臨界點,從0.804上升至1.095。美國物流企業整體智能化程度相對較高,但以京東為代表的中國物流企業正在加快智能化進程。

圖3 中美物流企業資本對勞動力替代彈性逐年演變趨勢
四 物流業服務轉型的技術應用
數字時代新經濟模式崛起,智能技術在物流業中持續滲透。總體來看,目前我國物流業發展程度并不均衡,大部分物流企業仍處于手工向機械化過渡的階段。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物流業在京東、順豐等龍頭企業的帶動下,步入智能化深度發展軌道,其服務轉型進一步表現為信息技術對服務系統和勞動崗位結構的重構。
(一)物流企業智能化服務系統架構
我國物流業服務模式正在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型。這期間,智能技術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如圖4所示,智能化進程中,物流業服務轉型采用的信息技術主要包括:物聯網、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分析、智能決策、自動化分揀、配送機器人等。這些信息技術推動了物流企業傳統服務方式的變革,重塑著物流業服務系統的組織架構。

圖4 物流企業智能化服務系統架構示意圖
1.信息技術重構物流業管理信息的底層邏輯。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以重塑信息管理底層邏輯的方式對物流業的生產服務組織形式進行改造,具體體現在:(1)確保數據采集的實時與精確,基于物聯網技術實現主體間的有效連接和交互。(2)提高供應鏈協同效率,降低信息成本,運用區塊鏈技術保護信息傳遞和共享的安全。(3)確保信息接入的靈活性、彈性以及韌性,采用云計算為供應鏈節點提供數據接入,滿足管理需求。(4)提升物流系統的整體響應能力,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提高供應鏈的快速響應能力,依靠人工智能迅速做出商業決策。(5)精準定位并滿足用戶需求,運用大數據技術,結合商業數據的收集和全網輿情數據的分析,全方位挖掘用戶需求特征,洞察隱性需求,并將隱性需求轉化為顯性需求,提升服務質量。
2.物流業執行層的基礎工作向少人化發展。傳統物流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企業的執行層聚集了大量勞動力。進入數字時代,物流業服務轉型最典型的特征在于運用智能化工具替代手工重復性勞動和體力型勞動,具體體現為將智能化應用于各個物流環節:(1)分揀環節,物流分揀日益依靠智能分揀、機器人設備、無人設備以及自動化設備等替代簡單勞動。(2)干線作業,干線作業的運輸活動由大型無人機和無人卡車來實現;物流企業也在不斷布局無人駕駛技術,眾多企業獲批開通無人機物流航線,亞馬遜已申請無人卡車的相關專利,而京東也在積極布局物流無人車。(3)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作業通過小型無人機和3D打印實現;2017年京東成立無人機運營調度中心標志著無人機在國內基本可大規模商用,在人口密集程度相對較小的區域如農村地區配送。(4)用戶接觸點,大量使用智能快遞柜這種成本低、應用廣的智能設備,對配送員的工作職能帶來巨大改變。
3.物流業管理控制和決策自動化、無人化。在智能化改造下,物流業的管理控制和決策向自動化和無人化發展,具體體現在:(1)生產服務組織形式以消費需求驅動,通過數據賦能,自動靈活調整配送體系以提高需求響應及時性,提升消費體驗。(2)倉儲和分揀作業逐漸走向融合,裝卸搬運作業是倉內作業和其他作業的銜接點,為了銜接的便利性和快速性,裝卸搬運逐漸和倉儲分揀活動共同走向自動化和無人化。(3)管理決策過程日益自動化,智能化進程促使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由進行業務流程重組或再造導致部分崗位調整,發展到機器可以模仿勞動者思維和行為,智能物流系統不僅可以代替手工勞動,還對管理決策勞動進行替代。(4)擴展企業邊界,協同產業上下游,基于物流云平臺,物流企業可以和上下游企業進行數據共享,實現了物流業邊界的延伸和拓展,同時將重構原有的服務模式、分工體系,進而影響勞動力資源配置。
(二)物流業關鍵服務環節中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
智能化背景下,物流業服務方式的改變造成各個業務環節中均出現信息技術與勞動力關系的重構。信息技術替代部分勞動力的同時,也催生了新的勞動力需求。物流業的服務環節主要包括運輸、倉儲、配送、裝卸搬運、信息處理等,表4對智能化進程中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的崗位,以及催生的新勞動崗位進行了總結。

表4 物流智能化背景下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
1.信息技術對傳統物流業勞動力具有顯著替代性。智能化進程伴隨著對從業勞動力技能的更新與重塑。若原有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較好,能夠較快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行業技能需求結構變化,則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性較小(鐘仁耀等,2013)。傳統物流業從業者以倉儲管理、配送等可重復、體力勞動者為主,這部分勞動附加值較低,勞動力面臨失業的可能性更高。運輸和信息處理崗位原有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相對與智能化的需求較為接近,更有可能經過培訓而適應智能化的生產方式。
2.智能化催生的勞動崗位普遍具備更高的附加值。智能化進程催生的勞動崗位分為三類:專業型技術崗位、銷售崗位和復合型管理崗位。專業型技術崗位對技術技能要求最高,銷售崗位對人際技能要求最高,復合型管理崗位不僅要求管理人員具備一定的技術技能和人際技能,還需具備相當的概念技能。這些崗位勞動力的知識水平較高,其勞動也具備更高的附加值。
3.智能化對勞動力重塑最終走向人機共生的狀態。智能化拓寬且加深了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影響范圍:傳統的機器和自動化設備代替勞動執行常規任務,解放了“手”;機器人和基于計算機的自動化設備可進行認知與分析,支撐決策制定,輔助了“腦”。基于智慧物流體系的架構,執行層的從業者有很大的可能被智能化取代;而計劃組織層及決策層通過利用智能化系統,基于算法和模型指揮企業的運作與管理,信息技術與勞動力形成互補關系,進入人機共生的狀態。在手工操作層面,智能化替代了簡單勞動力,而管理決策層面,智能技術成為勞動力的“第二個大腦”,人機交互協同創造價值。
五 數字時代我國物流業服務轉型的實施路徑
產業經濟系統實現有序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是協調好生產要素間的配比關系(欒大鵬和歐陽日輝,2012)。進入數字時代,新興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催生了以智能化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工業4.0時代,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生產服務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張雍達和宋嘉,2021)。基于前文分析,我國物流業服務轉型的實施路徑主要有:
(一)從業者勞動力升級:簡單重復→技術賦能
傳統物流業的服務組織形式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經濟下的簡單體力重復。數字時代,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驅動著物流業推進服務轉型,其生產服務組織形式向著自動化、智能化方向發展。物流業傳統的勞動力結構無法與智能化相適應。因此,數字時代物流業的服務轉型需以勞動力的升級改造為邏輯起點。物流業要將勞動力結構的優化與提升作為系統性工程,進行長期籌劃,促進信息技術賦能勞動力,讓技術應用帶動勞動力成長。物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勞動力從簡單重復到技術賦能的轉型:一是有效宣傳物流業轉型趨勢,幫助傳統的物流從業者,特別是工作在生產經營一線的體力勞動者,認清智能時代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趨勢,提前儲備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持續提升職業技能,擴大自身職業技能與機器能力的異質性,為迎接我國物流業走向機器大規模替代簡單重復勞動力的時代做好準備。二是加強信息技術實操技能培訓,面向智能時代的需要,開發適用于幫助傳統勞動力盡快適應數字時代變革要求的知識技能培訓課程體系,推廣科技向善理念,幫助傳統崗位從業者適應產業的智能化進程。三是提升勞動力技能結構復合性,提前部署儲備,穩步推進物流業勞動力結構整體升級以適應智能時代物流業服務模式的快速變化。通過技術賦能,推動勞動力升級,優化勞動力結構,積極推動服務轉型,以促進物流業優化升級。
(二)關聯產業融合推動:被動響應→主動嵌入
產業轉型是數字時代重要的議題。伴隨著國內要素成本增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我國的傳統產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亟待升級轉型(丁志帆,2020)。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低碳引領、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可見,物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撐服務作用。構成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物質、能量和信息。進入數字時代,數字信息成為產業生產的驅動要素,從而對傳統產業鏈的邊界進行了重構。只有信息技術在整個產業經濟領域普遍應用并引發產業全面變革時,才真正實現了新型工業化(周振華,2000)。數字化促進了產業合作與融合,大數據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對要素流通的約束,提供更多關于合作者質量的信號(江小涓,2017)。
一體化的產業合作體系,要求產業集群在具備相應規模的基礎上,面向全球提升資源整合與創新能力(黃利春和梁琦,2021),跨界融合是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肖旭和戚聿東,2019),而信息化通過跨界融合機制,使得傳統產業價值創造的邏輯發生根本性變革(丁志帆,2020)。如圖5所示,價值創造的過程依賴于現實世界的物質流通,物流業服務轉型同步于信息化對產業系統的影響,并且從被動響應式的業務提供向主動嵌入式的服務響應轉型。

圖5 物流業基于信息技術主動嵌入各產業集群
(三)生產服務運營數智發展:技術替代→人機共生
我國物流業需要在積極推動生產服務運營智能化發展的同時,注意信息技術對勞動力替代帶來的潛在社會問題。一方面,為了適應數字時代發展,物流業需要廣泛運用信息技術對生產服務組織形式進行重構,穩步加大智能化投資;對于企業而言,智能化的廣泛和深入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實現生產服務運營智能化發展,讓信息技術更好地支撐勞動力,實現人機共生;特別是對于挑戰性任務,人機協作的模式在現實中更為可靠(David, 2015)。另一方面,在物流業數智化發展的同時,政府需要采取合理的調控手段,維持信息技術替代與勞動力升級節奏之間的平衡。曹靜和周亞林(2018)認為對機器人征稅,將會減緩物流業智能化的速度,作為勞動力崗位轉換和再就業的緩沖,這部分稅收收入可用于支持勞動力再就業培訓,從宏觀上平衡信息技術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在物流業服務轉型的進程中,政府、行業、產業鏈、企業、從業者等各方需要形成協同,防止信息技術大規模替代勞動力的社會風險出現,調控相應的風險沖擊,促使物流業的智能化服務進入人機共生的良性模式。
六 結論與啟示
服務轉型是數字時代傳統產業升級的基本邏輯,其代表性特征就是生產要素投入的變化。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物流業的智能化進程正在對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圍繞數字時代物流業的服務轉型,基于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視角,試圖從三方面詮釋數字時代物流業的服務轉型:一是分析數字時代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構性變遷,梳理信息技術進步與勞動力關系的演化過程,進而通過物流機器人和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分析信息技術大規模替代勞動力的時間臨界點,而這個時間臨界點已經到來;二是梳理中美主要物流企業智能化應用現狀,通過計算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發現美國的UPS、中國的京東和順豐處于不同的智能化發展階段,分別屬于領先者、追趕者和后進者,中國物流企業正在加大智能化的投入;三是探討物流業服務轉型中信息技術對勞動崗位的影響,面向智能技術應用的具體操作設計層面,分析物流企業智能化生產系統架構,進而通過探討物流業關鍵生產環節中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分析勞動力替代的范圍與程度。
基于對現實問題的分析,發現我國物流業不斷深化服務轉型,向著全面智能化方向發展,行業整體逐步加大對智能設備的投資,走入信息技術替代簡單重復勞動力的進程。雖然相比美國物流企業,我國物流企業的智能化尚有較大提升空間,但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目前的發展水平與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適應性。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還有成長空間,物流業中存在著大量的體力勞動者,倘若信息技術替代勞動力的速度過快,可能會產生結構性失業,給社會系統帶來巨大沖擊。信息技術應用與創新的目的在于提升勞動力技能水平,而非取代對勞動力的需求(Trajtenberg, 2018)。信息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節奏需要與社會發展、產業成長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否則會導致系統性失衡。因此,數字時代我國物流業服務轉型應該從勞動力升級(從簡單重復到技術賦能),到重構產業底層邏輯(從被動響應到主動嵌入);在實現生產服務運營智能化的基礎上,推動信息技術與勞動力的關系由相互替代走向人機共生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