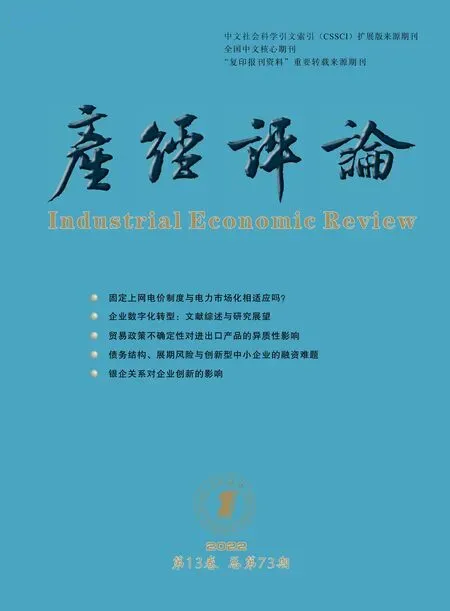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實證證據
陸海波 汪小圈
一 引 言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中國面臨的外部發展環境不穩定性明顯增加。美國近年來開始施行逆全球化戰略,對中國帶來最廣泛影響的是2018年對中國250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提高關稅,涉及貿易額占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一半,其中包括對5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對2000億美元的產品加征約15%的關稅,而2019年5月美國又將這2000億美元產品關稅提高至25%。在此期間,中國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對美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最終于2020年1月15日達成第一階段談判結果,但對絕大部分產品加征的關稅并未調整。可見中美貿易摩擦所帶來的貿易壁壘提升至今都影響著相關出口企業。投資決策作為企業最重要的公司金融決策之一,中美貿易摩擦對微觀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是什么?回答該問題不僅有助于解釋中國企業投資決策行為,同時為評估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提供實證證據,對后續中美貿易談判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遺憾的是,現有文獻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微觀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研究較少,與本文高度相關的僅有三篇實證論文,分別研究中國加入WTO對美國企業投資的影響(Pierce和Schott,2018),土耳其反傾銷政策對本國企業投資的影響(Avsar和Sevinc,2019),與中美貿易摩擦對美國企業投資的影響(Amiti et al., 2020)。與他們不同的是,本文基于2016年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2016-2019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季度財務數據以及美國對華征稅清單,以中美貿易摩擦為準自然實驗事件,采用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估計模型,首次考察中美貿易爭端對中國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
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投資的潛在影響渠道有兩個:一方面,中美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爭端和談判使得兩國的關稅政策出現非常大的不確定性,這種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對微觀企業投資決策產生很大影響。研究不確定性的文獻(Bloom et al., 2007; Bloom, 2009)指出更高的不確定性會使得企業投資決策更為謹慎,企業在短期內會暫停投資與雇傭,但在中期可能恢復其投資與雇傭。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的開始與升級使得中國企業面臨的貿易壁壘不斷提高,從而降低受影響企業的總體出口。出口減少的直接影響是受影響企業的總產出市場變小,企業投資帶來的收益減少,因此導致企業投資意愿降低。這兩個渠道對短期企業投資行為的預測一致,但中期的預測并不一致,因此還需要通過實證分析來確認哪個渠道占據主導。
本文利用美國對華征稅清單、中國海關貿易數據與中國上市公司季度財務數據,通過構建企業層面受美國對華出口品加征關稅的影響指標,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顯示,美國宣布第一次對華出口品加征關稅后,受此份征稅清單影響越大的企業會顯著降低其投資。此后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宣布第二份更廣范圍的征稅清單后,受兩次征稅清單影響越大的企業并未顯著改變新增投資率,而其投資存量甚至出現上升。為證實這些發現的穩健性,本文首先將研究對象縮小至制造業企業,由于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主要針對制造業出口品,因而制造業企業更能反映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樣本縮小后,基本結論不變。此外,本文還采用PSM-DID方法以緩解選擇偏差問題,為實驗組企業(受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找到與之傾向得分最接近的對照組企業(未受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基于這個新樣本的雙重差分模型給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最后,本文探討了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企業投資的渠道,通過對銷售收入進行境內和境外的分解發現,征稅清單公布后,境外銷售收入占比顯著下降,而境內銷售收入的絕對值顯著上升,且總銷售收入的絕對值變化不顯著,即原來銷往境外的出口品轉為內銷,說明“市場規模效應”這一渠道影響有限,因此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渠道主要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這一發現還從側面印證此后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性。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研究問題的創新,過去文獻缺乏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本土企業投資影響的證據,本文利用中美貿易摩擦來研究直接受到美國對華征稅清單影響的中國企業的投資行為。二是本文在企業-產品層面深度整合美國對華征稅清單、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與中國上市公司季度財務數據,全面考察和衡量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企業在投資行為上的變化,相比既有研究,指標的度量更為準確地體現了企業受到美國對華出口品加征關稅的微觀影響。三是為中美貿易摩擦及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提供一定政策參考,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長久且深遠的,而投資又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從微觀角度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投資的影響,可以幫助我們判斷未來如何應對第二輪中美貿易談判,以及在國內實施何種政策以減輕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而本文也從側面說明開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性。
后文內容具體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顧文獻,提出研究假說;第三部分為實證研究,介紹實證研究設定、數據,分析基準回歸結果,對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并討論研究結果的潛在原因;第四部分結合現實對全文進行總結。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與以下兩支文獻有關:(1)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影響的研究;(2)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決策行為影響的研究。下面將首先回顧這兩支文獻,并討論本文在文獻中的位置。然后基于現有文獻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
如引言中所言,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的影響的文獻不多。既有文獻對貿易自由化的研究稍多,主要集中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如達成單邊或多邊貿易協定,對企業投資的影響。Handley和Lim?o(2015)建立理論模型證明當需要投入巨額不可逆投資(Irreversible Investment)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降低企業出口投資行為,而達成特惠貿易協定則會增加出口投資。他們通過結構模型估計發現,葡萄牙加入歐盟獲得特惠貿易待遇帶來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可以解釋61%葡萄牙出口企業的增加與87%出口金額的增加。Pierce和Schott(2018)研究中國加入WTO(中國獲得美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對美國本土企業投資的影響發現,貿易自由化的“促進競爭效應”會導致進口競爭越激烈的行業投資下降越多,行業中工廠的退出是行業投資變化的主要來源。在全球化背景下,針對貿易壁壘增加的相關文獻更少,Avsar和Sevinc(2019)研究發現土耳其對外反傾銷確實顯著提升了本國企業對固定資產與研發的投入。而近年來逆全球化現象不減,使得貿易壁壘有所增加,本文研究中國企業在貿易壁壘增加后的投資變化,嘗試豐富這一問題的研究。
雖然國內沒有直接分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影響的研究,但不少研究探討了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賈倩等(2013)發現省級地方官員變更帶來的區域政策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顯著減少投資。李鳳羽和楊墨竹(2015)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對企業投資產生抑制作用。但饒品貴等(2017)進一步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高時,企業投資效率隨之提升。徐光偉等(2019)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準自然實驗,證實不確定性沖擊后,企業減少實物資產投資,同時增加金融資產投資。本文從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角度對這支文獻進行補充。
另一支相關文獻是中美貿易摩擦對微觀企業決策的影響研究。He et al.(2021)利用51job招聘網站上發布的職位信息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用人需求的影響發現,受美國對華出口品征收關稅影響越大的企業,發布招工信息更少、提供的工資更低。Cui和Li(2021)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對新企業進入的影響發現,美國對華關稅增加會帶來新企業進入率的下降。由此可以說明中國企業在美國加征出口關稅后會調整企業的外延邊際(Extensive Margin),本文考察企業是否會調整其投資策略,也是對現有文獻內涵和外延的補充。
與本文關注問題最相近的是Amiti et al.(2020)關于中美貿易摩擦對美國企業投資影響的研究,但他們采用的實證方法與本文存在很大區別。首先,衡量企業層面加征關稅的影響的方法不同,他們使用事件研究中的股票市場反應(可以視為“預期”影響)并對其進行分解得到加征關稅對企業的異質性影響,而本文通過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將企業產品層面的出口數據與美國加征關稅的產品清單合并,得到企業層面受美國加征關稅的“實際”影響,區別在于本文著重關注企業出口產品受到貿易摩擦的直接影響,而Amiti et al.(2020)的測度中則包含了直接與間接影響。其次,在考察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時,Amiti et al.(2020)利用投資Q理論中企業的市值賬面比等于其預期資本回報率,得出企業資本回報率,從而推算美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投資率變化,而本文直接使用企業在季度報表中報告的企業層面實際投資,區別在于Amiti et al.(2020)只能估計總體投資率變化,不能細化到企業層面,而本文基于企業層面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考察美國加征關稅對中國企業投資決策的直接影響。
(二)研究假說
下面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為什么會對企業投資產生影響以及會產生何種影響。
首先,中美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爭端和談判使得兩國的關稅政策出現非常大的不確定性,這種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對微觀企業投資決策產生很大影響。研究不確定性的文獻為預測不確定性如何影響公司決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實物期權理論指出,對未來投資收益狀況缺少信息讓等待更有價值(Dixit和Pindyck,1994)。更高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未來投資的實物期權價值,因為一旦投資失敗,不可逆的實物資產投資面臨高額的退出成本,所以不確定性增加會使得企業對投資決策更為“謹慎”(Bloom et al., 2007)。當不確定性突然提高后,企業會經歷短暫的快速衰退和復蘇,即在短期內企業會暫停投資與雇傭,但中期來看企業產出、員工和生產率會上升(Bloom,2009)。因此,不確定性的理論文獻較為明確地預測短期內企業選擇“等著看(Wait and See)”,降低新增投資,而中期可能會在投資上迎來復蘇。
其次,中美貿易摩擦的走向與結果使中美對雙方出口的貿易壁壘均提高。對貿易壁壘提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傾銷領域,這些研究對預測中美貿易摩擦對投資的影響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當外國對中國出口品提高關稅時,國內企業很可能失去發起國未來的出口機遇,從而導致涉案企業的產出市場縮小(Prusa,1996)。雖然受影響企業會向第三國市場出口更多產品以緩解反傾銷帶來的壓力,但總體而言貿易壁壘提高對受影響企業的出口會有負面影響(Konings和Vandenbussche,2008)。出口減少的直接影響是受影響企業的總產出市場變小,企業投資帶來的收益減少,因此導致企業投資意愿降低,稱之為“市場規模效應”。根據“市場規模效應”的預測,中美貿易摩擦引起的貿易壁壘提高會使企業降低投資。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本文的研究假說:中美貿易摩擦在短期內會導致企業新增投資減少,中期企業投資的變化方向不明確,取決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以及市場規模效應的綜合影響。
三 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本文關注中美貿易爭端這一外生貿易政策沖擊。2018年3月,美國公布對5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的計劃,在2018年7月實施。此后2018年7月,美國再次公布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的計劃。本文研究上市公司在中美貿易爭端開始前后投資率的差異,以考察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企業投資策略的影響。實證分析使用OLS估計以下雙重差分(DID)回歸模型:
y
, =α
+βUSList
*Post
+γControls
, -1+Fixedeffcets
+ε
,(1)
其中,被解釋變量是企業投資決策變量,衡量指標有兩個:(1)上市企業i
在第t
季度的投資率Invest
, ,將其定義為資本支出占總資產的比例。由于本文重點關注新增投資,因此資本支出這項即為“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2)上市企業i
在第t
季度的資本存量Capital
, ,將其定義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與其他長期資產的總和占總資產的比例。主要解釋變量為美國征稅影響程度USList
,衡量了中國上市企業層面受到美國對華征稅清單的影響程度,是個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具體為企業i
的銷售收入中多少比例受到美國對華征稅的影響,其計算如下:
(2)
由于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的可得性限制,最近披露年份為2016年,因此解釋變量中USList
的構造均基于2016年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與2016年中國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合并數據庫,由于這兩個數據庫沒有統一的公司代碼,因此根據公司名稱匹配兩個數據庫。要計算上市公司對美國出口金額中出現在美國對華征稅清單上的部分,還需要進一步與美國對華征稅清單匹配。美國公布的征稅清單為HS-8位碼,其前6位可以與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進行匹配,式(2)中的分子就是由清單上的HS-6位碼所涉及商品的出口金額加總得到。
本文將分別考慮第一次涉及500億美元商品的征稅清單和第二次2000億美元商品的征稅清單。美國第一次對華征稅清單公布于2018年4月3日,該事件在公眾預期之外,因而對中國企業此后的投資決策會開始產生影響。Post
為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事件的啞變量,在2018年第二季度及之后取1,否則取0。此外,本文還進一步考慮2018年7月10日第二次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清單的影響,宣布此消息時中美已處于貿易爭端之中,且第一次500億美元商品的征稅清單已做小幅修改。因此,USList
的分子中既考慮修改后的500億美元清單,也考慮新發布的2000億美元清單。此時,Post
在2018年第三季度及之后取1,否則取0。USList
*Post
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USList
*Post
的回歸系數β
代表征稅沖擊對不同企業在投資率上的異質性影響。上市公司投資比率受諸多因素影響,Controls
包括了一組公司財務信息的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
)使用對數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Leverage
)使用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例;國有企業(SOE
)是個啞變量,在企業股權性質為國有時取1,否則取0。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這兩個變量均采用滯后一期數值。本文還控制不同層面的固定效應:首先是控制所在省份固定效應(Province
)、所在證監會行業分類固定效應(Industry
)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Quarter
);其次是進一步控制企業個體固定效應(Firm
)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Quarter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控制年份季度固定效應的回歸中不放入Post
,控制企業固定效應的回歸中不放入USList
。(二)樣本、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研究對象為中國非金融行業所有A股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投資率及各控制變量根據上市公司季度合并財務報表計算,數據來自國泰安的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樣本的時間跨度為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9 年第四季度。
主要解釋變量中使用的對美產品層面的出口金額來源于2016年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該數據庫來自中國海關總署,包括每個企業、每種產品進出口價格、數量、貿易額等交易信息。本文通過公司名稱將2016年海關貿易數據庫與2016年A股上市公司進行匹配,剔除2016年后上市的企業,剔除2016年營業收入為負或總資產為負的企業,最終清理得到3067家上市公司。
計算受美國對華貿易制裁清單的影響時,需要在海關貿易數據庫與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合并數據基礎上整合美國對華征稅清單。征稅清單來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的新聞發布。2018年4月3日,美國發布301調查中需對中國價值約500億美元的HS-8位產品清單加征25%關稅。同年6月15日,美國發布第一批修改后的產品清單,為價值約340億美元、最終征收25%關稅的中國商品。同年8月7日,美國發布第二批修改后的產品清單內,為價值約160億美元、最終征收25%關稅的中國商品。而在2018年7月10日,美國公布另外價值約2000億美元的HS-8位征稅產品清單。由此可知,美國一共發布兩個對華征稅清單,本文分別考慮兩份清單的影響:考慮第一份征稅清單時以4月3日公布的產品清單為準;考慮兩份征稅清單的影響時,使用調整后落地的第一份征稅清單以及7月10日公布的第二份征稅清單的并集。在與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合并時,以國際通行的HS-6位碼產品進行匹配。
表1列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樣本中,僅有15.6%的企業受美國對華第一份征稅清單的影響,而有24.5%的企業受到美國對華兩次征稅清單的影響。美國征稅影響程度USList
1與USList
2都是企業層面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分別對應企業受到第一份征稅清單與兩份征稅清單的影響程度。USList
1的均值為0.
0002,意味著上市公司平均有0.
02%
的銷售收入在第一次征稅清單上。同理,USList
2的均值為0.
0006,意味著上市公司平均有0.
06%
的銷售收入在兩次征稅清單上。而USList
1與USList
2的75%分位數均為0,與前面提到的受兩次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不超過25%是一致的。被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均為3067家企業在13個季度上的面板數據(總樣本數小于3067*13是因為每年均有公司因各種原因缺失數據)。
表1 主要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量
(三)基準回歸結果
首先使用企業投資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雙重差分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表2列(1)、列(2)僅考慮第一份征稅清單的影響,Post
為2018年第二季度開始,列(3)、列(4)考慮了兩份征稅清單的影響,Post
為2018年第三季度開始。奇數列與偶數列的固定效應選擇不同,奇數列控制了省份、行業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偶數列控制了企業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這使得估計值在兩個回歸中代表的含義不同,前者代表企業投資率在同一省份、行業內在時間上的變化大小,后者代表企業投資率在同一企業內在時間上的變化大小。本文主要關注交叉項USList
*Post
系數估計值的符號、顯著性與經濟含義。從表2的結果可知,列(2)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在10%
顯著性水平上為負,這意味著第一份征稅清單發布后,受影響較大的企業相對此前顯著降低了新增投資率。由于本文采用OLS估計,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可直接揭示其邊際效應大小,當企業受第一份征稅清單影響USList
增加一個標準誤(0.0015)時,企業在2018年第二季度后的投資率將平均相對此前減少1.68%。列(3)、列(4)的結果顯示,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較大的企業在2018年第三季度前后的平均投資率與不受影響的企業相比并沒有顯著差異。由此可推測,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對中國企業投資率的影響較為短期,且主要發生在中美貿易摩擦剛開始的時候,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不可逆轉地提高出口品關稅,對相關企業新增投資的影響反而減弱了。
表2 企業投資率的基準回歸結果
然后考察用企業資本存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結果,如表3所示。表3結果的排列與表2一致,列(2)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在5%
顯著性水平上為負,這意味著第一份征稅清單發布后,受影響較大的企業的資本存量相對此前顯著下降了。USList
*Post
的邊際效應為,當企業受第一份征稅清單影響USList
增加一個標準誤(0.
0015)時,企業在2018年第二季度后的資本存量將平均相對此前減少0.
50%
。列(3)、列(4)結果顯示,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在2018年第三季度前后的平均資本存量與不受影響的企業相比出現顯著上升。以列(4)的估計值為例,當企業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USList
增加一個標準誤(0.0029)時,企業在2018年第三季度后的資本存量將平均相對此前增加1.07%。這說明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確實在短期內降低了企業投資,這與不確定性帶來短期投資減少的假說吻合。但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受影響企業的投資總存量反而增加了,這難以用不確定性理論來解釋,下文將進一步討論造成這一結果的潛在原因。
表3 企業資本存量的基準回歸結果

(續上表)
上述結果都是基于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的,而美國加征關稅的對象主要針對制造業企業的出口品,因此進一步考察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業子樣本(即企業證監會分類在C大類中),并采用企業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作為控制變量,得到表4回歸結果。其中列(1)、列(3)為企業投資率的結果,列(2)、列(4)為企業資本存量的結果。與表2、表3的結果相似,第一份征稅清單發布后,受影響較大的企業的新增投資率和資本存量都相對此前顯著降低了。而在第二份征稅清單發布后,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較大的企業的新增投資相對此前沒有顯著變化,但資本存量相對此前顯著上升了。這表明上文結論的穩健性,但同時也還需更深入研究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

表4 制造業子樣本回歸結果
(四)PSM-DID回歸結果
直接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D)可能存在實驗組(受美國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與對照組(不受美國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在很多維度上差異很大,對照組的企業存在選擇偏差,如美國公布的征稅清單可能是基于保護美國本土行業、市場或者技術的需要,而此類選擇偏差可能與企業投資決策直接相關。為更好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為實驗組企業(受美國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匹配傾向得分最接近的作為對照組企業(Konings和Vandenbussche,2008;Pierce,2011)。
進行傾向得分匹配的具體步驟為:首先,確定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定義,本文的實驗組為受美國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即USList
>0;對照組為不受美國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即USList
=0。匹配時選擇的解釋變量與基準回歸相似,包括:企業對美國出口金額占銷售收入比例(USExp
)、企業規模(Size
)、資產負債率(Leverage
)、國有企業啞變量(SOE
)以及省份、行業與年份固定效應。其中USExp
是未出現在基準模型中的變量,加入此變量是為了使對照組可以盡可能匹配到向美國出口的企業。其次,本文使用Logit模型來估計傾向得分,為實驗組企業找到最相近的對照組企業,并要求對照組企業的傾向得分在實驗組企業傾向得分的取值范圍內。最終得到受第一份征稅清單影響企業的對照組企業553家,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企業的對照組企業743家。得到新的對照組企業后,重新對雙重差分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采用企業與年份季度固定效應作為控制變量,結果如表5所示。交叉項USList
*Post
的系數符號、顯著性和邊際效應大小均與基準回歸(表2和表3)的結果非常相似,進一步說明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5 PSM-DID回歸結果
此外,本文還對制造業子樣本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分別得到受第一份征稅清單影響企業的對照組企業464家,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企業的對照組企業623家。在此基礎上進行雙重差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與表4中的結果非常相近,再次驗證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6 PSM-DID在制造業子樣本上的結果

(續上表)
(五)更多討論
上文主要發現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在短期內降低了企業投資,但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受影響企業的投資總存量反而增加了,這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假說的預測相符。但中期投資的增加與貿易壁壘提高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預測相反,接下來將著重討論這一問題。
中美貿易摩擦剛開始時確實帶來了很強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較為明確的是貿易壁壘上升是大概率事件且會持續較長時間。當貿易壁壘提高時,中國企業對美出口將受到重創,根據市場規模效應,會嚴重影響這些企業的投資意愿。然而本文依然觀察到中期企業資本存量上升,因此本文猜測是中國企業采用“出口轉移策略”,即將原來銷往美國的產品在中國國內出售。如果中國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化解了對美出口下降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那么中美貿易摩擦通過“市場規模”這一渠道影響中國企業投資的可能性則不大。
為了驗證這一猜測,首先考察中國企業境外銷售收入所占比重。在美國對華貿易壁壘上升后,中國企業的境外銷售收入占比應該會下降。上市公司會在“銷售收入”的附注中披露境外銷售收入(Foreign
sales
),可以據此推算出境內銷售收入(Domestic
sales
),以及計算境外銷售收入占總銷售收入比重(Foreign
sales
ratio
)。將境外銷售收入占比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得到表7中的結果。其中列(1)、列(3)為DID結果,列(2)、列(4)為PSM-DID結果。所有列中交叉項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均顯著為負,說明受美國加征關稅影響的企業在事件發生后,銷售收入中的境外部分都大幅下降。以列(3)為例,當企業受兩份征稅清單影響USList
增加一個標準誤(0.0029)時,企業在2018年第三季度后的境外銷售收入占比將平均相對此前減少0.70個百分點,大約相當于較均值平均下降3.50%。
表7 境外銷售收入占比Foreign sales ratio的回歸結果
其次,如果中國企業將對境外的銷售轉為向國內出售,那么境內銷售收入應該會大幅增長,而總銷售收入則大致保持不變。于是本文考察境內銷售收入和總銷售收入的變化,采用的被解釋變量是境內銷售收入的對數值和總銷售收入的對數值。同樣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分別得到表8和表9的結果。表8所有列中交叉項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均顯著為正,表9中交叉項USList
*Post
系數的估計值幾乎都不顯著,說明受美國加征關稅影響的企業在事件發生后,境內銷售收入顯著增長,抵消了境外銷售收入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因而通過“市場規模效應”對企業投資造成的影響非常有限。本文的發現進一步說明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中國企業投資的主要渠道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這一結果也從側面印證此后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性。
表8 境內銷售ln(Domestic sales)的回歸結果

表9 總銷售收入ln(Sales)的回歸結果
四 結 論
本文基于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提高對中國本土企業投資的影響,創新地利用美國對華征稅清單、2016年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與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數據構建企業層面受美國對華出口品加征關稅的影響指標,再結合2016-2019年中國上市公司季度財務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顯示,2018年第二季度后,即美國宣布第一次對華出口品加征關稅后,受此份征稅清單影響越大的企業會顯著降低其投資。此后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到2018年第三季度后,即美國宣布第二份更廣范圍的征稅清單后,受兩次征稅清單影響越大的企業并未顯著改變新增投資率,而其投資存量甚至出現上升。為檢驗這些發現的穩健性,本文首先將研究對象縮小至制造業企業,由于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主要針對制造業出口品,因而制造業企業更能反映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樣本縮小后,基本結論保持不變。此外,本文還采用PSM-DID方法以緩解選擇偏差問題,為實驗組企業(受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找到與之傾向得分最接近的對照組企業(未受征稅清單影響的企業),基于這個新對照組的雙重差分模型同樣證實研究結論成立。最后,本文深入探討了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渠道,通過對銷售收入進行境內和境外的分解發現,征稅清單公布后,境外銷售收入占比顯著下降,而境內銷售收入的絕對值顯著上升,總銷售收入的絕對值并沒有顯著變化,即原來銷往境外的出口品轉為內銷,說明中美貿易摩擦并未通過“市場規模效應”對中期投資產生影響,而是主要通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這一渠道發揮作用。
本文研究結論表明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影響是短期的。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慢慢消除之后,中國相關企業由境外銷售轉為境內銷售,企業投資也隨即恢復如常。由此可見,貿易談判的結果可能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釋放關于貿易政策確定性的信號,盡量避免因政策變化引起企業謹慎的投資行為。這一發現也從側面印證了中美貿易摩擦后,中國政府所倡導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