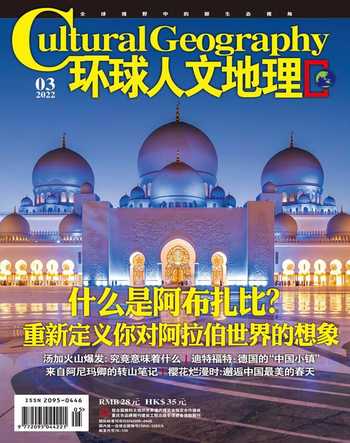一個人,一段路,一座山
周運
轉山是什么?
或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于筆者,是頭痛欲裂時看到發著金光的佛像,是沉沉夜色中的孤燈,是被藏獒圍堵時絕處逢生的奇遇,是能讓人忘記熊和狼的狂風暴雨……



這次轉山,轉的是阿尼瑪卿。
阿尼瑪卿,位于青海省東南部,呈西北至東南走向,主峰瑪卿崗日海拔6282米,為黃河流域最高峰。作為藏傳佛教四大神山之一,阿尼瑪卿是傳說中的世界九大創世神之一,主宰著山河大地,在安多地區的藏語中,意為“黃河地區偉大的山神先祖”。
阿尼瑪卿是我早就向往的所在。我沒料到的是,此行會有如此多的艱難險阻,恰似為我量身打造的“取經路上的八十一難”。時至今日,我都無法解釋,當時的自己是如何振作起來,一步步完成朝圣之旅的。我是個無神論者,但這一次神奇的經歷讓我相信,我在冥冥中得到了指引和庇佑。
不是我選擇了阿尼瑪卿,是阿尼瑪卿選擇了我。
一切還是從飛機在果洛瑪沁機場落地說起。
我帶著大堆行李踏上機場大巴時,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乘客的注意。他們好奇的目光,掃過我背上堆砌的大包小包,以及手里的登山杖和帳篷,終于成功地找到了我這個人在哪里。坐定后,隔壁的小伙兒問我:“是來登山的嗎?”我喘著氣回答:“轉山。”小伙兒年輕的臉龐流露出毫不掩飾的贊許和羨慕,原來他也很想去轉,苦于沒時間。小伙兒從事地質勘探工作,經常來回于瑪多和瑪沁,中途會路過阿尼瑪卿,但苦于工作太忙,每次都是擦身而過,這次又要匆匆趕往達日。
司機把我放在離賓館最近的十字路口,下車后我開始感到不適。畢竟瑪沁縣城海拔3750米,比拉薩還要高出100米。我坐在公交站的長凳上緩了好久,才敢扛起所有行李走到賓館。入住后,下樓吃飯順便曬了會兒太陽,一陣困意襲來,我打算回房休息,養足精神,明天就出發。但沒想到這一躺,竟是三天。
傍晚時分,頭痛來襲——我意識到自己高反(高原反應)了。因為毫無食欲,便用水壺煮了茶葉,喝了一杯就昏昏睡去,希望明早能夠好轉。夜里出了很多汗,難受得翻來覆去都睡不著,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于極難受中瞥見外面漫天彩霞——窗口正對著城北的喇日寺,我看到寺廟的屋瓦,還有山坡上那一尊巨大的金佛在陽光下閃耀。但此刻我的意識模糊,身體被頭痛、反胃、無力、耳鳴輪番碾壓……高反更加嚴重了。
就這樣躺到中午,口渴難耐的我掙扎著爬起來,沖了一杯葡萄糖水,喝下去沒多久胃里就一陣翻江倒海,嘔吐不止。身心交瘁中,理智讓我跌跌撞撞地下樓續房。回房后我坐在床角,試圖通過冥想和腹式呼吸減輕缺氧癥狀,可最終還是迷迷糊糊地躺下了。躺下后意識并沒有完全得以休息,我聽見外面大雨滂沱而過的聲音,聽見冰雹劈啪作響的聲音……漸漸感覺身體化作一灘泥,隨著雨水卷進下水道,越陷越深,在黑暗中喊不出聲,透不過氣。
不知何時,雨似乎停了,鼻子最先被喚醒,那是牛肉湯的味道。睜眼,窗外是熱鬧的裊裊炊煙。三十小時沒有進食的腸胃依舊不適,但似乎可以接受點甜的東西。我吃了少許八寶粥和幾個果凍,又吞下兩粒鹽丸。不敢喝水,微張著干裂的嘴唇維持呼吸。躺到半夜頭疼依舊不依不饒,只好又坐起來冥想,試圖用專注呼吸來緩解一點痛苦。正襟危坐間,透過窗外黑沉沉的夜,我兀自看到山坡上有一盞孤燈,不知那是誦經閣還是佛像的燈光。這時一個意念跳入腦海——計劃應該改變了。我原定走完阿尼瑪卿的西側之后,就放棄東側,直接前往玉樹,去轉另一座神山:尕朵覺沃。目前看來,玉樹是注定不能成行了。“將阿尼瑪卿轉完”,一個念頭說——如果能撐過當下高反的話。
隨即我又陷入昏睡。再次醒來,已是到達后的第三天早上了,身體似乎有所恢復。窗外天氣極好,天光云影在綿延起伏的山坡上靜靜流淌。我望著喇日寺那尊默默陪伴了我許久的巨大金佛,看見下方成片經幡獵獵飛舞,終于感覺到自己又“活了過來”。
到達后的第四天,雖仍有些許不適,但我終于重振信心,收拾好行李出發了。
被高反給了一個下馬威的我,終于坐上了從瑪沁縣開往瑪多縣的大巴車。班車離開城區,走上德馬高速,向西北方向而去。隨著路邊的風景從樓房街道變成鋪滿草甸的山丘河谷,此前高反帶來的低落情緒和城市的喧囂一起被拋在身后。
我真的要去轉山了,并且無法回頭。
車行約一個小時后,駛出雪山二號隧道,司機靠邊停住。下車,穿過高速公路,翻過護欄走下路基,鉆過一道鐵絲網后,我終于看見那兩座標志著轉山起點的佛塔。察那卡多正是這個路口的名字,渺小到不會出現在任何地圖上,卻是藏民口中取得“轉經鑰匙”的重要地點。
兩座佛塔都是十多米高,一前一后矗立在路旁,一座是白塔,一座被漆成璀璨的金色,塔基堆放著真言石板。它們旁邊有一座方形的祭壇,據說藏民開始轉山前,都要在此舉行祈福儀式,以求阿尼瑪卿保佑自己轉經路上一切順利。我看到祭壇上沒有灰燼,地上也沒有龍達(畫有神像或寫有咒語、祈愿的彩色小紙片,祈福時撒向空中)的痕跡,說明這兩天并沒有人前去轉山。我分別繞著兩座塔轉了三圈,以求得轉經鑰匙。當然,所謂的“轉經鑰匙”,并不是實實在在的鑰匙,而是象征意義上準許人們踏上轉山之路的許可,更像是一種祝福。取得“鑰匙”之后,我正式邁出了轉山的第一步。


如今在阿尼瑪卿東側已建起高速公路,西側則是可行車的砂石路。以往步行繞山一圈需要七八天,現在開車一天就可完成——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能用雙腳走完西側。說來神奇,剛才在車上時,我的腦袋還是暈乎乎的,此時背著行李走起來,高反癥狀反而徹底消失了。感知著腳下的碎石路,行走對我來說似有魔力,構建起我與這片土地的聯結,帶給我力量。
道路沿著陽柯河谷曲折延伸,路邊的山坡上有牦牛在吃草,偶爾能看到幾家牧民的房屋,卻沒有遇到人。大概走了半小時,我遠遠看到前方的路上有人和馬的蹤跡,便加快速度趕上去,企盼遇到結伴轉山的藏民,沒想到遭遇的,卻是兇悍的藏獒。
先是遠遠聽到一陣狗叫,尋聲望去,聲音是從河對岸一戶牧民房前傳出的。狗叫聲越來越近,一只黑色的藏獒正朝著我急速飛奔。它的叫聲驚動了另外三條體型較小的狗,同樣隔著河對我狂吠。很快,黑色藏獒從橋上過了河,沖到離我只有兩米的地方,露出尖銳的獠牙,口水橫流,滿臉兇相,發出可怕的吠叫。
我被嚇得大氣不敢出,生怕它撲上來咬我,只得采取回避的策略,強裝鎮定保持勻速向前走,以求盡快撤出它的領地。藏獒緊隨在我身后,絲毫都不放松。與此同時,它的三個朋友也快速跟進,沿著河岸張牙舞爪地追我。正在我數著心跳,丈量著還有多久脫離它們的控制時,前方的道路上突然竄出一條貌似維茲拉犬的土黃色獵狗,它看著我,我看著它——其體型之大,跟藏獒不相上下!那一剎那,我只感覺全身血液似乎瞬間凝固,暗忖這下難以脫險,被迫停下來想要狂奔的步伐,盤算著,只有僵持到有路過的車輛來解救我為止了。腎上腺素急速奔流,全身肌肉在匯報:已做好了搏斗的準備!
此時傳來天籟般的人聲,牧場的主人出現了,惡犬們立刻偃旗息鼓,劍拔弩張的態勢煙消云散。牧場主說他剛才牽著馬去對面山坡上放牧,聽到狗叫就下來察看。他及時為我解了圍,讓我不勝感激。
接下來的路程中,我遇到幾輛汽車。司機們很熱情,都會停下來交談,給我鼓勵的同時,他們也傳達了一個信息:前面并沒有和我一樣的轉山者。
天氣陰沉下來,在一段爬坡的中途,烏云裹挾著驟雨襲來。四下竟無處遮蔽,我只好拿出一次性雨衣,試圖穿上以包住前后的背包和腰上的相機。然而風之狂烈,單薄的雨衣還沒等我穿上就被吹爛了。我只好卸下掛在背包上的防潮墊,以便給背包套上防雨罩,再把相機放進背包里。我穿上雨褲,一手抱著防潮墊,一手拿著登山杖,在風雨中向前走。
身上的負重太多,衣物裝備、電子設備,加上食物和水,足足有38斤重,每一步都混和著充盈在天地間的密集的雨,壓得我幾乎要喘不過氣來。
走出這陣雨,一直走到大約在十公里外的一個坡頂,我得到了獎勵——阿尼瑪卿南端的雪峰,它第一次出現在我的視野盡頭。此時,我站立的山坡下開滿了橘黃色的野花——大地以大片明艷亮麗的色彩,映襯著山谷那頭快速壓近的黑云。云層縫隙間的光芒,層次錯落地出現,我心里冒出陌生的愉悅,而茫茫天地間,孤獨的風仍在獵獵作響。
傍晚時分,眼可見陽柯河的水量增大,泥漿般的冰河水翻卷而下。不多時,大雨便傾盆而下。
我迅速穿過一座水泥橋,只因橋頭有幾頂長方形的帳篷。快速搜尋,發現其中一頂里面有人,就扎進去避雨。帳篷內有兩個人,頭裹紫色格紋頭巾的婦人坐在火爐前,一側的床上坐著頭戴瓜皮小帽、身披大襖的男人。婦人是藏民,男人是回民。他們熱情地邀請我放下東西、坐在火爐邊,還給我端來熱茶和饃饃。
男人告訴我,他們來自海南州,每年這個時候都會到這里挖蟲草,一般住50天,今年已經待了一個月。聽說我打算獨自上山,他黝黑的臉剎時收緊:“山上有很多狼,還有黑熊,要吃人的……我們去挖蟲草時,經常在河邊看到斷掉的手,或是吃剩一截的腿。”他摩挲著自己的腿,心有余悸的樣子,“以前轉山的人多,挖蟲草的也多,還好些。現在進山的人少了,野獸就越來越多。我有一次就差點被吃掉了。”



正在我驚愕之時,門口人影一晃,又進來另一位略胖些的回民,他在另一張床邊坐下聽我們聊天,婦人則不時提著水壺添茶。摩挲腿的男人抬起頭說:“你知道嗎,昨天有四五個轉山的漢人上去,碰到那么大一只黑熊。”他的雙臂伸展開來比劃,圓圓的眼睛直盯著我,“還好他們有車,才保住命,逃了回來。”
他的話唬得我心跳加速,我在考慮要不要放棄一個人在山上扎營的計劃。這時略胖的回民哈哈笑了起來,他對我說:“你別聽他瞎講。”婦人也開口了:“他在嚇唬你呢。”男人見被戳穿,自己也笑了,擺擺手說:“要真是那樣,我早就攔著不讓你上山了。”他這才正兒八經地告訴我,狼和熊是有的,只是沒那么多,這些野獸白天不敢明目張膽襲擊人,到了晚上,只要挨著牧民的帳篷扎營,也不會有大礙。
雨停了,一個饃饃和幾杯茶下肚也有了力氣,表達過謝意后,我背起行囊走出帳篷。男人送我出來,指著前方的河谷說,今天走到埡虎(埡口,藏民的說法)是不可能的,可以繼續走兩三個小時,快到埡虎的地方還有其他挖蟲草的藏民,盡量在他們的帳篷邊扎營,晚飯可以去他們帳篷里吃。
我繼續沿著河谷向上走,一個個彎道接著一個個爬坡。大約下午6點時,我開始留意路邊的帳篷和營地。先是在河谷里的一塊草地上,我發現了兩頂大門緊鎖的帳篷。繼續前行,發現山坡上有兩座鐵皮小屋,仍是鐵將軍把關。我停下來,認真觀察了一下:小屋后緊挨著一道不算陡峭的懸崖,居高臨下俯瞰兩條河谷在此交匯;屋前有一垛壘得半人高的牛糞墻,下方的石洞中還住著一只肥碩的土撥鼠;二十步開外的地方,有一條清澈的溪流。站在兩座小屋中間的草地上,我決定:就在這里扎營。
當我快搭完帳篷時,從山坡的上方走下來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他的臉龐被太陽曬得黝黑,身穿一件軍綠色夾克,頭戴一頂黑色棒球帽,手上戴著棉線手套,握著一把三角形的小鐵鍬。我以為他是鐵皮屋的主人,一聊才知道,原來他住在我剛才路過的帳篷里,是一位挖蟲草的藏民。
他告訴我,這兩座鐵皮屋是牧民的夏季牧屋,一般到七月才會有人住;而他們這些挖蟲草的藏民則在四月下旬開始進山,六月上旬就陸續撤離,兩者互不干擾。他對我的露營裝備非常感興趣,特別是睡袋,請我拿出來讓他仔細瞧瞧。親眼看見這么小一個玩意兒竟然能迅速膨脹得巨大,他表示非常吃驚。到我跟他說睡袋保暖性非常好,他更是像小孩子一樣好奇,不禁伸手進去摸了摸。聊完睡袋,他站起身,邀請我去他的帳篷喝茶。
我背著相機跟他出去,走了幾步又回來拿上食物補給包,一是為了喝茶時能與他禮尚往來,不是一味蹭吃蹭喝;二是為了防止那只胖土撥鼠趁我不在,去帳篷偷吃。等我快步趕上,大叔——姑且叫他“蟲草大叔”吧,已經打開門,在河谷帳篷里迎接我了。
一進帳篷,就看到一個火爐,爐子上方一根鐵制的煙囪通向篷頂。其他布局倒也簡單,右側是一排通鋪,左側擺放著各種工具,中間一點的地方堆放很多紙箱,里面堆滿了食品和雜物。通鋪是用磚塊和木板架起來的,面上鋪著碎花墊子,床頭整整齊齊疊著八床棉被,鋪側的墻上掛著一些衣物和帽子。帳篷兩側各有兩扇窗戶采光,地面已經被踩成了堅實的泥地,通鋪下卻還長著青草,帶著幾分野趣。大叔告訴我,他和妻子住在另一個帳篷,這個帳篷是給年輕人住的。目前他們都還在山上,要過一會兒才回來。
大叔給我倒了茶,并從紙箱里拿出饃饃——在蟲草藏民的帳篷里,茶水和饃饃是招待客人的標配。接著,他從上衣內側口袋掏出一把黑黢黢的東西,放在床上的小桌板上,咧嘴一笑,對我說:“蟲草,今天挖的。”我湊上去端詳,一條條沾滿泥土的東西,依稀能辨認出蟲草的模樣。大叔捏起一條大的,說:“這個,能賣六七十塊。”又指著其他稍小的說,“這些,只能賣二三十塊。”
大叔很是健談,他告訴我,他們每年都來這里挖蟲草。以前收成最好的時候,每人一天能挖上百條。如今蟲草越來越難找,每天都要走很遠,去很偏僻的地方才能有所收獲。話題逐漸離開蟲草,作為兩個互相感興趣的人,我倆從各自的工作聊到收入,從婚嫁聊到買房。當然,聊得最多的還是阿尼瑪卿。從大叔口中得知,這個季節埡口的天氣比較穩定,明天如果不下雨的話,早點出發,翻過埡口之后大約兩三個小時,就會碰到其他挖蟲草的藏民,晚上可以借宿他們的營地。說到野生動物,他勸誡我不要單獨扎營,盡量挨著藏民的帳篷:“狼怕人,看到人遠遠就跑掉了,但熊不怕人,晚上要特別小心。如果不行,就住到我這里來。”


當我表示要走的時候,他立馬給我的水壺灌滿熱水。我投桃報李,拿出火腿腸、鹵蛋和蛋糕等零食,他卻死活不要,統統塞回了我的背包,最后只接受了我留在床上的一小條香蔥餅干。我給他拍了一張照,對他說我要記住他的模樣,到了埡口的祭壇,我會為他祈福。
我剛回帳篷沒多久,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帶著不可抗拒的姿態,密集的雨點像機槍子彈掃過帳篷,一輪比一輪猛烈。雨中夾雜著冰雹,與雷聲作伴,震得整個山谷隆隆作響。最可怕的還是風,風吹帳篷時像是四面八方都有一只猛虎,各自拽著帳篷一角拼命撕扯,似在激烈爭奪一頭獵物。即便拉上了所有風繩,外帳還是被刮得左搖右晃。我在里頭睡得提心吊膽,生怕突然整個外帳就沒了。此時我開始后悔,扎營的時候沒有扎在鐵皮小屋的背風面,而是選擇了暴露的一面,讓可憐的帳篷,直面從兩條河谷上游刮來的西北和東北風。然而事已至此,眼下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蜷縮在睡袋里默默祈禱風雨盡快平息。
可怕的暴風雨一直持續到清晨,托它的“福”,我一整夜都沒心思去擔心什么野生動物的事兒。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