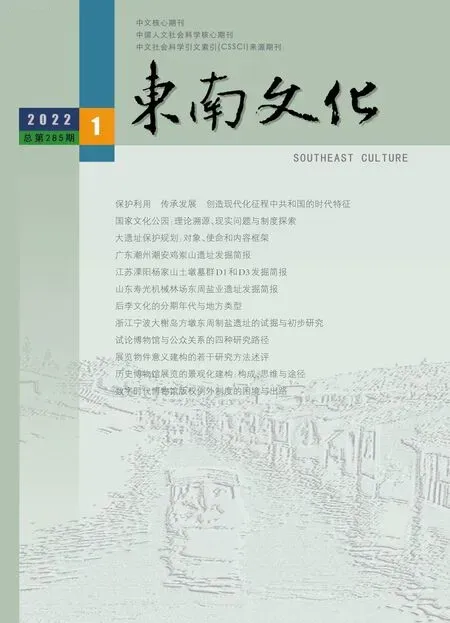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景觀化建構:構成、思維與途徑
巫 濛白 藕
(1.深圳大學藝術學部 廣東深圳 518060;2.中國國家博物館 北京 100006)
內容提要:歷史博物館展覽作為被觀看的客體,以歷史遺存為基礎、以敘事為核心、以沉浸式體驗為吸引觀眾達成展覽目標的途徑。歷史博物館展覽中的景觀意味著由文物展品與多種媒介物構成的具有一定敘事與意義表達的空間圖示,并具有“器—象—道”三個層面。景觀化可以廣義地理解為將零散的元素組織成為具有意義指向的整體。“象”作為蘊含著“器”與“道”的感知整體,是營造體驗、讓觀眾形成第一印象的關鍵所在,因而景觀化建構應以“象”為先,根據各自的基礎條件運用不同的建構途徑——利用天然的歷史景觀、重構歷史場景、景觀化的文物組合,從而有助于歷史博物館打造更具吸引力與更具傳播效能的展覽。
一、研究背景
博物館具有天然的歷史屬性,歷史博物館出現卻相對較晚,形成于現代國家建立之后。歷史博物館以歷史學及相關人文社會學科為知識框架,從時間維度呈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其展示的核心是人類社會各個層面狀態的變化。這意味著歷史博物館的底層邏輯與其他以“物”為核心的博物館從創立之初就有所不同,它以“事”為中心,通過講述國家、民族或地域的發展歷程,尋求相應的群體認同與相關的權力認可。因此,歷史類展覽成為現代國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媒介,建立在國家主流政治思想基礎之上,具有特定的意義指向,并從“以物鑒史”發展出“以物釋史”的展覽觀念[1],歸屬為敘事型展覽[2]。
歷史敘事及其明確的意義指向難以僅通過文物完成,還需要借助其他展示媒介,因而歷史類展覽與其他類型的展覽相比有所不同:使用更多的文字、圖片、影像及模型、場景等媒介物或輔助展品。多樣化的媒介物成為完成敘事的工具,媒介化成為建構敘事型展覽的途徑。文物等歷史遺存在歷史敘事中幾乎消解了主體價值,也成為闡釋歷史的一種媒介物。在歷史類展覽的各種媒介之中,相對于在大眾媒體中易于復制傳播的文字、圖像,文物和場景以圖示化的物質形態呈現出獨特的價值:直觀、真切、稀有、難以復制,是歷史博物館展覽中更具吸引力的元素。
隨著展覽技術的發展與觀念的更新,沉浸式體驗既是展覽吸引觀眾、有效傳達展示信息的途徑,也是各類展覽追求的一種目標。沉浸式體驗意味著打破了看與被看之間的界隔,讓觀看主體的精神與被看客體的存在融為一體:觀看主體因沉浸而專注,因專注而產生共情,因共情而更深入地理解被看客體;同時沉浸式體驗也能讓觀看主體忘掉平日的本我而產生一種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的奇妙感受。盡管因內容不同,體驗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但必定是深刻的。歷史博物館也不例外,營造歷史體驗意味著讓展覽空間成為一個富有感染力的整體,以空間環境的方式“包裹”觀眾,讓觀眾沉浸在一種空間尺度的歷史情境中直觀感受展覽。
綜上,根據歷史博物館展覽內容與形式的特點、當今展覽發展的趨勢以及對大量歷史類展覽的觀察分析,下文將分析景觀化建構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思維與途徑。
二、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景觀構成與景觀化
景觀(landscape)最初是地理學的一個概念,指某個區域內自然地理的總體,后來融入了人工構筑的內容,逐步形成人工景觀(artificial landscape)、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等概念。最初的景觀概念如今可以歸為自然景觀;如今不帶前綴的景觀一般指文化景觀,包括自然和人工兩部分,是兩者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結果[3]。從自然景觀到文化景觀,自然元素逐漸后退消隱,人類創造的物質文化及歷史遺存逐漸擴展彰顯,景觀中人工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大都市商業中心形成了一種幾乎可以忽略自然元素的人工景觀。更進一步講,構成文化景觀的人工物可以分為兩類:以使用功能為主的建筑物和以信息傳達為主的媒介物。在物質豐盛甚至過度的社會,媒介物所占比例呈現上升趨勢,當媒介物堆疊出的社會表象掌握了對社會精神控制的微觀權力,就形成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描述的景觀(spectacle)社會。景觀社會的景觀(spectacle)可以看作從文化景觀中新生發出的一個支系,其從基本性質來看是一種媒介景觀(media landscape)。媒介景觀可以是具體的——由很多媒介物構成的場景,如商業街;也可以是抽象的——由個體將日常所見的媒介信息在頭腦中構建出來一幅圍繞著自己的圖示,它作用于個體的時間更長、影響更大。Spectacle豐富了原有景觀(landscape)的內涵,拓展了其邊界,使其不再僅作為被觀賞的客體而具有了主體性的表達與影響力。
從landscape到spectacle,景觀并不局限于地球表面上人類的生存環境,而成為一種有意義的空間圖示以及由不同形態、相關聯的物質與圖像構成的整體,具有一定的敘事結構和表現張力(圖一)。“景觀化”即將原本缺乏聯系的客體轉化為一種景觀,可以廣義地理解為將零散的元素組織成具有意義指向的整體,由此景觀化成為一種視覺圖示與內容建構的方法,可以應用于博物館的景觀化展示等相關領域。

圖一// 景觀的發展與比較(圖片來源:作者繪制)
對應人類生存環境的景觀,歷史博物館的景觀也由“自然”與“人工”兩部分構成:文物展品與歷史遺跡等相當于“自然”部分——歷史中原本存在的,考古遺址之類的原貌呈現可看作博物館的“自然景觀”;展覽中承載歷史敘事的其他媒介物(如文字、圖像、模型、歷史場景等)以及烘托歷史感的空間環境,是基于“自然”的人為事物,相當于景觀中的“人工”部分。大部分展覽都是這兩部分結合而成的“文化景觀”。當展覽的媒介物占據主導而歷史遺留物幾乎可以忽略時,展覽即成為一種“媒介景觀”。歐美國家于20世紀中后期出現的社會議題博物館,如美國洛杉磯寬容博物館(Museum of Tolerance)、澳大利亞珀斯自由與寬容博物館(Museum of Freedom and Tolerance,West Australia)等,便是博物館積極參與社會發展事務而產生的一種新型博物館,它們聚焦于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重要社會問題,如人權、原住民、浩劫等,以問題導向代替知識導向,以思辨、批判性的媒介表達代替文物展示,并開展更多的社會交流活動[4]。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景觀化也就是將歷史遺留物、解釋性的媒介物及展覽空間環境結合成一個具有敘事內容與形式表現力的整體,令觀眾產生沉浸式體驗且易于接受展覽信息。博物館展覽的景觀化也可以看作語境可視化的升級版,語境可視化重點在于將文物展品的歷史背景信息通過圖像、環境等視覺化形式直觀呈現出來;景觀化則令展品與其可視化語境產生更強烈的聯結而形成一個整體。
無論在地球表面還是在博物館,從自然景觀到文化景觀再到媒介景觀,隨著人工物占比的增加,景觀整體的敘事性與意義指向性也在增強。對于歷史博物館展覽,這種發展同時也帶來一種風險:原真價值被意義闡釋蠶食甚至逐漸喪失。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三、以“象”為先的景觀化建構思維
“器”與“道”是中國傳統文化對物質與思想意識的指稱,《周易·系辭》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道”與“器”之間還有“象”,“象”蘊含了直觀具象的“器”與超越具象的精神之“道”。明末清初王船山由《易經》發展出“盈天下皆象”“天下無象外之道”的哲學思想,認為“象”具有乾坤一體、錯綜為一的特征,能夠實現兩端一致而各不偏廢[5],確立了“器—象—道”三位一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當今在反思中西方思想文化差異而確立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象”被重新發現,王樹人認為“象思維”是人類共有的本源性思維,其最初形態表現為前語言、前邏輯的思維,在“象形”的前提下和在詩意聯想中,通過“觀物取象”與“象以盡意”形成了一種感悟性的思維方式,達到主客一體之體悟[6]。
“象”的哲學思想也蘊含在展覽的構建與觀看之中。對于歷史博物館展覽,“器”是展覽之中的有形之物,以文物、歷史遺跡為中心;“道”是展覽傳達的歷史意義、精神、價值之類的無形觀念;“象”在蘊含著“器”與“道”的同時也連接著兩者的本體認知,是對展覽整體的直觀感覺——一種歷史感的審美體驗。“象”在中國美學中具有獨特的價值,在西方話語體系中可以理解為由“完形”構成的“場”。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7]認為“知覺到的東西要大于眼睛見到的東西;任何一種經驗的現象,其中的每一成分都牽連到其他成分,每一成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為它與其他部分具有關系”[8]。整體具有它本身的完整特性——并不決定于其個別的元素,也不等于部分之和;整體具有比部分之和更大的能量,整體能量構成一種場(field)對個體產生影響,并在個體心中形成“心物場”(psychophysical filed)[9]。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說“觀看先于言語。兒童先觀看、后辨認、再說話”[10]。這也是人類普遍的認知過程。對于展覽,觀看是信息傳達、沉浸體驗、觀念更新等幾乎所有目標達成的起點。觀看首先是視覺被吸引,吸引發生于觀眾走進展廳之際,此時觀眾尚未觀看到展品的細節——器之形,也未領會到歷史的意義——無形之道。觀眾觀看到的首先是“象”,感受到的吸引力也來自“象”——所有的“器”構成的“場”——具有歷史感的整體。在歷史博物館中,由“自然”與“人工”元素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景觀便是一種整體的“象”。例如在四川金沙遺址博物館“王都剪影”展廳中,沉穩的大地色系、靜謐昏黃的燈光、簡潔低調的空間造型以及古樸的陶器展品,這些元素共同形成一個整體的“象”、構成一個“場”,營造出極具歷史感的氛圍,觀眾進入展廳首先就會沉浸在展廳整體的“場”中。
敘事型展覽的構建過程一般是先明確主題,即確立“道”,再組織展覽中的各種“器”構筑景觀、形成富有吸引力的“象”,“器”包括展覽空間中的物質存在(如展品、媒介物、環境實體)。然而在觀展過程中觀眾首先被整體的“象”吸引,進而仔細觀看各種“器”,并結合媒介物的說明最終認知“道”。從觀看角度理解展覽,“象”是起點;從吸引觀眾的角度而言,如何構建“象”也應該是思考的起點。因此,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景觀化構建應以“象”為先,這是展覽的一種構建途徑,也可以看作一種基本的思維方法(圖二)。

圖二// 以“象”為先的歷史博物館展覽景觀化構建思維示意圖
四、歷史博物館展覽景觀化的建構途徑
文物展品與歷史場景作為歷史博物館展覽中最直觀真實的立體圖示,是最引人注目的元素,結合相應的設計手法可以形成不同樣貌的展覽景觀。
(一)利用天然的歷史景觀
有些博物館擁有大體量、空間性的歷史遺跡——天然的歷史景觀,它們帶來的歷史感是無可比擬的。在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下,館方策劃展覽主要集中于引導觀看與說明闡釋。說明通常是對于“器”的客觀屬性的解釋;闡釋則著重于“道”,通常采用歷史敘事的手法,“激活”沉睡靜默的歷史遺跡,呈現其背后的歷史故事,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這類展覽的“人工”部分在內容與形式上需有所節制,尤其是形式不能喧賓奪主,就像風景區的游覽設施在視覺表現上一般都比較低調,以保持自然風光的完整性和觀賞性。
德國柏林的恐怖地帶(Topography of Terror)[11]建立在被炸毀的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總部的建筑廢墟上,同時緊鄰一長段保留下來的柏林墻(Berliner Mauer),其展覽有室外和室內兩大部分。室外部分構筑在裸露的地下室殘垣之前,此處曾經有許多政治犯被拷打和處決。“1933.柏林.獨裁之路”(1933.Berlin.The Path to the Dictatorship)展覽主要以展示歷史照片和文獻的方式呈現,形式簡潔通透。參觀者沉浸在柏林墻下的納粹廢墟之中,相比其旁邊新建的博物館更讓人印象深刻。
如果條件允許,博物館也展示大體量的歷史遺跡,采用原物整體搬遷的形式將某地的歷史遺跡移到展廳,成為一處原汁原味的“自然”歷史景觀。整體搬遷工程大、耗時長、費用高且所需展示空間大,使得搬遷難度很高,然而這種非同一般的大體量“自然”歷史景觀能夠帶來最真切的沉浸式體驗。比如,江蘇徐州衛遺址明代兵器庫整體搬遷至徐州博物館“金戈鐵馬”展廳[12],安徽博物院展示了一座完整搬遷的徽州古宅馮仁鏡宅[13],美國迪美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院落中也有一座耗時七年從中國完整搬遷的徽州民居蔭馀堂[14],這種天然的歷史景觀可以讓觀眾瞬間“穿越”到過去的某時某地,仔細品味景觀細節,激發更多的歷史想象。
(二)重構歷史場景
大部分博物館不具備“天然”的歷史景觀,代而采用創作歷史場景進行景觀化的圖示敘事方式,以提升觀展體驗。場景本身即是一種景觀,歷史場景通常表現重要的歷史事件或典型的社會狀態。在普遍使用照片與視頻的形象記錄之前,歷史場景的具體樣貌并不能被準確獲知,因而需要創作。創作意味著一種從內容到形式的不同程度的重構。類似于視覺藝術從古典到現代經歷了從具象到抽象的發展,歷史場景的重構也從具象寫實到抽象表現,發展出多種形式。
歷史場景的重構中最為具象的是再現場景,以寫實的手法復原某一歷史情境,營造身臨其境的效果,在國內博物館尤其是近現代史主題的博物館中應用得比較普遍[15]。再現場景通常借用舞臺設計手法,在有限的展廳內以前景、中景、遠景表現現實的更大空間,前景可以布置文物展品,讓文物回歸到模擬的“故鄉”。全景畫是再現場景的鼻祖,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最早出現于18世紀末的歐洲[16],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人們對于沉浸式體驗的追求,之后被運用于博物館。
表現場景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是以藝術化的手法表現某種歷史情境。表現場景不追求寫實,重在情境的表達,也可以偏于具象或抽象,具有較大的自由度。表現場景在國內歷史博物館使用得較少,大概由于其與歷史博物館追求原真性的理念相差較大。然而,當歷史情境(尤其是時代久遠的)不能被準確獲知時,所謂的具象表達就會帶有演繹、編纂的成分,尤其在具體的細節上,表達得越具體就越有可能出現漏洞。表現場景的方式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在已有資料的基礎上以歷史想象為驅動、以藝術創作為工具,采用較為抽象、簡化的表達手法構建場景,提供一種剪影般的歷史意向,這也許是一種更恰當的方式。意大利博洛尼亞歷史博物館(Museo della Storia di Bologna)[17]的多個表現場景采用了非寫實的具象手法,比如9號展廳借鑒了現代戲劇舞臺的無背景設計,再現福斯卡塔戰役(La Battaglia di Fossalta)的場景;13號展廳采用二維平面的層疊制造出2.5維空間場景,表現查理五世(Charles V)在博洛尼亞的加冕典禮;文化展廳(Sala Della Cultura)借用鏡面營造視覺的豐盛,形式多樣而更富藝術氣質。
抽象場景主要采用抽象的空間語言營造氛圍,重點關注歷史的情感體驗而不是表現具體的歷史情境。德國柏林猶太人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即是這樣引發觀眾共情的典范,它最具感染力的是壓抑到讓人產生恐懼的空間環境。國內的建川博物館聚落也在空間氛圍上大力著墨,比如“紅色年代 章·鐘·印”陳列館有一處峽谷般的空間,其一側高墻為布滿老式座鐘的壁龕,座鐘單調的滴答聲在紅磚墻面之間回蕩;緊鄰的中庭是一個四面封閉的正圓形空間,除了窄小的入口外,只有頂面向天空敞開,圓心位置放置一個老式立桿麥克風,似乎在傳遞重要的聲音(圖三)。陳列館的各個空間共同構成了抽象的情境,仿佛是那個時代的隱喻,引發觀眾傾聽歷史的回音。

圖三// 建川博物館聚落“紅色年代 章·鐘·印”陳列館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三)景觀化的文物組合
博物館以收藏為根基,雖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性增加了媒介物的比例,出于對體驗的追求加大了場景數量,但是文物的歷史價值與原真價值不可替代,對于大部分展覽而言,文物展示仍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一般情況下,對于單個文物展品的展示重點在于“器”,因為單體難以形成敘事,也難以營造景觀化的體驗。當多個文物聚合為展品群時便形成了格式塔,物與物之間的關聯聚合呈現出超越個體相加的群體效應,形成具有敘事性的景觀化圖示。
文物組合而成的展品群具有類似人類社會的性質,品類越豐富,其敘事性就越強。美國鹽湖城教堂歷史博物館(Church History Museum)以大量實物陳列的方式講述了摩門教(Mormon)開創的過程,與衣食住行有關的物品聚集在一起,雖然沒有模擬某個具體場景,但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直觀的生活景觀,從日常物品的組合中,比如白色的蕾絲長裙、精致的家具、豐富的樂器,都可以看到摩門教徒的生活狀態及其對于美與精神文化的追求。反之,物品的品類越窄,敘事性就越低,展覽的說明性和研究性也相應增強,或者重在展示其藝術價值。
文物展品群所構成的景觀是一種由具體物品構成的抽象圖示,遵循著陳列的原理而形成一種抽象的秩序。文物景觀的秩序首先是圖底關系,文物展品與說明圖解構成突出于背景的“圖”,相對比較簡單。更重要的秩序是展品群組的內部關系,不同展品的文物價值具有隱性秩序,需要轉化為視覺層次來表達。豐富有序的視覺層次不僅可以優化整體視覺效果,而且可以形成信息傳達的層次以引導觀眾的視線與注意力,這種視覺與信息對應的層級關系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建構:(1)大小關系。體量大的展品一般更引人注目,小體量展品如果采用隆重的展陳形式或占據的空間超出普通陳列需要也能顯示其重要性,比如給小幅畫裝上多層級的大畫框,讓小幅畫作變成“大畫”。(2)疏密關系。展品的密集度與其重要性成反比,重要展品四周留白更多、占據的空間更大。(3)明暗關系。明暗關系是制造層次的重要手法,眼睛的趨光性會讓觀眾先注意到高亮度物體。通柜內的照度一般是明亮而均等的,但在景觀式的陳列中不同展品的照度應有所不同。(4)位置關系。從縱向來看,正常視高的位置最便于觀眾觀看,是視覺中心;稍低于視高的位置比高于視高的位置更易于觀看;距離正常視高的位置越遠,展品的重要性越低。從橫向來看,從左至右的書寫與閱讀習慣讓左側比右側的展品更引人注目,因而更重要的物品適合擺在左側。從前后縱深關系來看,前面的比后面的展品更重要,小體量展品陳列在前面稍低于視線的位置更便于觀眾觀看。(5)展具與陳列形式。展品有無展具及展具的不同形式都意味著展品的不同級別。對于三維展品,底座、托架、懸挑、懸掛等都是重點陳列的形式;對于二維展品,裝裱形式是其價值大小的視覺表達,可通過畫框的大小、層次、材質等體現。
根據展品的實際狀況綜合運用以上關系,就會形成一幅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的文物景觀。輔助展品與圖文說明的重要性處于文物展品之后,在視覺上也處于相對次級的層次。一般情況下,背景處于最底層,如果背景也是展品或背景中蘊含重要的歷史信息,其層級就會適當提前。
文物組合而成的歷史景觀最能體現格式塔心理學,如果觀者結合展板說明以及自己的歷史知識積累與想象,便能在腦海中構筑出更豐富的歷史景象。意大利博洛尼亞歷史博物館的23—28展廳共同表現了18—20世紀博洛尼亞的歷史發展狀況,每個展區的立面可視面都不大,但是進深比較大,遠遠超過了常見的通柜深度,這樣有利于形成展示的層次。如圖四所示,展區以懸掛的文物為展示中心,配合多種媒介物形成了六個視覺層次(1—6),文物又因展具的不同而構成三個小層次(1.1—1.3)。展區的元素是具體的,形成的關聯整體是抽象的,留給觀眾足夠的想象空間。

圖四// 意大利博洛尼亞歷史博物館展區(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五、結語
根據歷史博物館展覽的特點以及當代展覽追求沉浸式體驗的趨向,本文借鑒文化景觀的概念提出展覽的景觀化建構方式。歷史博物館展覽中的景觀意味著由多種元素構成的具有一定敘事與意義表達的空間圖示,由歷史遺留物與多種媒介物構成,并具有“器—象—道”三個層面。“象”作為蘊含著“器”與“道”的感知整體,形成吸引觀眾的第一印象,也成為營造體驗的關鍵所在,因而“象”是建構景觀的抓手。
在以“象”為先的景觀化思維之下,本文提出了三條建構途徑,并重點論述了各自的構成要素以及在應用上的關鍵點。利用天然的歷史景觀、重構歷史場景、景觀化的文物組合,這三條途徑中的前兩條屬于場景類,比較直觀,易于觀眾理解;第三條以文物為中心,更符合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性格,也可以擴展文物的敘事能力,應用面更廣。殊途同歸,不同的建構途徑適應不同基礎條件的博物館,都是為了更好地打造景觀之“象”,營造沉浸式體驗,進而更有效地實現傳播和闡釋歷史文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