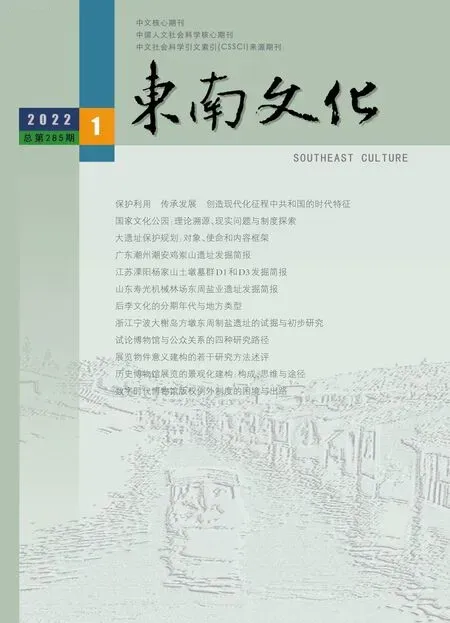夏商西周時(shí)期的定量容器與基本單位量淺析
劉艷菲 孔凡一 王 青
(山東大學(xué) 山東濟(jì)南 250100)
內(nèi)容提要:夏商西周時(shí)期是我國(guó)古代量制初步建立的重要時(shí)期,大口尊、盔形器、尖底陶杯、花邊陶釜、殷墟的部分銅容禮器和箕形器是這一時(shí)期比較典型的定量容器。通過(guò)分析殷墟箕形器和南河崖西周盔形器的容積,可知晚商的安陽(yáng)地區(qū)和西周中期的魯北制鹽作坊可能俱以250mL為基本單位量,與之配套的量制體系也可能已經(jīng)產(chǎn)生。
“量”指容量,“量制”即與容量有關(guān)的制度[1]。我國(guó)古代的量制在新石器時(shí)代晚期萌芽,到秦漢時(shí)期發(fā)展完備并實(shí)現(xiàn)全國(guó)統(tǒng)一,而夏商西周時(shí)期則是量制初步發(fā)展和承上啟下的階段[2]。《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夏書(shū)》有之曰:‘關(guān)石禾鈞,王府則有’”,韋昭注“《夏書(shū)》,逸《書(shū)》也。關(guān),門(mén)關(guān)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diào)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guān),衡也”[3],韋氏所言之意為夏代已有量制并用于稅收。《禮記·明堂位》則記載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治禮作樂(lè),頒度量,而天下大服”[4],或可說(shuō)明量制在西周時(shí)期已成為國(guó)家的基本制度。雖然歷史文獻(xiàn)對(duì)量制建立的時(shí)間和過(guò)程記載不夠明確,但可以說(shuō)明量制的初步建立大致就在夏商西周時(shí)期。
記載夏商西周時(shí)期量制情況的先秦文獻(xiàn)很少且語(yǔ)焉不詳,除上述外,《詩(shī)經(jīng)》和《儀禮》記錄了一些可能在西周時(shí)期使用的計(jì)量單位[5],但未詳細(xì)記載其量值、進(jìn)制關(guān)系等內(nèi)容。漢代有學(xué)者關(guān)注量制的起源問(wèn)題,認(rèn)為度量衡源于音律,如《史記·律書(shū)》載“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wàn)事根本焉”,索引按“律有十二。陽(yáng)六為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wú)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yīng)鐘”[6],后世的歷史文獻(xiàn)基本承襲此說(shuō)。現(xiàn)代學(xué)者如安金槐、丘光明、岳洪彬、方輝等曾對(duì)夏商西周時(shí)期的量制問(wèn)題進(jìn)行過(guò)一些探索[7],但史料和量器實(shí)物的匱乏使研究工作難以深入進(jìn)行,導(dǎo)致學(xué)界對(duì)夏商西周時(shí)期的量制情況尚未形成基本認(rèn)識(shí)。
實(shí)際上,除了歷史文獻(xiàn)和量器這兩類(lèi)能直接體現(xiàn)量制內(nèi)容的材料以外,定量容器同樣能為量制研究提供參考。定量容器是指容積被有意控制在特定范圍的容器,狹義的定量容器不同于由官方或權(quán)貴制作和管理、形制較固定、功能單一(專(zhuān)門(mén)用于盛測(cè)物體容積)的量器,而往往作為日用器皿和生產(chǎn)工具,種類(lèi)和功能多樣;廣義的定量容器則包含狹義定量容器和量器在內(nèi)。本文所說(shuō)的定量容器特指狹義的定量容器。有些定量容器雖然標(biāo)準(zhǔn)化程度很高,但實(shí)際上是批量化生產(chǎn)的結(jié)果,作器者和使用者對(duì)器物的容積可能并沒(méi)有特殊要求,如批量生產(chǎn)的日用盆、罐等。但有些定量容器則對(duì)容積要求較高,甚至還可能經(jīng)過(guò)了檢測(cè)和校正,以滿(mǎn)足使用者特定的生產(chǎn)與生活需要,它們與官方量制關(guān)系更加緊密,也更能反映當(dāng)時(shí)的量制情況。本文列舉的幾類(lèi)定量容器即為后者,文章主要討論它們的作用,并通過(guò)分析部分器物的實(shí)測(cè)容積對(duì)夏商西周時(shí)期的基本單位量提出自己的認(rèn)識(shí)。
一、夏商西周時(shí)期的定量容器舉例
1.大口尊
大口尊是夏商時(shí)期在中原地區(qū)廣為流行的日用陶器,以泥質(zhì)灰陶為主,整體呈筒形或細(xì)筒形,基本為大敞口,束頸,折肩或無(wú)肩,深腹略鼓或瘦細(xì)斜直,圜底或尖底。口部、頸部和上腹部多素面磨光,有的飾附加堆紋、弦紋或刻劃紋,下腹部與底部多裝飾細(xì)繩紋。在口沿內(nèi)部多刻劃有一個(gè)或兩個(gè)陶文記號(hào)(圖一)。安金槐先生認(rèn)為這些陶文記號(hào)絕大多數(shù)是從“一”到“十”的計(jì)數(shù)符號(hào),因?yàn)槎飴徬聦拥拇罂谧鹂谘貧埰校瘴挠浱?hào)相同者口徑也基本相同或極為相近,口徑相同代表容積也可能相同,所以他認(rèn)為這些陶文記號(hào)可能是大口尊測(cè)量容積后刻劃上去的,而大口尊的作用極有可能是糧食交易中的陶量[8]。但丘光明先生認(rèn)為大口尊并非量器,而是定量的糧食存儲(chǔ)器。因?yàn)猷鞯谆蚣獾椎奶攸c(diǎn)使其挹取和放置都十分不便,使用時(shí)必須置于坑洞中,而且其容積多在3萬(wàn)mL以上,明顯是存儲(chǔ)器的特點(diǎn)[9]。方酉生、岳洪彬、杜金鵬、許宏等學(xué)者則傾向于認(rèn)為大口尊是一種釀酒器或儲(chǔ)酒器[10]。

圖一// 夏商大口尊
上述幾位學(xué)者雖然對(duì)于大口尊的用途意見(jiàn)不一,但基本認(rèn)同安金槐先生的觀點(diǎn),即將陶文記號(hào)釋讀為與容量有關(guān)的計(jì)數(shù)符號(hào),筆者亦然。計(jì)數(shù)符號(hào)的含義應(yīng)是“大口尊容積與單位容積的比值”或“大口尊容積對(duì)單位容積的倍數(shù)”,但由于目前缺乏大口尊的容積數(shù)據(jù),我們無(wú)法得知單位容積的數(shù)值。至于大口尊的用途,其形制特點(diǎn)和巨大容積確實(shí)與量器特征不符,作為盛儲(chǔ)器的可能性更大。
2.盔形器
盔形器是商周時(shí)期魯北地區(qū)常見(jiàn)的陶器類(lèi)型,因其倒置時(shí)形似頭盔而得名。盔形器的質(zhì)地在商代以泥質(zhì)為主,在西周時(shí)期以?shī)A砂為主,其基本形制為直口、筒形腹、尖底或圜底,表面飾繩紋,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盔形器的主要用途是煮鹽(圖二)。王青根據(jù)文獻(xiàn)記載和山東壽光大荒北央西周制鹽遺址的發(fā)掘線(xiàn)索復(fù)原了商周時(shí)期魯北地區(qū)的制鹽流程,他認(rèn)為這一時(shí)期的煮鹽方法為淋煎法,分為攤灰刮鹵和煎鹵成鹽兩個(gè)主要環(huán)節(jié)。在后一環(huán)節(jié)中,需在鹽灶上放置百個(gè)大小相同的盔形器,然后向盔形器中添加鹵水煎鹵,最后破罐取鹽[11]。

圖二// 商周時(shí)期盔形器
盔形器的作用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或有體現(xiàn)。1954年山東濱縣(現(xiàn)濱州)蘭家村曾出土1件商代青銅卣,器身與器蓋均鑄“”字[12],方輝認(rèn)為該字為“鹵”,其字形與甲骨文中的“ ”(鹵)十分相似[13]。而據(jù)郭沫若等學(xué)者考證,甲骨文中的“鹵”即鹽[14],徐中舒認(rèn)為“ ”字“象盛鹽于容器之形。
為容器,其中之:為鹽粒。鹽為細(xì)小顆粒,嫌與他物相混,故并狀其盛之之器。金文……與甲骨文同”[15]。方輝據(jù)此進(jìn)一步判斷,與“ ”字形相近的“”“正像內(nèi)盛鹽粒的圜底盔形器之形”。此外,他認(rèn)為西周懿王時(shí)期的銅器銘文《免盤(pán)》所載“惟五月初吉,王在周,令作冊(cè)內(nèi)史易(賜)免鹵百(尊)”之“ (尊)”亦為盔形器[16]。
方輝對(duì)山東地區(qū)商周時(shí)期出土的盔形器進(jìn)行了測(cè)量,發(fā)現(xiàn)型式相同者尺寸、容積也比較接近,所以他認(rèn)為盔形器是食鹽特用的量器[17]。但筆者認(rèn)為盔形器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量器,而同大口尊一樣屬于定量容器。因?yàn)閺男再|(zhì)和作用上來(lái)說(shuō),量器是專(zhuān)門(mén)的測(cè)量工具,盔形器的主要用途則是煮鹽,兩者有根本區(qū)別。控制盔形器容積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控制食鹽的產(chǎn)量。筆者推測(cè),在淋煎法制鹽過(guò)程中,鹵水濃度可能是比較固定的,也就是說(shuō)一定量的鹵水在蒸干后析出鹽的總量也是固定的,那么若是想得到定量的鹽只需向盔形器中加入定量的鹵水即可。
3.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
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是中國(guó)古代川東地區(qū)的制鹽工具。尖底陶杯或稱(chēng)“角杯”,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漢初期,質(zhì)地主要為夾細(xì)砂的紅陶,少量為細(xì)泥磨光灰黑陶,直口無(wú)唇、薄胎斜壁、底部呈尖角狀或胡蘿卜狀(圖三︰1—4)。學(xué)界對(duì)尖底陶杯的具體用途意見(jiàn)不一,孫華、曾憲龍等學(xué)者認(rèn)為尖底陶杯是制鹽工具,“在被太陽(yáng)曬得滾燙的沙子里插上大量的裝有鹵水的尖底陶杯,并不斷往已經(jīng)蒸發(fā)的杯子里添加鹵水,最后獲得結(jié)晶的鹽”[18]。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尖底陶杯與蒸、煮無(wú)關(guān)而更可能是制作鹽塊的模子,如巴鹽認(rèn)為食鹽制好后會(huì)被倒入尖底陶杯中壓成想要的形狀,尖底陶杯主要發(fā)揮給鹽塊定型和后期運(yùn)輸?shù)淖饔茫?9]。但白九江則對(duì)鹽塊的制作過(guò)程持不同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尖底杯在制作鹽塊前被放置在帶火星的草木灰中加熱,然后在其中倒入鹵水熬成的高濃度鹽漿,鹽漿脫水和干燥后就形成了體積固定的鹽塊[20]。花邊陶釜或稱(chēng)花邊圜底釜,流行于西周至西漢早期,其口沿處抹壓成波浪狀,鼓腹圜底,頸部以下飾滿(mǎn)繩紋,形制與魯北地區(qū)的盔形器類(lèi)似(圖三︰5—7)。孫華、曾憲龍認(rèn)為花邊陶釜體量較大,“其圜底利于受火,可以將多個(gè)這樣的陶釜放置在灶上或支架上,用火加熱使鹵中的水分蒸發(fā),從而獲得結(jié)晶的鹽”[21],制鹽方法與盔形器有相似之處。

圖三// 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
與魯北地區(qū)的商周盔形器一樣,相同地點(diǎn)出土的同一時(shí)期的尖底陶杯或花邊陶釜容積大致相同,呈現(xiàn)出標(biāo)準(zhǔn)化甚至最佳化的傾向[22]。有學(xué)者對(duì)重慶哨棚嘴和瓦渣地遺址的尖底陶杯高度、口徑和比率進(jìn)行了詳細(xì)測(cè)算,發(fā)現(xiàn)兩個(gè)遺址的數(shù)值基本相同而且從始至終基本沒(méi)有變化[23]。花邊陶釜?jiǎng)t由最初的形態(tài)大小不一向形態(tài)大小相同演變,反映了專(zhuān)門(mén)化、制式化和批量化的發(fā)展過(guò)程[24]。尺寸相近的情況下,容積也無(wú)疑大致相同,所以?xún)烧邞?yīng)該都是定量容器。有學(xué)者認(rèn)為標(biāo)準(zhǔn)化的一個(gè)主要誘因是大小相同的制鹽容器能夠生產(chǎn)體積相同的鹽塊,而均一大小的鹽塊則可以作為很好的貿(mào)易交換單位甚至權(quán)充貨幣使用[25]。所以盡管尖底陶杯和花邊陶釜的制鹽方法存在爭(zhēng)議,我們?nèi)耘f能夠推測(cè)兩者可能同盔形器一樣在制鹽過(guò)程中發(fā)揮著控制產(chǎn)量的作用。
4.殷墟的定量銅容禮器和箕形器
岳洪彬等學(xué)者曾用蒸餾水測(cè)量過(guò)殷墟大司空M303和劉家莊北M1046出土青銅容禮器的容積,發(fā)現(xiàn)同類(lèi)容器的容積基本相同或成倍比關(guān)系,如爵的容量為250~260mL,觚 的 容 積 為 520~545mL,觚之容量恰好為爵之2倍[26]。《考工記·梓人》賈公彥疏引《韓詩(shī)說(shuō)》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斝)”[27],殷墟銅爵和銅觚正符合兩爵為一觚的記載。他們還對(duì)殷墟出土的多件銅斗進(jìn)行了測(cè)量,其容積分別為10mL(西北崗 M1380︰R001097)、25mL(M303︰180、M1046︰19)、50mL(西北崗 M1382︰R001096、小屯 YM331︰R002078)、100mL(M303︰98)、125mL左右(婦好墓銅斗),分別是250mL的1/25、1/10、1/5、2/5、1/2。根據(jù)這些測(cè)量數(shù)據(jù)和計(jì)算結(jié)果,他們推測(cè)“升”是晚商的基本容量單位,一爵即一升,1升=250~260mL[28]。
在小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過(guò)程中運(yùn)用經(jīng)典誦讀對(duì)于課堂教學(xué)效率與教學(xué)質(zhì)量的提高、小學(xué)生閱讀能力與寫(xiě)作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綜上所述,在小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中運(yùn)用經(jīng)典誦讀是促進(jìn)學(xué)生語(yǔ)文綜合素養(yǎng)養(yǎng)成的重要途徑。
青銅箕形器是殷墟常見(jiàn)的器形,因形似簸箕而得名(圖四)。在對(duì)殷墟出土的6件箕形器測(cè)量后,發(fā)現(xiàn)其容積基本是260g倍數(shù),因此岳洪彬等學(xué)者認(rèn)為青銅箕形器是晚商的量器,商代容量單位大致以260g為基數(shù)(以重量計(jì)算基本容積單位實(shí)際上并不合適,理由見(jiàn)下文)[29]。筆者認(rèn)為箕形器是否為量器尚有待商榷,因?yàn)榧词蛊淙莘e間有倍比關(guān)系,這種倍比關(guān)系也可能同殷墟青銅容禮器一樣,是出于將同類(lèi)器物的容積制作成倍數(shù)關(guān)系的生產(chǎn)習(xí)慣。所以目前將箕形器定性為定量容器更為穩(wěn)妥,要判斷其具體用途還需要參考更多材料。下文筆者通過(guò)對(duì)岳洪彬等學(xué)者測(cè)量結(jié)果的重新分析,得到每件箕形器的容積,進(jìn)而得出箕形器可能使用的基本單位量在250mL左右,與銅容禮器基本相同。

圖四// 殷墟的青銅箕形器
二、基本單位量淺析
基本單位量是指量制體系中基本單位的量值,其他量制單位通常與之成一定序列的倍比關(guān)系。例如東周時(shí)期齊國(guó)的量制以升為基本單位,以200mL為基本單位量,區(qū)、斗、釜、鐘等量制單位的容積均是200mL的倍數(shù),姜齊量制1豆=4升=800mL、1區(qū) =16升 =3200mL、1釜 =64升 =12800mL、1鐘=640升=128000mL,田齊量制1豆=5升=1000mL、1斗=10升=2000mL、1區(qū)=20升=4000mL、1釜=100升=20000mL、1鐘=1000升=20000mL[30]。由下述幾類(lèi)定量容器,可以大致計(jì)算出商周時(shí)期部分地區(qū)可能使用的基本單位量。
1.南河崖遺址群出土西周盔形器的基本單位量
南河崖遺址群位于山東省東營(yíng)市南河崖村,包含晚商、西周、東周、漢代以及宋元等時(shí)期的遺存。2008年3—6月,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聯(lián)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xiàn)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東營(yíng)市歷史博物館對(duì)該遺址進(jìn)行了發(fā)掘,發(fā)掘區(qū)位于第一地點(diǎn),發(fā)掘面積915.3平方米,“清理出一處西周時(shí)期的煮鹽作坊址,發(fā)現(xiàn)一批重要的煮鹽遺跡和大量陶盔形器”,各類(lèi)西周遺存的年代相差不大,均在西周中期前后,主要出土遺物盔形器的前后演變關(guān)系并不明確[31]。發(fā)掘者對(duì)此次發(fā)掘出土和采集的27件完整或可修復(fù)盔形器的容積進(jìn)行了測(cè)量,測(cè)容物選擇了與食鹽質(zhì)地接近的顆粒均勻的細(xì)沙。首先用細(xì)沙盛滿(mǎn)盔形器直至溢出,然后用直尺沿口沿抹去多余部分,最后將盔形器中的細(xì)沙盛入量筒中測(cè)量體積。盔形器的容積數(shù)據(jù)大致集中在五個(gè)數(shù)值范圍內(nèi):第Ⅰ級(jí)1250mL,1件;第Ⅱ級(jí)1500~1550mL,4件;第Ⅲ級(jí)1700~1800mL,7件;第Ⅳ級(jí) 1900~2150mL,14件;第Ⅴ級(jí)2700mL,1件。
按照出土位置由早到晚排列,可以看出盔形器在各個(gè)階段都有多種規(guī)格,而且同一時(shí)期同一單位中出土的盔形器也并不完全相同,如T0304F4和T0304TC1③中出土的盔形器都有Ⅱ、Ⅳ級(jí)兩種規(guī)格(表一)。盔形器的容積差異可能是制作者刻意造成的,目的可能是控制產(chǎn)鹽量,在不同規(guī)格的盔形器中生產(chǎn)出不同體量的食鹽。而通過(guò)進(jìn)一步觀察可以看出盔形器的容積大致都與250mL呈倍比關(guān)系,Ⅰ—Ⅴ級(jí)分別大約是250mL的5、6、7、8、11倍,換言之,250mL很有可能是這些盔形器的基本單位量。

表一// 2008年南河崖遺址西周盔形器測(cè)量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表
商周時(shí)期的魯北地區(qū)是生產(chǎn)食鹽的重鎮(zhèn),需定期向中央繳納食鹽作為貢賦,《尚書(shū)·禹貢》記載“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cuò)”[32]。貢賦的繳納需要固定的計(jì)量標(biāo)準(zhǔn),甲骨卜辭和西周早期金文中涉及鹽貢或用鹽作祭品時(shí)常作“鹵+數(shù)詞”和“數(shù)詞+鹵”的形式,而盔形器與食鹽的生產(chǎn)和運(yùn)輸關(guān)系密切,所以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一個(gè)盔形器所盛的食鹽可能即一個(gè)“單位量”[33]。根據(jù)本文的研究,盔形器的容積和產(chǎn)鹽量(也就是盔形器代表的食鹽“單位量”)可能都與250mL這一基本單位量密切相關(guān)。若此結(jié)論準(zhǔn)確,定然對(duì)日后進(jìn)一步細(xì)化復(fù)原商周時(shí)期魯北地區(qū)的食鹽生產(chǎn)過(guò)程有重要意義。
2.殷墟青銅箕形器的基本單位量
岳洪彬等學(xué)者通過(guò)測(cè)量箕形器盛重的方式計(jì)算出商代容量單位大致以260g為基數(shù)[34],但筆者認(rèn)為這種方法有不夠嚴(yán)謹(jǐn)之處。《周禮·考工記》對(duì)栗氏量、甗、甑、鬲、簋、爵、觚等容器的尺寸和容量作了詳細(xì)的規(guī)定,并運(yùn)用“以度審容”的方法計(jì)算容量(即通過(guò)校準(zhǔn)尺寸確定容積)[35],說(shuō)明工匠在制造量器和定量容器時(shí)更關(guān)注器物的容積而非盛重,所以我們?cè)谠O(shè)計(jì)實(shí)驗(yàn)時(shí)也應(yīng)如此。因此筆者重新對(duì)岳洪彬等學(xué)者的實(shí)驗(yàn)進(jìn)行了改良,從箕形器的容積出發(fā)討論基本單位量的問(wèn)題。
首先,回顧一下岳洪彬等學(xué)者的實(shí)驗(yàn)過(guò)程,他們選擇了6件箕形器,以小米為測(cè)量物,將小米盛入箕形器中,然后再將所盛小米分別放入天平稱(chēng)重。實(shí)驗(yàn)設(shè)計(jì)了兩種小米盛放方法:一種是讓箕形器盡可能多地鏟起小米,然后讓小米自然滑落至不再滑落為止(簡(jiǎn)稱(chēng)“A方式”);另一種是將小米鏟起后以直尺沿箕形器口沿滑動(dòng),將超出口沿的小米刮去(簡(jiǎn)稱(chēng)“B方式”)。將兩種方式的盛重?cái)?shù)據(jù)兩兩相減得到差序,得到A方式的所得差序基本為等差序列,因此他們認(rèn)為箕形器的正確使用方式為A方式(表二)。A方式下,6件箕形器的容量從小到大依次為260g的3倍、5倍、7倍、11倍和15倍,結(jié)合銅爵和銅觚的容量分別為260g(即測(cè)容物蒸餾水260mL,蒸餾水密度為1)的倍數(shù),他們判斷商代容量單位大致以260g為基數(shù)[36]。

表二// 箕形器容量測(cè)定結(jié)果統(tǒng)計(jì)表

表三// 小米測(cè)量結(jié)果統(tǒng)計(jì)表
總體來(lái)看4種小米的體積與重量比基本都在1.2左右,筆者以此數(shù)值換算6件箕形器的容積,得到結(jié)果見(jiàn)表四。

表四// 箕形器容量計(jì)算結(jié)果統(tǒng)計(jì)表
一般情況下,作為定制的基本單位量在一定區(qū)域內(nèi)具有統(tǒng)一性,而且很長(zhǎng)時(shí)間內(nèi)不會(huì)被輕易更改。根據(jù)殷墟容禮器觚、爵等容積與250~260mL呈倍比關(guān)系的事實(shí),假設(shè)箕形器的基本單位量亦為250mL,計(jì)算每個(gè)箕形器的容積與250mL的比值,可以得出如下結(jié)論:A方式的比值從1到6大致為19、14、8.5、6、6、3.7,B方式的比值1到6大致為18、12、8、5.5、4.5、3。顯然B方式的計(jì)算結(jié)果更有順序性,倍比關(guān)系也更加明顯,說(shuō)明250mL可能就是箕形器的基本單位量。而且可以想象,使用箕形器時(shí)若要控制所盛物品的體積或重量,B方式的精確度顯然會(huì)更高一些,所以B方式更有可能是箕形器的正確使用方式。
綜合殷墟銅容禮器和箕形器的情況,可以推測(cè)250mL可能是晚商時(shí)期安陽(yáng)地區(qū)通用的基本單位量,其對(duì)應(yīng)的量制單位可能如岳洪彬等學(xué)者所說(shuō)為“升”。而基本單位量的廣泛使用說(shuō)明晚商時(shí)期可能存在與之配套的量制體系。
三、結(jié)語(yǔ)
夏商西周時(shí)期人們已經(jīng)能夠通過(guò)有意識(shí)地控制容器的容量滿(mǎn)足某些生活和生產(chǎn)需要。大口尊是夏商時(shí)期比較常見(jiàn)的日用盛儲(chǔ)器,在口沿處刻劃計(jì)數(shù)符號(hào)可便于使用者了解所盛放物品的體積。盔形器、尖底陶杯、花邊陶釜均為商周時(shí)期的食鹽生產(chǎn)工具,定量的目的可能是更好地控制產(chǎn)鹽量。商人對(duì)殷墟部分容禮器和箕形器控制容積則可能是出于禮制需求。
殷墟部分青銅容禮器、箕形器與東營(yíng)南河崖西周盔形器的基本單位量均在250~260mL左右,這種“巧合”引人深思。如果它們能夠分別代表當(dāng)時(shí)的官方量制標(biāo)準(zhǔn),那么這意味著晚商時(shí)期安陽(yáng)地區(qū)的基本單位量可能沿用到了西周中期的魯北地區(qū),而且當(dāng)時(shí)可能已具備了與基本單位量配套的量制體系。有意思的是,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灣F901出土量器的基本單位量同樣在260mL左右[38]。由于材料所限,筆者目前無(wú)法判斷大地灣量器的基本單位量與商周基本單位量之間是否存在承襲關(guān)系,但這是非常值得留意的現(xiàn)象。另外東周晚期大部分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基本單位量值都在200mL左右,相比晚商和西周數(shù)值上略有減小[39],量值變化的原因同樣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