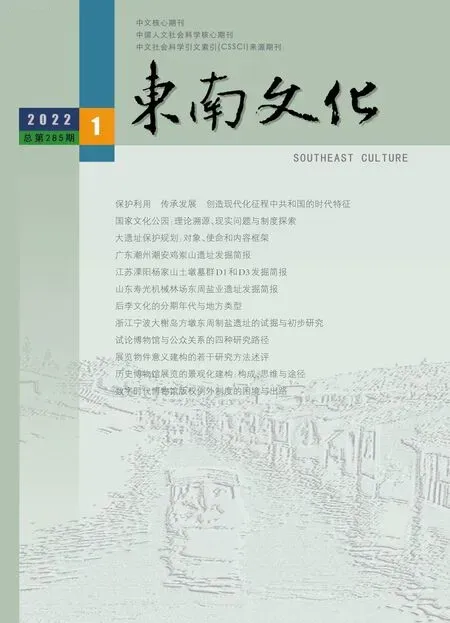以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為例探索利益相關者遺產話語權
張柔然 劉亦雪
(1.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廣東深圳 518060;2.上海師范大學旅游學院 上海 200234)
內容提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項目在各國的世界遺產申報過程中重視國際專家話語權,而忽視當地居民和游客的話語。在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申遺的過程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國際專家不能全面地理解國內專家在西湖申遺文本中陳述的價值。而游客與當地居民的話語不僅能夠理解西湖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也會將其與個人的情感、經歷和記憶聯系,構建出西湖的“民眾社會價值”。
自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以來,中國遺產保護工作從觀念到實踐都經歷了變革,世界遺產體系推動中國遺產保護工作不斷更新保護理念,革新保護技術,并向更高標準的方向不斷前進。在這一過程中,世界遺產體系與中國遺產保護雙向影響,中國遺產保護對世界遺產價值的認知也不斷深化。在世界遺產體系的推動下,中國遺產保護觀念經歷了從探索到熟悉再到積極參與的階段[1]。
2011年杭州西湖成功申報“文化景觀”遺產類別。在西湖申報的過程中,中國以國際化的方式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人文與自然關系,向世界展示了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詩意棲居的優秀中華傳統文化[2]。但是,還有一些與西湖有關的價值精髓沒能得到國際專家的理解。本文分析在西湖申遺過程中中外遺產專家的話語關系,對比中外專家與遺產當地居民和游客對于西湖所體現的中國傳統價值理解的異同,剖析當地居民和游客在參觀遺產地過程中構建出的“非權威遺產話語”,探索如何在世界遺產申報和管理過程中納入民眾話語。
一、以歐洲價值為中心的世界遺產話語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布了《世界遺產公約》,確定了評估世界遺產突出普遍價值的標準和實踐指南,世界遺產項目在過去46年的實踐過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截至2021年8月,全球167個《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中有1154處世界遺產,其中文化遺產897處,自然遺產218處,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39處。毋庸置疑,UNESCO世界遺產項目在世界范圍內非常有影響力,UNESCO積極開展的國際實踐與討論及所確立的遺產的國際定義,極大地推動了遺產項目的進程。
索菲亞·拉巴迪(Sophia Labadi)指出,UNESCO強調的普世價值觀念有些過于偏執[3]。首先,UNESCO世界遺產項目對遺產的定義過于狹隘,它將文化遺產定義為具有宏偉奇觀的歷史文物、歷史建筑、人類文化遺址等,同時認為這些遺產地具有“突出普遍價值”[4]。其次,世界遺產項目價值評定的話語權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WHC)、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專家主導,而這些國際機構的專家多來自西歐或受到西方哲學思想影響的國家[5]。國際專家在遺產價值觀的確定上有難以撼動的權威,他們構建了遺產話語的普世價值以及評估世界遺產價值的標準,這一點可以從《世界遺產名錄》(The World Heritage List)上反映出來。接近50%的世界遺產地均位于歐洲,這是基于偏向歐洲的基督教觀念和哲學思潮對遺產觀念的認知所造成的[6]。UNESCO在20世紀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試圖使《世界遺產名錄》更加開放,為此,UNESCO一直都在遺產方面融入新的觀念。
20世紀90年代起,UNESCO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領域,旨在反思以西方哲學思想為指導的世界遺產評定標準所造成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在《世界遺產名錄》中數量上的失衡[7]。《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以下簡稱“《操作指南》”)定義“文化景觀”為“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并將文化景觀分為三類:“人類有意設計和建造的景觀”“有機演進類景觀”和“關聯性景觀”[8]。文化景觀的出現對《世界遺產公約》自然與文化二元分化的概念提出了挑戰,強調二者的融合。UNESCO世界遺產中心前主任弗朗切斯科·班達蘭(Francesco Bandarin)指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了《世界遺產公約》積極吸納新思想的精神,它不僅打破了傳統的三大類世界遺產(包括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的格局,擴大了世界遺產的代表類型,還使人類與自然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了新體現[9]。
近三十年來,文化景觀的概念在各國遺產申報和管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涌現出一些問題。一些學者指出,文化景觀價值的評定標準話語權仍由西方的專家主導,而其他遺產使用者的話語權仍有待充實,如游客、當地居民、少數族裔或女性等[10]。每個國家、地區和社區都有獨具區域特色的文化景觀,從不同角度觀察,每處文化景觀都具有多種不同的價值,遺產從業者需要與當地居民溝通來了解這些價值。肯·泰勒(Ken Taylor)認為,文化景觀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銜接文化和自然的工具或方法,能夠幫助我們以一種更清晰的方式來認識遺產的價值[11]。怎樣去做、如何評判文化景觀的價值、又由哪些利益相關者參與和決策,這些是文化景觀遺產事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二、國際遺產話語權研究
21世紀初,世界遺產項目在實踐過程中屢屢出現問題,“遺產思辨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應時而生。勞拉簡·史密斯(Laurajane Smith)2006年的專著《遺產的利用》(Use of Heritage)是批判性遺產研究的里程碑[12]。該書的核心觀點是“權威化遺產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源于19世紀西歐建筑學和考古學關于遺產保護的討論,并以西方哲學思想構建自上而下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從專家的角度闡釋評估、保護和保存歷史建筑、遺址或人文景觀的價值,重視物質遺產的歷史價值、審美價值和科學價值,認為這些價值是有限的、脆弱的和不可再生的;并通過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規范、標準和全球性體系讓人們了解并傳承這些“突出普遍價值”的重要性[13]。
“權威化遺產話語”重視遺產的物質性及其歷史價值、審美價值和科學價值,卻忽視這些價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全球各地區不同文化利益相關者所賦予的。因此,“遺產思辨研究”關注不具備話語權的群體,即“非權威遺產話語”,如工人階級、婦女、少數族裔等,并從新的視角詮釋遺產的意義[14]。這樣做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專家為主導的權威話語對遺產解讀的壟斷,進而接受更加民主和開放的遺產觀念。
本文的研究框架立足于“遺產思辨研究”,認為遺產不是一個事物或一個地點,或者任何的物質,盡管這些物質的因素很重要,但不是遺產本身。遺產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和文化過程,該過程由多層價值和意義組成,并由人賦予其價值。這一過程不僅基于從傳統的由“專家”以“權威化遺產話語”為主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管理和實踐所組成,其另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當代遺產的主要利用者——“非權威專家”利益相關者,特別是遺產當地居民和游客的參與。他們不僅是“權威化遺產話語”的被動接受者,而且是遺產當代社會與文化價值的保存者和構筑者。當地居民和游客通過在遺產地的生活或參觀行為,將這種行為與個人的經歷、感受、情感、記憶交融在一起,創造出遺產的意義。本文以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為例,首先對比分析在西湖申遺的過程中西方權威化遺產話語與中國世界遺產話語的異同,然后分析當地居民和游客在參觀遺產地過程中構建出的“非權威遺產話語”能否反映西湖文化景觀價值,最后對如何將“非權威遺產話語”即民眾話語納入世界遺產申報與管理提出建議。
三、中國遺產話語VS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
杭州西湖有著“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整體格局,從唐代開始,西湖的美就被無數文人雅士稱頌。從南宋起,“西湖十景”就被認為是代表中國詩情畫意的理想典范,顯示了人與自然的完美融合。WHC2011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認為,西湖符合《操作指南》中突出普遍價值標準(ii)、(iii)和(vi)[15]。
西湖申遺的成功是我國專家不懈努力、力爭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體現于國際遺產事務的結果。但是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WHC和ICOMOS的專家并沒有全面地理解西湖所體現出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精髓。筆者曾對兩名主要負責西湖申遺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及三名直接負責編制《杭州西湖文化景觀》(以下稱“《西湖申遺文本》”)的專家進行深度訪談;并對比分析了《西湖申遺文本》《ICOMOS西湖申遺評估文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2011年世界遺產大會決議》,旨在探究在西湖申遺過程中,中國專家怎樣使西湖的“詩情畫意”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獲得國際專家認可;再從西湖的文化多樣性、發展與傳承以及其與龍井茶園的關系這三個方面對比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與中國遺產話語兩者之間的差異。
(一)西湖的“詩情畫意”
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分管西湖申遺工作的杭州市副市長張建庭喜極而泣,其原因是在申遺的過程中,國外的世界遺產專家很難理解西湖所傳達的價值精髓[16]。筆者于2013年11月、2014年2月、2017年12月和2018年10月先后四次對兩名主要負責西湖申遺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及三名直接負責編制《西湖申遺文本》的專家進行深度訪談。由于是匿名采訪,本文將不標明官員和專家的身份。
在上述訪談中,我國申遺專家表示,雖然UNESCO和ICOMOS等國際機構的專家最終認可了西湖的價值,但過程非常困難:“在西湖申遺之初,我帶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站在蘇堤,給他解釋什么是‘詩情畫意’。詩歌原本是要通過朗讀才能傳遞感情,畫作也是要通過觀看才能了解它的意思。但是中國哲學思想是人站在自然中,從水拍駁岸、風聲和鳥叫就能感受到‘詩情畫意’。我覺得自己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但是國外專家卻說他什么感覺也沒有。”隨后,杭州政府邀請了三個來自ICOMOS的國際專家為西湖申遺提供意見,國內申遺專家回憶:“第一個國際專家表示‘西湖要是能夠申遺成功,也算是你們為世界遺產體系填補了一個空白’,我原以為她只是客氣。但是后兩位國際專家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這就給我很大的壓力。”國家文物局主管西湖申遺的官員也表示:“一位來自北歐的ICOMOS專家參觀完西湖后,完全不明白西湖的價值,他問我們‘在北歐有數量眾多的湖泊比西湖更大更美,西湖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在哪里呢?’”
面對國際專家不能理解西湖之美這一問題,我國申遺專家開始積極尋找對策:“我在西湖申報世界遺產的時候研究了德國心理學家西奧多·立普斯(Theodor Lippsor)關于美學的解釋,特別是他在《美學空間》‘移情作用’的概念。我想學習怎樣從‘人’的角度解釋自然,但卻發現中國人的思想理念從來沒有分為主客體,一直都是人和物相聯系,也就是中國哲學所談的‘天人合一’。”“我們仔細研究《操作指南》,充分了解世界遺產申報的評估標準,并設立了一些西湖研究專題,旨在根據世界遺產的標準提煉出西湖的核心價值。”
最終,在中國申遺專家和政府官員的努力下,WHC和ICOMOS的國際專家終于承認并高度認可我國專家從中國文化藝術史中提煉出的西湖所代表的“提名景觀”和“中國山水美學”等傳統文化精髓,以及“寄情山水”和“詩情畫意”的東方審美方式。然而,西湖的申遺成功并不代表國際專家最終全面認識到西湖的價值,對于西湖的文化多樣性、發展與傳承以及其與龍井茶園的關系三個方面,國際專家所代表的西方權威化遺產話語與我國專家所代表的中國世界遺產話語存在明顯差異。
(二)西湖的文化多樣性
在《西湖申遺文本》中,我國申遺專家認為,西湖見證了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和傳統。其文化多樣性包括儒教、佛教、道教、忠孝之道、隱士生活、藏書、茶禪和篆刻。從12世紀杭州成為一個禪宗圣地開始,其佛教建筑見證了12世紀佛教在中國南方的傳播,“西湖十景”反映出佛教思想與景觀的融合;宋代的隱士林逋墓碑見證了隱士文化在東亞的傳播;龍井茶的種植被認為影響了東亞茶道文化;抱樸道院是中國最重要的道觀;岳飛墓是忠孝的象征,它傳達了儒家傳統思想,賦予了西湖精神層面上的意義[17]。
然而,國際專家在ICOMOS西湖申遺評估文件中表明,儒學、佛教、道教不能夠作為西湖突出普遍價值的特殊證明,因為在國內和國際其他遺產地存在著更為廣泛和重要的證明。國際專家還認為西湖在忠孝、隱士文化、藏書、茶禪和篆刻方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理由也并不充分[18]。
對于國際專家不理解西湖所體現的文化多樣性,西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申遺的專家認為:“ICOMOS專家并不理解西湖的多元文化。他們只認定了西湖的‘詩情畫意’的意義和對東亞景觀設計的影響。ICOMOS專家把西湖的儒教、佛教、道教、忠孝、隱士文化、藏書、茶禪和篆刻等元素拆分成獨立的個體來看,而在我們中國文化中,這些元素則被認為是一個整體,共同構成西湖文化。”
(三)西湖的傳承與發展
我國專家認為,西湖的發展從唐朝至今經歷了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是中國人利用古瀉湖創造優雅景觀、顯著改善人居環境的杰出范例。西湖對于當代杭州的意義在于,在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下,承擔了城市生態文明發展和旅游等功能[19]。
然而,在ICOMOS西湖評估文件中,國際專家不認可西湖是不斷發展的文化景觀。他們所認可西湖的突出普遍價值是和中國封建帝國時期的古典文學藝術和文化以及創造力相關,但這些價值在清代已經成形,因此ICOMOS專家不認為清代以后西湖的變化與突出普遍價值相關聯[20]。對于國際專家的評估結果,西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申遺專家認為:“西湖是在不斷發展傳承的,我們將西湖作為文化景觀類別申報就是想體現其不斷進化和吸取新的文化元素,新的價值在逐漸成形,就像‘西湖十景’并不是成形于朝夕。我認為不斷發展的過程是體現文化景觀的精髓,ICOMOS專家不認可西湖是不斷發展的文化景觀的決定是片面的。”
(四)西湖龍井茶園
龍井茶園被ICOMOS所代表的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建議從世界遺產核心區刪除,讓所有參與申遺的中國專家感到不解與失望。在《西湖申遺文本》中,我國專家這樣陳述:龍井茶園代表中國茶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結合,對東南亞的茶道文化有著深遠影響,是西湖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是西湖文化“完整性”的重要體現[21]。然而,ICOMOS西湖評估文件表明,國際專家認為龍井茶園是一種“農場”景觀,與西湖的突出普遍價值沒有任何關系,也不能體現西湖的美學理念。ICOMOS專家還建議,由于茶園被湖西邊的山丘遮蔽,沒有對西湖突出普遍價值產生影響,希望我國能夠縮小世界遺產申報的邊界,將龍井茶園和與之相關的村落排除在世界遺產核心區外[22]。
負責西湖申遺的專家談及龍井茶園,認為:“喝龍井,游西湖,這兩者原本是分不開的。我們在最初申遺的時候命名為‘龍井·西湖文化景觀’,但是受邀來給我們提供意見的國際專家不了解西湖所體現的‘詩情畫意’,以為我們要以龍井茶園景觀作為申報重點。這當然不符合我們的初衷,因此杭州市領導批復后最終確定申遺的名字為‘西湖文化景觀’,我們將申遺的重點放在證明西湖的‘詩情畫意’,并將龍井茶園作為西湖的一個文化元素。國際專家雖然最終認可了西湖的‘詩情畫意’,卻認為龍井茶園與西湖所體現的‘詩情畫意’一點關系也沒有。我們隨后找了很多典籍從歷史價值的角度證明龍井茶園的重要性,但是ICOMOS的專家仍然不認可,并要求我們必須將龍井茶園從世界遺產核心區移到緩沖區。我們在ICOMOS的會議上據理力爭了很多次,但還是沒有結果。為了不耽誤西湖的申報,只能忍痛將龍井茶園排除在世界遺產的核心區外。”
(五)中國遺產話語與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差異性
上述分析得出,ICOMOS專家所代表的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受限于西方哲學思想,不認可西湖的文化多樣性、傳承與發展和龍井茶園的價值。這些專家在世界遺產申報中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即便不能全面理解西湖所體現的中國傳統價值,卻能決定什么具有突出普遍價值,這使得《世界遺產名錄》中的西湖價值不夠完整。
中國專家在西湖申遺過程中試圖全面展示西湖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精髓,但在申遺之初卻發現以中國人的思維向西方專家解釋并不可行。隨后,我國專家及時調整策略,并深入研究《世界遺產公約》和《操作指南》等國際文件,用國際語言解釋西湖價值。最終國際專家高度認可了西湖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情畫意”及其對東亞各國景觀設計和文化影響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西湖的文化多樣性、傳承與發展和龍井茶園的價值未被國際專家認可。由此可見,中國專家和官員所代表的中國遺產話語雖然具有解釋西湖價值的責任和義務,但最終還需獲得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的認可。
實際上西湖申遺體現出的中國遺產話語與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的矛盾并不是個案。云南紅河哈尼梯田、廣西左江花山巖畫分別于2013年、2016年以文化景觀類別登錄《世界遺產名錄》。國際專家同樣對于國內專家在申遺文本中闡述的美學價值不予認同。例如,兩個遺產地都以文化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標準(i)“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一種創造性的天才杰作”為申遺的重要依據。我國遺產專家認為哈尼梯田是哈尼人與他們的所處環境之間巧妙互動產生的景觀,梯田是人與自然共同協作的產物,具有極強的美學價值[23]。而ICOMOS認為,梯田所呈現的美學價值并不是哈尼人有意設計的,與他們的審美創造力沒有關系。對于左江花山巖畫,國內遺產專家認為巖畫突出表現的繪畫技法體現了受到自然影響下駱越人的精神生活,而ICOMOS同樣不認可這一價值[24]。
在全球范圍內,一些學者發現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對于突出普遍價值的評定與部分世界遺產的本地文化屬性不相符。例如,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的土著居民認為其最重要的遺產價值是他們通過土地與祖先的精神聯系,但國際權威遺產話語將其列入世界遺產的原因卻在于其生物多樣性等普遍價值,而并沒有列入其精神價值。這一案例說明受國際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影響,世界遺產體系并不能充分理解地方文化屬性[25]。
四、當地居民與游客遺產話語分析
筆者于2013—2019年間曾四次前往杭州西湖,期間對參觀西湖的125名外地游客和83名杭州市民進行訪談。對于國際專家通過我國專家竭力闡釋才得以理解的西湖的詩情畫意,以及最終并未被國際專家認可的西湖文化多樣性、傳承與發展和龍井茶園問題,受訪的游客和當地居民卻能夠從個體或集體記憶的視角予以闡述(表一)。

表一// 杭州當地居民與游客話語摘錄
從訪談案例可以看出,游客和當地居民能夠理解我國專家在申遺文本中所闡述的西湖價值。第一,他們受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影響,話語中表達出對西湖“詩情畫意”真摯的情感,通過游覽體現出“寄情山水”的情懷。一些游客會用修辭手法來描述自己的情感和美學感受;或像蘇軾、白居易等詩人一樣,自己吟詩作對來表達情感;或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空間中與古人對話。第二,他們能結合自己的游覽經歷和生活背景,表達出對西湖儒學、佛教、道教、忠孝、隱士文化、藏書、茶禪和篆刻等文化的個人理解。第三,游客在陳述自己的游覽經歷時明確提到西湖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當地居民則關注西湖的新發展,并為此表達出自豪的情感。第四,受訪游客和當地居民從自身感受出發,主動將西湖的意境與龍井茶聯系,表示西湖龍井茶園是西湖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總之,受訪的游客和當地居民對西湖多元價值的理解帶有鮮明的國家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特征,并融入個人背景、情感、記憶和感受。他們代表的“非權威遺產話語”更加多樣化、詳細和生動,體現出浪漫主義與鄉愁,表達出自豪感與愛國情懷等多樣化價值觀。雖然游客與當地居民不具備遺產評估的專業知識,但卻能夠比國際專家更輕松地理解西湖的詩情畫意和文化多樣性等價值。
五、總結
“文化景觀”這一概念本身是西方反思遺產權威話語,彌補基于西方哲學中的遺產觀,即文化—自然二元割裂而提出的,我們應在文化景觀的框架下對其內容補充完善。文化景觀遺產的屬性是動態發展的,它的價值涉及多種屬性和不同的社區,隨著時間或情景的變化,社區和各類屬性之間的反應又會產生新的價值。因此,對文化景觀遺產進行申報和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需要本國專家和管理者與遺產地當地居民積極協商,并積極收集游客的意見,根據文化景觀屬性動態發展的具體情況來制定遺產申報和管理策略。
具體到實踐過程中,可以通過訪談、座談、參與觀察等方式記錄以當地居民和游客為代表的非權威利益相關者對于遺產價值的理解和情感表達,并在遺產申報過程中提煉出“民眾社會價值”。還可以借助大數據的方式,通過微信、微博、攜程、馬蜂窩等社交媒體和網絡收集當地居民和游客對于遺產地保護與管理的相關話語和評論,分析后得出“民眾社會價值”相關指標,整合并應用于遺產地申報過程中。“民眾社會價值”還能夠通過大數據的手段及時更新,能夠及時地挖掘遺產地價值,適用于遺產地的管理和監測。
在國際形勢這個層面,ICOMOS于2017年底頒布《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 on Heritageand Democracy)和《文化—自然之旅——Yatra聲明》(Yatra Statement)[26],兩份聲明均強調探索民眾話語對構建世界遺產價值的重要作用,這反映了UNESCO世界遺產項目開始實質性重視并支持民眾話語權。因此,中國在未來世界遺產申報和管理過程中,應重視民眾話語權所構建的遺產地社會價值,將中國專家話語與民眾話語相融合,俾能夠更加客觀全面地探索遺產地價值。
另外,2021年3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資源部與國家文物局共同頒布了《關于在國土空間規劃編制和實施中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將歷史文化遺產空間信息納入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臺”,“民眾社會價值”也應作為一項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空間子內容,納入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臺。
文化景觀遺產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遺產從業者不僅要保護過去,更重要的在于展望未來。回溯過去,英國的湖區(Lake District)是促使文化景觀遺產納入《操作指南》的典型案例,它于2017年以文化景觀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雖然英國人在1987年和1990年兩次為其申遺都以失敗告終,但卻引發遺產行業的廣泛討論——如何將代表文化與自然融合價值的遺產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92年將“文化景觀”概念納入《操作指南》是遺產從業者探索文化和自然融合價值的里程碑,但在實踐過程中仍存在諸多問題。2016年9月,在美國夏威夷(Hawaii)召開的IUCN世界保護大會上,為找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然與文化融合的方法,IUCN和ICOMOS共同提出了“文化—自然之旅”項目。該項目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考慮文化景觀,融入生物多樣性,關注各地區的文化和語言,鼓勵傳承傳統技術并積極利用新的技術,進而促進文化與自然的交融[27]。
自“文化—自然之旅”項目開展后,各國正在積極探索以不同的方式促進不同文化與自然的交融。對于中國而言,遺產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應關注“非權威遺產話語”,開展自下而上的研究,從民眾的角度探索遺產社會價值。中國的專家學者也應積極參與國際遺產交流,從民眾的視角將中國優秀的世界遺產管理和研究案例體現在國際框架中,講好中國故事。未來文化景觀的發展應寄希望于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價值體系來實現文化和自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