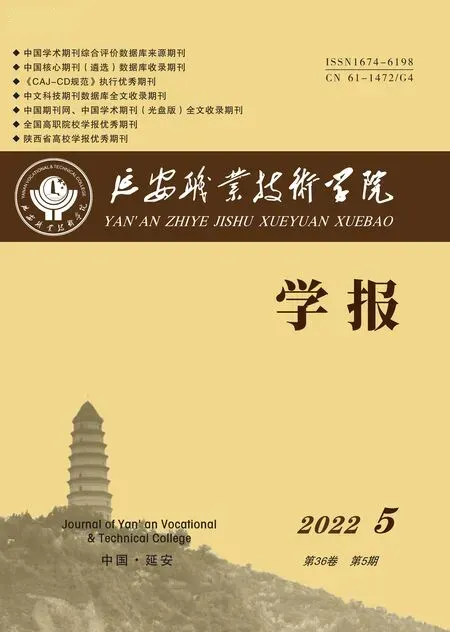論志賀直哉反戰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翟一溪
(唐山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
志賀直哉一生近乎經歷了日本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戰爭。少年時(11歲)時甲午戰爭爆發,青年時(21歲)目睹了日俄戰爭,中年時(31歲)見證了一戰,老年時(54歲)更是歷經了日本侵華戰爭。甲午戰爭爆發時志賀直哉年紀幼小未能發表反戰言論,而對于其余三場戰爭他都表現出明確的反戰態度。志賀直哉的反戰作品基本以篇幅不長的短篇小說、隨筆以及日記等形式呈現,展現了戰爭對于人性的蹂躪與破壞,戳破了浪漫英雄主義背后的獨裁專制的虛偽面孔,表現了他對戰爭踐踏人道的憤怒[1]78。人道主義是其反戰小說的核心,他從個體出發擴展到整個社會,追求個人與社會的愛與正義。
一、日俄戰爭時期
(一)戰爭對個人的扭曲
志賀直哉反映日俄戰爭的作品基本都立足于普通士兵來表現殘酷的戰爭,表現戰爭對人造成的外在傷害,深入人物內心,反思戰爭對人性的扭曲。他的短篇小說《插曲》將日本退役大尉作為敘述主體,以冷酷的筆調表現了日俄戰場上兇殘的日軍形象。小說中有兩個人物,分別是“我”和外號為“伯勞”的中尉。伯勞是一種兇狠的食肉性鳥類,進食時將獵物釘在鐵絲網上撕扯獵物,因此得名“屠夫鳥”。中尉正如伯勞鳥一樣兇殘無比,他殘忍地處理尸坑里的尸體,無情地殺死戰壕里尚未斷氣的敵兵。小說令人驚悚的描寫使得該作品直到二戰結束后才得以正式發表。故事的結局也耐人尋味,“我”被子彈打傷左眼,頰骨粉碎,身受重傷;而中尉卻獲得了甲等功勛,步步高升。志賀直哉用這一諷刺性的結尾表現了自己對于所謂正義戰爭的嘲諷。
小說《傷兵》也表現了日俄戰爭的殘酷狀況。作品描寫了一個在戰爭中負傷的殘疾軍人,他失去了雙手和一只眼睛,怪異的樣子令人心生恐懼。最顯眼的是他軍服上面有縫制過軍功章的痕跡。小說通過對執著于戰爭榮耀的個人的刻畫,表現了志賀直哉對戰爭的嘲諷。
志賀直哉未定稿的《甚吉》也描繪了日俄戰爭中一名普通士兵的遭遇。士兵甚吉參戰前受到當地人民英雄般的禮待,而當他在戰爭中失去雙目回到家鄉時,鼓勵他上戰場的父親已經去世,當地人也被折磨得麻木不仁。《甚吉》反映了日俄戰爭從爆發到結束整個日本社會人們的心境變化。1903年8月到1904年1月,日俄雙方由談判走向破裂并開戰。面對大幅增加的軍費開支,日本國民的生活舉步維艱。雖然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因如此,日本國民才從戰爭的狂熱中逐漸冷靜,開始反思戰爭[2]37。
(二)戰爭對集體的毒害
志賀直哉的文學作品不僅表現了殘酷戰爭對人性的扭曲,而且揭示了軍政府蠱惑民眾,企圖侵略擴張的野心。他于1908年創作完成的《可怕的迷信》表現了一般民眾的無知與日本政府的暴行。開篇他就寫到日本人中存在一種“可怕的迷信”,那就是“唯天皇的命令為是”[3]279。志賀直哉指出天皇讓民眾為他殺人后去送死,而這都以忠君報國為借口。他模仿但丁的《神曲》,讓戰士們的魂魄游蕩在地獄與天堂之間。這些“為國犧牲”的戰士死后被社會報道和祭奠,但是當他們來到生前天皇所許諾的極樂世界入口時卻被攔了下來。因為雙手沾滿別人鮮血的靈魂是無法升入天堂的,他們無奈前往修羅城。在修羅城他們遇到了曾經的名將北條時宗、源義仲、加藤清正等人的靈魂。最令人意外的是,日本中世紀武將楠正成也在其中,他對推翻幕府、鞏固皇權做出重要貢獻,被日本人奉為忠君愛國的象征。但是在志賀直哉的筆下,軍神不過是一個沒有自我思想的軀殼,是任由天皇使用的武器。志賀直哉對于傳統英雄形象的顛覆正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虛偽性的批判,由此諷刺了日本國民麻木不仁、缺乏自我的“愚忠”思想。
《覺中夢》更是志賀直哉向日本天皇制度發出的戰帖。作品講述了出生貴族的“我”目睹了天皇統治之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最后當政府授予“我”教授一職時,“我”果斷拒絕,并提出廢除天皇制。政府得知“我”的行為后,不僅將“我”列入黑名單,而且企圖暗殺“我”。《覺中夢二》作為《覺中夢》的續篇講述了“我”由于寫了被政府迫害的經歷而遭到政府查禁,“我”的孩子甚至被勒令退學。情急之下,“我”將孩子送到高爾基那里,十幾年后孩子回國與我一同成了革命斗士。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經濟迅速發展,軍事力量不斷增強,對外擴張的野心逐漸增強。狹隘的民族主義令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命令盲目服從,最終演化為以天皇為首的軍國主義對整個亞洲的侵略。志賀直哉在作品中安排天皇墮入地獄正體現了他對于天皇這種將自身利益建立在他國和他人痛苦之上的行徑的憤怒。
二、一戰時期
(一)白樺派的人道主義創作
一戰中的日本不僅投靠協約國,并與德國開戰企圖占領山東。日本政府不滿足于僅占領膠州灣,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后,進軍西伯利亞并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此時的志賀直哉已經不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加入了白樺派,與一群有識之士共同反對戰爭。一戰期間志賀直哉有過短暫的入伍經歷,這也令他更加關注軍隊生活與法西斯軍隊的野蠻行為。
1910年,日本一批物質生活條件優越的作家創辦了《白樺》雜志,志賀直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白樺派文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道主義,具體是指消除人種與階級間的差別,為實現全人類的幸福而努力。他們以積極、合理的個人主觀要求作為實現尊重自然意志的方式,在物質與精神的沖突中以精神克服非精神的東西,將人從束縛中解放,進而重新調整人與他者的關系,并達到至善的境界[4]184。白樺派反映了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生存與思想狀態,并對日本文壇產生了深遠影響。芥川龍之介曾評價白樺派“為文壇帶來了清新的空氣”;西鄉信綱也認為白樺派恢復了自然主義所抹殺的對人性的信賴,而將“近代的人道主義引進文學界”。可見,白樺派作家的作品蘊含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4]183。
白樺派作家在吸收托爾斯泰與梅特林克人道主義的基礎上,摒棄了其原有的復雜含義而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人道主義。白樺派的人道主義的核心是“正義”與“自我”,作品中對弱者的同情、對戰爭的鞭撻、對人類自由與發展的追求都是追求自我與正義的體現。志賀直哉就是一個同情弱者、批評社會不公的人道主義思想家,他尊重人性、同情弱者、弘揚社會正義。從他的《到網走去》和《正義派》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志賀直哉在與白樺派作家相互學習、相互啟迪中以對弱者的關懷,呼喚和平與正義的到來。
(二)兵役制度的批判
志賀直哉創作于一戰期間的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對日本政府義務兵制度的批判。日本政府在一戰爆發前就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征兵,征兵的對象除日本民眾外,還有殖民地的人民。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就堅定地否定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倡導個人主義。他在被奉為“時代的英雄”的乃木大將面前直言:“軍人不曉得人的價值。”[5]109顯然,當時的“人的價值”指的明治時代的以忠君為基礎的愛國,而武者小路所說的“人的價值”則正是白樺派所強調的以善和美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白樺派作家認為政府的兵役制度將人作為侵略的工具用以發動戰爭,這是一種違背人道主義的行為。乃木大將在天皇病死后剖腹自殺,他的殘忍與愚忠成了志賀直哉作品中軍人的典型形象。
1910年從東京帝國大學退學的志賀直哉被進行征兵體檢,在體檢通過后,為了縮短服兵役的時間,他提交了“一年制志愿兵”申請。同年12月,他被迫前往千葉縣市川鴻臺的野戰炮兵隊。軍隊生活令他覺得十分厭惡,“換穿軍服的時候感到一陣厭煩”,想到長達一年的服兵役時間他又感到“悲哀”[6]447。對軍隊深惡痛覺的志賀直哉通過柳宗悅和井田磐楠等人的關系,在服役后的第九天以“耳鼻疾患”被免除兵役。《一個男人·姐姐的死》中描繪了退伍回家時的激動與興奮,“終于回來了,終于回來了。渾身充滿了喜悅與疲憊,好似從異國漫長的旅程中剛剛歸來”[6]447。他的興奮不僅在于逃脫了直面死亡的威脅,而且是個人對抗軍國主義的勝利。經歷了短暫的軍隊生活后志賀直哉對于征兵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那些被迫入伍的士兵更加同情。在《片斷》一文中,他批評死刑被認為是酷刑,但是戰死沙場卻被認為是光榮,而日本的強行征兵制度本身就是在強迫日本民眾接受自己家人的死,還強行稱之為“榮譽”[7]233。對于政府這種無視國民意愿的做法,志賀直哉十分憤慨。
同年“明治節”時,志賀直哉與表弟一起去柴崎買鴨子的時候碰到了節日期間進行演習的部隊。灼熱陽光的照射下,士兵們不堪重負,暈倒者也不占少數。見到如此情景的志賀直哉將士兵與無力抵抗的鴨子作比較,感慨他們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而寫下了《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事》。志賀直哉對于明治時期推行的非人道的征兵制度的批評實質上正是對戰爭對人的異化的批判。
三、二戰時期
(一)管制下的“沉默”
大正時期,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地位有所上升。由于受戰爭之后經濟蕭條和關東大地震的影響,昭和時期開始出現金融危機,社會動蕩加劇。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攜手,加快了法西斯軍國主義步伐。他們發動“九·一八”事變,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在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壓制著國內的言論自由,對無產階級作家進行了殘忍迫害。“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小林多喜二被選為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書記長,全力投身革命事業。日本法西斯的殘忍迫害令革命黨人被迫轉移地下,1933年初的一天,東京筑地警察署逮捕了小林多喜二,對其進行了嚴刑拷打致其死亡[8]101。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引發了全世界的憤怒,志賀直哉更是冒著危險為小林多喜二的母親寫去了慰問信。同年,另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被逮捕判刑。志賀直哉在表達痛心的同時也更加清醒地意識到軍國主義對于人性的踐踏。
1932年,日本對于中國的侵略進一步加深,并炮制出了“一·二八事變”。國民黨政府被迫向英法主導的“國際聯盟”提起訴訟。“國際聯盟”經過調查后認定,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為屬于侵略,否定其建立“滿洲國”的主張。日本軍政府見到這一裁決惱羞成怒。志賀直哉對此曾發文諷刺日本政府以為能像控制國內輿論一般控制國外,但是只要“看透軍部的意圖就越不可能被支配”[3]642。他于同一年創作的小說《菰野》進一步將矛頭對準了日本財閥政治的真面目,認為“國防協會”不過是以愛國為旗號搜刮民脂的騙子。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進一步擴大,對日本文藝界的管制也逐漸加深,表現日軍暴行的反戰小說《護著的士兵》《戰神之歌》等都遭到查禁,即使是單純描寫男女愛情故事的也被認為“充滿女人味”會妨礙國民精神而遭到禁止。當時的政治形勢已經令志賀直哉無法自由創作。與許多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賣命的文人相反,戰爭期間直至戰爭結束他幾乎沒有發表過作品。志賀直哉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始終采取厭惡不合作的態度,《早春的旅行》《寂寞的一生》是這一時期僅有的作品[9]427。日本侵華時期也正是志賀直哉的第三個創作空白期,前兩個則是日本學界公認的大正三年至大正五年(1914—1916年)以及昭和十七年至昭和二十年(1942—1945年)[10]42。
(二)戰爭后的“反思”
1945年,隨著日本宣告戰敗,日本國內的言論自由隨之恢復。經過第三個創作空白期的志賀直哉寫了大量關于社會生活的時評,這些近似隨筆的短文很容易被人忽略但卻真實反映了志賀直哉對戰后日本發展的思考。
志賀直哉于1945年11月所作的《銅像》一文辛辣評判了世界歷史上的戰爭狂人。他第一個批評的對象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傳奇名將豐臣秀吉,日本人“像孩子一樣崇拜秀吉”,贊美他攻打明朝的行為,然而卻忽略了背后犧牲的生命[11]313。日本的“大陸政策”并不是近代才開始的,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后就曾兩度侵略朝鮮[12]133。德川幕府末期出現的“海外熊飛論”從不同角度討論了針對中國與朝鮮的對外擴張思想,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近代的日本。志賀直哉通過對傳統英雄豐臣秀吉的批判,表明了他對于軍國主義操縱下戰爭實質的領悟。同時他將拿破侖與希特勒比較,因為他看到拿破侖在傳播資產階級先進思想的同時也為其他國家帶來了苦難。文章的最后他呼吁,為防止第二個東條英機的出現,要造一個銅像,要讓人們永遠記住痛苦的歷史,防止軍國主義思想的復蘇。《銅像》之后他還創作了《不可屈服于壓力》《鈴木貫太郎》和《桂美子的老師》等作品,進一步掀掉了軍國主義為自己辯護的遮羞布。
志賀直哉對戰爭的反思并沒有停留在對于戰爭本身殘酷性的譴責,為了國家能夠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他更加注重對青年一代的引導。《特攻隊再教育》揭露了戰時特工隊所接受的自殺式洗腦教育,他認為曾經的特攻隊員如果不能適應新時代,那么將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法西斯政府毀掉的青年一代的善后工作也應當由現政府承擔起來。此外,他還寫過《第一年》和開幕詞《致青年一代》,表達了他對于年青一代精神重建的關心。戰后的志賀直哉對于天皇制度的反思更加深入。《天皇制》中他所反對的不再是肉身性的天皇,而是作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它本身的脆弱性決定了容易
被其他勢力所利用。
結語
志賀直哉三個時期的反戰文學各有特征。日俄戰爭時期集中表現戰爭對個人與集體的扭曲;一戰時期以日本化的人道主義思想為武器對戰爭和兵役制度進行了批判;二戰后又開始思考戰后社會的精神重建。作為白樺派成員之一的志賀直哉從批判自然主義出發,追求自我確立與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無論是早期的尖銳批判,還是晚期的沉默與思考,堅決反對戰爭的態度可以看出志賀直哉確是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